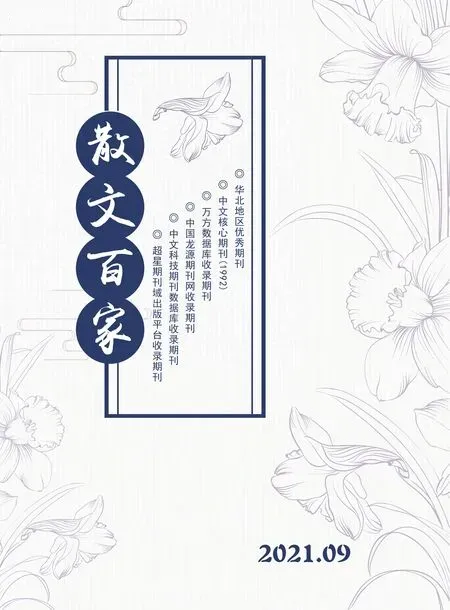“冰”与“火”的抉择
——论《蚀》三部曲中对立的女性形象
2021-11-12楚涵
楚 涵
河北大学文学院
《蚀》三部曲中有两类对比鲜明、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静女士、方太太、陆女士同属于安静、沉稳、内敛一型的,而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则是活泼、性感、浮浪、充满生命活力的一型。这两类女性都是经历了“五四”解放思潮洗礼过的新时代女性,她们不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藏于深闺的女性,她们都选择走出闺房,走向社会,奔向革命的洪流。关于这两类女性形象,前人已论述颇多,但以往的研究仅仅将这两类女性视为保守型与解放型,或是是仅从东西方审美意识差别角度浅层分析探讨,而并未注意到这两类女性形象在文本中的对立与冲突。曹伟《冲突与抉择——谈茅盾笔下两类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历史内涵》一文,虽然略提及《蚀》中两类女性的冲突,却忽略了静这一类女性形象身上的先进性,把两类女性形象的冲突简单归结为审美情趣、封建禁欲主义理性与资产阶级纵欲主义的对峙。本论则详尽地分析了这两类女性形象在文本中的冲突与对立,梳理了作者不同的描写笔触,并深入挖掘这两类女性形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与静女士、方太太类的女性相比,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一类的女性更为热烈张扬,她们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肉欲的荷尔蒙,她们在两性关系上开放、不拘小节、视男子为排遣欲望或捉弄的对象。她们恰如火一般的热情,烈艳,是“火质”女子。而与她们在书中形成对比的静女士、方太太一类的女性,恰如冰一般温婉雅静,她们爱惜自己处女的身体,不肯轻易恋爱,躲在庄严、圣洁的帷幕之后。她们珍惜或向往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静女士、方太太一类的女子是古代“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形象,静女士、方太太并不刻意冷落疏远旁人,她们对自己的爱人和家人也柔情似水,只是因为她们的形象与同在书中出现的似火般特质的女子相对立,故称其为“冰质”女子,只是此“冰”不是冷漠之“冰”,而是雅静之“冰”。关于《蚀》三部曲中这两类女性形象,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则通过分析《蚀》三部曲中对立的“冰质”与“火质”的女性形象,从而探讨这两种分裂的形象背后所蕴含的作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与动摇。
茅盾在描写“冰质”与“火质”两种女性时,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描写方式。写“火质”女子时是立体的描述,从声音、嗅觉入手,并着重强调女性的身体曲线的勾勒;这些“火质”女性,还都热衷于革命事业,不仅性格是火的,连对革命的态度也是火热的。而茅盾描述“冰质”女子时,则是简单的平面勾画,从外貌、气质入手塑造人物形象,不强调她们的身体曲线和性吸引力。从“冰质”与“火质”女性的形象塑造可以得知,“火质”女性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性吸引力,她们是欲望的化身;而“冰质”女性则是典雅、端庄、幽静的形象,作者的描写也是去欲望化的书写,“冰质”与“火质”女性,正恰如张爱玲笔下对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描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
《蚀》三部曲中,“冰质”与“火质”两类女性,不仅在性格上对立相反,互为映衬,在感情上也总是处于对立的状态,虽然作者并没有让这两类女子陷入正面的冲突和交锋,但却总让“冰质”与“火质”女子处于情敌的尴尬关系。《幻灭》中的男子抱素先是对静女士心生喜爱,后来心意又逐渐转向慧女士。三人在电影院观影时,抱素的心意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他近日的奔波,同学们都说是为了静,但他自己觉得多半已变做为了慧。”《幻灭》中的男子抱素在“冰”与“火”的抉择中选择了“火质”女子。《动摇》借助胡国光的视角勾勒出方太太的形象特征:温雅和易,抚育孩子,照料家庭。男性角色方罗兰在小说中一出场,就在胡国光的自白中恍惚分神,“火质”女子孙舞阳的艳影如苍蝇般勇敢顽固,挥之不去。独处的方罗兰甚至把南天竹幻想为孙舞阳的绿衣。但此时的方罗兰还能控制住自己动摇,在方太太的温柔乡里抹去孙舞阳的艳影。手帕风波在方氏夫妻之间种下不安的种子,方罗兰不肯在太太面前承人自己对孙舞阳确有爱慕,只一味辩解清白,埋怨妻子思想过于保守封建。当方太太下定决心要与方罗兰离婚时,他又因喜欢维持现状的性格不肯离婚。孙舞阳在他面前袒露了发光的胸脯更衣时,方罗兰又对孙舞阳表白,决定离婚愿意牺牲一切爱她。被孙舞阳拒绝后的方罗兰又不断地改变主张,真是契合小说的题目《动摇》,转眼间回到家中,面对方太太的负气中的哀怨和拒绝中的留恋,方罗兰又短暂地逃离了彷徨,将妻子拥入怀中。小说结尾中,逃难中的方氏夫妇与孙舞阳相遇,“冰质”女子方太太和“火质”女子孙舞阳同时出现在方罗兰眼前时,“火质”女子旺盛的生命力令方罗兰禁不住心跳神驰。方罗兰将太太放置一旁与孙舞阳热烈探讨,在“冰”与“火”的抉择中,他也选择了“火”。到了《追求》中,则是男性角色张曼青在“火质”女子章秋柳和“冰质”女士朱女士之间抉择。曼青看到章秋柳欲与昨日告别从今开头的文字时,他也想过切实做人的秋柳或许接近自己理想女性的形象。但这想法只有短暂的停留,曼青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静缄默的朱女士。由此可见,《蚀》前两部曲中,当小说中的男性面对“冰”与“火”的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活力四射的、热衷于革命的“火质”女子,而在第三部曲《追求》中,“火质”女子的活力和热烈已经滑向了注重感官享受的纵欲主义深渊,男性角色最终选择了“冰质”女性。
茅盾赋予“火”类女子们性感的身体、摄人的诱惑力和充沛的生命力,她们在书中呐喊着身体的欲求,蔑视传统道德,放荡不羁,是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化身。有论者将“冰”类女子比作传统闺秀型女性形象,并认为“从《蚀》中的静女士、方太太开始,传统闺秀型女性形象与时代丽人型女性形象一道,在茅盾的作品中相伴相依,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茅盾小说中的爱情序列里,总是扮演着‘白玫瑰’与‘红玫瑰’式的角色,代表了东方式女性与西方式女性在新时代思潮中的碰撞”。诚然,茅盾笔下的“冰”类女子温婉静雅,更符合传统的审美意识,她们确有传统闺秀女子的缩影,但在充满张力的文本之中,如果说“火”类女子的深层内涵映衬着西方思潮,那么“冰”类女子的内涵则直指传统的、中国本土的价值与伦理观念。那么作者将这两类女子处于对立之中,并不厌地描写男性角色在这两类女子之间的抉择,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可理解为是作者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抉择。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变革之中,各种思想激烈碰撞交锋,茅盾曾这样描述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西方科技发达,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西强东弱”,广大知识分子从西方的新思想中汲取营养思求救国富强之道,再加上五四启蒙思想的洗礼,以西方思想为利器打破封建思想的枷锁,西方的价值观念,自由民主思想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茅盾也不例外。因此,《蚀》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男性角色在“冰”与“火”的抉择中往往选择代表着西方价值观念的“火”类女子,而到了《蚀》三部曲的《追求》,男性角色在“冰”与“火”的抉择中选择代表传统审美意识和伦理观念的“冰”类女子。西方的自由、人性解放观念走向极致后便是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者最终还是选择了传统。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之中的茅盾,也有着深厚的旧学积淀,茅盾曾说:“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骄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三百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尔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在对待西方文化上,茅盾也并非盲目追随,也担忧在西方新文化冲突之下中国如何自立,“在一九一八年,自欧美新文化传播以来,全球风靡,后进之国,莫不效之。我国自改革以来,举国所事,莫非模拟西人。然常此模拟,何以自立。”由此可知,在《蚀》中,茅盾让男性角色不断的处于“冰质”、“火质”女性的抉择中,并最终选择传统色彩更浓郁的“冰质”女性,这一安排的背后体现着茅盾文化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传统烙痕。
处于新旧变更的20世纪,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蚀》三部曲中传统并不与封建思想直接对等,这种传统浸润了西方思想又融合了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观念。比如《蚀》三部曲中象征着传统伦理和审美意识化身的“冰”类女子静和方太太,她们也是受了新思潮影响的时代女性,她们在革命中或许没有“火”类女子积极,并不是因为她们木讷冷漠,而是因为形式变化的太快,各方势力交错杂乱,她们才成为旁观者,一旦方向确定,革命的道路正确光明,她们是会参与其中的。封建伦理强调夫为妻纲,承认一夫多妻,男子移情合法。但是静默温婉的方太太得知丈夫倾慕孙舞阳时便坚决要求离婚,打算离婚后出去工作养活自己,她身上也体现着时代女性的独立和决断,因此可以说“冰类”女性是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并保存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中国审美意识的化身,作者最后安排男性角色在“冰”与“火”中选择了“冰”,也是意寓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最终还要回归传统,但最终回归的传统并不是等同于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观念的传统,这是一种新的传统,是一种汲取了西方先进思想而又保留本民族精粹的传统,是一种从本民族内部打破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