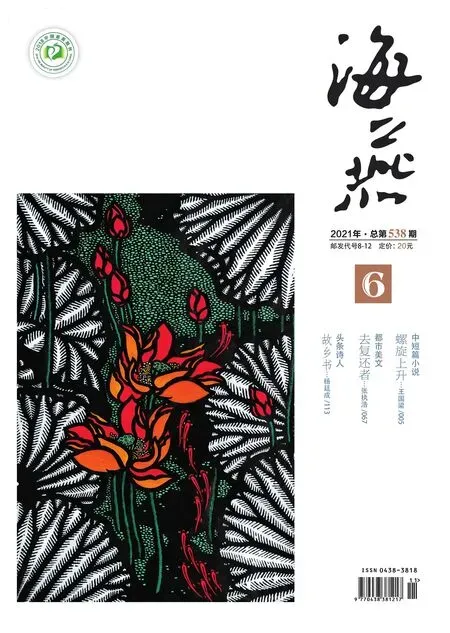河湟谷地,不断返回的故乡
——杨廷成诗歌的底色和标志
2021-11-12燎原
燎 原
与杨廷成的交往大致上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随后断断续续地一路走到今天,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对他的诗歌比较熟悉,但当他把近年来的创作全貌展现在我的面前时,还是让我产生了不小的意外。第一个意外是,这些诗的诸多地理场景,已经溢出了他原先一直所致力的故乡地理范畴,故乡的主体场景中,汇入了诸多“远方月光”的照耀。其次,是他诗歌中的多种色彩信息——包括个人情感信息和艺术审美信息的涌入。这诸多元素的融汇,使得他的诗歌空间明显地更具张力和弹性,也呈现出一位诗人走向成熟期的开阔与丰富。然而,无论其写作形态变得如何丰茂,但横亘在其中的主体,依然是有关故乡的主题。这是他整个写作进程中的主脉,也是他诗歌的底色和标志。
对于我们这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的民族和传统农业大国,有关乡村的书写,曾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诗歌主题。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整个诗坛进入了一个以现代主义观念和技术为王,此起彼伏的潮流性写作时代,乡村题材的书写也日渐式微。当乡村再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已在不同诗人的笔下,被分解为不同的概念类型和写作类型。其中最常见的一类,是寄寓乡愁的书写。一般而言,这又是一种记忆性的书写,是把记忆中的乡村,作为一个纯净精神空间和古老文明的象征,以与喧嚣的现代城市压力相抗衡。另外一个大类,则是时代变迁场景中新闻性的诗歌书写,这是有关乡村书写中一个特殊的中国现象。这一类型的写作,从上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此后经过长时间的中断,到了近年来又重新启动。介入这一类型的写作主体,当年主要为定点下乡、“体验生活”的专业诗人,近年来则由作协系统组织的下乡采风团队来担当。
两种不同类型的书写,给出的是两个不同的乡村,在此我们无须探讨哪个更为真实,但无论是这一路还是那一路,写作者在强化这一面的同时过滤掉相反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大差不差的事实。此外,这虽然是两种类型却又是两个系统的写作,但跻身于任何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无不表现为写作的阶段性乃至即时性,一俟这一波的心理热度消退或采风任务完成,便会转向另外的题材关注。也因此,你在当代诗坛可以列举出大量的,以长期的写作积累形成鲜明个人标记的诗人,但以持续的乡村书写而著称者,却鲜有其人。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待杨廷成的写作,他便成了一个罕见的个案。在他从少年时代开始直至现今的写作中,乡村,具体地说,也就是作为其故乡的青海东部河湟谷地中的乡村,一直是他诗歌中持续不断的主题。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过去,对于当初从乡村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位少年诗人,你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清新感;当他汇入城市人流的多少年后,依旧行走在这条道路上,你既会从其作品中感受到相应的丰富,又会对这种近乎“一根筋”式的行走,产生一种封闭、木然的迟钝感;然而,当他一直走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其笔下的乡村物事已汇聚成一个意态缤纷的云空间时,你会突然意识到,他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走成了一个“标本”式的存在和现象。
这种“标本”式的存在,既是指他几十年乡村写作形成的庞大体量和系统性,还在于其诗歌内质的纯粹。也就是说,他笔下的乡村,既是一个与他共时性的鲜活存在,又是由不同时段这些鲜活物事所构成的历时性完整系统。事实上,这也是以上两种写作之外的第三种写作,其与前两者一个标志性的区别是,乡村之于他既不是一个消解乡愁的客体,也不是一种记忆性的存在,而是他出门在外时刻心念相系的家,又不断回到其中的共时性的现场。
但这样说又似乎很难使人信服,因为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进入了自己人生的“城市时间”。城市,不但给了他充足的发展空间,也把一个简单的乡村子弟,造就成了人生舞台上不时额头发光的人物。
对此,我们只能用血液的秘密来解释。在持续不断的四十来年间,从当初的乡村少年直到现今,他的诗歌之所以一直沉迷于相距不到百十公里外的故乡,这显然不只关乎“热爱”,或在“邮票”大的故乡,下挖一口诗歌深井的策略性考虑,而是关乎本能——由那种乡村纯血所主导的本能。进一步地说,假若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带有这种乡村的血液,那么这种血液之于他则是控制性的,并赋予了他以根基性的心性特征和文化心理结构。一个特殊的佐证来自我们当年的交往:在通常情况下,他是那种极为真诚友善的人,但却时而会以智力过剩的乡间“皮小子”式的“诡诈”,跟你“坏”上一把。这种喜剧性的性格闪电,一直被我视作精彩的乡村智慧,也是我们长期保持交往而不觉得乏味的重要原因。但也是在这样的场合,只要几个人的交谈一转入某个陌生的诗歌话题,他则会立马支起耳朵,一脸的认真模样。
一个深刻的记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气氛热烈的诗歌神聊中,他突然向我提起几位河北诗人,随之就背诵起了姚振函的《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六月,青纱帐是一种诱惑/这时你走在田间小道上/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声/吆喝完了的时候/你才惊异能喊出这么大声音/有生以来头一次/有这样了不起的感觉……”然后感叹:“姚振函表达的这种感觉真好,每次回到乡下的老家,我就时常想趁没人的时候,使劲吆喝上这么一嗓子。”继而,他又提到了刘小放《我乡间的妻子》,等等。的确,两位诗人的这些诗作,当时也出现在我的阅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开了当代诗歌中真实还原乡村生活先河的写作。但此时我们都沉浸在西部诗歌的潮流中,对此并无更多的惊奇,而当时的杨廷成却马上心领神会。此刻想来,他应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看清了他在与我们不同的那条道路上,走下去的依据和目标。是的,对于杨廷成,那一刻的感觉也的确真好——“有生以来头一次/有这样了不起的感觉”!
同样一首诗作,在这个人的心中只能留下泛泛的感觉,在另外一个人那里却能激起强烈的共鸣,并使之如获天机,这无疑取决于特殊的个人心理机制。搞清了这一点,你也就不难明白,杨廷成在成就了他的城市与他已经离开了的乡村之间,看似矛盾的心理取舍。虽然这仍然有些吊诡,但唯有这种吊诡赋予的矛盾与张力,才是诗人的正常心理逻辑。
毫无疑问,城市,作为现代人类居住空间和资源空间的最高文明成果,几乎对应了现代人类所有的物质欲望和生存想象,并正在对它的人群实施全面同化。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对于那些完全生长在城市中的新新人类,乡村或将只是一个概念。但对于杨廷成,乡村则是一个大于城市的世界,存在于他血液源头的一个信息密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首先是他降生的那座村庄,也是村庄内部和周边世界关系的总和。它文化属性中的崇尚禁忌、方言习俗、乡谣民谚、花儿野曲;自然形胜中的山坡谷地、村庄河流、树林飞禽、寺院庙宇……这一切植入一个人血液中的信息密码,决定了你一生的心理反应机制类型、价值判断尺度。决定了你会对什么视而不见,又会对什么做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反应。
也因此,你就不难理解,当他在城市中一听到“昨夜西风消息/说河谷里麦田一片金黄”,就何以会涌起莫名的激动,且霎时会回溯到自己的过往——“我曾经也是秋风中/最饱满的那一株麦穗”“多么想在这个时刻/回到山坳里炊烟四起的村庄”,在夕阳里眼含泪光……
而这片河谷,亦即河湟谷地,则是乡土中国山坳中一个最小的地理单元。在几乎已被当代诗歌穷尽了的青海高原,当游牧的高原自西向东一路倾斜而下,而至这片河谷所在的东部农业区,转换出另外一重天地中的青海时,当代诗歌的追踪兴致却突然终止——农业区的青海不再属于诗歌的青海,农耕的山乡也不再属于诗和远方。然而,当杨廷成遥想他的山乡这样眼含泪光时,沉默的山乡随之影影绰绰:父亲那柄不肯生锈的弯镰整夜里嚓嚓作响,母亲在世时向他挥动的手臂炊烟一样摇晃。再接着,沉默的山乡随之五彩缤纷:寺庙“山门下的一丛老杏树/沉醉于花枝如火的憧憬”;山野中青豌豆的藤蔓手拉着手,“是一群群情深意浓的乡下姐妹/同享着春日雨丝的喜悦”;“三月,铜唢呐的声音震耳欲响/穿一身红嫁衣的姐姐走出了故乡”……
这是多少年来,一直萦回在他诗歌中之于故乡的欢畅基调,但在近年来的诗作中,他此前诗歌中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一种元素:夹杂在这欢畅基调中无法稀释的暮色,却在字里行间悄然弥漫。弥漫的暮色中,是情不自禁的“回家”意绪:
“倾听古寺的钟声在暮色里响起/远方的游子踏着夕照梦回故乡”;
“远在路上行走的人/梦呓中叙述着遥远的归期”;
“老父的酒歌已刻上祖坟的墓碑/亲娘的叮嘱早就在土地下长眠……//故乡,我只是赶在夕阳落山之前/流着泪走在回家路上的那个孩子”;
……
这样的意绪有些感伤,甚至是恓惶,但却蓦然间映现出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心理处境,以及纠集在他们心头的焦虑。被裹挟在一个繁华喧嚣、心为物役的现代时空中,他们不时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心在何处的茫然与惶恐。回家,也因之成为一个时代的心灵哲学命题,但对于离开故乡年深日久的城市子民,故乡之于他们已是另外一个时空中再也无法融入、无法返回的所在。因此,许多人已不知家在何处,并且无家可归。
而杨廷成,却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故乡,也就是可以在内心笃定地宣称,他是有故乡的那个人。事实上,他所生活的城市与其故乡不到百十公里的距离,尤其是他与故乡之间超乎寻常的血亲呼应,已构成了他特殊的心理反应机制和诗歌写作机制。离开故乡的时日,使他获得了一种拉开距离的视角,并在城市生存的反照中,深化自己对于故乡的心理体认;不断返回的时日,则使他的心灵处在被不断激活、持续滋养的良性循环中,也使他得以同步感知岁月迁延中故乡的变更脉络,从来不感到陌生。因此,他才一直血脉通畅地既能走出故乡,又能返回故乡,并始终与故乡相互拥有。因此,尽管他关于故乡的书写总是伏藏着沉重与疼痛,以及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但主体基调却是炫耀式的抒情,在天真式的炫耀中,一个人重返乡村少年时代的烂漫与欢畅。
而这种天真、炫耀式的抒情格调,从心理原型的角度来看,还有着更深的内涵。杨廷成的那片河湟谷地,又是著名的“河湟花儿”的盛行之地,因此,它所对应的,是一种只有河湟谷地的乡村时光,才能赋予的歌谣式心理原型。而所有歌谣的本质特征,都是由古老的民间经验和智慧所滋生的天真,在历尽了疾苦、看透了万物后,却把这一切化解在单纯天真的歌唱中,给予沉重的人生以安慰,使沉重的人生在沉重中吐气,在欢畅中扬眉。
正是基于以上的这一切,杨廷成的诗歌才如同大谷地中的“花儿”一般,在那片灵性的土地上扎下根须、开出花朵、结出果实,并在当代诗歌的乡村书写领域,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