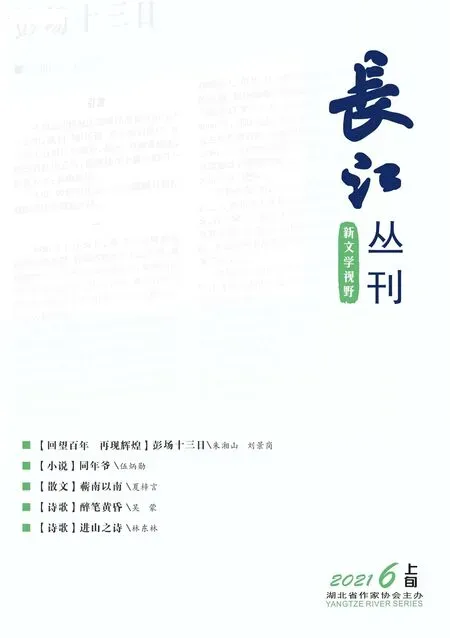心 债
2021-11-12■关金
■ 关 金
闵建华退休几年了,一直在北京带孙女。2021年元旦小长假回白鹤坪老家,给过八十岁的哥哥祝寿。宴罢宾客,兄弟妯娌难得一块叙叙家常。闲聊时,哥哥说起兰秀的事情。说兰秀教子有方,两个孩子都有出息,大学毕业后,一个在机关、一个在国企,做了一段两兄弟又出来自己创业当老板,家里很殷实。可惜人到老年,福还没享,罹患重病。“前些日子听她娘家人说,兰秀得的是白血病,发现已是晚期,带病细胞转移很快,怕是危险了。”闵建华闻言心里一沉,陷入久久沉默和阵阵悸痛。消息太突然,毫无心理准备。从未停止的思念、自责、愧疚、悔恨,又在脑子里翻江倒海。
兰秀叫郑兰秀,白鹤坪同村同塆人,是闵建华的初恋。虽然分别四十多年了,再也未见过,未联系过,但一刻也没忘记过。闵建华曾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大意是,在男人的情感世界里,最不能忘记的,不一定是曾经最喜欢的人,不一定是曾经最痛恨的人,而一定是曾经最对不起的人。这话不期竟在自己身上印验了。唉,真是走错一步,愧疚一生。
1970年。闵建华17岁,因文革期间没书读,已经回村里劳动了两年。郑兰秀15岁,只上到小学,也在村里劳动。她衣着整洁,瓜子脸、樱桃口,明目皓齿,秀发齐肩,清秀可人。更兼心地善良,待人谦和,说话轻声细语,做事中规中矩,更得长辈称赞,小伙青睐。不论下地干活,还是上街赶集,在队里那群姑娘中,都有着最高的回头率。
经郑兰秀的族姐作媒,两个人这年订了亲。说是订亲,没有任何仪式,也没叫到一起见个面,只是族姐问问两边家长,都点头同意,就算订了。订了亲,也没按当地习俗逢年过节走动。可能由于离得太近,家里觉得少接触比较好。因此,两人很少单独在一起,也没有说过几句话。
1971年春天,闵建华当上了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那年秋天出的林彪事件,初冬才传到白鹤坪。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用影印件下发,要求宣传到家喻户晓。大队就组织学校老师到各生产队去开会传达。闵建华分到的任务中有白鹤坪。
会场就在一户人家门前的打谷场上。一个队,来的也就六七十人,有的搬个凳子,有的在场边草堆挽个稻草把子,席地而坐。闵建华开始念文件,妇女们全副心思地纳着手中鞋底,男人们一边嗞嗞地吸旱烟,一边摆弄手中点火用的麻杆捻子,文件里说的事多数人没在意。只有几个通点文墨、比较关注外面事情的年长者,听的认真,表情惊讶。
闵建华站在稻场边的台阶上,眼睛能看到所有人。郑兰秀坐在人丛中,微红着脸,低着头,样子好像在认真听,其实也没听进文件说了啥。她在意的是念文件的人。虽说订了亲,但没有像别人一样作为亲戚走动。一个在队里劳动,一个在学校教书,数月也见不着一次,真正的咫尺天涯。但站在台阶上念文件的青年,是自己心上人,这一点是确定的。在那个城乡分隔,参军、招工、升学等“跳农门"机会少之又少的年代,民办教师也能让人高看一眼。此时又在自己的眼前,给乡亲们念中央文件,自然觉得脸上有光,心里甜甜的。郑兰秀坐在人堆里,自顾自地想心思,心里像有小鹿乱撞。想看看他的样子,又不敢抬头。越这样越不自然,就像被人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脸更红了。
闵建华知道自己到白鹤坪传达文件,郑兰秀会高兴,会喜欢这种光彩。他享受被郑兰秀喜欢的那种感觉。但没有勇气往郑兰秀坐着的方向看,更没有勇气在开会前或散会后,走过去跟她打声招呼说句话。不过,知道她来了,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在那,也就很满足了。
因为不走动,不交往,不显露,学校老师们并不知道十七八岁的闵建华订了亲。一次学生家访后,一位中年教师从白鹤坪回来,跟闵建华说:"你们队里那个小姑娘郑兰秀,眉清目秀,玉润珠圆,要面像有面像,要身材有身材,要白是白,要红是红,真是太漂亮了!不知将来谁有那个福分?"
一分感慨,十分赞美。谁不喜欢漂亮姑娘,谁不希望找到漂亮姑娘!闵建华不好意思说郑兰秀是自己的女朋友,只好不搭腔。但听到别人对郑兰秀的由衷夸赞,心里总有说不尽的甜蜜,更加美滋滋的。
郑兰秀参加了大队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当时的时髦话讲,叫“为革命大喊大叫、大蹦大跳"。不仅有政治活动和逢年过节时,集中在大队部唱歌跳舞,平时也分别到各队演出。选郑兰秀当宣传员,不是因为她的文艺细胞比别人多很多,而是因为她比别人更漂亮。大队领导的考虑很实用,很简单。漂亮姑娘养眼,表演有人看,就有宣传效果。
宣传队闹过的一个笑话,也让领导们更确信自己的决定正确。一次演出结束,宣传队贯彻走群众路线精神,让一位老贫农提意见,老贫农连忙说没有意见。宣传队一定要让老贫农帮助提一条意见,以便进一步改进。老贫农再三推辞不过,就说:“别的都好,就是二重唱不太整齐……”。这事虽然只被人们当着茶余饭后的笑谈,却也让领导们更清楚,对于成天劳作、干粗重农活的庄稼人,艺术水平不必是最被看重的。
过了不久,郑兰秀又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胜选团支书,不是赢在能说会道,凉水点灯。恰恰郑兰秀言语少,平时与人交往总是听多说少。商量工作也是在大家说完后,简要地明确一下任务和要求。胜选赢在朴实漂亮。人一漂亮就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就是凝聚力,有凝聚力就能团结组织青年参加活动,完成任务。这叫先天优势。
队里没有给闵建华定任务,闵建华也不要队里工分,插多少是多少,不用赶工。闵建华心里惦记的,是同在一块地里干活的郑兰秀。虽没有讲话,也不敢抬头多看,知道她在,心里也紧张,同时也幸福。
聪明的郑兰秀知道闵建华想见到她,想亲近她,自然会主动为他创造条件。远远看到闵建华要来秧苗田挑秧,郑兰秀便挑上扯好的秧苗往大田走,创造迎面相遇的机会。
闵建华也看到了郑兰秀的动作,明白她了的心意。更难得的是,这段路要经过一片可以遮住人们视线的竹林。闵建华一阵激动,下决心要跟郑兰秀说上话。几百米远的距离,米把宽的田埂,转眼就走近了。郑兰秀满怀期待地抬头看着闵建华,闵建华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来人,心砰砰砰地跳,却红着脸低下了头。郑兰秀无数次在舞台上表演,无数次在会议上讲话,见过多少场面,再怎么害羞也能找到开口的话题。但到底是女孩儿,她要等闵建华先开口。就这样,两人一楞怔,竟低头擦肩而过。
"没出息,窝囊废!”闵建华无数次地骂自己。一次次的胆怯、退缩,辜负了郑兰秀,也辜负了自己的真心,让他越来越没有了自信。以至几十年后,时过境迁,仍不能释怀,仍在失悔。
当面不敢说话,为什么不写信呢?闵建华缺情商的脑袋总算开了点窍。而且传书的鸿雁就在他的班上——郑兰秀的小妹郑菊秀是闵建华教的学生。
放学后,闵建华不去教师办公室,躲在班上的教室里写信。平时牵肠挂肚,千言万语,可拿起笔又不知从何说起。这第一封信连用了三个下午。
“有什么好为难的,又没有当面,不妨有话直说。"闵建华都吃惊自己少有的果敢。
兰秀你好!
我揣着嗵嗵嗵的心跳给你写信,就是想说出对你的无尽思念。
真的太想念了!你好听的声音,秀丽的容颜,时刻在我脑际萦绕。有时做着事,好像你就在旁边。有时走着路,好像你就在对面,或者说希望你正从对面走来。有时想入了迷,就像得了痴症,坐着发呆,惊醒过来又怕被人发现,吓个大红脸。
你们宣传队在各队演出的时候,听到锣鼓家什响,我心痒得就想冲到现场,又战胜不了怕人笑话的怯懦。每次都是跑到学校后面的坡顶上遥听遥望遥想。
唐诗中写恋人苦思的诗很多,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恋人相思得都嫌夜太长了,整晚睡不着,起来看月亮,想亲人。我大概也算与千年前的诗人同病相怜了。
秀,在心里拥有你,是我得到的最大财富。何况,我们不光是相互在心里拥有,而且是关系确定的、实实在在的恋人。同龄人在一起,大家会经常聊起自己的感情,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女朋友的,没有我的优秀。正在寻觅的,看着那些焦急模样,我心里踏实满足,还有些得意。
秀,我们大队办学迟,我比你大,先在集上的公立学校上了学,后来也没转回来,很遗憾没能跟你同学。留住我的目光,拴住我的心,是在你十二三岁的时候。你那么清纯,文静,勤快,知礼……,我看着就眼亮心热,有一种不仅仅是好感的特别感觉。用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语言讲,就是心仪了,暗恋了。随着年龄增长,你慢慢长大,越来越出众,越来越优秀,我开始着急了,生怕有人捷足先登。谢天谢地谢族姐,她扭转了这种紧急状态,成全了我们的好事,让我做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那只蜻蜓。每每想起,私心窃喜。
前些天,参加大队团支部组织的批林批孔会,事前通知我准备发言。我对这类活动本没有兴趣,原想找个借口请假。转念一想,团支部是在你的领导下,团的活动就是你的活动,或许让我发言,原本就是你的意思呢,我又变得很积极很兴奋。
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不怕你笑话,现在小学没有历史课,学校也找不到资料,我连《论语》都没读过,整个《四书五经》更不用说,法家儒家的主张到底是什么,除了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没有再多的了解。我的发言都是抄的。不过抄前先想好了要说的几个论点,然后按论点找论据,抄的也算对题。为了不让你丢面子,尽量让发言有文采点,我可熬了两个晚上。发言效果不错。虽然得到大家的好评,但你有事没参加,心里着实失落。因为我不在意别人的感觉,只在乎你的感受。在这里又把这件事说出来,不是怪你,也不是显摆,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为了你才那么认真努力的。
你看到满塆满墙的标语了吗?那是我写的。大队让学校派老师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造浓氛围造大声势。学校说我大字不错就让我去。要刷标语,只有人布置任务,没有人准备工具,没有排刷,没有颜料,我是用奶奶洗锅用的刷帚醮石灰水写的。一桶石灰,一把刷帚,我干了一个星期。在各家各户的墙上,我用梯子把标语刷得高高的,把字写得大大的。包括你们家墙上的那条大标语。估计只要房屋不拆不倒,这些标语十年二十年都会存在。
我还在你去大队部,天天要经过的铁路道口斜坡上,用碎石铺底,再涂上石灰浆,刷了条“农业学大寨"的大型标语。说来奇怪,大队让我刷这些标语,在我的感觉中,好像就是为你刷的,刷上去就是为了让你看的。所以,尽管天天爬上爬下,满身尘土灰浆,有累不觉累,干得劲逮逮。
……
十几页信笺纸的长信,换来郑兰秀专门去照像馆,照了自己的一沓照片让小妹送来。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心细如发,善解人意。有什么是比这更让闵建华想要的礼物呢!
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白鹤坪与毗邻的罗家垸实行了并队。这里的地貌,原本就是几道岗一块坪的低丘,人户不是很集中。两个大队合并后,南北距离拉长到七八公里。罗家垸也办有小学,为了方便孩子们就近入学,合队不合校,改称白鹤坪小学为南校,罗家垸小学为北校,教师适当交流。
合队后第二年的春季开学,有人提议开展人员调整后的推磨联谊,方式是下午散学后,老师们集体出动,轮流去各家聚餐。既增进感情,又改善生活,两全齐美,全体举双手赞成。
有一次,去原在北校的一位老师家里聚餐。天阴沉着要下雨,去时天没黑,回来已是深夜,路上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一行人,听得见说话声音,看不见人影,只能手牵着手摸索行进。最后还是不行,不得已改走铁路道线。因为铁路虽有不平整的枕木碎石,但不会有落入沟壑的危险。
好不容易走到白鹤坪车站。当时铁路新建不久,经常要从沿线社队抽调民工上路培基加石。这段时间白鹤坪民工由郑兰秀带班,此时正在铁路道班睡觉。春寒料峭,夜已子时,下了铁路就没法走了。
有老师就喊:“闵建华,你去找郑兰秀借个手电。不然,我们只能冻死在这里了!"
“人家早睡了。这半夜三更的,我怎么好从被窝里叫醒一个姑娘!"闵建华心里嘀咕,腿脚不动。
同行的一位女老师连忙出来解围,主动去敲门叫醒郑兰秀,借了手电给大伙照路。
"手电借到了,用完了,还回去不用再代劳了吧?"又是那个让闵建华窘迫的老师在调侃。
这个任务正中闵建华下怀。第二天,郑兰秀从小妹手里接过手电,回屋展开来信。
郑兰秀知道学校的事不用担心,也不需要劝勉。她不写回信,而是拿起已经生疏的针线女工,用几个晚上,给闵建华做了一双鞋,让小妹带到学校。闵建华如获至宝,哪里舍得穿,一直珍藏着。
路走长了,难免遇到沟沟坎坎。
第一次是个小浪花,发生在闵建华去教书时。
那时天天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批“师道尊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从教育文化战线发端,“臭老九"最先成为牛鬼蛇神,斯文扫地。但在农村,教师还是受人尊敬的,教师职业也是回乡知青们所向往的。郑兰秀一句“他都当老师了"的担忧,通过族姐传给了闵建华。
“莫说当老师,就是当校长,我也担心配不上她呢"。闵建华的心迹通过族姐,又传回到郑兰秀。这事就风平浪静了。
第二次算是水面上吹起的一阵微澜,发生在郑兰秀带民工帮铁路维修。
焦柳铁路修建和试运营阶段,白鹤坪就有三个比郑兰秀大一茬的优秀姑娘,因抽到铁路上做事,不久就通过招工和上铁路学校读书,进入铁路系统,当上了国家职工。
我们国家过去穷,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实现工业化,只能从农业积累资金,从农村集中资源。为此又不得不实行城乡分离的户藉管理制度,造成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三大差别"越来越严重。这种差别的严重程度,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人们,难以想像和体会的。从当时农村不少漂亮姑娘,宁嫁城里瞎跛聋哑,也要找个吃商品粮的现象中,可见一斑。
得知郑兰秀如今又上了铁路,闵建华不踏实了,着急了。如果郑兰秀被招了工,不要说她变心,就是遇到个插足的,闵建华一个"背米袋子"的民办教师,肯定争不赢人家吃商品粮的铁路工人。后来知道这只是一场虚惊,因为铁路运营早已进入正轨,基本不缺人不招工了,闵建华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三次浪头比前两次高,发生在闵建华上大学时。
那时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农村青年一到这个年龄就要结婚生子。跟闵建华和郑兰秀同龄的人,早都成家了,有些还小几岁未到法定年龄的,也有了孩子。闵建华的哥哥已成家,父母膝下孙子孙女满地跑,所以家里没人再催他。郑兰秀的家里也不催不管,由着她。两个人不说谈婚论嫁,在一起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
那年月,但凡肚子里装了点墨水,有了外界视野的年轻人,多不肯只盯着脚下的土地。在回乡青年中,闵建华有几个挚友,白天各自教书的教书,劳动的劳动。晚上大家就挤在一个床铺上,聊外面的世界,聊国家的形势,更主要的是为前途忧心,不知道将来自己去哪里,能干啥。焦虑,徬徨,无助,有时候没有话说,就默默坐着,夜深了躺一会,天亮了各自再回到昨天的岗位。
几年后,这帮朋友也陆陆续续地走了,有的参了军,有的招了工,有的上了学。闵建华还当着民办教师。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青春一年年地蹉跎。闵建华不知道前程在哪里,又不甘心一辈子呆在这里,也没心思考虑结婚。苦闷煎熬,一等再等。等到1976年,南校创新“民办公助"办学经验在教育战线的影响,公社文教组点名推荐闵建华上大学,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
拿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两个人见了面。郑兰秀单刀直入:“有什么考虑?早说!"
“你看你看,招生政策和志愿表上写的明明白白,‘哪里来那里去',三年就回来了。你等着吧。"闵建华信誓旦旦。
事与愿违,那时的大学生实行国家包分配制度。系领导讲,毕业分配计划由学校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制定,方案保密,去向保密,个人服从组织安排。别人什么情况不知道,反正从来没有老师征求过闵建华的意见。分配方案宣布后,闵建华才知道自己被留在省城,进了机关。据说是单位人事部门到学校看了档案后点着要的。
闵建华回原藉的计划被吹了,白鹤坪离省城好几百公里,今后怎么弄?不利消息一个接一个,不停冲击两人关系。当年几个同时回乡的好友,订了亲的解除了婚约,没订亲的也加入游说团,劝闵建华认清现实,直指今后长期的牛郎织女生活,只会耽误别人的青春:“跟守活寡有多大区别?”
闵建华不可能预见到改革开放后,人员自由流动的宽松,自主择业空间的广阔,确实起了犹豫。郑兰秀不傻,眼下的情形心知肚明。更主要的是,郑兰秀是个有人格尊严、意志坚强的人,不会乞求人依赖人,更不会哭天喊地,胡搅蛮缠。两人平和地见了最后一面,郑兰秀没说一句埋怨责怪的话。这却比骂一顿让闵建华心里更难受。
闵建华知道,郑兰秀表面平静,内心滴血。不论怎么说,别人都认为是她被甩了,面子里子都没了。分手不久,郑兰秀经好心人介绍,闪婚嫁到了县城近郊。她要远离熟人,远离白鹤坪这个伤心之地。
闵建华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卑鄙小人。想起来就在心里骂自己自私、冷血、龌龊、无耻。闵建华跟郑兰秀的关系不存在了,但郑兰秀仍然占据着他的心,脑袋里满是郑兰秀的愁眉苦形。闵建华由衷地希望郑兰秀好,希望她早点走出伤痛。甚至幻想郑兰秀找到的是比自己强十倍百倍的人,愿她得到更好的归宿,让她觉得离开闵建华不是损失。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的负罪感才会轻一点。
闵建华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感情。大学的女同学,单位的女同事,也有给他抛绣球的,他一个不接。闵建华现在才发现,没有了郑兰秀,他的心里再也装不进别人。他更是故意在情感上禁锢自己,折磨自己,作践自己,以此来赎抵罪责。
带着深深的愧疚和无尽的自责,闵建华把精力心力全部转到工作上,有事抢着做,经常加班加点,零点以后睡觉是常态。勤奋吃苦肯钻研,又因文笔基础和当校长历练出的组织能力,几年之后就成了单位干将,升职也是同批人中最早最快的。
事业的成功,不能抵消情感的伤痛。事过多年,闵建华越来越深切的体味出,分手不仅带给郑兰秀巨大打击,也让自己受伤,甚至伤得更重。郑兰秀的痛是阶段性的,时间久了可以走出来,因为她不亏任何人。自己作了亏心事,自己的内疚悔恨是自找的,这种痛会痛一辈子,永远消除不了。
转眼人到中年,闵建华已是资深剩男。敌不住世俗的眼光,更不忍年迈父母继续心碎,经人撮合,与一位大龄姑娘组合,也算有了柴米油盐、不咸不淡的日子。
50岁后,闵建华还在做着相思梦。他不是对妻子不忠,是自责太深,赎罪之念萦绕不去。心有所思,睡有所梦。梦境里,改革开放多年了,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已成历史,市场放活,农村走出的务工经商人员遍及城镇,“农民工"成为时代大潮。以闵建华的身份地位,开个店,找份差,安排个家属已不是难事。郑兰秀有时是在闵建华单位烧锅炉,有时是生意做大了,当着老总……。闵建华好不惬意,终于赎回了自己的过错。
58岁那年,按照“七上八下”不成文的干部任职规则,闵建华卸掉单位一把手职位,转到政协做了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现行体制下,单位主官临退前到人大、政协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政协实行委员制,可以不坐班,没有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职位硬性责任。一句话,比较清闲。平时工作调研多,考察多,闵建华也有了闲情逸致“多走走、多看看"。现实环境的变化,带给梦里情景的升华。两人经常利用闲暇,或背包,或跟团,三山五岳,天南海北,饱览秀美河山,尽诉心曲衷肠,把从网上搜索到的5A景区欣赏了个遍。
年轻时郑兰秀是白鹤坪宣传队的骨干,闵建华则五音不全,无缘入列。半退后赶紧报上老年大学,学声乐,学二胡,弥补当年留下的遗憾。白天教室上课练习,晚上梦里琴瑟和鸣,无数次地圆着年轻时的梦想。
退休后,这些年带孙女,闵建华又像回到了工作时的状态,早上六点起床准备早点,开始接班,晚上七点孩子们下班回来吃完收完着手交班。交班后及周末才是自己的自由支配时间。吃喝拉撒睡,抱喂洗漱遛,眼睛一睁,忙到熄灯。闵建华甘愿接受这份劳累,他要把对妻子女儿的欠账,从孙女这儿补回来。他调侃自己是在疲乏其身,愉悦其心;老有所为,将功补过。他觉得这种日子有苦有乐,苦多乐多;自找苦吃,自得其乐。有老同事问,带孙子跟带班子比,如何?他只拿退居二线后的日子作比,笑称:在政协的工作状态是,“无责无压力,心闲事不急,忘时忘日过,不知星期几”;带孙女的情形是,“盯紧不眨眼,心手都不闲,一年又一年,只盼星期天。"哈哈哈……。
人们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闵建华说孙女是爷爷的丝棉袄。闵建华虽然是姥爷身份,但小孙女一开口就教她叫的是爷爷。看着稚嫩可爱的小孙女在自己怀里、肩上慢慢长大,越来越乖巧,越来越会亲近人,闵建华漫长的心情阴冷期开始变暖,对郑兰秀虽念念不忘,但负疚的重压有了部分转移和缓解。
谁能料到,音信隔绝近半个世纪,听到的竟是令人窒息的消息!人,不能做亏心事。亏人自责,亏心天谴。犯了错,老天爷未必给你补偿机会。闵建华追悔莫及:“这笔心债今生是还不清了!”
百感交集的闵建华,脑中回放着几十年来,心灵遭受反复击打的一幕幕。一辈子的思念,一辈子的愧疚,一辈子的牵挂,一辈子的忏悔。由于生性怯懦,各种顾虑,闷在了心里一辈子。一念之差,伤人伤己;痛定思痛,亡羊补牢。闵建华终于下定决心,他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当面向郑兰秀说一声“对不起!"
主意拿定,闵建华毫无保留地向老妻坦陈自己的心路历程。得到理解和支持后,毅然登上了开往鄂钟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