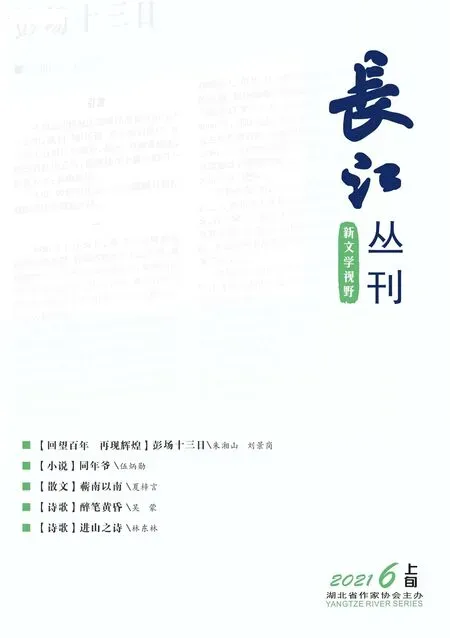圈
2021-11-12■吴斌
■ 吴 斌
在我的朋友圈中,联系最频繁的是牌友圈。为了不让自己“闲置”,一段时间,我像“小猫钓鱼”。同学朋友约我打麻将时,我在想读书写作的事;关在书房码字时,又在后悔打过的几张臭牌。牌友谬赞我是麻坛的文化能人,文友称赞我是文坛的麻将高手。输钱不输人品,那是血染的风采;输钱又输手气,却是癞子脚板长疮,上下都有毛病。
每次想打牌娱乐,我总是联系张富强、徐峰和田歌。我们几个退职后,经常在一起打小牌抽头子喝酒。输赢不是目的,时不时在圈里冒冒泡,是为了宣示存在感。有的同学长时间不联系,一打听,不久前离世了,徒生一些悲哀。
张富强曾在城北高中当校长。徐峰在职业高中当校长时迟张富强几年。徐峰平时有点不买张富强的帐。我和徐峰、张富强都是蒿子口中学的同学,一直以同学的高度相互衡量。但他俩都是校长,似乎特别在意对方的看法。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见面就掐。仿佛前世的冤孽。既是同学,又是圈子内的人,似乎没有隐私可言,也不需要设防。相互调侃不光彩的事,散布鲜为人知的八卦,仿佛是彼此的乐趣。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我就从中斡旋。但凡俗世之人,都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都在意荣辱毁誉,都想赢得他人的尊重。尊严像私家车一样需要定期维护和保养,才不会拉缸烧瓦。但是,凡人的偏执情绪往往隐藏在不会包容的狭隘中。
国内疫情缓解,我就迫不及待约人打牌。这天,我把人约好后,就提前去阿杜的餐馆等候。踏着轻快的脚步,犹如笼中鸟被放飞的感觉。春暖花开,燕子穿梭在屋檐下筑着乡愁。沐浴和煦的阳光,仿佛是在享受难得的奢侈。我用手遮住额头,眯着眼睛看着暌违已久的太阳,深深地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哼着“宅家”和外孙女一起唱过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阿杜餐馆规模不大,以家常菜为主。老板名叫杜茂林,小名憨子。他以前在老家当个村干部,镇上开过小餐馆。因孙子在张富强的私立学校就读,就在城北花园小区附近经营阿杜餐馆。既可以抽时间照顾一下孩子,也让生活过得去。我和张富强、田歌、徐峰等聚会时,一般都在阿杜的餐馆。他的乡土菜地道,蚌憨子腊肉霉豆渣火锅、糍粑才鱼、卤菜、清炒豆皮别有滋味。他老婆腌制的酱菜特别下饭,不少回头客吃了还捎带。因他的小名叫憨子,每当客人要品尝蚌憨子火锅时,他就非常动情地说,我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款待贵客,希望大家多多关照,然后深深地一鞠躬。熟悉的人点这道菜,就直接叫憨子。渐渐地,蚌憨子腊肉霉豆渣火锅成了餐馆的一道招牌菜。
几个人见面,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唏嘘。阿杜一边倒茶一边说,你们要是再不来,我就要关门了。大家伙各自抒发“宅家”的感慨。
张富强说,在家里憋坏了,头发几个月没剃,蓬头散发像乞丐。女儿过年帮我买的新羽绒服还没来得及穿,季节就过了。好在乡下的亲戚送的过年的干货多,老婆变着花样做饭,一家人的日子也过得踏实。
徐峰说,封城期间,尽管我没有出去打乒乓球,老婆没有去广场跳舞,但在家里学会了炸油条、蒸馒头、包饺子,老婆的厨艺大有长进,日后一定会讨儿媳妇喜欢。只是老婆把年货准备少了,老要我跑超市戴口罩测体温排队买食品。有时限量,运气背时,还买了两包变质面条。几个月呆在家里没事找事,经常吵架还真成了事。
田歌说,我也是,疫情期间,除了照顾外孙女,就在小区帮忙值守。
我说,女儿女婿都是医务工作者,封城之前就一直战斗在一线,一大家子的年饭都是分几处吃的。整天客厅厨房卧室,围腰睡衣拖鞋,除了三次下楼协助社区管理人员值班,整天在家里不是看书,就是逗二个外孙女玩。今天打牌不抽头子,我做东请大家,中午随便点几个菜,下午安排几个硬菜喝酒,庆贺“大难不死”的余生。
随后,我拿了二包烟。张富强戒了烟,就提议,打牌时尽量少抽或到外面抽。徐峰不高兴地说,你以前又不是不抽烟,还把你熏死了不成!张富强解释说,前几天到医院体检,发现肺部有的问题。徐峰又幸灾乐祸地说,看来是活不了几天啦?
我赶忙拦住话题,都是六十岁退休的人,头上都生白发了,你们能不能少争吵几句?
徐峰还是没完没了,我打牌就要抽烟。人家张校长现在还是上班族,年薪十多万,特别在意身体。
田歌说,你是在嫉妒人家,有本事你去。
徐峰用指头把烟蒂一弹说,我才不去讨私营老板轻视。别以为私企老板的钱好赚,他不会为你提供免费的午餐,一旦你的人脉资源、管理理念被榨干,你就失去利用价值,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
田歌说,你别说,这次疫情期间,他们学校线上线下没有耽误学生的课程,还幸亏张校长组织有方。
几年前,“理工男”张富强就出版了三本书。尽管是教育管理方面的书,但至少说明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张富强能到私立学校当校长,也充分说明他的管理能力。单就文章而论,他担任校长多年,即便是随笔也透露校长的架子,像述职报告,情感的表达有些不真实。张富强有底蕴,思路敏捷,用他的话说,不比我读的书少。
我随后将麻将推进自动洗牌槽内说,废话少说,打牌。
徐峰一边打牌一边不依不饶地埋怨我,你就只知道针对我。
田歌打出一张牌说,谁叫他是领导。他既像是在恭维我,又像是在挖苦我。
我故作正经地说,我上幼儿园时,老师就说我是当领导的坯子,但是……
徐峰抢着说,还坯子,是呸、呸、呸!
领导讲话你能不能不插嘴。我打断徐峰的话说,我还有但是没说,一直到高中,才混了一个科代表。享受副班级待遇。
徐峰趁机反击,你是打娘胎里生下来就不肯长。光一个副科就原地踏步二十年。
张富强和了一把牌,就得意地凑近徐峰说,听说你从校长退下来时,有教工拿着扫帚在你的办公室扫你出门?
徐峰朝他喷了一口烟,辩解说,全教育系统都知道,那个人是上面挂了号的“翘扁担”。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校长被免职,不也有教师在操场燃放鞭炮送瘟神吗?
张富强站起来,眯着眼睛皱着鼻子,右手不停地驱散弥漫在室内的烟雾,随手拉开门,吸了一口气。冲着楼下大喊,服务员,上菜。
上菜时,张富强看了一眼服务员说,这姑娘见着面生,小巫姑娘呢?
徐峰说,就你喜欢那个姑娘。下次再来,我要阿杜把她调过来。
田歌说,你还别说,人家小巫姑娘也挺喜欢他的。
徐峰揭发说,他读高中“开门办学”时,就喜欢看弯腰劳动的女同学的胸部。
张富强也口无遮拦地说,你呢,上课打个响屁,还用手对女同学比划,像打枪似的。
我笑着补充道,他屁股一撅,快速在屁股上捏一把,然后就用臭不可闻的手捂身边男同学的鼻子。身边的男同学只要一听到他的屁响,就立马走人。
哈哈……几个人的眼泪都笑出来了。阿杜也过来凑热闹,说起蹭饭的顺口溜:“进门笑嘻嘻,桌上像夫妻,肚子吃饱了,去他妈的B”。张富强对阿杜说:“万水千山总是情,来盘赊帐行不行?”阿杜接着说:“洒向人间都是爱,相信哥哥不耍赖。”笑着笑着,酒也倒满了。
“国粹”麻将仿佛是我们步入老年后的专用产品。人生如打麻将开门,选好筒、条、万的门子就能和牌,犹如人生,选准了方向就是打好了基础,就可以一往无前。打牌也能看出人品。出牌快的人肯定是豪爽之人;出牌不慌不忙的人肯定藏有不为人知的稳重;老要别人催着出牌的人绝非干脆利落之人;爱摔牌发脾气的人肯定是急性子;爱把牌抽进抽出的人绝对是优柔寡断之人;总爱对上下家絮叨手气差、牌不好的人绝不是坦诚之辈。我总是标榜自己是牌坛“急先锋”。
我的父母和徐峰的父母当年下放蒿子口时,我与张富强、徐峰高中同学一年。母亲后来调回县城,我就在县城读高二。毕业后,我下放知青队时,与徐峰后来的老婆刘玉英同一个队。徐峰当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就在张富强家附近。招生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徐峰和刘玉英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学院。而张富强则考入了县师范。我是第二年上的师专。大学毕业后,徐峰直接分配在城北高中教书,次年,我也从某镇中学调到城北高中。张富强则在乡镇中学教初中。他俩差不多在撤县建市时提拔的副校长。而张富强则是从乡镇中学校长调到城北当校长的。早徐峰任校长几年。外人都知道,尽管级别一样,但不可同日而语。从教学质量上看,城北肯定比职高强,城北拥有绝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不言而喻的差异摆在了明处,同学的高度在现实中很难平衡,两人的较劲也就拉开了序幕,但从不撕破脸皮。作为同学,我双方都不得罪,两边打圆场。他俩似乎都对我都不设防,充分相信我不是传是道非的小人,不管有什么想法,不是在我这里发泄,就在田歌面前絮叨。
张富强认为,农村出生的孩子不能和城里长大的孩子比。徐峰的父母是南下干部,有先天的优越感,性格比较强势。
徐峰觉得,张富强不外乎是一个中专生,通过函授拿的本科学历,不值一谈。但是,他的自尊心很强,唯恐别人小觑。他当校长的架子大,但不能总惯着。
张富强说,在职高当校长,就是强盗看皮影戏——混时间。要我到职高当一把手,还不如在城北当副校长。
徐峰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他凭什么想管我?他跟副职还争抢过小车。我就不信邪,以后靠升学率说话。
我始终觉得,他俩较劲,只要不侮辱人格,不带脏字,并不是一件坏事。似乎还印证了一个浅显的哲理:很多人都是在被人瞧不起的境况下奋发的。只是很少见像他俩在一起就掐,不在一起又互相惦记。至少,他们比使绊子、戳路子的小人磊落,比当面喊哥哥,背后摸家伙的伪君子坦荡。这一点,田歌也深有体会。张富强上报提拔担任教导主任多年的他为副校长时,就被一封匿名信给耽误了。理由:一是告张富强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亲信;二是告教音乐的田歌不务正业,责任心不强。不仅经常擅自与老师调课打麻将,还利用课余、节假日补课捞外快。等上级纪委落实还他清白时,黄花菜已经凉了。官场提拔考核公示干部的时间差,比中国女排的技战术“时间差”微妙。一场球错过“时间差”没有打好,主教练可以重新调整布局,而人的机遇是“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
他俩当校长期间,在外人眼里他俩是铁哥们。遇到需要帮忙的,都各尽所能。徐峰的关系要上城北高中,张富强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张富强的关系在职高要减免费用,徐峰也会大大方方地承诺。张富强出版的书,徐峰尽管不看,但照样给他推销,反正又不要他自己掏腰包。他们似乎不是在互相帮忙,而是在向对方显示一种权利,一种让对方意会的自傲,更是在为换手挠痒埋伏笔。他们相互之间的吃请一般都邀我参加,也就显得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微妙。不像有的同学或朋友,只以观察员的身份作陪客,从来不做东道主。并且,每次在散席前都承诺,下次算我的。用农村的土话比喻:“只打雷不下雨”。
平日里无聊像坐茶馆整天打牌,饭菜就按开支抽头子。一般情况下,每和牌一次超过六十元,就抽十元作饭钱。一场牌局下来,输赢三五百元不等,能抽头子三百多元,吃饭绰绰有余。万一酒水超标,就由赢家垫付。有时候,四家都输,像AA制,人均几十元的开销。抽头子给餐馆老板做了贡献,“扩内需”。我打麻将的原则是:不是圈子里的人不打;开钱不爽快的人不打;打牌磨磨唧唧的人不打;经常责怪上家不给牌吃的人不打;赢了钱就想跑的人不打;可以和女人喝花酒,不和女人打麻将,好男不和女打。
一天,徐峰请张富强吃酒。快散席时,他们趁着酒兴想玩几圈麻将,而陪客又有事,徐峰只好给我打电话,说是三差一,要我快来救场子。等我赶到时,只见杯盘狼藉,三人酒气熏天,说话舌头打卷。顿时,我气不打一处来:哼!吃酒时没有想到我,三差一就打电话,我这个级别就是你们打麻将的“赖子”——想往哪儿靠就往哪儿靠。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给我打电话。后来,徐峰几次联系我喝酒,都以有事委婉地推辞了。
徐峰的母亲前不久过世,又让我们几个聚到一起了。守灵,仿佛也是我们打麻将喝酒的平台,说笑声比哀乐声还高出几个分贝,根本没有顾及亡灵的感受。忙完徐峰母亲的丧事,本以为相安无事,田歌却给我和张富强打电话说,徐峰两口子在闹矛盾要离婚,约哥儿几个和徐峰两口子再聚一聚,商量解决办法。徐峰和他老婆刘玉英都是招生制度改革后的首届大学生,同在一所大学,只是不同专业。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城北教书,是当时让同事们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
田歌分析,夫妻吵架,不外乎经济和情感。他俩几十年相濡以沫,未曾听到绯闻,肯定是经济上的事。
我说,困难时期挺过来了,青春躁动期也挺过来了。以他俩现在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在座的都要好。刘玉英退休后在私立学校代课,年薪十好几万。儿子在省城买了房和车,啥都不缺,只等抱孙子。他俩闹离婚,是没事找事,是更年期过后的无病呻吟。
张富强叹息道,清官难断家务事。
徐峰叼着烟耷拉着脸姗姗来迟。
田歌没见他老婆,便问,刘玉英呢?
徐峰极不高兴地说,要她来干什么。
徐峰的母亲去世,要大姨妹安排她儿子的车送葬。大姨妹私下对姐姐说,每个送葬的司机应该给一条烟。刘玉英也不加思考,就把这话转给了徐峰。徐峰顿时火冒三丈,为自己的家人送葬,要什么礼品!又不是雇请的外人。联想到以前的好多事情,就噼里啪啦地像竹筒倒豆子,将不快发泄了一通。大姨妹困难时,找他借十几万买门脸房开餐馆,他毫不犹豫地帮衬,没见她一包烟。他当校长时,也没少给她餐馆做生意,姨妹好像认为是应该的。二姨妹找他借钱二十万炒房,他也同意了。这次用了侄子一次车,就巴不得他们按“市场规律”办事。思前想后,怀疑是三姊妹合伙在骗他的存款。老婆是骗子,弟弟又在打父母房产的主意,这日子还能过吗?他还要刘玉英催促二姨妹还钱。在家里看这不顺眼,看那也不舒坦。不是责怪她把稀饭煮稀了,就是抱怨将菜炒咸了。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残羹剩饭,刘玉英单独加热他说份量少,合在一起他说是大杂烩。如果不是刘玉英告诉田歌的老婆,大家还蒙在鼓里。
田歌笑着说,你这是新仇旧恨,老账新账一起算。
张富强说,是不是徐峰在外面有新的情况了?他好像还惦记下放时候的一个女知青。
徐峰横了一眼张富强说,你少挑拨离间。
田歌阴阳怪气地说,离了婚,找个小老婆也讨不到好。她可以让你戴绿帽子。即使进单身离异交友圈找伴侣,也不是善茬,都是骗钱的主。听说学校七十多岁的郑副校长,前几年找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伴,还领了结婚证,目前正和他的子女为财产打官司呢。俗话说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携手相看两不厌。”
我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件好事。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在他们两口子身上的反映。你想啊,以前为鸡毛蒜皮的事闹矛盾或因癖好、习惯、“情况”争吵,白天闹,晚上就能和好,加之还有老人、孩子充当润滑剂。现在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节奏慢下来了,老人不在了,孩子自立了,身体内情感的润滑剂干枯了,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的激情也消失得无踪影。执手相看两眼,竟无语可言。他们吵的是有钱的架,闹的是快活矛盾。再说了,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父亲去世时,尸骨还没有火化,我的姐姐和妹妹就在灵堂问我,房产怎么处置。唯恐我这个儿子将仅值几十万房产的独吞。
田歌说,我兄弟姐妹多,知道我家境困难,生小孩的住院费都是借的,所以,这些年从来不找我的麻烦。
张富强接着说,这恰恰说明刘玉英单纯,没有心计。
徐峰反驳道,什么单纯,简直就是憨子。
我打抱不平地说,就你聪明!疫情期间,我听刘玉英说,你们本来食品准备的就不充分,她要将白菜梆子和包菜梗子做泡菜,而你却非要扔掉不可。于情于理都是你的不对。泡菜既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作配菜炒豆制品和其它食材。她是“里里外外的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学唱着《红灯记》里的唱段。
的确是的,徐峰也不是精明之人。张富强附和我说,他刚当校长的头二年,就把学校几百万的债务还了百分之八十,就不知道少还一点,多给教职员工发点福利。现在哪个领导不把员工安抚好,哪个单位不是借债搞建设。当然,他爱校如家的情结是值得表扬的。张富强说完朝我眨了几下眼。
徐峰依然不依不饶地调侃,你少埋汰我,就你会拉拢群众。据说,你到私立学校当校长,受了不少窝囊气,几百元的进餐费都是班主任给你报的。
这是无稽之谈,纯属造谣。张富强觉得徐峰的话有损他的形象,即刻反驳说。
我又回到正题说,其实,人世间的邂逅,看似偶然,实是缘分,仿佛前世圈定。包括婚姻,红颜、蓝颜知己和交际圈。圈子的宽窄决定人生的走向和命运。古人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土话“鱼找鱼虾找虾乌龟配王八”。当初徐峰刘玉英结婚时,好多人羡慕他俩郎才女貌,好似一对金童玉女。
田歌说,其实,徐峰是非常爱刘玉英的。上前年,刘玉英在省城某私立学校代课,因病毒性感冒引发心肌炎,徐峰连夜赶去照顾,路上还痛哭流涕。只是还没等刘玉英出院,他就跑回来打麻将了。
张富强抢过话题,这个你就不清楚了,那天晚上他酒喝多了,司机是我安排的。司机回来说,他哭到毛嘴就睡着了。
说得我们哈哈大笑。从出发地经过毛嘴也就十来公里的高速路。
一天,我和张富强在阿杜餐馆陪客吃饭,阿杜端着酒杯进来对我说,有个麻烦事要请你帮忙。什么事?我放下筷子问。阿杜说,我同学的儿子开车回老家时,因不熟悉新城区路况,收到两张违章罚单。能不能找关系将此事摆平?
张富强主动说,这事简单。徐峰有个学生是交管的副支队长。我们以前常找他学生帮忙。等徐峰、田歌回来后,我来联系他们,你负责把生活安排好,为他们接风洗尘。
阿杜问,他们到哪里潇洒去了?
张富强说,田歌夫妻俩陪他夫妻俩到利川散几天心。阿杜说,你们怎么不一起去呢?
我说,现在老张不是还走不开吗?
最近这几年,我每年都邀约单位的几个好兄弟开车出去旅游一次。自驾游,AA制,选择门票打折的淡季。出行只需在网上确定一个终点目的地,返程不重复就行。如前年的目的地是山西的大寨村,过南街村。去年的目的地是江苏的华西村。
阿杜问,怎么不往风景名胜地跑?
我接着说,那是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寻访影响我们几十年本心的原点。沿途景点一路欣赏,遇到美景多流连;对名不副实的景区,就走马观花。碰到好吃的美食,就大快朵颐,多喝两杯;看见中意的土特产品,就带点回来送给朋友。年纪说大就大,毕竟是退了休的老干部;说小就小,如果根据人的平均寿命八十岁而论,人生可分成四个年龄段,我们现在正处在第四年龄段的青春年华。基本摆脱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羁绊,基本解决了老有所养的后顾之忧。只是经常打牌,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少了,相互沟通也就少了,指不定还会产生新矛盾。
阿杜说,网上说经常打麻将动脑子,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张富强也说,大赌伤身违法,小赌怡情混点,相当于开启结伴养老新模式。我的合同今年到期,明年咱就可以出去潇洒了。
三国时,吴国的韦昭在《博弈论》中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老有所乐并不是要天天打麻将。一上桌就想着如何算计别人,还提防别人算计自己。麻将声在烟雾中缭绕,荤段子在酒精里发酵。惶恐与忧虑缠绕,困惑共颓废纠结。且不说一天到晚心神疲惫,还经常为钱的事扯皮,不仅影响团结,更影响时不我待的身体。生闷气、发脾气,血压就往上冲;讲义气、图豪爽,饮酒八两不嫌少。身体垮了,谁管你?牌朋、酒友能来看你一下就是最讲感情的了。这看似淡定的消磨,也常常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用旁门左道的麻将来参悟人生哲理,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就这样算了吧!就当一次不值得回味的擦肩,当一次不愉快的旅游。趁现在能走动,脑子还灵活,来一场真正的旅游。览一览祖国的河山,看一看社会的变化,是最好的养老形式,不仅愉悦养性、消疴驱烦,还能效仿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难以摆脱的圈,仿佛是一个人前世注定的世界。它制约人的活动范围,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既像无影无形的圈(juàn),也像孩童用肥皂水吹出的一串串大小不等的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