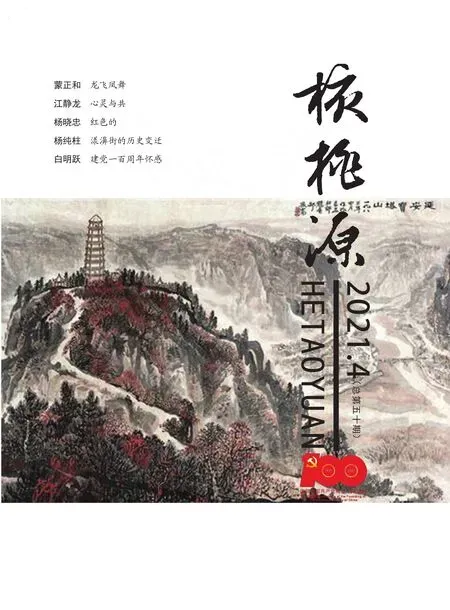三生记
2021-11-12吉海珍
吉海珍
一个梦,总在不同季节的深夜重复着走向黎明。
面积不等的两间院落,小院有一间正房、一间耳房、一间厨房,一面围墙。大院有两间猪圈、一间牛圈。那里住着人、物件以及人在时间里与其他人和物件之间的回忆,那里是情感的发源地,也是心灵的归属地,那是一院旧居所。
沿着梦里的亮光,走进厨房,火塘里火苗不停地舔舐着周身布满锅烟的铜壶底部,壶里的水扑哧扑哧冒着白汽,这一切是仿佛从那根灯芯中映射在红色的土墙上,又仿佛来自那一堆火。火塘,一口一口吞噬着干透了的栗子树柴块,时间在火塘中燃烧变成灰尘。确实是灰色的,更准确的说是灰白色。柴块越来越短,时间也越来越短,万物都在一瞬间一瞬间地成长,苍老,最终走向自己的归宿。
归宿,无非就是像柴块和时间一样变成灰白色被埋藏在泥土深处,说不定还能滋养出一片草地或是一棵苍天大树,那么就让树或草替我们继续活着。我说的也包括梦里的那间南北向的正房,现在应该称之为老屋了,老屋的前身是更老的老屋,新屋子替老屋子活着,仿佛除了时间一切都没有变,其实恰恰就是在看似没有改变的时间里什么都变了。
每一天,一些变化在时间里有形或无形、有声或无声地发生着,在我们进行任何劳作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这些变化就已经在发生,即便我们睡着的时候,那些变化依然没有停止。瓦片在某一天的正午悄然断裂,瓦浆草在某一场雨后突然冒了出来,土墙在一阵风中掉落了几块……这些变化就这样发生着,在我的出生地。
出生地,作为一种独特的形象,烙印在每个扎根在异乡的人心中,那里是一块圣地,每一个游子都向着那里朝圣。那里亦是一片净土,封存着儿时的纯真和友善,最后,那里是归处,安放灵魂。每个人的出生地都是其他地方取代不了的特设,对于我,亦是如此。父母亲,我,儿子,在不同时代降生,在血脉的传承和生命的延续中,一些新生命和新物件不断诞生,不断推着旧的老的东西走向衰老、颓败。
1
在偌大的存储回忆的容量里翻阅,在这段故事里我仅仅只是一个聆听者。那是发生在1962的事,那时冬天已经结束,牛圈背后的桃花刚刚冒出花骨朵,父亲像是赶着来看春天的第一朵挑花,就急匆匆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那时候,土地贫瘠,收成不好,人们也穷苦,这似乎也决定了父亲要开始他艰难的生活。父亲那一辈,每家几乎都有五六个孩子,多的有八九个,要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就要不断扩大土地的面积,开垦,耕作,耕作,开垦,这是祖辈们一代代唯一可以走的路。脸朝黄土背朝天确实是很形象地总结了劳作这件事,也描绘出了一个被称为农民的群体的形象,这也是我出生地的村庄以及整个无数个他人的出生地上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的一种境遇,确切地说是处境、困境。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所有的族亲就这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着,直到父亲以及舅舅走出村庄,才有了另外一条可以走的路,生活才有了另一种选择,这也使得我在后来的时间里不用延续族亲们重复而又艰难的生活。
在这样一条生活的变化史中,时间长成一个巨大的裂谷,这条裂谷叫时代,那些我们所熟悉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更早的年代,常有人说,我们之间有隔阂,这便是因为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和遭遇不同,而造成对事物的认知、对生活的感受等方面的差异,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60年代、70年代的歌,歌曲似乎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特点而又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传唱的,这也是除了文字以外,记录时代的一种方式。
如果要为父亲的一生写一首歌,那么建房应该算是重要的事件,而整首歌应该以忧伤为主旋律,这个忧伤来自奶奶的离世,那时父亲不过九岁,对死亡充满了未知,所面对过的死亡还极少,即便如此,心中的疼痛应该不会亚于任何一个成年人,所以,至今我都不敢向父亲问起任何关于奶奶的话题,这种疼痛在父亲心理埋藏了这么多年,一定蓄积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摧毁父亲的坚强。是的,父亲是坚强的,幼年丧母的父亲,不得不挑起比同龄人更沉重的生活担子,外婆时常会说起父亲的勤劳、节俭,说起父亲上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要自己挣生活费,所谓的生活费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钱,而是一些可以食用的食物,譬如南瓜、洋丝瓜,更多的时候甚至是一些野菜。走过了幼时的苦日子,少年时代父亲又扛起了建房的重担,生活总是在父亲的双肩压上一副担子,越来越重的担子。
阳光,随着父亲的锄头,高高低低地窥探越来越深的屋基,原先的它们只是铺在大地的表面,从未想过还可以到达更深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土地太抗拒,阳光试探再三只能疲倦地躺着,那一刻,它们跳进了父亲刚挖好的基曹里,挤得父亲踉跄地后退。
石头还未填充到基槽里,基槽已经被阳光占领,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连石头的表面都是,父亲不忍心砸伤这些阳光,选择了一个阴天,把石脚下好。
木头像是从石脚里长出来,即便没有根也稳固,这些以及之后的一些过程,在村子里称之为竖房子,所谓竖就是竖大梁,位于正中间的横梁是最为重要的,横梁正中间的位置用画着八卦图的红布裹着,预示着家宅平安。糖果、粑粑、硬币、水被分批吊上中梁,这是整个仪式的高潮部分,安梁师傅一边念着吉利的话,一边向下抛撒粑粑、糖果、硬币,待大家去拾捡的时候,另一个安梁师傅对着拾捡的人群洒水,这个过程叫抢粑粑,主人必须抢到最大的粑粑才算吉利,所以少不了湿身,参与的和围观的都开心。每一家竖房子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会在村子里传开,讲上好几天,待下一家竖房子的时候,还会被提及某家竖房子抢粑粑的过程中发生的趣事。(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家建盖木头房子了,也不用人力挖地基,机械化取代了父亲曾经干过的活计,钢筋水泥,没有了可以竖的木头,一些乐趣也就消失了,比我更小的已经不知道村子里有抢粑粑的风俗了,那些故事也像被人讲厌烦了一样,再也没有被人提起过来。)
由于阳光好不容易找到的领地被父亲用石头和泥巴填充,因此父亲在舂墙的时候,阳光总是恶狠狠地盯着,有时是父亲的脸,有时是胸膛,多数时候是父亲的背,以及他扛在肩上用竹子编成的簸箕和簸箕里红色的黏土上,它们把自己所有的重量都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那穿着红色背心的肩膀被压得通红,有时他们也尝试把所有的热量都投向父亲,让父亲的皮肤越来越黑,甚至撕下一层薄薄的皮。阳光,还像无数个监工,监督父亲是否把墙舂得结实,有时父亲生气,也会把簸箕翻过来,把一些阳光埋在泥土下面,然后用力锤,把一缕缕阳光锤得比叶片还薄,有些阳光被锤子打碎和土黏在一起,最后把它们永远镶嵌在墙里,这也是当我靠着墙时总能感到温暖的缘故。
一排排的草敞开身子,躺在一排留有间隙的松木上,让自己完全被阳光,风雨,星辰拥抱,仿佛有一种守护父亲的使命,他们对父亲绝对忠诚,绝不让父亲的梦被这些东西窥探到,哪怕它自己,也不看。但时间一长,它抵抗不住阳光和雨水的折磨,开始慢慢发白,房屋开始透光,阳光、星光、时光。
草房,作为人们的居所,曾经普遍出现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民族形成了农耕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单从字眼上看就是磨难的,艰苦的。它是一个时代产物和缩影,曾经具有普遍性。一代人从茅屋里离去,一代人在茅屋里出生,我就出生在茅屋里。
茅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几乎席地的床,一盘石磨,一个火塘,遇到下雨天,屋后的阴沟,水就从火塘和床之间、从门坎的木头下往外流,雨天的很多时候,屋里屋外一样湿漉漉的,这大概是我对草屋最初和最永恒的记忆。
是的,我就出生在这间茅屋里火塘边的小床上,母亲就在这间潮湿的茅屋里做月子。父亲和母亲属于同一个村同一支的人,外公和爷爷家原本就是本家,两家分别住在坎上和坎下,我们通常说上坎下坎,两家人说话大声点都能被另一家听到。那时,总有很多人填不饱肚子,听外婆讲过到山里挖草根,外婆说她坐月子的时候喝芭蕉芯煮的汤,好多人都这么喝,结果很多人得了水肿。许多人对58、59年印象深刻,那是充满饥饿的年代,听老一辈人说起,村里有人因为饿,晚上偷了玉米偷偷到山里烤吃,最后活活把自己撑死了。对于这样的死亡方式,很多人难以理解,许多像这样以及更难理解的事情发生在那个时代,回到现在的社会,这些事情遥远得仿佛是虚构。
2
父亲、我和妹妹都——离开了村庄,只留下母亲一个人守着老家的房子、守着干瘪的田地,多少年了,母亲站在梧桐树下迎接和送别我们的场景始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迎接我们时的激动和送别时的失落形成了深深的对比,多少次我都不敢回头,可即便不回头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看着后视镜里母亲越来越远、身影越来越小,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着我,母亲估计也偷偷落过不少泪。出生地是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从中汲取养分,写成了我的《出生地》,用来怀念因缺水而荒芜的梯田,因长期离家而渐渐陈旧的房屋,也用来展示越来越走向富裕和美丽的村庄。
房子是村庄变样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外婆那一代人盖草房,父亲这一代将草房变成瓦房,我们这一代又将瓦房变成平房,这种变化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时间改变了村庄,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打破了人们对美多年不变的看法和做法,改变成为了推动时代发展的动力,成为了破除陈旧的利器,同时也成为了走向富裕的路径。
那是发生在还没有成功走出贫困之前,在母亲回忆里的某一天,具体日期母亲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星期六,刚好是赶集天,那天早上家里的油刚好吃完,按照母亲的计划,赶集天去集市上买,那时在农村里一周所要吃和用的都要在赶集天去买,可是刚好那天早上家里来了客人,家里没有油母亲无法做菜。直到现在母亲讲起此事都是一脸的难为情。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是父母通过自己的双手依然把瓦房盖了起来,妹妹就出生在新建盖的瓦房下。
我是闻着干草的味道出生的,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母亲就为了能拥有一间自己的草房而不辞辛劳,那大概也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父亲用所有力气把墙舂得牢固,母亲把最好的草割回家,我的家便这样诞生了,那是我记忆里最老的老屋,当然对于一个孩子,更多的记忆几乎都是来自父母的描述,可那些画面仿佛就在眼前,眼前都是父亲挖基曹、下石脚、母亲割草以及一些建房的动作。
就像那时的父亲想不到他自己能住进瓦房,能走出大山,母亲也不曾想到过自己会割舍下她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土地随着我们到县城生活,其实母亲割舍不下的不止那些陪伴她多年的土地,当然还有她和父亲亲手建盖的属于他们的家,家不仅是老屋,家是一家人一起经历过的艰难和幸福的容器,对于生活在农村的母亲来说幸福其实就平平淡淡,平平安安。一些美好或痛苦的回忆随着母亲来到了县城,渐渐被时间埋葬,但总有一些记忆深处的痛便与老屋一起守着那个我出生的地方,成了母亲内心的结。
我的身份证就摆在桌子上,如同从纯净的金黄色的染料中浸泡过的阳光就照着这个时间,是的,那就是1985年。
通过历史资料可以知道这一年发生了六十七件大事,一些会议召开了,一些法律出台了,一些任务完成了,一些规划开始实施了,但对于生活在偏远深山里的父母,这一年最大的不平凡就是我的出生,其次才是那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母亲说不上是什么日子知晓的农村经济十项政策的颁布,十项政策她也说不全,她只听说好政策要来了,心里也跟着乐不停。她知道她的女儿再也不用重复她对票的渴望,粮票、布票、油票。她讲述一家人如何利用人均一尺七的布,由于农活对衣服裤子的磨损厉害,尤其是裤子,那时不仅父亲,许多和父亲一样与土地和牛打交道的几乎都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有些缝补得实在穿不了的也舍不得扔,把能用的部分剪下来用来补在其他裤子上,日子就这样在母亲的缝缝补补地走了过来。不止母亲,整个村庄里的人都是这样缝补着把日子熬过来了,那些带着补疤的日子像肌肤上的疤痕,永远长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事实上我确实没有穿过打着补丁的衣服,但我的许多同龄人那时依然穿着补丁的衣服,并且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我想我的幸福大概便是从那时就延续下来的了。)有些回忆对于母亲是刻骨铭心的,譬如生活的艰难,再如父亲重组家庭,我是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才理解了母亲的酸楚,才明白了对于母亲来说生活的艰难根本算不上什么,内心的艰难才是母亲这一生都无法痊愈的伤口和疼痛,这种疼痛同样在我和妹妹的心里生长。
这些母亲和村子里的人说不出的政策,让整个农村突然活了起来,也是父母能够将瓦房盖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户、两户,瓦房慢慢多起来,如今政策越来越好,尤其脱攻攻坚开始以后,贫困户建房几乎不用自己掏钱,其它农户也能享受其它的政策,从危旧房改造到住房质量巩固提升,农村的危房被全面消除,在这个过程中草房、垛木房、一些危旧的瓦房被拆除重建,一般的房屋得到了巩固提升,许多人借着好政策,干脆把瓦房换成了平房、别墅,这样挺好,再也没有人山上砍树,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密了。
在我的理解里,四面墙、两檐瓦就是一个家,土墙围住的不仅是阳光,还有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以及其中的一些吵闹和关心。除了房子,交通的重要性被人们不断认知,“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被人喊了无数年之后这个口号逐渐实现了。采蕨菜、捡蘑菇、烧炭是嫁到高山的三姨妈家生活主要的来源,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些牛马路,每个赶集日头晚三姨妈就要将第二天要卖的山货装在竹篮子里,第二天在黎明到来前起床,点着火把,背着山货去赶集,每次走到半路天才微亮。卖完山货,又从集市上换回油、盐、米等生活用品,回到家已经天黑,被称为“两头黑”。说到路,七十多岁的外婆也忍不住感慨,那时候她在县城上初中,到县城要走两天的路,从鸡街走到龙潭,从龙潭走到跃进(现在的顺濞),再从跃进走到漾濞,翻越无数座山,趟过几条河,最终才能进城,走到哪里天黑了,就在就近的农家借宿一夜,有时候就从路上的稻草堆里,拉几把稻草铺开,再拉几把盖在身上度夜,第二天继续赶路。外婆的经历我也有过,只不过路程缩短了好多,只是从鸡街走到龙潭,只有二十五公里,那时我在龙潭上小学,确切的说我是在小学四年级开始才到龙潭完小上学的,两个乡之间虽然通了公路,但由于车辆极少,且一般都是运输物品的货车,很难搭到顺风车,所以回家都要走路,有一次很幸运地约好了可以搭顺风车,结果等到天黑都没有等到,母亲只好把妹妹寄在外婆家,带着我和同村另一个也在龙潭上学的女孩子连夜赶路。母亲在讲述这次经历的时候,说我从小胆子就大,路过大片坟地的时候都丝毫没有一点胆怯。一般母亲都是从那个时候闭塞讲到如今的四通八达。
最近几年,每次回老家,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小路变成了大路,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这样的变化发生在无数的大山深处,道路把一个个闭塞的村庄相连,再把它们与城市连接起来,把村庄的原生态推向城市,把城市的先进引向村庄,也正因为有了无数这样的道路,一群群大山里的人才能走出山村,走向城市。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源源不断地吸引着人们走进它。
丈夫家离县城不远,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儿子回家与老人聚聚,每次回家都看到对面山上热火朝天的“大漾云”高速路施工现场,那里白天黑夜从不曾停歇,沿路还有正在修建的“大瑞”铁路,这些通道将把漾濞在更大范围内与外界相连,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又可以见到曾经作为茶马古道、盐米古道交汇处的小城的繁华。
3
在时代的选择上,儿子似乎比我看得更准一些,他选择一切就绪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出生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前一个甚至两个时代将从此划上句号。
《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的愿望就是稍微过上安康的生活,这应该就是“小康”最早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朝代的不断更替,小康从西汉的一种模式逐渐演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直到现在变成了可以看得到、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发展,人们能够共治社会、共享成果。
小康与房屋和路都息息相关,也与其他更多的东西有关。三代人,从草屋到瓦房再到平房和别墅,从小处说也是一个家庭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房屋的变化成了记录时代最好的见证。
一些事物在时间里塌陷、消陨,另一些事物又悄然而生。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我们看到某些东西在疯长,某些东西在塌陷也在重构。塌陷,心里的塌陷和实物的塌陷。譬如,由于我们的离开,老家的那些建筑,瓦房,杂物房,猪圈,牛圈,围墙,还有那扇快要完成坍塌的大门,这些都将随着时间的前进而逐步变成废墟,随着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故乡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废墟,所有的废墟都将在遥远的一天彻底消失,仿佛从来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其存在又有迹可循。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往事的回忆次数会逐渐增多。细算下来,回忆是对过往生活的一场场回放,里面有着无数具体的事件和人物组成。比如经历,比如味道,比如情感,比如家庭,这些都是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的,经历了多少时光,那么多时光中的人和事都没有将其磨平和取代,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这种感觉我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随着侄儿的出生,母亲随妹妹到了城里生活,如今已经五年,在离开土地的漫长的时间里,她总是不经意间就聊到了小溪边的菜地、黄果园的黄果,河边的稻田、高山的核桃地还有只剩下半截土墙的专房……当然牵挂最多的还是外公外婆,每隔一两天,母亲便会拨通外公或外婆的电话,聊上一会,聊聊自家的事,再聊聊村子里的变化。
4
是的,就像塌陷每天都在发生,废墟每天都在增加一样,村庄每天也在发生着变化,更为自豪的是,我曾以一名驻村工作队长的身份参与了这些变化的发生。我曾经在驻村日记中写到,我们开始了对一群陌生人进行分析,对他们所得的贫困之疾病进行诊断,剖析,再根据病症所在对症下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像一批进驻村子的医生,将村子及居住在村子里的人的贫困疾病治愈。贫困确实是一种疾病,这个疾病已经延续了几代人,而这个疾病要在我们这些人手里被治愈,这就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使命。
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一个庞大的群体依靠着土地和天生存,并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包括我的族亲,而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又被剥离出更需要被关注被帮助的一部分,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愿意被冠以一个特定的称号,因为从他们的行动上来说,他们都是自强、自立的,只因一些他们自己无法克服和改变的困难,这些困难或是交通不畅,或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或因疾病缠身,这样一群人在各自的村庄艰难地想要摆脱贫困,这就是被陡缓不一的泥土路串连起的炙热的词语——贫困户。
这也让我想起了先秦时期的农家,以及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但始终存在的农民群体,这个带有时间、空间、价值、领域四维特性的群体,他们拥有和土地一样的慈祥,他们用自己厚厚的老茧丈量着大地的宽度,用自己额头排满的皱纹记录大地的纹路。他们依赖着土地,随着土地制度的改革而不断变化着与土地的关系。
事物总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在发展,草房,瓦房,平房。是房屋的演变史,赶马路,泥巴路,水泥路是道路的进化史。经济社会发展是其最大的推动力,房屋、道路经历了三次重生。时代在房屋和道路的变化中不断发展,父母亲、我、儿子三代人,有着阶梯式的变化,越来越宽敞的路,越来越明亮的房屋,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小康,从原来一个概念逐渐变成了现实,变成了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衣食住行。从一户人家的小康,到另一户人家的小康,从一个聚集地的小康到另一个聚集地的小康,我们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将贫困这个标志慢慢淡化,直至全部消除。
最近一次回老家是清明节,核桃树已经开始发芽,在点点的翠绿中,一栋栋农村别墅向人们展示着村庄以及别墅里的人们的新生活,所谓新生活是与过去相比来讲,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草房、瓦房相比,房屋外形、结构、材料的变化,也是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提升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我想要说的关于房子的三生记。房子在一代代的变化,村庄里的人一代代延续,只有一代代的血脉延续,一代代人的回忆连接起来才有了时间的连续性。
房屋把母亲、我、儿子联系在一起。路把村庄、城市联系起来,把远方变成近处。时间把过去、现在、将来联系在一起,连成一幅历史长卷,无论何时打开都有某个时段的印记。在这长长的画卷中,我,我的老屋,我的族亲,我的村庄,都是一个历史的缩影,我们所经历过的、正在经历的和即将经历的都是对社会生活的记录,无论是人还是像老屋一样的建筑都是一本本历史书,不论是父母亲还是我,即便是儿子也将成为后来人的历史,我们都是人类璨若星河的历史中的一颗小星星,在各自的固定的轨道上自转和公转。当人们打开这些历史书,人们会看到中国历史的某个时间段在某个坐标上,这是许多人、许多村庄一起迈向小康和实现小康的历程。
历史的长河从未停止流动,人类的进步也从未停止,变化也从未停止,县城东片区又有新的楼盘即将竣工,还有不少楼盘将开盘,一套套的新房、一栋栋的别墅又将成为不少人的新家,房屋的三生记远不是终点,是在时间坐标上的另一个变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