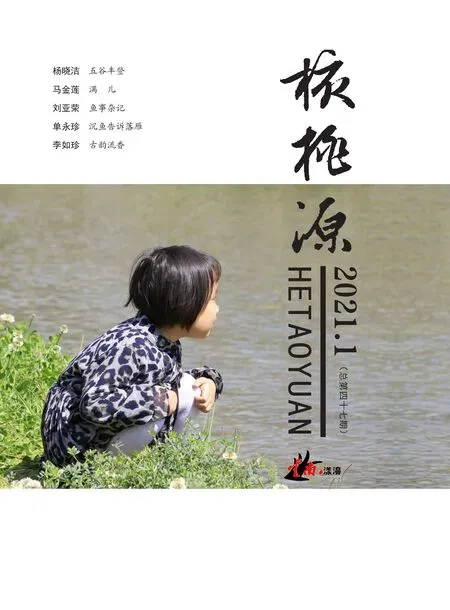一次旅行
2021-11-12
在十字路口的一个烤羊肉串摊子上吃了三十串羊肉,喝完了两瓶啤酒,抽了一棵烟,抬腕看表,夜里十一点整。结了帐,刚直起身,蹦蹦车就很有眼色地停在了身旁。平时横冲直撞、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蹦蹦车,这时倒不觉得十分反感了。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是如此。此一时彼一时。勾腰撅屁股地钻进车棚,说了声火车站,这就出发了。
从固原上车的不是我一个。还有安澜。此刻就坐在蹦蹦车上跟我胡谝。
早晨八点,还在被窝里躺着的时候,杨顺就打电话说:我刚刚得到信息,有一个叫安澜的人,出差在固原。他说他认识你。他会跟你打电话联系,他不回银川了。你们两个直接从固原上车。但火车票我是从银川买的始发票,硬卧。免得你们中途上车没地方。
候车室里灯火辉煌。到处都是人影,晃来晃去。特别扎眼的是一堆勉强将几块艳布挂搭在身上要害部位的女子。她们散淡随意地坐在候车室的硬椅上,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额头眼角装饰的星星在盼顾之间闪闪发亮,晃荡在双乳前面的彩色手机不时亮起红黄蓝绿的信号,香艳的味道裹拥着一堆白花花的肉体,在候车室里动荡起放浪形骸的意味。
候车的男男女女从她们面前走过来穿过去,面色沉稳,眼珠子乱转。
安澜坐立不安地走了两个来回。对我说:看见吗?小姐们异地交流很频繁啊。我希望她们跟我们同一个车次,陪我们到西安。不行,啤酒喝多了,我要上厕所。
上完厕所,安澜满脸的惬意。点着一棵烟说,这一下舒服多了。
列车马上到站,乘客检票进站。我和安澜的票都在杨顺手里。检票员不让进。
安澜像被提起来的鸭子,伸着脖子看着已经检票进站的小姐们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人在固原,可我们是从银川买的票,而且还是硬卧,为什么不让我们进站?
检票员说:我没到银川去过。
我拉着安澜出了候车室的门,从南面的斜坡上大踏步上去,就到了月台上,站到了那一堆小姐的身后。
别的火车站我不敢说,固原火车站还是熟悉的。老老实实挤挤巴巴像犯人出狱一样地接受检查那是傻子。如果有车,我连车都能开到这儿来,还别说是个人。我对安澜说。可是很明显安澜现在并没有心思听我说什么。我也就不说了。
钢铁与钢铁的碰撞所产生的轰鸣从远处沉重而缓慢地传来。列车的顶灯并没有像利剑那样刺破夜空,在站台灯火通明的映照下,如同一盏瓦数不大的灯泡,失去了它应有的亮光。
车门一开,穿着白背心、黑色大裤头、腰里缠着大钱包的杨顺和一身清爽打扮的梁燕就跳下车来,远远地伸着手说:欢迎欢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们误车。现在总算放心了。
梁燕的手温热而柔软。
我说:热烈庆祝两路大军顺利会师。
然后登车。
列车上比站台上还要凉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梁燕说:我们运气好,这是空调车,今天第一次运营,就让我们碰上了。
我眯着眼打量着梁燕说:梁燕,以往你下基层来采访,我从来都没有发现你穿得这么少过。怎么今天……形象大变!
梁燕说:怎么?这样打扮不好吗?
我赶忙说:不是不是。只是以往你在穿着方面太严谨了,突然开放,穿得这么性感,让人感觉怪怪的,一下不好接受。
旅游嘛。对不对?何况这么热的天。像你这样穿着,到不了福州,保证整个人都捂馊了。带没带短裤?梁燕问。
没有。
没关系,到西安我买条短裤送给你。
车窗外漆黑一团,远处的灯火忽明忽灭。固原,早已经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列车富有节奏的铿锵声中,我感觉到累了、困了。
说了这么半天话,我还不知道今晚我的窝在哪儿呢。这是你的铺吧?我说。
梁燕握着我的手说:人常说良宵苦短。怎么,跟我还没说上几句热心话,就想睡了?我还以为你要跟我相拥而坐,倾诉到天亮呢。别忙着睡好吗?来,喝水。
这是你无法拒绝的,就像这康师傅绿茶。它除了有能解渴的水,还有能提神的茶,更添加了满足口感和顺肠润肺的蜜。在我跟梁燕的几年交往中,她总能在恰当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给我类似于康师傅绿茶一样的东西,让我对她既言听计从,又心甘情愿地鞍前马后。
杨顺走过来问:安澜呢?这家伙从一上车就不见了人,到哪儿去了?
我说:你顺着车厢走。看哪儿有一群小姐,安澜就在那儿。我的话,不会错。
杨顺笑得直拍大腿。说:有知音了有知音了。我这就去找他去。你的铺就在这儿。就在梁燕的对面。你们两个可以好好说说话。安澜的铺在上面。
我说:杨顺,我的票呢?
杨顺说:在我身上在我身上。你用不着担心。查票的时候我统一让他们验。大家分开拿着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杨顺一走,梁燕也站起身说:你要真的觉得困,就睡吧。我还得去看看其他人。总共要三十四个人,举行座谈会,游览市区,召集上火车,在银川就折腾了一天。当个领队真是麻烦。
困倦疲惫由情绪控制。梁燕这么一说一走,明明想尽快入睡休息的我,反而精神了起来。对呀,这又不是日常生活,明天还要早早起来按时去上班。现在是出去旅游。旅游不是花了钱在火车上睡硬卧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天天说在口头上,写在稿纸上,真正落到实处的有多少呢?梁燕下基层来订报、采访人物事件,什么时候穿着露出肚脐眼、光着两条胳膊的短衫?大冬天连高档一点的羽绒服都不穿,就一件军大衣裹得全身上下像只绿色的桶。现在看看,线条毕露。人家这才叫既有工作能力又会享受生活。自己才是真正的老土。平时巴望着能和梁燕多接触好说说心里话,而且潜意识里还时不时地想入非非。今天这是怎么了?机会来了,话没说上两句,就想蒙头大睡。有病啊?是不是觉得梁燕平时很严谨,尽管自己没有得到她,除了她丈夫,别人也没有染指的可能。现在人家把该露的都露出来了,但人人都有观秀色以养眼的权力,并不是特别地关照你,心里觉得委屈?
越想越生自己的气。
好!我也去找找安澜和杨顺。就去找找小姐看。端详美丽的姑娘又不是罪过。不是瞎子谁不会啊?
还真在硬座车厢把两个王八蛋和那群小姐给找着了。
杨顺停下手里的牌,望着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好好好,我们的队伍在壮大。坐下来玩两把?
我说:玩什么呢?
安澜说:扎金花!有刺激。来不来?
杨顺问:梁领队呢?
我说:她到车厢里看其他的人去了。
我这座位上出彩。你接我。我找梁领队有事要商量。你来。
杨顺让出座位给我。
我的两边是小姐;两个小姐中间是安澜。这是分开坐的,免得熟悉的人挨在一起作弊。赌注不大,每次每人下底1 元。担心被乘警发现,钱就没往桌面上放;而且只能叫一次牌,次数多了记不住。一局下来就付帐。
洗牌间隙,安澜随意地问我:你没有向杨顺要车票吧?
我说:要了呀。可是他没给我,说是他一起拿着方便。
安澜骂我:你真他妈傻逼!
我说:怎么啦?
安澜说:你想你我的票他们能给我们吗?你不看硬卧车厢里还有多少空位!他们不可能从银川就给我们买票。我们在固原上了车,梁燕就缠着你,打掩护,好让杨顺有时间去补票。杨顺是全陪,梁燕是领队。你瞧着吧,这才是刚开始,宰大伙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还当着梁燕的面要车票,这不是给她难堪吗?
几个小姐等不及。说:哎,两位小哥,还玩不玩?
我还玩个什么劲。情绪控制困倦和疲惫。这会儿,我又想蒙头大睡了。
在西安等待换车的时候,梁燕买了一条宽大的短裤送给我。
安澜恭维我:你真有本事,让梁领队给你买短裤。你算是板回了几十块钱的本。
全程旅游费用是每人三千八百元。报社负担一千八,算是对优秀通讯员和发行员的奖励,另外两千个人负担。个人负担的费用在“记者旅行团”出发的前几天就已经汇寄给了报社,由报社统一交给银川铁城旅行社。通知上写得很明白:这些费用包括交通(豪华空调硬卧;地面豪华空调客车);地面上的一日三餐(中、晚餐十三菜一汤;早餐视情况而定,但不得少于每人八元的标准);所有旅游景点的门票;地面上的住宿(每人每晚一百二十元的单间);银川铁城旅行社优秀全程导游和各地旅行社优秀导游;旅游全程个人人身安全保险。
很明白,火车上吃饭要你自己付钱。
尽管是空调车,但过了陕西进入河南,车厢里还是无可奈何地热了起来。
那群小姐在西安下了车,安澜就平静和安稳了下来。他没有别的事可干,加上天气又热,就拉上我直灌啤酒。到了正经吃饭的时候却又不吃饭,连方便面也懒得泡一碗。
吃什么饭。你我参加这个所谓的记者旅行团纯粹是上当受骗。安澜跟我坐在空荡荡的餐车里喝着啤酒发牢骚:我跟你说这话,我就成了我们报社的报奸了。但不说那是对不起老乡了。你说报社组织这么个所谓的记者旅行团,有几个是记者?你是记者吗?大不了是个通讯员罢了,说着好听,让你高兴就成了。再说旅游费,用得了三千八吗?你自己出的那两千就够了。报社乐得既奖励了你们,还不用出一分钱,省下每人一千八,还不是报社的几个头儿私分了?派了个发行部的主任做领队,怎么不见一个总编来呢?人家不稀罕!明知道做领队大热天地跑这一趟有点油水,那就给发行部主任得了,她为报社做出了贡献,就用这种方式来奖励。怎么样?三十四个人,地面上的标准是十三菜加一个汤,结果呢?每人一碗面。还说是上菜时间来不及,怕误火车。让你连脾气都发不起来。这一顿宰去了我们多少你算得出来吗?
我说:你在报社里,你明知道这些内情,你还跑来挨这个宰,你不也是傻逼?
安澜扬脖灌一口啤酒。我傻逼?组织了三十多个通讯员兼发行员去旅游,我这个报社里正经八百聘任的发行员不参加行吗?难道好事都让她梁燕占了去?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就出了两千块钱。你清楚,谁订的报数是谁的。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跟工资挂钩的。你说说,你今年是不是要把订数算在我头上?
我很含糊。我说:我今年也没多少,也就几千份……
不少啦!整个固原地区的订数都在你老兄的手里握着呢。这次旅游整个固原地区不就你一个人吗?咱们是老乡。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之所以提前跑到固原去,就是为了抢在梁燕前面把你的这部分订数拿到手……你,没有提前给了姓梁的吧?
我说:根本就没说什么订数的事。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今天就请你当一回县团级,在这餐车上吃一顿高价饭。
拳头大的一碗米饭是两元;三口就能喝完的鸡蛋汤每份是五元;其他的菜价我没看,我喝醉了。
一觉醒来,满眼荷花满眼绿。车厢里飘荡着柔和优美的早安曲。到了江南了。
七月早晨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梁燕的脸上。她还在沉沉酣睡。我不知道自己昨天夜里是什么时候才睡的。反正我和安澜在餐车上喝得东倒西歪地回来,看见她还在同几个发行员一起玩扑克。我同安澜的醉态一定相当的狼狈。梁燕当时的脸色很不好看。不知道是谴责安澜的狂饮无度呢,还是正如安澜所说,是担心我将订数算给了安澜。但我没有深究。我已经被啤酒所控制,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一觉,把啤酒和安澜的话用梦境来过滤掉,让我的身体和思维都能轻松一些。
现在,在如此清新、翠绿的一个早晨,看着车窗外的青山绿水,听着相隔不足三尺的梁燕那平稳、匀和的呼吸,我开始怀疑安澜的说法。
几丝乌发散乱下来,搭在梁燕细嫩、白净,在睡梦中显得十分安详的脸上,让人无端地产生出一缕替她难受的情感来。她的睫毛细细地、密密地排列着,就好似她坚挺灵巧的鼻梁上方,挂着两叶黑亮的弯月。整整一夜,唇膏被嘴唇吸干,显出一种秋打残红的雪青来。但那脂粉的香气似乎更多地凝结在那微露着凄清的唇齿之间了。夜来或许是凉,她将那洁白的被单盖在身上。但是现在,那被单有一半被挤脱在了过道上。梁燕的两个乳房,在单薄的黄色紧身衫下,像会呼吸的活物一样,一挺一伏。两节白皙的小腿裸露在被单之外,如同两个听话的婴儿,紧紧地并排在一起,悄没声息。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梁燕并没有穿丝袜,而是赤着双脚。十个指甲盖儿,全被涂了不同的颜色,像是十个排列有序的精致钮扣。
在火车上旅行,真是奇妙。它可以将一对夫妻像陌路之人分床而居;又让一对并无关系的男女,如此近距离地安然入眠。而在早晨起来,如同丈夫俯视娇妻一样地对着那未醒的女人出神。在这个早晨,我在心底里推翻着安澜的所有说法。这样的一个女人,离夫别子,就跟我离子别妻一样,睡在这火车上,浑然不觉地被另一个男人注视着,哪怕她就如安澜所说的那样,使着一些手段,耍着一些心眼,也是为了生活而奔波,为着多增加一些收入而敬业,而吃苦受累,又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不对,又有什么过错,又怎么不叫人敬佩她爱怜她呢?
我轻轻地下了床,弯腰将拖到过道上的被单拾起来,小心地覆盖在她的身上。
她醒了,不由自主地伸展着双臂打了个哈欠,随之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早晨好!你酒醒了没有?
我说:好多了。我看你睡得正香,就没有叫醒你。
安澜腾地从上铺跳下来,满过道找鞋。说:娘的,这泡尿把我憋得贼死。我的鞋呢?谁把我的鞋放哪儿去了?
梁燕迅速地下了床,揉揉眼窝,抹了把脸,将头发拢了拢,很利落地将床上收拾整齐。问我:到哪儿啦?
我说:鄂州刚过。
梁燕说:这么快?照这样跑下去,下午四五点就能到邵武。看见杨顺了吗?
我说:刚刚端着刷牙缸过去了。
卫生间门外和洗漱室里挤满了人。乘警来来回回在车厢里走动,不知在搜寻什么。列车员忙着打水扫垃圾。售货员推着售货车一路吆喝着“啤酒牙膏矿泉水,香烟牙刷方便面”走过去又走过来。好像人一睁眼不买点东西就过不去这一天似的。
早晨的那点难得的凉爽马上被活动开的人群吸收干净了。车厢里又浮动起令人烦躁的闷热和杂乱的气息来。列车从小站上飞弛而过。那样的一个小站,也挂着“斗酷暑,战洪水,决战一百天”的大幅标语。一条江水,伴着铁路,在杂树野花的那一面,并着火车,一会儿在左侧,一会儿在右侧,急急地奔流。
车停南昌。我害怕安澜再请客,赶着下去买了两份盒饭。我对安澜说:我只能请你吃盒饭,希望你不要见怪。
安澜看一眼正泡方便面的梁燕说:咱俩谁跟谁啊,还计较这些。
梁燕望着我说:我宁肯顿顿泡方便面,也不吃车站上的东西。不图省钱,就图个干净卫生。你要请我客,就给我泡方便面,千万别请盒饭。不过我这是自作多情。很显然,你并没有要请我客的意思,我只是说说罢了。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将盒饭从车窗里扔出去。
车窗外是顷刻而来的骤雨。
雨点击打在玻璃窗上,然后扯成水线,急速地滑落下来。这是江南雨中的景致。那么多的绿树在风雨中飘摇,那么些花朵在雨中低垂,那么些骤雨汇成的水线在急速地奔流,有些人在雨中缓慢地行走。很快地,雨过天晴,骄阳似火,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升腾成淡淡的雾气,将一切都朦朦胧胧地罩起,不大真切了。
车到邵武。雨又下起来,而且更急更猛。梁燕在车厢里窜来窜去,召集大家收拾好行李下车。她对杨顺说:你先下去看,这么大的雨,车来了没有?
杨顺站在过道上说:让大家快下车!我早联系过了。他们的车就在站上等着。
武夷山山水旅行社的导游甘永牧是个精瘦干练的小个子男人。说着一口尽量控制的普通话:啊!各位团友,热烈欢迎大家到武夷山来观光旅游。啊!各位团友。现在我们乘车,啊!前往下榻的宾馆。啊!明天,大家就可以欣赏到武夷山奇妙的自然风光。啊……。
我估计,他之所以说那么多的啊,是为了减低语速,好让他的普通话使大家都能听得懂。
山水大酒店坐落在武夷山风景区内。门前有一片开阔而倾斜的草坪。树、凉亭、三三两两随意散落着可以坐人的石头将草坪点缀得无限可人。南面,是缓慢流淌的江水;江水的对岸,便是风景区。山不高,但形异;峰不险,但态奇。从西北荒漠高原的固原来到这山清水秀的东南福建,在烟雨朦朦的傍晚,伫立在宾馆房间的阳台上,呼吸着饱含了水分的空气,望着淡蓝的江水和幽幽的青山,我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然的怀抱,我不想再让那纷扰的世事来搅乱我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心湖了。
一整天冒着细雨跋山涉水,饱览武夷山的秀丽景色,到傍晚回到宾馆,人困马乏。换了干爽衣服下楼来坐在饭厅里休息,等待开饭。连最活跃的安澜也懒得与其他发行员再套近乎,坐在饭桌前喝着啤酒,静静地抽烟。
饭菜端上桌来,大家急不可耐,狼吞虎咽。但梁燕只吃了两口,便甩了筷子大骂杨顺,让杨顺滚出来。
因为全陪和地陪不能和大家同一个标准就餐,所以杨顺和甘永牧坐在雅座里一人要了一盘米粉在吃。
杨顺听到大厅里声音不对,便从雅座间伸出头来。问:梁领队,怎么啦?
梁燕气得脸色发青,用手指着满桌的饭菜说:你过来吃吃看!米饭是馊的,凉菜是热的,热菜倒成了凉的,一道汤除了三个贝壳外,还有什么是海鲜?这就是你们的十三菜一汤的标准吗?
杨顺从大厅里穿过,桌椅板凳挡得他东倒西歪。他低声下气地对梁燕说:梁领队你别生气,别生气。大家有啥意见尽管提。你先别生气。
梁燕气鼓鼓地坐倒在椅子上,双臂抱在胸前,不说话。杨顺转着脑袋望着大家。大家吃得差不多了,都停了筷子不动嘴,也不说话,看着他。
杨顺低声对梁燕说了几句话。梁燕腾地站起来说:行了!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跟地陪藏的什么猫腻那是你们的事,别把我裹在里面内外不是人。在西安你已经克扣过我们一顿了。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不跟你计较。今天中午又用盒饭凑和了一顿。我理解你们,时间紧迫,景点又多,大家是出来观光的,不在乎一顿饭吃得好不好。但怎么说晚上这顿饭应该好一点吧?得像点样子吧?你怎么,不想再陪下去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你们旅行社再派个人来,我们全体人马就住在这儿等新的导游来。
甘永牧擦着鼻梁上的汗从雅座间走出来,向梁燕赔不是。说:我让服务员全撤走,重新上,啊,重新上。菜由你们点,啊,直到你们满意为止。啊。服务员,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撤走。
梁燕说:等一等。这事关系大家的利益,我一个领队不能做主。大家都在这儿,我把话说明了。从西安算起,大家有两次在地面并没有享受规定的饭菜标准,算上今晚这一顿,应该是三顿。我的意见,让旅行社增加九曲溪竹排游的项目,费用算旅行社的。以后饭菜严格按规定保质保量。今天这顿饭,就凑和吃一点吧。大家看怎么样?
饭厅里哗啦啦地响起了掌声。下午大家登山的时候看到下面九曲溪的竹排,都嚷嚷着要去。听到没有安排,就很遗憾,同时又越加向往。现在由梁领队提出这个条件,大家没有不欢迎的。
于是大家说:同意!
梁领队说了算!
就听你的!
安澜低声对我说:他妈的,姓梁的厉害。我认了。
我说:不是她厉害,而是她有理。她是在为我们大家伙谋利益。
安澜吐着烟圈对着我的耳朵说:算了吧。什么为大家谋利益。她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收买人心,为自己拉订数而毁他们三个人的联盟。这叫做舍车保帅,又做得天衣无缝,真他妈绝!你吃这米饭是馊的吗?这凉菜是热的吗?鸡蛋里面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不是看她是个女的,而且她男人出了车祸丢了两条腿在家里躺着,我非站出来揭露她不可。
我倒真没觉得饭菜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但是既吃饱了饭,又不用再掏钱,还能坐竹排畅游九曲溪,何乐而不为呢?
离开武夷山前往厦门,火车在站上停留十分钟。大家都上了车,杨顺和甘永牧在车下道别。甘永牧毫不掩饰他的愤慨,故意大着声让车上的人都听得到:我告诉你杨顺,啊!如果以后还有这么麻烦的人作领队,啊!我们就,啊!拒绝接团。最后一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是句闽南话。
我看到梁燕微微一笑,对我说:骂我呢。这时候骂什么都没用,何况我也听不懂。
看惯了荒山秃岭,小沟溪流,突然间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每个人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把海滩游安排了整整一个上午。客车刚一停稳,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跳下车去,站在海滩上面对着大海狼一样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安澜像条吃人肉吃红了眼的疯狗,两眼放光,从海滩这头跑到那头,盯着那些穿着各式各样、色彩艳丽泳装的大姑娘小媳妇出气不匀。我们这一帮人大多数没有游泳,都被大海的波涛震住了,想游也不会,只是脱了鞋袜,卷起裤腿,在水边踏浪,在沙滩上捡贝壳。梁燕倒像个游泳的老手,在人下完了的客车上换好了泳装,下了水。紧接着,杨顺也扒掉衣服穿着裤头下了水。两个人一前一后,窜到游泳区去了,加入到那些如同在开水锅里翻滚的饺子一样的游泳的人群中了。
无风无雨。海面广阔而平静。浩浩渺渺之间,那些遥远的轮船如同一些移动的礁石。南国的骄阳撒下千万根炙热的钢针,将人的全身扎得千疮百孔,热汗直流。初见大海的激动过去,剩下的只是难耐的焦渴。好多人都跑到沙滩上的冷饮摊前去乘凉喝饮料了。
怎么说,也算是见过一回大海了。我感叹着走到一个冷饮摊前,对厦门的导游小姐欧阳文清说。
欧阳文清是个丰满漂亮的姑娘。着装打扮一如我在固原上火车时见到的梁燕的装束。但言谈举止之间,透露出一股明显的精明之气。
欧阳文清看到我说:怎么没有下海游泳?接着对冷饮摊主说:加杯啤酒。
我坐下来,伸直两腿说:看看,下海了,连裤子都湿了。游泳嘛,就免了。我是西北的一只旱鸭子,只敢在小水坝里胡折腾,看见大海,早吓呆了,手脚都不敢乱动了。
接下来,就顺当得多了。一个有着十年婚龄的北方男子与一个情窦初开的南方女孩应该有说不完的话题。与陌生人谈话就有这个好处,用不着担心暴露隐私,也用不着担心被人告密,更用不着担心会伤害到对方的什么利益。而且这种男女之间的斗嘴既充满了欢愉和智慧,同时又显得琐碎和无聊。
就看见梁燕和杨顺双双从海水中走出来,摇晃着脑袋,甩着在阳光下发亮的水珠子,向客车旁走去了。杨顺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梁燕先上车去了。杨顺像个放哨的士兵一样四下里看着。过了一会儿,梁燕光彩照人地下车来了。杨顺双手抓着车门,扭头看着梁燕的背影,有些不舍地上车去了。看那情形,谁会想得到在一天前,两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曾经发生过的争执呢?我甚至怀疑,那是梁燕和杨顺两人演的双簧给我们大家看的。现在,两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好处,自然可以很融洽地相处。银川人,那要比固原人狡猾得多。安澜说的,应该是对的。
我就和欧阳文清继续斗嘴,而且将头深深地埋下去,跟欧阳文清的头抵在一起,显现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来。我并不热眼和嫉妒梁燕跟杨顺的亲密,就是这个意思,还偏要让梁燕看出来。
海水据说是咸的,没有喝过不敢断定。但是现在裤子上的海水经过太阳的暴晒都蒸发掉了,那些盐的成份变成了裤腿上的白色斑痕,很刺眼地挂在那儿。
梁燕走过来说:你应该换条裤子,不然腿可吃不消。我不是给你在西安送了一条短裤吗?
就穿着它回到固原去,让大家都闻到大海的气息有什么不好的呢?我说。但并不看她,而是对着欧阳文清。好像这话是对欧阳文清的一种表白,而不是对梁燕的回答。
梁燕低着头看了我一阵,对着冷饮摊主说:一杯橙汁。
再没有说话。
三个人就那么不尴不尬地坐着。
在去石鼓山的路上,车头一拐,进了一家养殖场。欧阳文清对大家讲: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一家国营珍珠养殖场。珍珠养殖是厦门的特色产业。我们参观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大家亲眼目睹珍珠的产出过程;另一个目的是要大家掌握真假,以免在游览石鼓山的时候因买珍珠制品而上当受骗。好了,养殖场到了,请下车。
没有看到养殖场的员工。只看到两间出售珍珠制品的店铺。店铺门外,是一个不大的停车场。南面,有两个水池。一个穿着蓝制服的女人,大概是惟一的员工,正拿着工具在水池边面无表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大家围过去看的结果是:她正在从一个海洋生物的体内往外抠珍珠。
梁燕对这种明显属于拉客销售的行为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反而饶有兴趣地站在水池边细致地观看。她提问说:这就是天然的珍珠吗?
女操作手说:真正天然的要到大海里去寻找,这是人工养殖的。当然也可以说是天然的。如果你们去石鼓山游览的话,你们会看到遍地的假珍珠。
梁燕说:我们怎么才能分清真假呢?
女操作手把抠出来的珍珠放在水磨石的池面上用力一划,水磨石上留下了一道并不怎么明显的白痕,并伴有细微的粉粒。她说:这是真的珍珠,痕迹不明显,而且有珍珠粉末;假的一划,不会掉渣。因为是用有机玻璃制造的。
梁燕指着店铺问:那么店铺里的制品都是真的了?
女操作手说:那当然。因为这是我们养殖场自己加工出售的。
梁燕用胳膊肘碰碰我说:给你老婆买点纪念品吧?
我哼着鼻子冷笑了一下。
梁燕对大家说:有四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选购物品。不买什么也没关系,进去看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大家便一窝蜂地涌进店里去了。店里面有空调,外面是白花花刺眼的阳光。
我没有进去。我不想买任何经别人介绍的东西。如果我想给老婆买纪念品,我也不会买珍珠之类。平民百姓戴珍珠制品似乎有些奢侈和不相宜。更何况我明显地感觉出这是两个导游加梁燕三个人同养殖场串通好了的。我可不想明明白白地挨宰。就站在水池旁边看女操作手操作。
梁燕从店铺里出来,把我拉到大客车的另一面,展开了手。简直像变戏法一般,两枚晶莹圆润的珍珠耳环平稳地停在梁燕汗津津的手掌里。梁燕用眼睛“挖”我:你个吝啬鬼,全没有一点绅士风度。咱们交往这么多年,你也不买点什么东西送给我,反要我买礼物送你。
我说:我并没有要你买东西送我啊!
梁燕把耳环装到一个红绒盒子里,塞给我:行了。这是我为你老婆买的。权当是我感谢你,这几年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我想起了安澜在西安说的“板本”的话,就没有再推辞,像一个偷了东西的贼,赶忙把盒子装到裤兜里。这会儿,我觉得那对耳环戴在我老婆的两只耳朵上再恰当合适不过了,一点儿都不显得奢侈和不相适宜了。
梁燕看了一眼店铺。说:你可别没良心,一转眼把我送的东西又送了人。欧阳文清可不稀罕这东西。
我面红耳赤,争辩说:你……乱说什么呢?
梁燕说:加紧追。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有艳遇。
就看到欧阳文清扇着凉帽从店铺里出来了。
果然,在石鼓山山门入口处,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珍珠耳环、项链,还有手镯。在养殖场买了项链和手镯、耳环的人,纷纷去打问价钱。十块钱可以买三条项链。于是都买了好几条。把在这儿买的项链和在养殖场买的项链放在一起比较,比较来比较去连自己都昏了头花了眼,分辨不出真假了。只好全拿出来在石板上“划”。划来划去,并没有看到哪一条掉渣,只看到满石板横七竖八的白痕。这时候反倒全没了脾气,心里安慰说,总有一条是真的。总有一条是花了三百八十五块钱买的。反正也就给老婆举了这么一点心,现在连假的价钱也知道了,可以给老婆交代了:假的十块钱三条,我这条是在养殖场买的,真货,三百八十五块。还是看导游小姐的面子打了折的。这就行了。
石鼓山实际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到处都是游人,到处都是香火,到处都飘荡着锣钹木鱼的声音。这三十多人都有些文化,看到每一处题刻,每一幅楹联,都要做抄写研究的工作,因此没法统一游览,只规定下午六点在山门外集合上车,然后就星散了。
有地陪欧阳文清率领,杨顺乐得清闲自在,躲在大树的阴凉里不走了。安澜喜欢欧阳文清那身清爽的打扮和她身上那股咸咸的、蓬勃四散的南国味道,因此跟在屁股后面走了。
梁燕对我说:愿不愿意和我私游?
我愿意的是和你私奔。我说。
梁燕拉着我的手说:那就奔吧!
杨顺站起来问:你们去哪?
梁燕说:没你的事儿。我们要私奔。
杨顺便顺着树根溜下身子去坐了。
坐在一截硕大的、裸露在石头外面的树根上,将双脚从闷热的鞋壳里解放出来,浸到凉爽的流水里,听着耳畔的鸟鸣,看着庙宇里熙熙攘攘的人流,闻着梁燕那温热的、散发着女性胭脂味的体香,我感觉,石鼓山之游是完美的。
梁燕说:你的那几千份订数,就订给安澜吧。我已经跟安澜说过了。
我说:为什么?
梁燕说:你们是老乡,我不想让你为难。再说,这一路走来,大多数发行员把发行数都给了我,安澜拉的订数很少。他跑这么一趟全是自费。不像我,报社可以报销的。再说,他要是完不成订数,报社就可以解聘他。
我说:那你还给我买东西?
她说:那又不是贿赂你。那是我为你老婆买的。养殖场给了我一条真的项链作回扣。我自己掏钱给你老婆买了一副真耳环。你不用担心那是假的。
我说:你给我老婆买跟给我买,那还不是一样?
梁燕把石子扔进流水里,溅起的水花飞起来,落到我们的脸上。她盯着我,摇着头说:不一样。那是我自己掏钱买给她的。是对她的补偿。明白吗?傻瓜。
我说:对她的补偿?
梁燕说:对,是补偿。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补偿。她抓住我的手,用另一只手在上面抚摸着。我知道你们男人的心思。我也知道你对我的一些想法。这么多年了,我难道会没有感觉吗?但我一直压抑着,我知道你也是同样。有些发行员可不像你,他们是直截了当的,甚至想拿手中的订数要挟我,想使我就范。哼。瞎了他的狗眼。我宁可唾他一口,也不想要那些订数。但你跟他们不同。你是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我。我知道。
梁燕将她的双唇紧紧地压在我的嘴唇上。她的手蛇一样地缠绕了我的脖子。
如果你愿意,晚上到我的房间来。如果你觉得一副耳环不足以补偿你老婆,也可以不来。梁燕将嘴唇俯在我的耳边说。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石鼓山。
石……鼓……山。
同样是夜里,十二点整。火车在固原火车站喘息着停了下来。记者旅行团的人大部分都在沉沉入睡,安澜也是一样。到银川还有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七八个在西安上车的小姐,哼着流行歌曲,抽着女士香烟下车去了。她们把淘金的梦想放到固原来做了。
从西北到东南,然后再返回来,就像经历了一场梦,很繁杂也很短暂。但现在梦醒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的固原。
只有梁燕送我下车。
好像两人之间把所有的话都在那一夜里用动作说完了。现在,互相拉着手,竟想不起来道别应该说什么话了。我感觉梁燕的手是冰凉的。梁燕应该也能感觉到我的手同样是冰凉的。
没有语言的拥抱和亲吻。那么的轻微,似乎害怕把什么东西惊醒,把有些东西唤起。就像蜻蜓,在清澈的水面上一点,却不敢深扎下去,怕那清水,将整个的身子淹没,永远地挣扎不出。
固原的夜风吹起,把身上的热气掠走,就像掠去了我对生活的热情。
看着梁燕独自走上车厢,我的眼泪,顺着两颊,缓慢地、无声无息地下滑。
火车开动,梁燕将脸贴在车窗上,我看见,就像顷刻间下了一场雨,将她的脸和挥别的手势淋得模糊不清,朦胧如罩。
很快的,连火车都看不见了,只看见两行铁轨,在灯光里闪闪地发亮,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的漆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