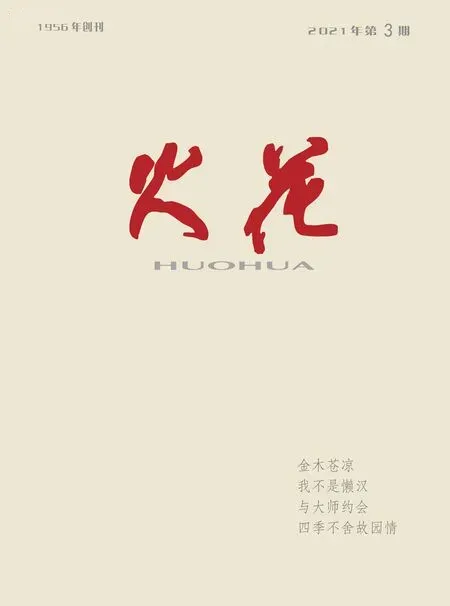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中渗入喜剧元素的共性研究
——以《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为例/ 张珈玮
2021-11-12
如果我们考虑到两位文人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戏剧创作之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属于各自国家戏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英国,由于宗教改革以及对古典主义的重新建构,戏剧经历了一个从稳定化到世俗化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就是宗教戏剧被取缔。同样,在汤显祖所处的明代,戏院变得越来越精致,女性的柔美越来越在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明代社会,戏剧作为“精英化”的艺术已经被打破,戏剧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也逐渐被世俗所取代,李贽的“反禁欲主义”等启蒙思想使得描绘市井百态的喜剧很快上位,这样的思潮也使得自汉以来一直是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受到了很大挑战。所以在这次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将努力分析:连接两位戏剧家进行相同戏剧创作的连接线可能是一种较为彻底的现代化思维和深刻的人文主义情感。
一、以“梦”为主的意境架构
《仲夏夜之梦》是一部利用梦来诠释多重主题的喜剧作品,在这部戏剧作品之中其实是提供了将梦作为一种“自主存在意义”的透视模式。莎翁笔下的梦就好似一个可以变形的实体,不断地在改变它的性质,将人性的边界故意模糊化,使做梦者和观众都很难从虚幻中辨别真实,从做梦到出梦,作者其实是通过梦境混淆了他们的意识,为观者呈现出一系列的梦想形式。在戏剧之中,梦几乎是一种连锁反应,围绕着每一个人物以及观众进行展示,并最终揭示了自己作为戏剧和艺术创作的隐喻。因此,在莎士比亚看来,梦境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是在睡眠中产生图像的简单潜意识行为。相反,它们往往是通过侵犯清醒生活的领域,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和多样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在莎翁笔下的“梦”具有双重的本质:空洞与无物。总之,它是“奇怪的和令人钦佩的”,因为在梦中。人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试图揭示而不是隐藏,在此剧的“梦”中,这一种关系其实是涉及到了对“真爱”本质的探索。所以综合来看在莎翁笔下的“梦”是基于想象力而存在的,它其实是与诗歌和魔法一样具有超然的本质。
而在汤显祖的戏剧之中同样可以构建一个类似的话语体系,在《牡丹亭》中梦和幻象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虽然说汤显祖在辞官之后戏剧创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从作品中感觉到了一种汤显祖自身对于时代的背离,但是他本人对于“梦”的实践与追求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首先,汤显祖似乎也认同了梦的本质——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梦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字面”形式,主要体现在它们发生的时间是在个体睡着时。然而,随着行动的展开,在梦中他却揭示了一个个有趣的隐喻内核,《牡丹亭》中的女主角杜丽娘在梦见自己与柳梦梅在一起之前,她其实是一个端庄柔顺的十几岁女孩,她偶尔会忘记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偶尔在白日梦中“消磨时间”,这里其实已经为日后杜丽娘的行动做下了一定的铺垫,她的无所事事其实是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封建大家庭式教育的不满与怨恨。然而,正是由于她在游园之中做了一场“春梦”才使得她的情欲被激发了出来,进而使她爱上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所以从这点来看,梦境在两位作家笔下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喜剧元素,男女主人公在梦境之中时而迷失自我创造出不断引人发笑的故事,时而在梦境之中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并向着自己的爱情不断地靠近。
二、“情欲”主题的一致化
之所以没有用“爱情”而是用了“情欲”二字主要是出于对两部作品文本本身的考量,对于东方而言,“情欲”二字可能较为的开放,但是根据调查发现,《牡丹亭》无论是之前的研究者还是近几年的研究者,他们其实都主要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戏剧中“情、理、人性、人欲”等方面。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之中说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如作者题词一般,作者一开始就说明了杜丽娘是个有情之人,但是这种情却不知道从哪来,观者可以知道的只是这种情感很深,深到可深可死。在陈最良讲解完《诗经》之后要求女学生进行模字,这时春香因为拿错了笔墨纸砚于是进行了一连串的代表着青春爱情的行为:“画眉细笔”、“鸳鸯砚”等等。除此之外在表现杜丽娘的“情动”时,汤显祖并没有直接通过丽娘之口进行表述,而是间接性的通过春香进行表达,例如:“侥幸感动,小姐吉日时良,拖带春香遣闷,后花园里游芳”(第十二出《寻梦·夜游宫》),这里作者在构思时其实是有安排的,因为有些话此时此刻丽娘即使想说也不便说,一来说了也与小姐身份不符合,二来小姐直说的话这一层“情欲”的含义就削弱了很多,如此看来,春香这一人物的设定的确是使得此剧情欲的表达达到了一种朦胧的效果。
而在《仲夏夜之梦》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男女主人公对于情欲的追求与渴望。海丽娜作为一个女子,在心爱的人面前她竭尽全力展示自己对于他的爱恋与追求,在第二幕开场时狄米特律斯即使说出了:“滚开,快走,别跟着我”,而在赫米娅的梦中拉山德离开了她,她不顾一切地去寻找拉山德“要是找不到你,我定将一命丧亡!”。对于赫米娅而言她不相信拉山德会离开她,就像不相信自己会离开拉山德一样。她要去找到他,找回失去的爱,在山上、在林中,在黑夜的怀抱里。可能正是出于赫米娅对拉山德的深深的爱恋,她才会对狄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表现出极度的愤怒。在拉山德进入到“迷幻”状态时,赫米娅对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进行了深恶痛绝的谩骂,可以看出,西方戏剧在进行人物关系的表现时,显得更为的直接,而这样一种表达其实是与《圣经》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在第三幕第二场,赫米娅质问并斥责狄米特律斯:“你真的把他杀了吗?从此之后,别再把你算作人吧!”这里其实可以参见《圣经·创世纪》4·14,上帝诅咒杀弟的该隐说道:“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须飘荡在地上。”,而该隐则恐惧地哀叹:“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当然与在西方戏剧中出现的这种直白的、通俗的话语不同,东方古典主义则更加注重语言的委婉,在《牡丹亭》中汤显祖表现杜丽娘一种情欲的爆发可能更为的含蓄。
三、人文色彩的戏剧植入
伯特兰·罗素曾说:“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的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其它的一切。”莎士比亚选择了爱情题材来描绘人性的觉醒,毕竟这样的选材与沉重的社会题材相比,爱情是更为的甜美而私密的。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经过了一种人文色彩的渲染与洗涤,使得每个艺术家的创作风格都在向着一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风格不断探索与前进。英国传奇的历史通常以希腊和罗马为基础,在《仲夏夜之梦》的第二幕之中,莎翁巧妙地将提泰妮娅、拉山德、海丽娜、狄米特律斯、昆斯等主要人物进行了一个“大杂烩”,看似混乱不堪的局面的背后,却有着较为鲜明的线索架构。事实上在这之中莎翁是进行过不断地规划与设计的,赫米娅在和拉山德私奔到森林之前,同时受到了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的追求,而海丽娜却追求狄米特律斯,在森林之中受到魔汁的影响之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赫米娅失去了她的爱情,海丽娜意外得到了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的追求,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赫米娅与海丽娜的友情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但最终经过仙王和迫克的调解使得两对恋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在这之中想要谈到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如若没有赫米娅父亲的禁令也就不会有赫米娅和拉山德的私奔,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一出出的好戏,所以这样来看赫米娅的出走,也成为了本出戏的一个最重要的情节点,事实上根据雅典的法律,赫米娅生活的城镇,如若违背父亲的意志“不是收到死刑就是与男人永远的隔离开来”,但是赫米娅为了追求她自己的爱情放弃了自身的荣华富贵,勇敢的踏上了私奔的道路,这样的戏剧情节在十六世纪之前其实是很难看到的,从这其中也能看出莎翁对赫米娅这一角色灌输的人文主义色彩。
而对比来看,在《牡丹亭》之中杜丽娘与柳梦梅受到封建思想的阻挠其实是要比《仲夏夜之梦》中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恋爱更大一些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从小被父亲严加看管,其实是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特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十六岁之前她其实都不知道家中有个后花园,在这之前她对于爱情的幻想也只是来源于书籍,当她第一次看到花园中的美景时,发出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的感慨。而在园中做了一场春梦之后的杜丽娘,在之后却为了梦中之人茶不思饭不想,最终抑郁而终。由此可见当时封建制度以及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人们思想的毒害之深。之后在爱的感召之下,杜丽娘终于得以重回人间,收获了自己与柳梦梅的爱情。但是此时却遭遇了父亲杜宝的反对,杜宝身为其父对于女儿的婚事不仅不感到高兴,反而还不认自己的女儿。可见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观念对于人物的伤害之深。但最终汤显祖是将皇帝搬上了传统戏曲舞台,使得整部戏剧的矛盾冲突得以化解。不难看出,在此部戏剧作品之中,人文主义色彩的元素的渗入可能并没有《仲夏夜之梦》中那么的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明代那样一个思想较为保守的语境之下,作者很难将进步思想与文学作品进行一个深入的结合。
四、结语
《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在主题上都是以“爱情”为中心,并且借助“梦”的形式表现作者对封建制度、家族包办婚姻、禁欲主义的反抗和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追求。虽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不一样,但其思想体系中都有关于对“人本”的观念的强调。事实上,汤显祖的戏剧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使用了一种“悲喜杂糅”形式的戏剧框架,它将从悲剧到喜剧的对立转化为了“悲喜交加”的戏剧模式,同时也结合了丰富的源情节和叙事层。特别是变质元素的加入有助于喜剧性地表现一种基于宇宙、人类想象力和欲望的混合的机制,使得人类与自然的高级力量进行完美的糅合。因此,中西方戏剧在长期发展中其实是向着一种“悲喜混合”的趋势进行发展,这种表现形式与悲剧不同的是,此类戏剧中主体架构强调的不是对命运周而复始的感叹,也不是对命运的消极逆转的悲哀,而是最终承认了命运的有序性以及爱情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