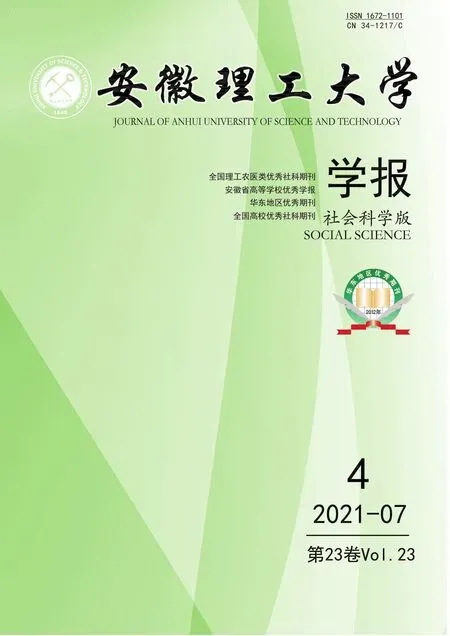论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的译介成果、挑战及对策
2021-11-12丁立福郭智莉
丁立福, 郭智莉,张 健
(1.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2.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3.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 )
一、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
中医药自形成起,便在对外交往的基础上开始了最为朴素的国际化传播,可谓历史悠久。基于现有研究文献及中医药发展历史,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可分为如下四个历史阶段。(1)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末:秦汉时期中医药开始传入东南亚邻邦及西域诸国,之后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医药传入阿拉伯,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医药译介对后人影响甚微。(2)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明末清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广泛译介中、西典籍,由此掀起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个翻译高潮。传教士译介活动当然涉及中医药及其文化,如17世纪上半叶卜弥格向西方系统译介中医药,并著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中医指南》《中医的秘密》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的第二个阶段起点应定于公元17世纪前后较为合理,此后中国才开始与欧洲诸国有了最初的医学交流,掀开了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新篇章。这期间“先后翻译了156部有关中医药的书籍,针灸学占63部”,译语多为拉丁语和英语,随后相继加入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俄语等。(3)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中西交流加强,随之中医药与西方医学亦深入交流,“据不完全统计, 这时期共有近200部有关中医的书籍或杂志问世”。翻译重点逐渐从针灸学转向医学史、药学,一些中医药经典著作的完整翻译开始提上日程,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从事中医对外译介工作。(4)20世纪80年代迄今:改革开放及其相关政策为国际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中医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对外译介工作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期间个人、国家及国际组织最大程度地协同起来,中医药英语著作频频出现、中医药英语教材入选规划行列、经典中医药书籍先后得以翻译。综观中医药国际化传播进程,中医药译介历史看似悠久,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相对缓慢,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发展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中医药翻译工作才实现了有效突破。朱文晓、童林、韩佳悦等学者发文详细概括了改革开放之后40年(1978-2018)中医药译介研究的主要领域,即中医药翻译理论、中医药应用翻译、中医药口译研究、中医药翻译技术、中医药书评译介、中医药翻译史及其他,而后指出当下中医药译介传播研究存在“缺少时代命题,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不足”的遗憾。为补此憾,本文基于中医药国际化的历史进程,着重探讨中医药译介成果、挑战及相应对策,以期为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提升中国软实力乃至国家形象提供些许启示。
二、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医药译介
中医药在阴阳思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等传统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经千年历史积淀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如医疗成本低、中草药毒副作用小、防治疑难杂症和慢性病效果好等,这些独特优势是中医药得以国际化传播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甚至可以说,中医药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播史,期间对外译介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下文在总结国际化进程中中医药译介成就的基础上,亦直面中医药当下对外译介中遇到的一些挑战,进而提出一些应对策略。
(一)译介中医药既有成就
1.中医药英语著作频频出现。客观而言,改革开放之后有为数不少的涉外语中医类工具书和英汉对照中医系列丛书相继出版。其中有影响的代表性工具书有:《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谢竹藩、黄孝楷,北京医学院,1980)、《中医药大词典》(李照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简明汉英中医词典》(李照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新世纪汉英中医词典》(左言富,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英汉汉英医学分科词典:中医药学分册》(孟和,世界图书出版社,第2版2008/第1版1998)、《新汉英中医学词典》(方廷钰、稽波、吴青,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2版2013/方廷钰、陈锋、王梦琼,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第1版2003)、《汉英双解中医临床标准术语辞典》(李照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德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等。此外,影响较大的系列丛书有:《英汉对照实用中医文库》(张恩勤,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0)、《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徐象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1994)、《(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左言富总主编,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03)、《中医药英文版图书》(刘公望,华夏出版社,2006)等。颇值一提的是英国医师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早年曾来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归国后长期从事中医及针灸方面的实践工作,同时研究并撰写中医药方面的英语著作,相继问世的有Tongue
Diagnosis
in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舌诊》,1987)、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学基础》,1989)、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中医临床》,1994)、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妇科学》,1998)、Diagnosis
in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诊断学》,2003)等,而且被译成德语、法语、荷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等并成功出版。马万里“被誉为欧洲从事中医实践最成功的当代‘中医之父’”,也是外国学者尝试撰写中医药著作的杰出代表,其实践与理论成果客观上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作出了巨大贡献。2.中医药英语教材入选规划出版行列。上世纪外文出版社集中推出的一批英语中医药著作比较突出,主要有《中国针灸学概要》(中医研究院针炙研究所,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中国针灸学》(程莘农,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当代中国针灸临证精要》(陈佑邦等,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中医针灸经穴部位标准化》(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外文出版社,1990)、《中医基础知识》(印会河,外文出版社,1992)、《中医内科学》(谢竹藩、廖家桢,外文出版社,1993)和《中医药学临床验案范例》(陈可冀,外文出版社,1994)。其中,1987年英文版《中国针灸学》(Chines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由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针灸”代表性传承人程莘农院士编著,后于1997年、1999年、2019年分别再版,“现已成为海外人士学习中医的规定教材”。另外,较有影响的中医药英语系列教材有“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学苑出版社,1998)、“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汉英双语创新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2015)、“国际标准化英文版中医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英汉双语创新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2015)。所列每一系列都包含数套相关中医药英语教材,而且在众多医学专业学生中使用,有望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经典中医药典籍先后得以翻译。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一大批甚称其杰出代表的中医药典籍。这些典籍大多言简义丰,且在术语体系、思维方式及主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故对外译介困难重重,但近年来仍取得了重大成就。以中医典籍之首《黄帝内经》的译介为例,其约成书于西汉中后期,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海外传播及译介“应始于1925年P. M. Dawson在《医学史年鉴》(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
)上发表的介绍《素问》的学术论文”,开中医药对西方译介之赞歌。随后陆续出现一些节译文,如,1949年美国伊尔扎·威斯(Ilza Veith)节译《素问》前34章,时由威廉姆斯及威尔金斯出版社出版(Williams & Wilkins),196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其再出新版;1950年中国黄雯节译《素问》前两章,刊于《中华医学杂志医史专号》单行本上。约摸40多年后始现全译本,主要有美籍华裔(Wu Jing-nuan)的《灵枢》译文(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旅美华人吴连胜吴奇父子的《素问》《灵枢》合译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美籍华裔倪毛信(Maoshing Ni)的《素问》译文(Shambhala Publication Inc., 1995)、德国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的《素问》译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和《灵枢》译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中国李照国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5)和《黄帝内经·灵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译文与罗希文的《黄帝内经》英译文(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另外,“近些年来,《黄帝内经》在海外出现了西班牙语 2010 年图解译本。意大利语 2014 年《素问》全译本和《灵枢》全译本,以及葡萄牙语 2008 年《灵枢》评注译本。葡萄牙语 2015 年《黄帝内经》解说译本等”。再来看《难经》,约于东汉时期成书,唐代以前原本早已散佚,至北宋有王九思等校勘,后人继之重刻《王翰林集注八十一难经》,遂成传世通行本,简称《难经集注》。《难经》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是Henry C. Lu译本(1985),其后有文树德译文(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2016)与美国中医师Bob Flaw译本(Blue Poppy Press,1999);另外,西班牙学者María Luisamanchado Torres于2008年、Hoang Ti Emperador Amarillo于2016年分别将《难经》译成西班牙文,在同一家出版社Ediciones Literarias Mandala出版,“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典籍在西班牙的传播和影响”。此外,诸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也纷纷有了节译文和全译文,大抵都经历了一个从节译到全译到多语译文并存而且近来加速的译介过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可谓硕果频现,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此处需突出两位学者:一位是上海师范大学李照国教授,积30多年努力于2017年12月前,“翻译完成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外经》,其中《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黄帝外经》是世界上首部英译本”,在典籍译介方面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国内中医药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另一位学者是加拿大籍华裔吕聪明博士,组织人员耗时10年于1978年完成了《黄帝内经》《难经》全文翻译,后于1985年在Academy of Oriental Heritage合集出版,2004年由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再版,在海外持续产生良好影响;此外,吕聪明还在自己的译本中阐释了适用于中医药典籍翻译的基本原则,即“保持原文的连贯性以及与中国医学的现代理论一致”,为中医药典籍译介理论与实践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4.个人、国家及国际组织全力协同成效显著。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广泛参与中医药文献译介,并深入探讨翻译标准、原则及技巧等理论问题,直接为中医药译介传播添砖加瓦,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极富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而国家层面也陆续出现法律、政策扶持倾向,如2017年7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目的是振兴、传承、保护与激励中医药发展,必将在法律层面上最大程度地“保证中医药发展的规范性和延续性”;再如国务院《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提出“将中医药服务从医疗扩展到养生保健、康复、养老、贸易等七大领域”,一定程度上引导并促进了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开设、一些专业协会的成立以及各级各类研讨会的召开。在个人、国家乃至国际组织的全力协同下,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2019年5月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即是明证。“ICD”是当前最权威、最基础的国际统一疾病分类标准,历经百年不断修订完善,其第11次修订将于2022年1月1日生效,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医疗人员带来不一样的治疗思路、给病患人员带来不一样的福祉,将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和使用中医药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将更有力地推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二)译介中医药面临挑战
1.中医药原著深奥难懂,缺少专业性译介人才。中医药经典著作数量众多,闻名遐迩的《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都是根据先人多年的行医经验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且都运用古汉语编撰而成。这些原著言简义丰,往往需要阅读者具有极为深厚的古汉语功底方可把握原著内涵,因此对于今天从事中医药学的专业人士来说极具挑战性,而对于仅仅从事翻译工作、对中医了解不多的翻译人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中医的药名、药方、病名等都具有较强的古文风和文学性,虽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但也因此增加了今人的理解难度。例如中医术语“五心烦热”,其实是指两手两足心发热,并自觉心胸烦热,然而却经常被理解为“五颗心都感觉烦躁、闷热”进行翻译。类似错误翻译的情况时而有之,主要原因就是译介人员对中医药专业知识存在盲区,其运用第二外语的语言转化能力还有提高的巨大空间。
2.中医药文化迥然不同,难以加快国际化进程。中医和西医各成体系,但二者经常很难在对方领域找到与己方领域对等或相应的概念及术语,而概念及其术语又是中医和西医赖以构建的基础,尤如地基之于高楼大厦。在各自特有概念及术语的基础上,中医和西医便发展为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医学体系,相应地便有了颇不相同的中医药文化和西医药文化。具体而言,“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以较多抽象概念为思维,西医则是实验室医学,以现代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进行具体分析,更偏向于一种理性思维”。其次,“欧美国家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教,哲学思想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即使抛开科学层面而言,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也导致了两种文化体系的人思维方式差异巨大”。中、西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极大地影响着汉语与外语在词汇、语法、句式等方面的转化,由此使得外译文必然与汉文存有差距——这种差距或被宽容接纳,或被误解排斥,但都会延迟中医药文化的快速、有效传播。
3.中医药翻译尚未规范化,国际化仍存不小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翻译发展势头良好,不仅译介成果丰硕,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中医药译介人才,如罗希文、李照国等等。然而,一方面有关中医翻译采用的译法数目多、种类杂,但层出不穷的翻译技巧尚没有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归纳分类;另一方面国外许多中医学者没有得到专业的指导,翻译时统一意识和规范性不足,最终致使中医药的国际化传播仍存在不小困难。仅就中医药名词术语翻译规范化而言,2000年起国家乃至国际中医药机构才开始联手研究,先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总编,2007)、《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西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总编,2011)、《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总编,2011)、《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意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总编,2013)、《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德对照国际标准》(李振吉总编,2017)等一批标志性成果。然而,中医药翻译在其他方面,如独特的翻译选材、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等远没有达成指导性共识,与国际社会对医药及治疗所期待的规范化、标准化仍存有不小差距。
4.智能化时代悄然跟进,语言服务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密切、频繁的对外交流促进了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智能化时代更是直接推动了语言服务行业从萌芽阶段升级到蓬勃阶段,语言服务行业开始涉及各行各业及各个领域,中医药翻译领域亦然。一方面,中医药翻译领域基于移动应用翻译、医疗翻译等模式的翻译业务相继出现,并且不断更新升级,其准确率、专业度等亟需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现有的科学技术并没有充分运用于语言服务行业,语言服务技术水平正处于发展之中,这也使得与中医药相关的语言翻译服务并不是很令人满意。例如,受限于语料库的容量大小以及中医药文本的特殊性,用户很难通过移动应用翻译获得内容准确、界面友好的译文,于中医药语言翻译服务而言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赖语言服务技术的不断提高,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三)译介中医药应有对策
1.协同推进标准化建设,与国际标准接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法规文件。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尽管国家层面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地方基层部门、机构及个人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国家及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指导与监管力度,地方机构及相关专业协会需要认真落实与紧抓实干,相关专业学者需要积极交流、深入探讨中医药国际进程中的问题尤其是翻译问题及传播问题,以期协同努力在中医药译介选材、翻译标准、翻译策略、术语统一等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指导、规范中医药译介,最终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与国际标准接轨。
2.开展中医药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中医药翻译专业人才是中医药翻译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力量。客观而言,国内中医药院校大多注重中医药知识的学习,较少关注中医药的译介传播,更缺少国际化视野。因而,中医药院校应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及人才培养方案,如,开设中医药翻译课程,或者直接将中医药翻译设置为一个专业,将中医药翻译融入中医药理论教学中,并适当占一定的学分;适时聘请高水平中医药教师或者有医学背景的外教授课,增强师资力量;举行类似夏令营、冬令营的交流活动,与国外的医学院校加强学习交流,培养学生第二外语的语言环境,使得中医药翻译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总之,相关院校应一手抓中医药理论学习,一手抓中医药翻译学习,双管齐下培养中医药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3.创建中医药翻译进修学校,弥补专业人才短板。当下中医药国际化进程正处于关键时期,亟需把以中医药材和医学典籍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及其理论研究成果完整、精准、全面地译介到海外,但现实是懂得中医药理论知识的人才翻译能力欠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才中医药理论知识空白,这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医药对外译介的国际化发展进程。面对暂时困境,可以尝试创建一批专门的中医药翻译进修学校,进而由学校根据学员自身需求,安排合理的课程学习,甚至可以开设个性化课程,以期全面提高进修效率。另一方面,建议教育部可以与各中医药高校合作,为在职人员或个人时间不集中的进修学员开创“线上教学+校园上课”双模式的学习方式,满足中医药人、翻译人的求学需求,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安排学习时间。
4.尝试建立语言服务研究机构,为国际化进程添翼。信息全球化促使语言服务市场蓬勃发展,衍生出以移动应用翻译等为代表的新型翻译业务,有力地推动着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这些新型翻译业务紧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展空间很大。就此而言,社会及官方机构可以尝试建立适用于语言服务应用的科研机构,集中资源开展语言服务与管理领域的研发及推广,如语言服务理论、翻译术语学、本地化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传播与技术写作、翻译项目管理等理论方面的研究,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语言服务需求调查、企业语言资产管理、企业国际化语言服务战略、企业语言服务成熟度评估等实际应用方面的探讨。理论研究需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必须着眼于中医药国际化现实,并能有效促进其国际化进程。此外,我们需要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从语言服务视角切入标准化研究,将中国标准走出去作为研发重点之一。所论语言服务研究机构,一方面可为制定中文标准服务,包括国内外标准技术差别比较、国际标准技术趋势、国际标准情报分析等;另一方面可为中国标准走出国门服务,包括标准英文版翻译、标准国际化、标准化技术写作等。
三、结语
随着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医药有望进一步挖掘潜力,实质性地提升影响,其国际化进程亦会进一步加快。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都应采取实际行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及振兴。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应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与保障,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世界各地区的中医药市场,加快中医药翻译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进程,为中医药翻译的国际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各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翻译学术组织、语言服务机构、中医药翻译的工作人员等,应当从国际视角出发,不断提升中医药的发展高度,强化学术研究,总结翻译经验,制定出规范、统一的翻译标准,稳步提升翻译水平。其中,实质性提升中医药译介水平,不仅能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从而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还能借助中医药国际化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及文化自信,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有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