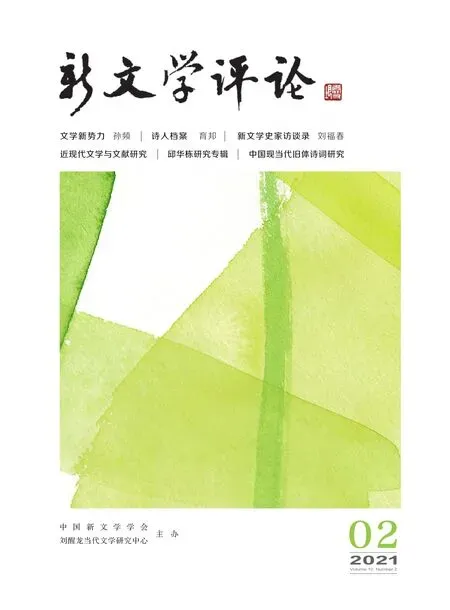黄裳致范用书信系年推求
——《来燕榭书札》考释之二
2021-11-11□徐强
□ 徐 强
现代杰出记者、散文家、藏书家黄裳(1919—2012)一生在文化界交游广阔,书札往还众多。2004年1月,其书信集《来燕榭书札》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系李辉主编“大象人物书简文丛”之一。全书收入书札253通,其中致黄宗江17通、周汝昌46通、杨苡86通、范用26通、姜德明40通、李辉38通。这些书信最早写于1943年8月15日,最晚写于2003年6月10日,跨越60年。相信这仅仅是黄裳书信的一小部分,但已显示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史料价值来说,黄裳所与交游者不乏现当代文坛大家巨擘,很多书信记录了文界鳞爪,透露了书界内幕,臧否了某些人事。就文学价值而言,黄裳对传统书信文学有很高评价,说“从传世的文学选本中可以发现,有些名作其实都是书信。信札有长短,用处各不同……五花八门,风采各异,要分清楚也难。但相同的是都写下了真实的事物、情感,都有优美的文笔,都表现了不同作者的个性与风格”。黄裳本人的有些书信也可作如是观。他阅历丰富,浸淫典籍既久且深,眼光敏锐,行文典雅,风姿绰约,独具一格,其人虽不善言谈,但与熟友修书,每饶多趣味,亦不乏诙谐,很多书信本身就是上佳的美文。
编者在《〈来燕榭书札〉整理说明》中说:“黄裳先生细心地校阅每一封信件,并尽其所能回忆写信时间。”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信件的日期标注有很多错误。这给读者阅读、引述带来困惑和麻烦,也难免影响到其史料价值的发挥。笔者加以考校重排,试图还原其本来面目。每封信件的时间考校,在提出结论后,一般从几方面给出依据。有些信札,只要一两条理由即可证明,笔者有时仍不惮冗繁提出多条理由,权作是为原信相关人事作“笺注”,也不算无意义之举。
本篇董理的是黄裳致范用书信。
范用(1923—2010)是著名出版家,抗战期间即开始从事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曾策划出版《随想录》《傅雷家书》等著名图书,也是《读书》《新华文摘》等的创办人。1979年以后开始与黄裳交往,后陆续经手出版了黄裳多种著作。《来燕榭书札》收黄裳致范用信26通,均只缀月日(个别甚至只缀月份或只缀日期)、不缀年份,其中第1、2、3、26号这四封信,编者加了年份,但不全可靠。其他22封,笔者通过比堪,也一一予以系年。下面按照原书排列顺序,逐通申述。
第3号:原信缀“十一月二十八日”,编者系为“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不确,笔者系为1981年11月28日。
信中说“昨天寄上《山川·历史·人物》一册,请哂正。此书忽然印出,我也没有料到”。按,《山川·历史·人物》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11月初版,寄赠范用断不可早于此时。又,信中谈及自己近期作品出版计划,说“《黄裳论剧杂文》,给四川人民出版社,江苏也要去一本《金陵五记》”。据1981年10月10日致杨苡信,当月黄裳携《金陵杂记》(出版时改名为《金陵五记》)稿赴南京,交给出版社负责人章品镇。因此,第3号信当在1981年。
第4号:原信缀“七月六日”,笔者系为1979年7月6日。
信中说“今天遇到巴金,他的《随想录》也拟在写满三十篇后交港三联印行”。按,巴金自1978年12月1日开始写《〈随想录〉总序》及《随想录(一)》,启动《随想录》的写作计划,逐篇在香港《大公报》连载,至1981年8月11日写完《随想录(三十)》。稍后,《随想录》按照巴金的计划,于1979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据此,该信必写于1979年7月6日无疑。
第5号:原信缀“七月六日”,笔者系为1983年7月6日。
信中说“在京承热情招待、照顾,浪费了你许多精力、时间,三联同志们又热情帮助,在在使我感谢、不安,这次短暂的停留是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的”,说明这是刚在北京小住回沪后写的信。在“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上北京了”的情况下,黄裳分别于1980年6、7月之交和1983年6月两次到北京小住。其中1983年这一次住在东单,地近三联书店编辑部,后有《东单日记》发表,其中时有与三联同仁盘桓之记录,如“中午到和平饭店去参加一个宴会,见到了范用、亦代、毕朔望、冯牧、董鼎山、沈昌文诸位”(6月5日)。
信中说“回沪后把《关于美国兵》重看了一遍,写了一篇重印前言,现寄上。此书是否宜于重印,希望您再审阅一下,如可能,‘前言’就以‘往事’为题,算是给《读书》的投稿”。《往事》刊于《读书》1983年第9期,文后缀“1983年6月”。
又信中主要谈《银鱼集》书稿修改问题,提到“‘后记’发表时有些错字,现寄上改定本一册,请酌改”。《〈银鱼集〉后记》刊于《读书》1983年第6期,则该信必在1983年6月后不久。由此可断定其为1983年7月6日所写。
信中说“余英时文剪报暂留我处,颇想写点什么谈谈《柳如是别传》”,查余英时当年关于陈寅恪的文章,有《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1月号、2月号。当是范用将剪报给黄裳看。后来黄裳写了几篇关于柳如是的文章,其中与此时间最近的是1983年11月16日重校旧作《关于柳如是》(1977年作,1978年作“后记”)并写重校记,稍后的1984年1月又写下了《钱牧斋》一文。
第6号:原信缀“九月十七日”,笔者系为1984年9月17日。
信中说:“近来上海天大热,我家又在大修房子,中间还开了个热闹空前的文代会。”关于大修房子一事,在致黄宗江第10号信(1984年下半年)信中提及,“最近我家在大修房子,大混乱”。“文代会”当系指1984年8月3日到9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此信当写于1984年9月17日。又说“《读书》脱期两本,甚为焦虑,已遇到好几个人问起。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写点什么”。按,《读书》创刊不久,黄裳就和范用熟悉起来,成为经常撰稿人之一。该刊1984年第1、3、4、6、10、12期各有文发表,那么“脱期两本”指7、8两月未发表文章,与上述系年结论吻合。
第7号:原信缀“四月十七日”,笔者系为1981年4月17日。
信中说“知道《榆下说书》已发排,很高兴”,“《说书》印时,请留三十本毛边的”。按,散文集《榆下说书》为三联书店1982年2月初版。该信写于《榆下说书》编校完毕、已进入排印阶段之时,当在此之前不久。又,信中说“潘耀明……已回港,关于《富春集》的出版,不知尚有什么问题,我想一切都可由您处理”。按,《富春集》是黄裳拟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的散文集,1981年11月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山川·历史·人物”。那么这封信应写于1981年11月之前。准此,该信当写于1981年4月17日。
第8号:原信缀“十四日晨”,笔者系为1983年6月14日。
信中说“还要住两天,名胜一处都未去,总要去一两处的。少暇当走访”,说明此时黄裳在京。又说“李一老要给他的一部书题跋,不知您处有笔砚否?如无,我可找朋友处借用。题跋写好后,原书还请您转交”。《跋李一氓藏〈宋元词三十一家〉》“癸亥端阳节记于东单客寓”,时在1983年6月15日。1983年黄裳到京,情形参见上述关于第5号信的说明。李一氓请黄裳为藏书题跋,黄裳客中无笔砚,14日写信求借于范用,15日题跋,正相符合。
第9号:原信缀“一月三十日”,笔者系为1983年1月30日。
该信所谈为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10月出版的散文集《晚春的行旅》。信中说“《晚春的行旅》编好了。全稿附上”。在该书出版前夕,黄裳遵出版方要求,于1984年6月11日写了一篇《序》,落笔先交代:“《晚春的行旅》是去年年初编成的,我曾为了完成编选工作而满心高兴。……前两天得到编辑部通知,说是书将付印,希望补做一篇新序。”据此,该书编成当在1983年,信则写于当年1月30日。
第10号:原信缀“四月十六日”,笔者系为1984年4月16日。
信中主要谈自己将要出的几本书。“昌文、秀玉同志来,带来新书数册,拜收。”信中写听到沈昌文、董秀玉所谈出版界近况,表示高兴,又“听说《珠还集》因与《银鱼集》性质相近,恐将推迟至明年、后年,想想周期似过长些”。信中问“《榆下》不知何时重印,问询者甚多,都无法回答”。《榆下说书》1982年2月初版,谈重印计划必在此后。又已知《银鱼集》1985年2月出版,《珠还记幸》同年5月出版,两书只隔三个月。假如该信写于1985年4月,那么当时前书已出,后书即将出版,沈、董不可能告诉黄裳“要推迟至明年、后年”,因此只能作于1984年。
第11号:原信缀“十一月二十九日”,笔者系为1980年11月29日。
信中提到即将编完《榆下说书》《富春集》两书,交付三联出版。“《富春集》不知能否放在港版的那套小书内,可以印刷得漂亮些。”“富春集”为游记散文集初拟书名,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改名“山川·历史·人物”, 1981年11月初版,1982年5月花城出版社重版,又改名“花步集”。考虑到出版周期,写信的“11月”不可能是书正式出版的“11月”,最晚也当在1980年11月。又,信中提到“夏公的集子和《唐弢书话》”印得好。这里指的是《夏衍杂文随笔集》和唐弢《晦庵书话》,分别于1980年8月、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黄裳写信时已见其书,则必在9月以后。由此可知,该信写于1980年11月29日。信中说“另写了‘后记’各一篇,附在稿末”。查文集,《花步集》后记写于11月26日,《榆下说书》后记写于1980年11月28日,进一步坐实上述结论。
第12号:原信缀“六月二十日”,笔者系为1981年6月20日。
信中提到,“知道《说书》已付印,进度之快,出乎意料”,则信必写于《榆下说书》出版(1982年2月)之前;又提到港版《富春集》已决定改名“山川·历史·人物”。据前述第11号信,该书1980年11月编成,1981年11月出版,那么这封信必写于1981年6月20日。
第13号:原信缀“六月”,笔者系为1982年6月。
信中说“《榆下说书》样书已看到,甚为满意”,则信写于《榆下说书》出版时间(1982年2月)之后。又说巴金“最近写了一篇谈出版事的文章(也是随想录)……对国内出版之慢说了两句”,当指《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随想录》第八十八篇),写于1982年5月27日,文中抱怨当前“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据此,信当写于1982年6月。又信中说“刚才巴金托我写信便中告诉您,他的随想录完稿,题《真话集》,等最后一篇见报后即贴好寄上”。据《巴金年谱》,当月18日,黄裳与黄宗江、姜德明一起看望巴金,巴金谈到当年编辑“文学丛刊”事。因此可以推断,写信具体日期或许即为会见当日,即1982年6月18日。
第14号:原信缀“四月五日”,笔者系为1986年4月5日。
该信是收到《翠墨集》稿费后的回复,同时索要样书。按,《翠墨集》出版于1985年12月,稿费当在此后寄奉,因此该信不早于1986年4月。信中告范用“《明报月刊》一册,前挂号寄还”,联系第21号信(1986年1月27日,系年依据见下文)“前寄下《明报月刊》散叶,早收到”,则黄裳在1986年1月前收到范用寄来的《明报月刊》,阅后寄还。据此,4月5日信确当为1986年的。
第15号:原信缀“一月十四日”,笔者系为1982年1月14日。
信中告知范用,自己“编了一本散文选集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已付排”,此指《过去的足迹》,1984年8月出版,信当写于此前。又说“一月号《读书》有一氓同志文,极好,得此老挂头牌,关于古籍一方面可以有所瞻依,也不再寂寞了”。查历年《读书》上的李一氓文章,1月号的唯有《关于黄侃的词》一文,刊1982年第1期。由此可断定,黄裳此信写于1982年1月14日。
第16号:原信缀“一月十六日”,笔者系为1985年1月16日。
信中仍谈自己的书出版事,说“三联分出事节后或有进展?我只盼一切较为顺利,两本书早些印出”。按,黄裳著作在三联密集出版,当数1985年,一年内出版了《银鱼集》(2月)与《珠还记幸》(5月)、《翠墨集》(12月)三书。该信所谓两书,必指其中某二;系日为1985年1月合乎逻辑:此时《银鱼集》出版在即,黄裳当已知道,“两本书”指另外两本。又,“三联分出”指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三联书店正式恢复独立建制在1986年1月1日,但此前一两年间就已在谋划此事。
第17号:原信缀“十月廿八日”,笔者系为1984年10月28日。
信中说“《银鱼》及《翠墨》两集何时可出,甚盼拨冗见复为盼”。按,《银鱼集》《翠墨集》分别于1985年2月、12月出版,信最晚当写于1984年。又说“去安徽旅行了十天始归,先复此信”。安徽之行,曾到安庆、枞阳、贵池等地,留有游记《好山好水》(1984年12月作,收《黄裳文集》卷一)。因此,该信当作于1984年10月28日。
第18号:原信缀“一月七日”,笔者系为1986年1月7日。
该信谈《翠墨集》出版事。此前,黄裳收到了范用寄来的《翠墨集》封面、插图,书付印在即,因此黄裳叮嘱“书如付印,请留几本毛边的”。该书出版于1985年12月,则信写于此前后不久。谈到该书印数少,难免赔本,说“今后除自己有仓库,有发行网,则情况很难改善”,正好折射了刚刚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三联书店的情况。因此,写信日定为1986年初是合乎逻辑的。
第19号:原信缀“五月二十二日”,笔者系为1985年5月22日。
信中说“我于前日自兰州返沪,这次出去了三个星期,畅游一通”。按,1985年4月25日,黄裳赴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然后游览三峡、重庆、西安、敦煌、兰州等地,留有系列游记《黄鹤楼》《江上日志》《重访山城》《五日长安》《天下雄关》《敦煌》,皆收《河里子集》(香港博益图书公司1986年版),信中所指即为此行。信中又告知范用,自己已收到《珠还记幸》《翠墨集》样书。据上文所述两书出版时间,将该信系为1985年5月22日,正是情理中事。
第20号:原信缀“五月十八日”,笔者系为1993年5月18日。
信中附言提及“王世襄兄昨午见过,他近来为上海博物馆设计明代居室布置的,兴致甚好”。按,据曾焱《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一文载述,1992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王世襄的藏品捐献上博。据此,王世襄到上博应在1993年。信中对范用提议为黄裳举办书展表示感谢,“兄有兴趣为我搞书展,甚感,但所说三书是否能于年内出版,甚至能否付印,都不可必”。至于所提及三书,“其中有《河里子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市秋茶》,广州旅游出版社。《书林一枝》,陆灏代编,我亦不知出版社名”。按,《河里子集》先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4月出版。《一市秋茶》,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书林一枝》,迟至1998年才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写该信时,诸书尚未面世,或刚出版而黄裳本人尚未见到。信中还说“《读书》稿亦久不寄,实因无话可说之故耳”。按,《读书》1992年第4、8、10诸期都有黄裳文发表,1993年上半年均无黄裳文,第8期始有一篇,1994年第3、7期各有一篇。斟酌之下,“稿亦久不寄”一语唯1993年中说出最合逻辑。因此,该信系于1993年5月18日所写。
第21号:原信缀“一月廿七日”,笔者系为1986年1月27日。
信中说“航寄《翠墨集》样书两册收到”,则信当在《翠墨集》出版(1985年12月)后不久。又谈到自己听说范用“已离休,现仍主持编委会,又在与‘人民’紧张分家之中”。三联书店于1986年1月1日正式独立建制,则信又当写于此前后不久。因此,应为1986年1月27日所写。
第22号:原信缀“一月廿二日”,笔者系为1985年1月22日。
信中说“此次在港,曾由博益图书公司的编辑主任吴永圻陪同在电台‘对谈’,他约我出两本书,已答应他”。按,1985年10月4日至13日,黄裳随以艾芜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港,其间参加多项文学交流活动,信中提及的即是此行。博益所约书,系指《河里子集》,后于1986年1月出版。信中又说“《翠墨集》不知何时可印”,因此该信应在《翠墨集》出版(1985年12月)前。显然,该信当写于1985年11月22日。
第23号:原信缀“四月十二日”,笔者系为1985年4月12日。
信中说“我大约在二十五日离沪,先到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游三峡,然后到西安……”。此指1985年4月的中西部之行,见前文对第19号信(1985年5月22日)的说明。因此,该信系出发前不久所写,即当月12日。
第24号:原信缀“九月一日”,笔者系为1985年9月1日。
信中说“春天到西北去跑了一趟,《读书》无稿已数期”。此仍指1985年4月的西北之行,见前述说明。又,《读书》1985年只有第2、3、4期各有黄裳文章发表,此后即无。据此,该信系写于当年9月1日。
第25号:原信缀“四月四日”,笔者系为1985年4月4日。
信中也提及“四月下旬我要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则信写于1985年黄鹤楼笔会前夕。因此,应系于1985年4月4日。
这样,黄裳致范用的26通信,按照时间顺序应作如下排列:
1、4、2、11、7、12、3、15、13、9、5、8、10、6、17、16、22、25、23、19、24、18、21、14、20、26
注释:
①黄裳:《“书简文学”》,《黄裳文集》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②参见唐金海、张晓云《巴金年谱》中相关纪事,此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③黄裳:《前门箭楼的燕子》,《黄裳文集》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页。
④黄裳:《东单日记》,《黄裳文集》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页。
⑤关于改名过程,见致范用第12号信,笔者系为1981年6月20日。
⑥据黄裳该信中说,此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作回忆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