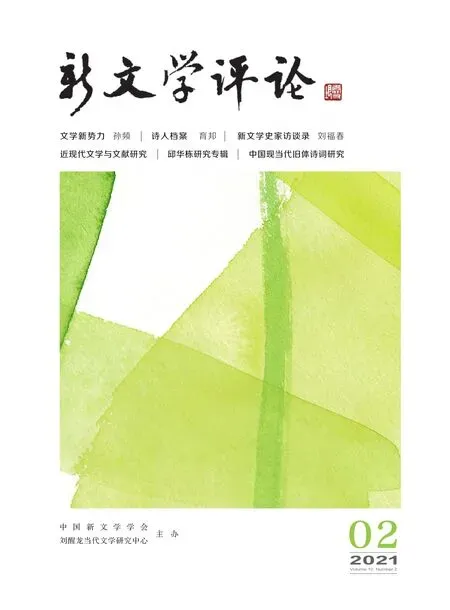作为“专业”的中国现代文献学可能吗?
——刘福春先生访谈录
2021-11-11刘福春
□ 刘福春 李 哲
李哲(以下简称李):
首先想请您就一个基本问题做一些解释。最近这些年,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文献”来界定您和诸多同行的工作,但在早些时候,大家包括您自己都爱称呼自己是“史料工作者”。那么根据您具体的工作经验,这两个词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刘福春(以下简称刘):
其实“史料”和“文献”这两个词一直在用,它们的区别一定是有的。从理论层面,好像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可能更想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进文学所那时开始的一个变化。这不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应有一个时间线索的梳理。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叫“史料”,而是叫“资料”。那个时候做这样(研究)的一些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搞资料儿的”。在“文革”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材料”,“材料”跟“资料”好像又不一样,“资料”有点中性,“材料”好像是有意在做某个人的“材料”,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太好的。我到所里工作的时候,“材料”的说法一般不会用了,当时更多使用了“资料”这个说法。比如说那个时候像咱们研究室老的一代,他们就不大说“史料”,说自己是“搞资料儿的”,包括咱们做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也是用“资料”的说法,而几乎没有用“史料”。我想后来显然是觉得这个称呼有点太轻了,就更多使用了“史料”的说法,像马良春他们出书,都用“史料”取代了“资料”。到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这个学会在最初成立时以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为主,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88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那次会议人还是挺多的,像台湾的秦贤次等都来了,还有香港的学者。“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这个名字现在大多数人都叫不好,“史料学学会”是个有点别扭的称呼,在“史料”后面又加了一个“学”,好像如果不加这个“学”,就觉得它的理论成分不是很高,我觉得这跟我们工作的方法和自信心还是有一点关系。最近这些年,“文献”的说法更加流行了。我为申请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去查了一下,发现那里面的题目已经很少用“资料”了,“史料”偶尔也有一点,但是更多的是“文献”。我觉得从“史料”到“文献”的变化当然可以从理论层面来进行辨析,但更多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跟大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自信”有点关系。现在,我当然觉得“文献”比“史料”更加正规,或者说更加完整庞大一些。史料嘛,它就好像更小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从理论的层面上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李:
这个太有意思了,也牵涉到很多特别重要的学科史和学术史问题,也很值得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再做一些辨析。刘:
我觉得做史料也好,做文献也好,大部分都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学科成熟,它确实是需要理论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建设,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操作层面,即具体怎么来做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我更像一个厨师,但是这些年逼得你不断要阐释一些什么美食理论。我可能会把菜做得还可以,或者做得很专业,但是你要让我在理论上说得那么清楚,或者要从什么营养学方面再说出一些话,那就说不上来。我写的好多所谓“理论”文章都是跟我实践有关的感想,我觉得它缺少一个在理论层面上对这个学科的系统思考,这本身就是我的不足。李:
“史料”“资料”和“材料”的问题,是否跟七八十年代之间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状况的变化有关?这些词背后是否对应着当时人们一些特殊的心态和感觉?比如“资料”在当时就常常和“情报”连用……刘:
你讲的这个让我忽然想起来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做资料、做史料的这些人都来大陆交流了。记得九十年代初,来了一位台湾的诗人,见面当然谈一些诗歌的问题,没想到他说自己对台湾那些搞资料的人特别讨厌,原因是他们搞得太细致了。我当时很惊讶,搞资料肯定是越细越好啊,但那位诗人说那些搞资料的太气人了,他们连哪个诗人哪个作家是党员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不给国民党提供情报吗?李:
沿着您刚才说的线索再提一个问题吧。从“资料”到“史料”再到“文献”的名称变化,是否也伴随着我们这个学科不断“规范”的过程?刘:
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学科的成熟或者叫独立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过去做材料、资料,还是一个附属的关系。后来称呼虽然变成“史料”,但还是会附属到“阐释”或理论研究的后面。但我觉得,史料和文献工作更多关系到求真求实的问题,它还是应该和理论阐释区分开来,它们各有各的目标和方法。李:
史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总是占有一个位置,一般研究者不可能不利用史料工作者的“成果”,但大家对史料的态度在各个时期却有很大的不同。作为资深的史料工作者,您对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否也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刘: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还是发生在最近这些年,大家对史料工作的整个评价变高了。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国家社科基金,这样一个倾向性的东西不能不说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我看了一下国家社科基金里的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很多题目都是“整理与研究”,与“史料”相关的似乎更容易申请成功。但你看那些题目,“整理”后边还是要带一个“与研究”的尾巴。所以我就想问,如果只是做一个“史料整理”,能申请到基金吗?其实对我们来说,“整理”本来就是“研究”,没有“研究”又谈什么“整理”,所以大家还是没有做出很好的区分。李:
史料整理工作的从属性应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吧。刘:
是的。比如我们常常说“资料热”或者“史料热”,其实最热的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咱们文学所(主要是现代文学研究室)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就是一个国家级的社科项目,当时各个高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好多都参与了工作,在当时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过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研究资料还是作为“副产品”出来的。比如有学者要撰写《冰心传》,前期要收集资料,所以捎带着编出了《冰心资料研究》。就是说,他们的资料工作从缘起、观念和具体操作上都是服从于“阐释”的。所以我为什么总是在考虑学科的独立问题,因为这里边确确实实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大家都做了,做了那么多,但是真正把心思都放到这上边的人并不是很多。李:
您觉得史料文献工作从属性问题是什么原因呢?刘:
一是大家对“史料”有一个评价,好多研究者心态上觉得你本来就是服从于研究的,而且你们这些人只能是给我们“做资料”的;二是在成果体现上,成果出来的时候,我们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评价标准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个跟“古代”学科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提到的“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最开始还是以“现当代”为主的,后来“古代”的逐渐加入进来了,到后来开会的时候,“现当代”就成了一小撮了。这里有一个不均衡的问题,人家有专门的古籍所,资金充裕,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跟人家相比,我们现当代做史料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成果,我觉得在评价上肯定是不够的。另外反过来讲,也不能不承认,我们所做的这些成果,跟“古代”的相比,专业性还是差一些,这里确确实实有一个学科建设的问题。李:
您刚提到社科基金偏重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然后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的题目和成果。但也正如您所说的,我们确实是水平不如人家古典文献,那么我们要怎样提高我们的水平?其实是需要更多的人能投入进来,你东西出来了,然后在大家的评价之中再提高规范的要求。所以恐怕还是要呼吁,应该承认史料的整理或者说文献本身的价值,这其实是我们提高水平的一个前提。刘:
成果的评价问题确实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确实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史料文献工作现在一下热了,很多人在做,它仿佛忽然变成了一个非常容易操作的东西。但是就我见到的一些成果来说,真不能说是专业的。大家都热心来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是你只要想做就能做,我觉得这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见到有一些还比较大型的东西,从文献的专业角度来看,还是非常成问题的。李:
您能围绕这个问题从经验层面具体谈谈吗?刘:
比如近些年出的比较大的那些影印的(资料),我当然觉得非常有用,总比没有强。但如果从专业上考虑,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比如我想做一个关于诗歌的影印资料,那我就必须对诗歌有专业的了解,我得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版本,这个版本我在影印时必须找到放进去,而不是说现在我能找到什么就往里塞。再比如,当时的一些出版物后边有好多广告,但我曾见到一套影印资料,居然把广告都删了。还有就是封面。很多影印资料会把封面弄得非常小,就像咱们在网上看的那样,几乎让你看不到封面。我跟李怡老师也在做影印资料,我费劲比较大的就是找封面,因为封面残缺得太厉害了。我找到的书如果缺封面,我会尽量去很多图书馆找,把那个封面补上,因为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它,才能把资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现。还有这几年去世的作家,对他们的相关资料也在整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从专业上来考虑,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资料编辑者介绍作家去世的消息,只说来自新华社,来自《文艺报》,但《文艺报》哪月哪日登出来的,都不清楚。这些其实非常重要,作协认为非常重要的作家,那是第二天或者当天就能见报的,但如果他们认为不是重要的作家,就会扎堆(报道),集体发一些,或者发的位置不显眼,等等,这些都是“很专业”的信息,如果以后有人研究的话,能根据这个看出当时对这个作家的评价。我觉得要让更多的人关心这个,让真正做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往专业上做。现在这个东西忽然时髦起来了,大家一哄而上在做,这种做法我觉得可能对于文献的建设未必很有利。李:
您谈到当下资料整理工作的专业性问题。您能结合自己的经验说说史料文献工作完整具体的过程吗?尤其是在过去,不只要动手翻书,还要全国各地去跑图书馆,“动手动脚找材料”,这跟今天数字化时代的专业性有很大区别吧?刘: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要“动手动脚”,只动手还不行,必须动脚,就是你说的“跑图书馆”。我在做新诗集目录的时候,跑了五十多家图书馆,也看了一些个人的藏书。那个时候大家做得还是比较辛苦,每一条资料那都是从报刊里边翻出来的。那时候可以看原书刊,但是报纸只有缩微胶片,看那个其实是挺费劲的。要坐到那儿一个上午,一卷一卷对着看,有的时候看过了又倒回去。那时候没有电子文档,全部是手工劳动,你要去跑。李:
那时候找材料难度最大的是什么呢?刘:
难的就是人家不给你看。当时好多图书馆的公共性还不够,基本上是拒绝给你看,所以我还记得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咱们所里有一个北大的借书证,因为咱们所前身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虽然分开了,但是咱们还有一个证。那个证所里好像只有一个,但是你要去的话,你可以拿着那个证去,你可以跟北大的师生一样凭证看书。我记得当时去他们那里借诗集抄写目录,由于一次借阅的册数有限,只能是管理员从库里取出几本诗集,抄完了,再去找她取。有的诗集里边根本没有几首诗,那时候诗集也薄啊,一会就抄完了。管理员当时就非常愤怒,说:“你这么反复地拿呀,自己进去找!”那是我遇到的让我最开心的一次“愤怒”。他们的书库像咱们图书馆,一进去就发现了好多在别处发现不了的东西。所以后来我经常盼着什么时候她再“愤怒”一次,但实际上也就只让我进去那么一回。不让看归不让看,但一旦亲自看到,你能接触到原始文献还是会有很大的好处。前些天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开了一个“70—80年代校园诗歌群落学术研讨会”,同时办了一个展览,我拿出了一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始的非正式诗歌出版物。我问参会的学生:“你们看复印的和原始的刊物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好像回答不出来。其实文献是否“原始”不仅仅是清楚不清楚的问题,还关系到对那个时代的感受。
李:
能再具体说一说吗?刘:
比如那天,诗人邓翔拿来一本1983年的《第三代人》,这个刊物很重要,因为跟所谓“第三代”有关系。但如果你把它电子化了或者重新影印了,你就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了。当然,你能看出来它是个油印的,但是你很难感受它当时是一个多么“艰苦”的东西。邓翔当时没有钱,他用的纸张都是非常薄的,油印只能单面印,双面印就透了。所以那个纸你一拿过来,放到手里边,你就感觉你面对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如果现在把它影印了,重新出版了,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还有,那个时候它为什么小本为什么大本都是很重要的信息,但现在如果重版了,开本大小也会有一些改变,那重要的信息就流失了。再比如,你看抗战时候的文献,拿来的时候会发现它就是土纸,一摸都轻飘飘的,是不是?所以这些感觉现在从网上看是很难再有了。李:
但我们现在确实进入数字化时代了,搜索引擎、数据库确实在研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您对这些怎么看呢?刘:
怎么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很多所谓网络诗歌或者网络文学,还只是把纸质的“搬”到网上去,这种机械的“搬”其实会出现很多错误。有的是不大认识繁体字,把字弄错了;还有就是把从右向左的书名弄反了,就永远查不到了。除了这些错误之外,这种“搬”也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的特性,它跟网络特性的关系也没那么紧密。其实我和四川大学的同事也在思考,如何利用网络的优势,而不是简单地把我们现在的文本“搬”到网上去。比如将一首诗放在网上,只要我点击这首诗,就能出现与这首诗相关的各种信息,朗诵的录音,相关的影像资料,包括关于它的评论等等,都能充分显示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代文学文献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整理对象是现代文学,也意味着我们的整理方法也应该是“现代的”,能够不断地更新。所以文献的数字化,其实还是一个专业性问题。好多做文献数据库的公司都不是很专业,他们会请一些没有经验的年青人,给文献分类时分得乱七八糟,好多书都找不到了。再比如文献录入,其实也是非常专业的问题。在李怡老师的重大项目里,我负责做诗刊目录,我就跟大家说,目录呈现并不是简单地把目录复制下来,因为一本书或一个杂志的目录和它的正文常常是有区别的——有的目录有正文没有,有的正文有目录没有。再比如诗歌刊物中有的诗歌是组诗,它在目录里边呈现的只是组诗的题目,但这组诗究竟包括了哪些诗,目录里是显现不出来的。还有“诗四首”“外二首”之类,也是如此。但现在很多人做的时候,就简单地把目录页复制一下,只要没有错误,能把繁体字都认识清楚了,就算“专业”了,实际上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李:
我感觉您强调的专业性,其实已经超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了,文献的“专业”反倒给我们提出了许多“跨学科”和“跨专业”的要求。所以再提一个小的问题:作为一个文献的使用者和研究者,我们怎么能够让文字文献的数字化保留更多我们纸质文本的历史性,或者说,那些纸质文本的社会性包括它的物质性,怎么能够更好地在网上呈现出来?有没有可能防止那些东西被模糊掉,影响到研究者对文献本身的认识?刘: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完整性,在关注某个特定文本的时候,也不应忽略和它相关的信息。比如某一首诗,它所发表的报刊我要关注,但从文献学的眼光来看,我要知道它是放在头条还是放在末尾,是否是补白,还要看和它相关的这一版里还有谁的东西,甚至也不能忽视它前面和后面的相关部分。这在五六十年代会非常明显,比如某个诗人的某首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你翻看前面的时候看到头版有党中央的声明,那么两者就可能是有关联的。有段时间我特别想读《人民日报》,但那个时候读原报不方便,就在网上看,开始觉得也挺好,但后来就不读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网上的《人民日报》相当于只是一个“选本”,一篇一篇地看,我想知道同一版都发了什么就很难了。但现在就有技术了,有的网站可以把条目单独拿出来放大,能够看到整版的版样,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所以电子资源怎么能对文献完整呈现是第一位的,此后才能讨论如何更丰富、更立体地呈现,但第一步现在都很难,“完整”这一块都没有做到,所以我们的专业之路还是很长的。李:
我自己感觉,您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条非常核心的准则,即追求完整性,对材料应收尽收,最大限度保存历史原貌。这条准则说起来很朴素,但一旦着手去做又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且相比“现代文学文献”,您最近文章讨论的“当代文学文献”可能更会遭遇这一挑战。在“当代”的情境之下,所有的“文献”并没有成型,而且处于不断变动的不稳定状态。所以当我们对它做整理工作时,“全”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有所选择,而且无论如何也会有一些选择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全”的理想追求和“选”的现实标准之间,是否会存在张力?您作为史料文献工作者,又如何在具体操作中处理这些问题?刘: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献工作者应该是求“全”的。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全”,而只能向“全”努力。我觉得文献工作尽量不要去“选”。我在做“编年史”的时候,难度最大的就是选择问题。有人说“文学史”应该是越来越薄,但“薄”也应该建立在“厚”的基础上,或者说“全”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你怎么“选”都是有问题的。这里面可能有向度的不同,写“史”的话当然要有选择,不可能把那么多东西都放进去,但是作为文献的话,我觉得第一要完整,即求“全”。但实际上这只能是一个理想,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李:
比方说您做新诗文献,肯定是以应收尽收为准,这可以说是追求“全”。但把“诗”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拎出来,或者说把“新诗”从众多的诗歌作品中拎出来,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另一个层面的“选”呢?刘:
就拿我做的“编年史”和“诗集目录”来说吧,这就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工作原则。“编年史”虽然有文献的意义,但是它的目标还是做一个“史”,这就要有选择,如果没有选择的话,我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但选择非常困难,首先就是文献不全的困难,比如说诗刊,诗刊出了多少种,每一种出了多少期,这些都不清楚,我想尽量把它做清楚。在实际工作中,在做“编年史”的时候,主要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这“选择”有两个方面的困难:一个就是我曾讲过的,我常常担心由于我的选择遮蔽了书刊的原貌,又害怕因为我的疏忽遗漏了可能最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这毕竟是一个“编年史”,而不是一个“叙述史”。比如一本诗刊,因为你一“选”就可能把一个刊物“选”得面目全非了。假设我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很烂的刊物,它可能只发过两首好诗,都被我选进来了。但人家看我的“编年史”里面对这个刊物的记录,就会觉得这刊物厉害啊,水平这么高,可实际上它就那么两首好诗,那就等于说我的选择就把刊物的原貌遮蔽了。还有一个困难是因为我的选择可能会漏掉很多更有文学史意义的东西。所以我的“编年史”在处理刊物时用了两种方式,先是不“选”,刊物推出的头条我一定要记录,尽量地保留一点原貌,然后再有我的一点发现和选择。所以严格地讲,“编年史”不是一个文献的著作。
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是我做的“诗集目录”,当初叫《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这个书目原本是有注的,出版的时候因为要与其他卷体例统一,所以把大量的注都给删掉了,有点可惜。诗歌卷跟其他卷最大的不同,就是那里边有大量的注。注的是什么?就是我将目录与正文进行了对校,把二者的不同处都注了出来。还有诗集的各种缺项,比如有的没有时间,就要根据其他资料补充。当时为什么我会跟那些诗人通信那么多,好多都是在确定这些问题。诗集没有时间,请诗人大致回忆一下,根据诗人反馈回来的信息,我就在下面加一个注释。我认为“诗集目录”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那里边没有我的选择,我见到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比如目录是有序的,正文没有,我会注上“所见本未见序”。“诗集目录”不用我来选择,它收了什么诗,我一点选择都没有,也自然没有选择的痛苦,我觉得这才是文献。我个人更喜欢“诗集目录”,但是没办法,好多人都对这些东西评价不高,总觉得是“编”出来的。
李:
您在那篇讨论当代文学文献的文章中也提及了特殊文献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材料的使用是否有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刘:
这些特殊文献,还是要看你在哪个方面使用,总的来说,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辨别。传统文献学有辨伪,当代文献可能无法直接称之为辨伪,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辨析,你直接拿来作为“信史”肯定有问题。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当初公开的一些文件,这些文献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经历了,都知道这些文件不能直接使用。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发现的大批档案材料,这肯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但不加辨析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检讨文献,检讨的动机和过程都很复杂,比如有的人就是要不断地检讨,一次检讨不合格,就得再检讨,越来越上纲上线,有的要检讨好长时间。还有就是揭发文件,揭发者的心态也完全不一样,有的混混过关,有的是想把个人的“私货”也夹杂进来。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还牵扯到一些其他问题,如版权的问题等。古典文献做李白、杜甫的资料,很多隐私啊、小道消息啊只要可靠都可以用,但我们在使用现当代文献时很多就会受到版权限制,版权所有人不准你用。很多当代作家的问题,我们没法说等到版权失效了再来做,我们等不起,但一旦要用,就会涉及版权以及伦理问题。如果材料涉及好多个人隐私,是不是都能拿到研究层面直接使用?其他关联的问题还有很多,我觉得都需要大家认真讨论。当我们用当代文献去叙述历史的时候,问题可能会更多。我做“编年史”做到最后的时候,最不敢用的一个词就是“真实”,越做我觉得离真实越远。我虽然用了大量的所谓第一手资料,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把一个已经被简单化的历史重新还原,还原出它的丰富性,但是能够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心里边也没底,我不认为那些东西全部是真实的。
除了“文本”之外,还要跟“人”有大量的接触。这是现代文献与古代文献的一个不同。这有利于我们的文献收集,但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位诗人,我当时找他的诗集,找来找去找到一本,但看他当时出版的关于自己的介绍,他有好几本诗集。我给他写信,他也告诉我他有什么诗集,可还是找不到。因为毕竟是老先生,我也不好意思问得太直接,就写信给他问诗集的出版社,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说我出版过那些诗集呀?我只是说我有我自己编的诗集。”也还有另一种情况,诗集已经出版,但诗人自己却忘了。我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马加的两本诗集。我当时问过他,他说,“我告诉你吧,诗集根本就没有出出来”,还告诉我没有出的原因是如何如何,但后来我跟他说,我在图书馆见到了他的诗集,他听了又很高兴,还让我帮着去复印。
总之,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历史文献,包括档案,公开的不公开的东西,都必须要辨析。此外还涉及史料文献工作中的“拾遗补缺”问题,有些问题需要讨论,比如现在网络上有的是不是还要去补,是补网上有而全集没有的东西,还是补网上没有的东西,等等。
李: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当下究竟应该怎么界定“佚文”?刘:
这个问题很复杂,鼠标一动就能找到的东西,是不是还叫佚文?另外,全集里没有的也不能直接称之为佚文。比如卞之琳,他的好多东西文集里都没有,因为在编的时候,他自己说他那些东西都不要。还有,当你找到一篇文集或全集中没有的诗文,要确认为某个作家或诗人的佚文是需要辨析的。当初我编《牛汉诗文集》的时候就找到一首诗,署名为“谷风”。那个时候牛汉用“谷风”的笔名写了很多诗,但这一首读起来就不大像他的东西。后来我就问他,他连看都没看,直接说“我不可能在那种刊物上发”。因此今天如果只是按照笔名去找佚文,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拾遗补缺”,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功夫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而且现在有一些这类的工作是从小到小,我希望能从小到大,从一个小的发现引申出大一些的问题,当然不能说必须就是宏大的问题,但总要大一些,这当然有难度。现在“文献”这块有点热,但我觉得我们做文献和做史料的人自己要有一些反省。我们现在做文献的条件还是比过去好得多,应该努力有一个从“拾遗补缺”往“系统整理”的迈进。并不是说“拾遗补缺”不需要,但我觉得更需要的还是系统地整理,把那文献做得更大一些。
当然,也不能说越大越好,“大”本身也应该有标准。我们现在做得太容易,常听人说“在某某方面积累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在这方面我还算个专家,我想说,几百万字太容易了,带着学生就能做,用鼠标点出几百万字并不算困难的事。但重要的是,在网络之外,你究竟又增加了百分之多少的新东西。哪怕增加10%,就很可以了。但现在大家不管这个,好像几百万字就了不得了,可这几百万字都是大家能找到的。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标准。
李:
当代文学文献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对象并不是现成的文献,而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文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刘:
首先还是要强调文献工作的眼光,尤其是包容度,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先留下来,不要急着做价值判断, 如果过于强调价值判断,就等于是在做“选本”,这会伤害我们以后的研究。好多工作可能是“前无古人”的,前面没有人做而我们做了。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后无来者”的东西,如果你现在不做,或者说现在没有一个文献学的眼光,你就永远把它失去了。好些东西,你当时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后来再找那就费劲了。比如当时可能一个访谈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时间一旦过去就不可能那么简单了。其实访谈也是很需要专业性的。现在访谈也常常被当作最容易操作的东西,常常有人拿着一个访谈提纲,就“放之四海而皆准”了。跟人家说你谈谈你的学术经历,连人家做什么都不知道就访上了。这还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我要访谈,我就必须对访谈对象有深入了解,而且能找出最关键的别人访不出来的问题。我最近整理谢冕老师的东西,他被访谈过好多次,但不少人连谢老师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很有名,写过《在新的崛起面前》,其他的也没有深挖,也挖不出来,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大都是千篇一律,不痛不痒的。李:
当代文献的工作确实和古典文献有所不同。刘:
做当代文献,其实要求更高。古典文献当然非常难,需要进行历史考古,而当代文献既要考古,又要同步追踪。这时候真的不能简单做价值判断,要有更宽容的态度,尽最大可能把文献保留下来,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是如此。比如我的书目,已经做得够包容了吧,收录的标准是只要“成书”就收,我也不必选择,诗写得怎样我也不看,主要看版权页就好。但实际上还是会有遗憾。比如说当时对油印的书刊,我就没有重视,只有北岛等几个诗人的油印诗集放进去了。而现在做这个课题,我才发现油印太丰富了,而且这些东西现在“抢救”就有点晚了。如果20年前有这个意识,会有更丰富的收藏。我觉得这真的需要一个文献工作者有更专业的眼光,或者是更包容的心态。不能只是“选”,我真的最怕选,看到选本就头大,因为你选就遮蔽了好多东西,而且这选本会让别人上当。李:
我们那会儿上学写论文的时候,老师就要求注释一定要引用原刊,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整理出来的东西了,但是你不能用那些东西,你一定要用原刊,如果用别人整理好的本子,就说明你没有用功。这是读书时候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是也反映出对那些整理出来的资料的不信任?刘:
很多东西确实是有问题的。如果说真正有一个高度专业性的资料集,为什么不能用呢?为什么你要去重复劳动?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专业,是否值得信赖。李:
这个问题在网络上电子资源上可能会更加严重,读秀电子书中有些书的版权页和封面都会出现不统一。刘:
知网上也有一些错误。刊物有季刊、月刊,还有上半月刊、下半月刊,期数的标法不完全一样。比如《诗刊》,有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虽然一年实际上是出刊了24期,但期数是2020年12月号上半月刊和2020年12月号下半月刊。在知网上我见到是把期数顺序地排了下来,《诗刊》2020年12月号下半月刊成了2020年第24期。李:
这就引申出一个关于何为原始材料的问题,您刚才说自己当年到图书馆看原始材料,其中可能包括某本诗集的初版本或初刊本等等,但今天这些东西可能被数字化到读秀或大成老旧期刊之类的网站上,那还算不算原始资料呢?还是说它们应该算另外一个“版本”?刘:
有些特别的研究,如果你不看真正的原始资料,可能就不会意识到,比如我刚才说的纸张和印刷等问题。我觉得你刚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子资源做得不够专业,如果真正专业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原始资料。问题是专业性不够。张秀中有一本诗集叫《清晨》,这本诗集缺少封面和版权页,网上有的数据库也不查工具书,简单地依据该书代序确定书名是“月下的三封信”,导致很多人查《清晨》时根本就查不到。有不少的书都没有原汁原味地把原始文献呈现出来,比如书的版权页有时候在前,有时候在后,但在数据库里就把它们全弄到前面,或许是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当代文献应该更专业些,更可信些,它提供的东西应该做到让研究者直接进行阅读。但现在不行,研究者直接用往往会上当。李:
您刚才谈到的很多都是具体经验层面的东西,但它其实也涉及很多理论性问题,但仅仅用特定的理论去整理这些经验肯定会简化,那应该如何去处理复杂经验和理论之间的张力问题?刘:
这些经验确实要上升到理论问题,我们刚才主要围绕文献问题来谈,但这些问题其实不只是文献,还是中国文学的经验问题。我们的文献和美国的文献应该是有不同的,比如,很难想象他们会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多关于检讨、揭发的文献。所以他们的理论肯定不能全部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理论可能会刺激我们,也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视野和方法,但真正把中国经验说明白,真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李: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现代文学的史料文献工作既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实际上也没法直接视为历史研究,“史料”本身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刘:
对,我们处理的这些文献,还有人认为这不是文献。而对这些文献怎么处理,怎么打开,我们真正能“进去”,同时又不被它们所左右,这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在阅读的时候就发现,只要仔细辨析,每次读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最近我就读了一些从前读过的材料,但感觉好像跟没读过似的,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了。比如我的“编年史”,有人说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做了30年,其实我觉得做了30年也是最大的问题。30年前我的眼光是什么眼光?30年后我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李:
感觉值得展开的问题越来越多,但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刘老师,也很期待以后有机会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