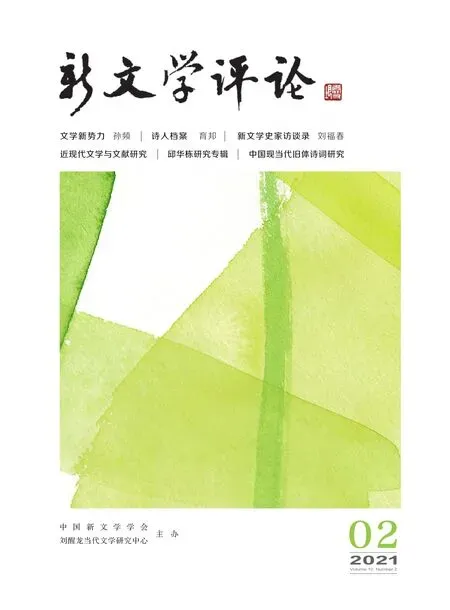从词语中选择可信赖之物
——简论育邦
2021-11-11李德武
□ 李德武
一、雪的前世今生
育邦的写作很宽泛,不仅诗写得好,小说、随笔和评论都同样出色。育邦身上有着六朝文人的清雅气质。他在善文的同时,兼通琴书。近年来,其诗日趋从容平和,言以达心,自然诚实,毫无奇诡伎俩,且常有妙语,显示出心性与艺术的双重成熟。育邦作为文学期刊编辑,选稿编刊极为严谨,而又能慧眼识珠。同时,不慕功名,潜心修学,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艺术修养。育邦无论为人还是为诗,都是一个诚实且有正气的人。
“因为雪……我们把墓志铭刻在大海上。”这是我读当代关于“雪”的诗歌中,印象最深刻的句子。这一句诗出自育邦的《因为雪》。就凭这一句诗,我看到了育邦独特的眼界和宽阔的胸襟。古人多有写雪佳句,比如韩愈“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柳宗元“独钓寒江雪”,齐己“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苏轼“风力无端,欲学杨花更耐寒”。写得最妙的恰恰不是这些大家,而是宋代诗人刘一止。他说:“人间未识,高空真侣。”这句妙就妙在“高空真侣”。刘一止号太简居士,识得雪非俗物非圣物,而是自己本来面目。真侣者,心性相伴,凡圣不二。难怪吕本中、陈与义赞叹道:“语不自人间来也。”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心灵伴侣,育邦的心灵伴侣就是雪。那不是粗鄙的感官依附或情绪的攀援寄宿,那是一种心境的融通。通过“简单的矛盾,最后的玫瑰”抵达生命和爱共同的路径。在另一首《四行诗》中,育邦写道:
面向未来,我从不掩饰
对于雪的喜爱
只有雪才是世界给予诗人的奖赏
其他的都是零
“其他的都是零”有“高空真侣”的气象。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诗歌也一样,展卷篇篇诗,尽是烟火味。几日前,我在手机上随意写下一句话:“下雪了,一口气又活过来。”好的诗歌就是要有让人一口气活过来的魔力。“因为雪……我们把墓志铭刻在大海上”让我觉得真做到了,这个世间就没有什么还能阻挡我们漫天飞舞。
二、中年与返乡
中年是一个困惑丛生的生命阶段,但丁在《神曲》中把“中年”比喻为走向黑森林的“歧途”。他认为中年需要具备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通过三个引领者体现出来:第一是智慧,通过引领者维吉尔体现出来,这是中年走出黑暗地狱的意志和思想的力量;第二是爱的能力,通过引领者卑德丽采体现出来,这是中年活力和热情的源泉;第三是信仰的力量,通过引领者上帝体现出来,体现了中年生命自我饱满和富足的自信和从容。中年的困惑和反省不是一般利益得失的反省,而是对天命的自我辨认,是在艺术上对自我目标、使命和责任的确定。育邦已进入中年,他所做的自我拷问的目的也正是验证并肯定命定中的自己。
育邦以敏锐而尖刻的目光审视自己,包括审视灵魂的本真样貌、此生使命以及归途。他写道:
我知道
我与世界的媾和
玷污了我的日子以及从前的我
我有别于我自己
——《中年》
这样的反省似乎只有到了中年才会有。而在《返乡》一诗中可以看出育邦为自己理想生活勾勒的蓝图。
我背负木剑
从世界的另一边
乘船归来
车轴河里落满了我的光阴
在海的那边
靠近星辰居住的小镇
是我的故乡
——《返乡》
育邦要返回的是一个唯美的诗意故乡,一个星光笼罩的神圣故乡,一个脱离了尘世的喧嚣和污浊的精神故乡。“木剑”在这里象征着艺术的权利,“世界的另一边”暗示当下生活残酷的现实性。诗人通过审美和诗意将自己的内心带往自由之境,如同海德格尔强调的通过内心澄明抵达诗意栖居地。“澄净”和“自由”是育邦连接艺术与生命的两根血脉,依靠这样的血脉,育邦能够从容地游走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而不失本色。
我想到荷尔德林,在荷尔德林心目中自然永远给予我们力量、信心和归处。而这些,机器技术是无法带给我们的。人此时对自然的爱与原始蒙昧时代的单纯依赖不同,此时的自然是人对抗机器技术时代的一个美的王国,是人走向自由和至乐的最高法则和目标。自然不再是外在的自然,更是人内在的自然,人通过将心灵的向往和行动内化为一而获得存在的自足。荷尔德林称其为“与万有合一,这是神性的生命,这是人的天穹”。
三、守卫内心的独立
但这样的自然,我们今天回不去了,成了“异乡人”。为什么回不去了?为什么成为“异乡人”?既然自然从本质上没有改变,规则没有改变,我们为什么回不去了?这是因为,人发生了太大的改变,回不去不是自然抛弃了我们,而是我们抛弃了自然。面临教育、科学、技术、理性、规则等广泛影响,人越来越丧失自然的本性,也使得自然的神性被理性所改写,甚至取消,在人的眼里,自然不再是美的自然,自然成为一个系统、物质和推演的复杂公式,曾经携带我们飞翔的自然神性“收敛了翅膀”。自然的对立物在这里逐渐明确下来,就是科学和教育。我想育邦应该怀着同样的失望吧,若不是沦落为“异乡人”,又何必思念着要“返乡”呢?
在《返乡》的背后,我们看到育邦从现实中获取的“反向动力”,那是无奈的、挽悼的和凄别的骊歌。他唱道:
修栅栏的人走了
砍树的人来了
鲜花一直在撒谎
树木则保持沉默
…………
走吧,马车来了
我们动身吧
——《挽歌》
哀婉在这首诗里表现为育邦对现实的一种责任和良知,正如表现主义不把现实看作真实,而把表现出的现实看作真实一样,这里育邦令我们感动的是他对现实的表现和态度。也许时开鲜花的这个现实未必是育邦的真实存在,这和道德的纯粹性无关,而和诗歌对他本真心灵的呈现有关。也正因为他在强大的世俗世界内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小小的界限,让他成为渴望“远离”现实的人。当他写下“走吧,马车来了/我们动身吧”时,这种带有传统挽歌式的祈请不是说给别人的,而是说给自己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诗人追求的独立如果只是要求自己是一个不必要宣示出来的东西,而当我们宣示出独立性时,他就不只是关于对主体边界的划分与维护,而是带有对集体或公共区域的剥离与界定。换句话说,独立性不是说给自己的,而是说给集体的。这种宣示,若不是为了获得个体尊重,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若不是为了在尊重中获得个体存在的价值认同,就不必要对着更多人大声嚷着“我”“我”“我”。独立性或集体一体化是作为权利被宣示的,当然,权利中包含了对利益的整合与分配,独立性受权利和利益的裹挟,事实上已经无法完全自主,而一个相对的独立性,更像是集体或群体的变相附庸,我们希望独立性从概念到实质都是一个边界十分清晰的词,希望这个词的能指和所指可以作为人固有的或特有的部分被指认出来。
这总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纯粹的人这种品质并不难找,比如在曼德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卡夫卡、保罗·策兰、里尔克以及兰波身上都十分明显,这些人身上的共同特质就是不向集体性交出灵魂。他们可能生活上不得不依从某种集体的东西,比如卡夫卡也要在保险公司工作,曼德斯塔姆也要加入作协一样,但是他们在与集体性的对峙中还是回到独立性的阵地上,成为战斗至死的守军。
四、精神谱系和词语伦理
基于对现实的疏远,育邦通过语言构筑他诗意的谱系和伦理,以便让自我的世界具有可交际性。我们看到,在这个被认同了的交际场内,存在着神(《与神灵书》)、亲缘(《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友情(《与仁波切夜游锦溪》)、家居(《登如方山》)等等。
《登如方山》是一首和育邦目前生活密切相关的诗。育邦为了逃避城市的喧嚣,而在远离南京的如方山购买了别墅,只为享受山野清香的空气,愉悦的鸟鸣。如今,他已经在此居住多年。我有幸到过育邦的别墅,目睹了这片幽静的山水之美。“如方山”在育邦的心目中就是李白的“敬亭山”,他本应相看两不厌的。但事实上,从诗中我们感受到育邦的失望而沉重的心情。育邦看到了什么,让他对自己已实现的理想开始怀疑、动摇?育邦写道:
当你收回目光
丈量着眼前这有限的世界
就会轻易地洞察
邪恶并未因冬季的到来而减少
野兽如此疲惫
早已让位于人类
那只红腿小隼恐惧的瞳孔中
倒映的是焚毁的星辰
和人类最后废墟的场景
我知道,我能看到
当月出树梢时
它扑腾着折断的羽翼
愤怒而忧郁
以鲜血
污染着这片大地
当育邦登高远望,他看到遥远的地方是空阔的蓝天,而当他收回视线,眼前的景象令他失望。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居住区,它是按照满足人各种欲望的方式设计的。从前,它可能是一个清净地,但随着人们蜂拥而来,这里已经与闹市无别。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免不了滋生邪恶,当人的欲望被放大时,自然和动物就将被迫退让。这首诗反映了育邦对人性的深层洞察,对人类生存现状的痛心与忧虑。
一个诗人与生存土地的关系是微妙和复杂的。审视彼此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关乎政治或道德的问题,而是关乎语言的问题。抛开出生和血缘的因素不谈,一个诗人天然地热爱他的母语——我的母语就是我的祖国。育邦的《也许你叫中国》在我看来正是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和自我辨认。这首诗以主体之间的对比方式展开,将本不对等的关系置于审视的“窗前”。这期间,诗人发现他和其土地之间若即若离,彼此并不是一种“母子情结”,而是陌生中的相遇。“我”作为话语个体始终寻求摆脱语言的“普遍性”存在,而事实上,就算“隐没深林深处”,也还是寄居于母语的“普遍性”之中。这是每个诗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优秀的诗人是那些给母语增加活力的人,是那些展现母语更深魅力的人。有这样意识的诗人才算得上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育邦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当他深入其中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联系的复杂性也展现了出来。
当读到育邦一些以“我们”的口吻书写的诗歌时,我很好奇,暗自追问:“谁是真正的言说之人?谁又是听者?”我注意到育邦在一些游记类和唱和类的作品中,常以“我们”的主体身份说话。这让我想到“他者”的理论——权力语境下的身份认同。这些诗的语境变得复杂,交织着对现场的复述和创作当下的联想。有时,“我们”是一个含混的所指,他并不带有身份识别,而仅仅是一种声音识别,但“我们”不是说者,“我们”是诗人创作中潜在的交谈者。比如《三角湖》《在永康》《南田生活指南》等,诗中的“我们”不意味着群体同声,这些诗歌仍是育邦个人的声音。其中《三角湖》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对话语境,尽管这里面交替出现“我们”和“他们”的身影,因为,从头至尾,这首诗都没有显露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以及不可弥合的界沟,而是以一种“发现”的方式,看到了“他们”和“我们”本是同道者,甚至是我们崇尚的榜样。育邦写道:
他们只是拥有每一个时刻
每一片羽毛,每一片树叶
都像一滴水那样
走向纯洁,接近无限
叫我们心生嫉妒
因为我们殚精竭虑
探究一生
也没有长出一片
“他们”在这首诗里特指“卜居者”,这些从前的修行之人成为育邦内心真正的交谈对象,这些当下缺席的交谈者通过育邦内心的关照而复活,并且仅仅复活在他的内心。这一点,就算与育邦同行之人都难以感知。因此,我觉得这首诗中的“我们”仅仅是一个谦辞,出于对“同行者”情义的回报而选择的礼节性称谓。
不同的是,《南田生活指南》则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达了对“他者”的崇敬与肯定,并借助对六百多年前刘基弃官隐居生活的呈现,映衬出诗人内心对人生的生活崇尚和精神追求。从语境的一致性上看,叙述“他者”之人,叙述的也正是他自己。这样的语境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但这不是关于时间和历史性的交汇,而是关于人精神性的交汇。这样的“神交”没有先在的差别,也没有人为划定的边界,“他者”与“我”超越时空,同体同心。《三角湖》反映出育邦谦谦君子的修养,《南田生活指南》暴露了育邦内在的精神谱系。
五、神性即神秘性
神性是宏大叙事的亘古话题,这是关乎生命终极归宿的问题,也是关乎死后灵魂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从古至今有了无数的解答,包括原始神话、哲学、诗歌、艺术、宗教和科学等等,但没有一种解答可以让人真正破除对神性的迷惑,神性不仅作为信仰,也作为神秘性问题影响并伴随着人类的每一步进程。诗人对神性的关注是必然的,这意味着他的写作离不开对神秘性的探究与触及。这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鲜明的信仰特征,比如对宗教或偶像的崇拜;另一个即艺术自身呈现的神秘性效果。这两点从育邦诗中都可以看到很深刻的印迹。
比如诗集《伐桐》中“七月之光”所辑作品,是育邦为数不多的深入探索生命秘密和宗教境界的长诗,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其中《七月之光》中诗人以自然的七月阳光炽烈,雨水丰沛,果实趋向成熟这一“成长季”为背景,从不同侧面歌赞了一个人自我提升的选择与努力,以及对风暴、酷暑和一切困难考验必不可少的经历,突出了对精神自我锤炼与升华的必要性。这首诗显示出了育邦深厚的艺术功力和饱满自足的精神涵养。
《薄伽梵说》则是育邦受启于佛初说法结成的《经集》,模仿古印度智慧之书《薄伽梵歌》的样式创作的长诗,体现了育邦对佛法的深刻领会与见地,具有神谕和灵性召唤的魅力。育邦写道:
当白雪覆盖我的全身
那个世俗世界里吃饭、上班、写作的我
在傍晚时分
就会毫无愧色地离开
我神圣地生活在家庭次宇宙中
努力处理好古老的欲望和物质的种种关系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感受到育邦那颗向往圣境之心的搏动,那是一颗不断把生命从世俗引向高广之境的心灵,这颗心作为内动力始终助推育邦成为一名星辰追慕者。
从语言中寻找可信赖之物:构建语言的亲缘关系或精神与信仰谱系,对自我进行甄别、纯化或丰富。这一切构成诗人生命的动力。但这个动力是反方向作用于现实的。现实作为压缩的空间逼迫人自我拓宽向度。现实给出的是压力和逼迫,是紧张的驱动和掣肘。它是机制的,目的的,竞争的和幻灭的。诗人向外或向内或向虚无投注感情,都表明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艺术并不能改变世界,艺术只能改变人们面对现实的态度。拒绝、抵抗、参与同谋或嘲讽都只是人在无奈现实面前做出的自我选择。艺术对待现实的有效性不能评估,因为没有固定的标准,它只能被想象和信仰,心诚的人会看到感动和奇迹,怀疑的人会看到虚幻,甚至欺骗。
今天,诗人对写作身份的确认不再是关乎乌托邦问题(莫尔贵族式的社会理想),也不再是反乌托邦的变相选择(福柯的异托邦),而是一种由个人完成的对人的证明(哈耶克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有,而不是集体主义)。我们今天也许才更透彻理解里尔克说“我独自担负人类的苦难”以及“有何成就可言?挺住意味一切”的用意。这不等于说诗人可以拒绝集体性存在,脱离组织和社会,成为纯自然人,而是要在集体中成为个人自由自证的人。这是对集体性的警觉和疏离,也是对人过度集体化、社会化(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种矫正。
育邦在我看来正是这样写作者的代表。他对生活和工作的选择都围绕最大化发挥写作个性而决定。比如,他的日常生活选择都是想最大化减少社会性或集体性对他生活的制约。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作为好朋友和写作上的同伴,他的思想、个性、情趣和才华都令我敬佩。2020年夏天我们在昆山有一次深入的交谈,精神向度的趋同更增添了我们友谊的厚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