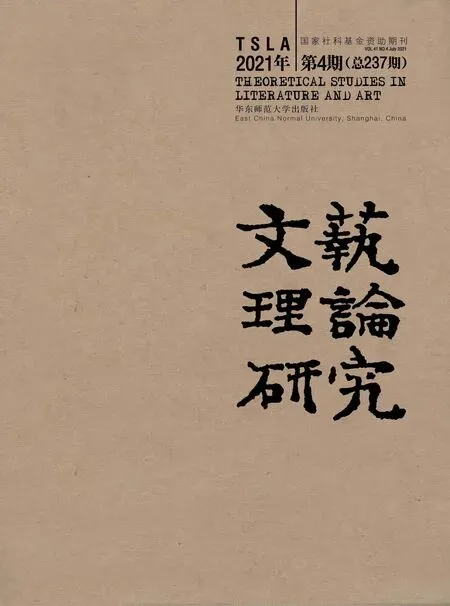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与生成文学
2021-11-11葛跃
葛 跃
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上明确指出,一些译者把斯宾诺莎以拉丁文写成的《伦理学》中的affectio
与affectus
作同样的译法,均译为affection,德勒兹认为这么做“是灾难性的”。斯宾诺莎“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原则上他总是基于一定的理据,[……]因此,我用‘情动’对应斯宾诺莎的affectus
,用‘情状’(affection
)对应affectio
”(德勒兹,《德勒兹》3)。德勒兹这里特地提出情动的翻译问题,目的在于把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术语呈现出来,从而绘制出一个情动的话语矩阵。这里不纠缠于德勒兹是不是正确理解了斯宾诺莎,更多关注情动理论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理解世界的切入点,为文学阐释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一、 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
不同于笛卡尔,斯宾诺莎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实体,而实体具有两个属性: 广延和思想。这两个属性“都是表现在无限数目的样态之中,广延属性表现于无限数目的具有特殊形态的个别物体里,思想属性表现于无限数目的特殊观念和意志情感活动中”(洪汉鼎194)。当西蒙·德·福里就自己理解的斯宾诺莎理论向他请教:“一当我们把思想同所有的观念分离开来,我们也就消灭了思想本身。”(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书信集》36)斯宾诺莎是这样回答的:“关键的问题我想我已经充分明白而且清楚地证明过: 理智虽然是无限的,然而是属于被自然产生的自然,而不属于产生自然的自然。”(41)斯宾诺莎委婉批评了福里没有理解自己的思想: 首先,观念是思想的样式,观念即思想,二者不可分离;其次,观念是思想的活动方式,或者说,思想的智性活动样式体现为观念,然而其逆命题却不一定成立,思想的样式不只有智性活动,还有其他样式。情动和观念都属于思想样式,德勒兹指出“情动预设了观念,[……]观念和情动是两种具有不同本性的思想样式,不可彼此还原,而仅仅是处于一种如此这般的关系之中——情动预设了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如何模糊”(《德勒兹》5)。
洪汉鼎认为,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据他推测,虽然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基于对笛卡尔相关理论的批判,但更受霍布斯的影响,因为斯宾诺莎使用了霍布斯“努力”这一术语,“努力”指的是“一切自然事物所具有一种保持自我存在的天然倾向或趋势”(洪汉鼎630)。“这种努力,当其单独与心灵相关联时,便叫作意志。当其与心灵及身体同时关联时,便称为冲动。[……]欲望可以界说为我们意识着的冲动。”(斯宾诺莎,《伦理学》107)具体到人,则人保持其存在的努力,如果停留在思想属性的样式,可以称之为意志;而如果不仅表现为思想属性的样态,也同时表现为广延属性的样态,则称之为冲动;如果这种冲动是在意识之内的主动行为,则称之为欲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欲望的对象不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好的”而被追求和寻求,“我们判定某种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107)。欲望体现的是生命的内在冲动,而非因为被外物吸引才去行动的被动行为。“正是通过欲望,斯宾诺莎找到了感觉的起源和基础。”(107)仅仅从上面的文字把握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很容易滑入心理学领域。塞格沃斯和格雷格认为,斯宾诺莎情动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是身体,“首先,身体的能力永远不会被单一的身体所界定[……]其次,‘认知身体’的‘未完成性’与当今的相关性要远远大于330年前斯宾诺莎写完他的《伦理学》之后的那个历史时期”(塞格沃斯、格雷格21)。情动和身体由此成了互为支撑的存在,情动理论的提出“是一种极具特殊性的努力,旨在配置一个身体和它的情动/被情动、它正在进行的对世界的情动构成,以及世界和身体的此性”(21)。在斯宾诺莎的视野里,情动是一种力,身体是这种力的暂时性显现和特定时刻的形式。身体即情动,情动在身体的互动与变换中流动。
不可否认的是,情动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概念中的位置是被边缘化的。斯宾诺莎依然沿着笛卡尔的哲学决心寻找知识确定性的方法,所以,他试图通过模仿几何学的论证方法构建哲学体例,从界说和公理入手,推导出各种定理和命题。他把感觉参与其中形成的知识称为意见和想象,认为不能给人真正的知识。“只有当观念来自理智的内部时,观念才是清晰而明确的,思想才能必然地理解它们之间的相异、相同和相反关系。[……]即推理知识和直觉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王雨辰、刘斌、吴亚平203)情感是被动的,如果人被情感左右,那么人也会被外在的力量左右。他坚持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神的必然本质,从而把握人和神的必然关系。认识得越充分,生命就越自由和圆满,快乐就越多,越接近至善。虽然斯宾诺莎在《伦理学》和其他著作中颇费笔墨谈论情动,但给予它的地位并不高。
稍稍回溯一下可知,比斯宾诺莎稍早的笛卡尔同样认为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比如梦境猜测(dream conjecture)和恶魔猜测(evil demon conjecture)。霍布斯认为感觉是外在物质和精神活动的中介,并没有给感觉重要的位置。斯宾诺莎在笛卡尔和霍布斯的影响下,把感觉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德勒兹把斯宾诺莎的情动一词拈出来着力阐释,此刻的情动已经不再是斯宾诺莎的情动,而是去背景化的情动概念,或者可称之为德勒兹的情动。
二、 德勒兹的情动理论
无论从当时的哲学传统,还是寻找确定知识的哲学冲动来看,斯宾诺莎没有重视情动理论顺理成章。德勒兹是在新的社会与知识背景下关注到情动理论的。无论是上帝之死后对人的重新定位,还是二战后对理性人信心的丧失,都位于“世界历史的转折处,这转折不仅关系到对世界的看法,还同样关系到人类存在本身的方式方法”(洛维特28)。德勒兹试图重振哲学,但不是传统哲学,而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创造概念的艺术”(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201)。德勒兹所指的哲学不再关乎真理,指向的是事件,即概念所关联的“时间、场合、感受、景物、人物、条件以及未知条件”。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不是指一个外在的人物,[……]而是指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得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活的范畴”(202)。换句话说,德勒兹哲学所创造的概念指向的是存在的事件: 具体时间、地点和诸条件下的存在状况,即此在。但这个此在的焦点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人,而是人于特定时刻进入具体关系网格中的状况。如果他不能摆脱个体或集体的人、经验或超验的人这种二分法,以及随之而来选择非此即彼的立场,那么德勒兹就依然走不出非左即右或者摇摆不定的传统哲学之路。他需要新的起点以及与之关联的新的支撑。对于人之存在而言,他放弃了讨论人的超验性,集中关注人的经验性存在。但这里的经验不是唯理论传统中作为理性幼稚期的经验,而是生命自身的体验,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中,杂多性的生命体验并存的生命感。所以,德勒兹注意到了被斯宾诺莎边缘化的情动概念。
对于德勒兹而言,六八事件的解释困难对他刺激很大。1968年5月,在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前提下,法国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即使到了今天,整个事件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淌而消逝,反而一再地被提及和诠释。保守派视之为一次社会性动荡和混乱,试图从青年的教育、福利社会等各条进路解释它,但无法取得统一且让人信服的结论。激进派视之为一次革命活动,但这次革命活动没有明确的纲领、组织领导和路线,或者说,这是一次众声喧哗的革命活动,是让以往的革命理论集体失语的运动。既没有统一的革命主体,也没有统一的革命对象和目的,人们各自反抗着自己认为应该对抗的东西。“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学生发动与领导,而非工人,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于治中15)于治中还处在寻找革命代言人的传统革命理论逻辑中,而德勒兹却悬置了这些革命理论的预设,从人的存在状况开始思考,或者说,思考应该使用什么概念绘制人的存在状况。
对于人的存在之认识,德勒兹在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基础上重新论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一方面是身体、物理实体、‘事态’——德勒兹所谓的实际性(the actual);而另一方面是一个非肉体的层面,包括这些事态所产生的非人格效应和潜能,即他所谓的虚拟性”。当肉体和非肉体层面的存在交织为一体,“它进入了一种生成,一种虚拟性的实际化。[……]处于纯粹形式中的生命——‘一种生命’——正是这个虚拟维度上的众多情动与感知,此外,个体化便是对实际时间内该维度之众要素的组织”(贝克曼103—104)。任何人都是肉体和非肉体维度的相互捕获,而且人总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刻,不存在纯粹的零状态。德勒兹认为,人的存在状况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世俗性的人或者社会人,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线条贯穿交叉和缠绕着人们,在各种场域中赋予人特定的位置以及权力和责任;一种是块茎式的人,这是和树状的层级结构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这样的人没有被固定的结构和秩序俘获,他们和毗邻者只有临时性的地理性的差异关系,没有主次从属和主客关系。这种判定方式的依据不源自外部,而是内部,即自我欲望和自我感觉的自治。这样的存在样式就是游牧民。社会人和游牧民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社会人是人进入具体社会场域时刻的“登记”状态,而游牧民则是内在欲望冲动下的自我法则状态。在登记状态下,你是父亲、母亲、职员、男人、美人等,以及与之对应的常识和固定权责。游牧民则自我立法,没有完全被社会的各种秩序与规则捕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理解的困顿和表述的障碍。无论是社会人,还是游牧民,都是此在的存在状态,德勒兹没有由此倒推出人应该具有一个原初状态,而是从此在入手,讨论人的存在潜能。此时,情动可以发挥作用,“感受(affect)不是从一种体验状态向另一种体验状态的过渡,而是人的一种非人类的渐变。[……]是一种极度的毗邻性,发生在两个不相似的感觉的彼此相拥之时,[……]能够明确表达这个东西的只能是感觉。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地带”(《什么是哲学》451—452)。德勒兹情动理论所指的“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地带”,暗示了人的流动性与生成的性质,人的存在处于流动和持续生成差异中,一部分被社会力量捕获,通过回溯形成存在的轨迹,但这个轨迹就像“飞矢不动”一样,是静态和间接性的,而非生命的全部;另一部分与前者不同却与之共振,它持续生成着,竭力让生命敞开,呈现出非固定主体和非统一主体的分裂性特征。
德勒兹视野中的人的形象已经不以认知主体的核心形象出现,而是在社会运行中作为要素被装配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社会性存在不是孤立的,是事件性和被动的,被各种法则定义和限制,虽然号称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作为社会人,“我们被给予一个自由选择,附带条件是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齐泽克,《暴力》140)。情动视角的确立,使“我们能够通过一种前个人知觉的形式来思考感受,[……]在我思考或进行概念化之前,存在着一个先于任何决定的反应的要素”。许多外在的力量作用于身体,通过视觉、听觉、光线、温度等,人们意识到某种存在但“不是将一个事物对象化和量化,[……]德勒兹因此诉诸强度”,对于德勒兹而言,“它有助于解释作为身体的我们是如何去回应和欲求各种形式(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即使这些是我们不感兴趣的形式”(科勒布鲁克46—49)。在人被社会这个强大的外在力量装配的过程中,德勒兹认为符号充当了权力输送的毛细血管,符号与意识形成了复杂连接,符号进入人的意识且进行非肉体转化后,在具体社会场域法则的支持下形成社会实践。所以,德勒兹从语用学入手探索瓦解权力的模式,这里用瓦解而非对抗一词,是因为对抗本身就是在强权之外再树立另一个强权,而瓦解则不包含再树权力的意图,瓦解的方式就是描绘除了人的理性图像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生命情动之力的存在。
三、 情动和生成文学
情动的关键之处在于显示生命的流动性,提出情动理论的意图在于冲破社会场域规则对人的捕获所形成的僵化、重复的生命图像,让它摇晃、破裂、敞开,生成新的、流动的生命图像。从情动视角审视文学,文学场域现存的所有法则都是突破的起点和对象,德勒兹则聚焦于两点: 一是人的流动维度,即如何让人的存在流动起来,生成全新的生命图像,形成游牧民形象;另一个是语言的表达维度,让语言流动起来,形成了语用学理论。德勒兹称这样的文学为生成文学,他一再强调生成就是生成弱势,是因为生成突破了现有规则的捕获,制造了解域和逃逸行为,却没有预设具体的目标,逃逸路线面向的是敞开的生死未卜之地。这里的弱势是与既有规则的强势之力相比较而言的较弱之力,是一种新的力量。由此可知,生成文学就是生成弱势文学,就是打破文学规则形成全新面貌的文学现象。
“一种承受情动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度或一种强度的阈限。[……]实际上正是想要以一种强度的方式来界定人的本质。”(《德勒兹》15)情动虽然是非表象性的,但是它无法脱离一定的形式,即使伴行着表象或者概念形式。伴行,是因为情动就在表象或概念形式旁边。从德勒兹举的皮埃尔和保罗的例子可知,情动作为一种流变伴行在皮埃尔和保罗的观念边上。“正是此种连续流变的旋律线将情动既界定为它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又同时界定为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7)德勒兹生成文学理论指向的就是情动的流动和流动过程中某个时刻的惊鸿一瞥。生成文学分析具体文本和现象,都是回溯性的,吊诡的是,生成文学中呈现出来的阅读障碍和理解困难,恰恰彰显了对既有文学规则的挑衅与突破,消解了回溯性分析与阐释造成的对流动性的静态描绘。
生成-动物是德勒兹生成文学理论中最典型、最具有可观性的部分。生成-动物不是人变成动物,而是人和动物的毗邻,人和动物的无限多重互动。德勒兹的生成-动物在文学中的应用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被动物所吸引从而生成一条逃逸线;另一类是人无限接近动物,或者已经在表达式中处于动物的位置。德勒兹尝试用“联盟(alliance)”“共生(symbiose)”“缠卷(involution)”进一步描述生成-动物活动,他在图腾崇拜中发现了更多的生成-动物,以此指明生成-动物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历史现象,甚至是一种日常现象。德勒兹以《白鲸》为例,文中熟悉亚哈船长的人都认为他是为了复仇才疯狂地追捕白鲸莫比·迪克,而其他人出海捕鲸是为了赚钱。这里出现了两种与鲸鱼的关系: 复仇与赚钱。无论复仇还是赚钱,都是对既有社会关系的重复。文中的莫比·迪克已经不简单地等同于其他鲸鱼,它是鲸鱼的另类,甚至不仅仅是鲸鱼,人们“宣称莫比-迪克不仅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是不朽的(因为不朽就刚好是无处不在的);认为尽管它身上插遍了簇簇的枪头,它还能无恙地游走了,或者万一它确会弄得浓血猛射,这种情景也不过是一种鬼蜮伎俩而已,因为再一会,它那洁白的喷水,又会在几百英里外的毫无血迹的波涛中再度出现”(麦尔维尔174)。在亚哈船长的带领下面对莫比·迪克时,捕鲸者使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可怕”和“金币”。对于亚哈船长而言,他“从来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觉,感觉,感觉”,他用他所有人类关于海洋和抹香鲸的知识去感受莫比·迪克,他在众人眼里就是个恶魔。莫比·迪克是鲸鱼中的异常者,“它是一种现象,但却是一种边缘现象,”位于鲸鱼和神性之物的中间地带,“这是一个边缘位置,它使得我们不再清楚异常者是仍然还在集群之中,还是已然外在于集群”(德勒兹、迦塔利,《千高原》345—346)。而亚哈船长似乎和莫比·迪克订立了无声的盟约,他的行动和感觉,都和他心里的莫比·迪克密切相关。亚哈与莫比·迪克的连接形成的张力场,制造了一个特定的情动景观。
这种人和动物的混杂感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鲜见。《变形记》中,萨姆沙真的变成了一只虫子,“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卡夫卡106)。但他依然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变为虫子的萨姆沙改变了家庭的格局,他不能赚钱、不能劳动甚至不能像人一样活动,即使他的妹妹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大家还是接受了他是个虫子的结果。无论萨姆沙怎么强调和声明自己是父母的儿子、妹妹的哥哥,在其他人眼中,他就是一只虫子。或者说,他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从人位移到虫子,所以他只配拥有虫子的待遇。生成-虫子不再像亚哈船长那样处于人和白鲸的深度纠结及摇摆中,社会身份并不以自我认识为依据,而是根据社会对个人的认定和定位。被认定为虫子后,无论你承不承认,社会都会自动给你匹配虫子享有的待遇。生成-甲虫的被动性情动和生成-鲸鱼的主动性情动告诉人们,生成-动物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关键在于形成一个感觉的聚块,一个有待进一步探明的存在,把人带离“正常”状态,呈现出全新的生命状态和形象。
如果说生成-动物现象挑战了人的封闭性和完整性的设定,那么生成-外语则是对语言秩序的挑战。德勒兹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陈述——就是口令。[……]语言不是用来被相信的,而是用来被服从和使服从的。[……]语言不是生活,它向生活发号施令;生活不进行言说,它倾听并理解。”(《千高原》100—102)就当下而言,语言先于人而存在,人们生活在语言中,对于未学会说话的人而言,所有的语言都是外语,一旦学会说话,就坠入象征秩序之网,拉康称这个象征秩序为大他者,“大他者的这些无意识的欲望与愿望经由语言而流进了我们的骨血”(霍默96)。社会中流动着看不到的规则和秩序,它们通过语言沉淀进入人体并塑造着人的意识与行动,“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现实永远需要服从某种超我的命令,需要某种‘就这样做!’”(齐泽克,《斜目而视》224)。德勒兹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许多语言的异常现象,“它恰在语言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这并非另一种语言,而不是重新发现的方言,而是语言的生成-他者(devenir-antre),[……]是逃离支配体系的魔线”(德勒兹,《批评与临床》10—11)。在文学语言的谵妄现象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复杂的杂语现象,“鲁塞尔构建了一种与法语同音异义的语言,布里塞构建了一种近义的语言,沃夫森则构建了一种与英语近音的语言”,目的是“摧毁母语”(20)。把现有语言高度分子化后进行重组实验,在支离破碎的表达中抽空了语言的意义基础,形成了表达的空壳。揉碎的语言中既没有自由间接引语的位置,也没有表述的主体,丧失了一切主体化的可能。“你越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实在的陈述,你在精神实在中就越是作为表述的主体而进行统治,因为,最终是你自己服从于自己,你所服从的正是你自己!”(《千高原》180)有人会忧虑这种对表达的肆意实验与破坏,会不会导致出现通篇的胡言乱语。对语言的破坏是基于这个事实: 人是被抛进语言的,也无法选择拒绝语言,对语言口令功能的挑战和破坏,就是在语言内部让语言结巴、短路或者杂交等等千奇百怪的实验,打破人们面对语言时的习以为常和麻木状态,让人们在语言实验中看到新的可能性。德勒兹的生成理论就是巧妙地以一切成型的存在为跳板竭力一跃,从而提醒置身于微观政治场域中的人,在被口令时刻规训的情况下,在语言的内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契机,让语言无法完成传输权力的功能,同时折射出权力的毛细血管运行的轨迹。
抄写员巴特比用“I would prefer not to”应对所有与他的沟通,无论别人说什么,他只会说: I would prefer not to。这个句子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别人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有趣的是,文章的结尾处看似无意地提及巴特比曾经的职业是邮局死信处理员,代表着沟通渴望的死信在他这里走到了尽头。他面对着一堆现成的语言,但没有一个的陈述对象是他,他也无法与之对话。交流的死局使他注定无法登陆到合法的表述位置,“这不是一种渴求虚无的意愿,而是意愿的虚无性的增长”(《批评与临床》146)。与此不同的是,卡夫卡正是通过双重主体的身份给父亲和女人们写信,而尽量避免面对面的交流,因为书信“保持着两个主体的对偶性: 此刻,可以区分出一个作为写信者的陈述主体,和作为一个书信内容形式里言说的表述主体。[……]两个主体的对偶性交换或反转,作为表述主体承担的工作一般情况下也是表述主体的权属范围,产生了主体的双重性”(Kafka
31)。主体的对偶性本来意味着一个主体的问题同时也是与之对应的另一个主体的问题,但在具体的表述中呈现了主体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德勒兹称之为“卡夫卡作品中的分身手法”(31)。在特定行为关系中的身份把看似整体的人分裂,就像在书信行为中的表述主体和陈述主体,离开特定的情境,那个退位的身份还能负责吗?或者说,作者能为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负责吗?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是什么关系?这种双重性仅仅是信件最直观的对偶性主体现象,如果把一个人复杂的身份铺陈开来,例如一个坏爸爸却是一个好职员。如果把一个坏爸爸和好职员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该如何评价?这里呈现了情动的线条,巴特比奇怪的表达既有生命的抑郁,也有通过表达消极抵抗的尝试,他内心需要这样的尝试,通过喃喃自语顽强地给自己争得一个位置,即使这个位置在别人眼里十分怪异。卡夫卡通过内容里的表述主体去完成陈述主体不敢做的事情。身份的多重性或者说分裂性给生命撕开了一个裂口,创造了逃逸的机会,逃离单一主体无法行动的困境。看似奇怪的表达不是生成文学追求的目的,对强势语言的污染和巧妙处理制造出新的视角从而引发全新的感受才是目的。有时是故意抛出去挑战特定社会场域人们的承受阈限,当用意第绪语大声朗诵的时候,朗诵者的快感和听众的反感或惊奇是共存的。德勒兹认为观念和情动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样式,情动预设了观念,且情动的转化与流变由观念所确定,但观念并不可还原为情动。情动和观念是不同的两种思想样式,就生命的肖像而言,观念的流变和情动的流变体现了两种生命样态,观念的流变是认知的转换,情动的流变是生命力的起伏。这样便可以解释《一条狗的研究》中那条狗为什么为了成为一条音乐狗而固执地昂着头,冒着不能进食而饿死的风险。它只有昂着头才能和音乐连接,从而成为一条音乐狗,它的生命情动是愉悦的。当船长摒弃了捕鲸者的利益追求,疯狂地追寻莫比·迪克的时候,他已经偏离了所有世俗观念和普通生活的逻辑轨道,进入了情动的生命力之增强和愉悦状态。虽然情动是不表象任何对象的思想样式,但这不表示它和任何表象无关,它预设了某个表象,一个尚未存在的表象或观念。《审判》和《城堡》的无限延宕,前者对审判结果的期盼,甚至让他不再考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后者的求职之路变得无限漫长,漫长到一眼看不到头。但二人都期盼着,期盼着一个自己并不能明确的、模糊的表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的生成文学和情动的一致性。生成文学首先体现了生命力的流变和起伏,在愉悦和悲苦之间。其次,情动是敞开的,面向未来的。人们无法根据既有的知识和经验,对这条和音乐连接的狗进行识别和归类,只好勉强在狗的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进行命名。而迟迟不来的审判,把约瑟夫·K卡在罪与非罪之间。
意识流小说就像情动的交响乐,最大限度上模糊了表述者和倾听者,在回忆的各种观念构筑的形象和轮廓中,情动起伏流转,复杂的是,以往觉得悲苦的事在回忆里反而有了某种快乐,而往日悲伤的事在回忆中反而有了些许甜蜜。甚至很多回忆模糊不清,只有残留的味觉或嗅觉痕迹,但相应的欢愉或悲伤依然随之起伏,流转无碍。情动和观念伴行却不重叠,它在理性思考的旁边直接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还原为观念或理性思考,所以德勒兹在斯宾诺莎研究中批判了“目的因之幻觉”“自由命令之幻觉”和“神学的幻觉”(《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23—24)。即使理性思考给你提供选择和“好”的行动方式,也无法遏制情动的波动: 快乐或痛苦。
德勒兹在论及生成文学时,一再强调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成型的典范供人模仿,生成文学的每个具体文本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预示着它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即不存在单一的或普遍的生成文学的方法和现象,现在不存在,以后也不存在。生成文学带给人们的遐想和希望在于,它挑战了几乎所有的既有立场和观念,它鼓励持续不断的遭遇和身体的连接,引入新的力量让现有的力场变得不稳定。它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是“这样一种事态可能需要努力解释,[……]我们会感觉到一种瞬间的(有时候是持久的)方法论或概念的自由落体”;另一方面,“照亮身体所作所为的‘未完成性’,在呼之欲出的未来图景中画出希望的一笔(虽然也是忧心忡忡的一笔)”(塞格沃斯格雷格22)。
结 语
人是被抛进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符号传输着口令、培养着思考和行动的习惯,“习惯正是那种构成我们身份的东西。在习惯里面,我们演出并定义我们实际上的社会存在。这种存在常常和我们的自我观感背道而驰。正是在习惯的透明度之中,它们是社会暴力的中介”(《暴力》145)。德勒兹把情动放在权力微观化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把人的存在问题化,提问的不再是“人是什么”,而是“身体能做什么”,即作为社会关系集合体的身体,它承受情动的能力,从而探究身体和心灵中间这个模糊地带。德勒兹在文学中发现了传输口令的通道被阻塞甚至截断的方法,发现了作为关系集合体的身体被配置、被驯服的种种情况,同时也发现了身体敞开的新方式,这样的文学他称之为生成文学。文学因此成了一种事业,一种挑战权力创造新的情动力量的通道。文学不再现什么,它应该始终追问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德勒兹的生成文学理论显示了情动视角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潜在功用,它迫使我们聚焦于文学的生成现象,揭示新的人类本体论是如何影响政治的。段似膺考察了詹姆逊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情动理论后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蕴含生命哲学思想的‘身体’及‘情动’确有可能成为撼动社会固化现象的能量。”(段似膺89)同时也应该看到,情动理论的未完成性和敞开性,预示着情动的力量并不是一种必然导致进步的力量,“这些看似饱含希望的时刻也完全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塞格沃斯、格雷格25)。
注释[Notes]
① 在贺麟的斯宾诺莎译文中,一般把affectio
和affectus
通译为感觉、情感或情绪。② 张祖建翻译的《什么是哲学》(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迦塔利合著)把affect译为感受,这里保持原译文,没有改为情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芙丽达·贝克曼: 《吉尔·德勒兹》,夏开伟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Beckman, Frieda.Gilles
Deleuze
. Trans. Xia Kaiwe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克莱尔·科勒布鲁克: 《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Colebrook, Claire.Gilles
Deleuze
. Trans. Liao Hongfei.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记录》,《生产 德勒兹与情动 第11辑》,姜宇辉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22。
[Deleuze, Gilles. “Deleuze’s Lecture Transcripts on Spinoza in Vanceneuve(1978-1981).”Producing
(11
):Deleuze
and
Affect.
Trans. Jiang Yuhui. Eds. Wang Min’an and Guo Xiaoya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16.3-22.]——: 《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 Trans. Liu Yunhong and Cao D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
[- - -.Spinoza
’s
Philosophy
of
Practice
. Trans. Feng Bingk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吉尔·德勒兹 菲利克斯·迦塔利: 《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
? Trans. Zhang Zujian.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7.]——: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 -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2
: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Jiang Yuhu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 Trans. Dana Pola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段似膺: 《“情感的消逝”与詹姆逊的“情动”观》,《中国图书评论》5(2018): 80—90。
[Duan, Siy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Affection’ and Fredric Jameson’s Conceptualization of ‘Affect’.”China
Book
Review
5(2018): 80-90.]肖恩·霍默: 《导读拉康》,李新雨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Homer, Sean.Jacques
Lacan
. Trans. Li Xinyu.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洪汉鼎: 《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
[Hong, Handing.A
Study
of
Spinozist
Philosophy
.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第1卷,洪天富、叶廷芳译。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Kafka, Franz.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z
Kafka
. Vol.1. Trans. Hong Tianfu and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卡尔·洛维特: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 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彭超译。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Löwith, Karl.Heidegger
—A
Thinker
in
the
Age
of
Poverty
:On
the
Position
of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 Peng Chao.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2015.]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曹庸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Melville, Herman.Moby
Dick
. Trans. Cao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格里高利·J·塞格沃斯 梅利莎·格雷格: 《情动理论导引》,李婷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 20—29。
[Seigworth, Gregory J. and Melissa Gregg. “An Introduction to Affect Theory.” Trans. Li Tingwen.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2019): 20-29.]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伦理学》,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Spinoza, Baruch de.Ethics
. Trans. He L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斯宾诺莎书信集》,洪汉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
[- - -.The
Letters
by
Baruch
Spinoza
. Trans. Hong Hand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王雨辰 刘斌 吴亚平: 《西方哲学的演进与理论问题》。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Wang, Yuchen, et al.The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Inquiri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 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03.]于治中: 《五月的吊诡(中文版序)》,《法国1968: 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1—22。
[Yu, Zhizhong. “The Paradox of May.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 Trans. Zhao 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11-22.]斯拉沃热·齐泽克: 《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季广茂译。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Žižek, Slavoj.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 Trans. Ji Guangmao.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暴力: 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张嘉荣译。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 -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 Trans. Tang Jian and Zhang Jiarong.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