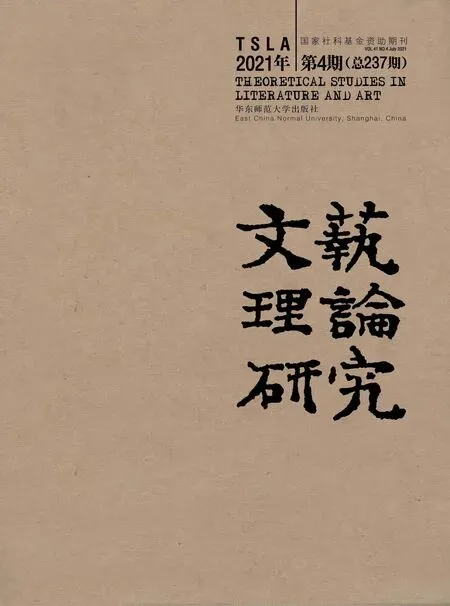崇高的性别维度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崇高论
2021-11-11陈榕
陈 榕
201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发表了《神魔知道》,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聚焦美国文学的专著,其副标题是“文学的伟大与美国的崇高”。布鲁姆在书中列出了符合他心目中崇高尺度的12位美国伟大作家: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麦尔维尔、瓦尔特·惠特曼、艾米丽·迪金森、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与哈特·克兰。其中只有一位女性: 诗人艾米丽·迪金森。他在2011年的《影响的剖析》中也讨论过崇高的文学传统,当时他的讨论重点是英美诗歌史,三位代表性作家分别是作为“文学的崇高的代表”的威廉·莎士比亚(Bloom,The
Anatomy
41)、“理性崇高浪漫主义者”的珀西·比希·雪莱(143)、“美国崇高”代言人的瓦尔特·惠特曼(9),均是男性作家。著作还提及了数十位诗人,男性作家占绝大多数,其中约翰·弥尔顿、威廉·华兹华斯、W.B.叶芝、T.S.艾略特、克莱恩·哈特等均有相当篇幅的论述,女诗人只有3人被提及,分别是艾米丽·迪金森、伊丽莎白·布朗宁和伊丽莎白·毕肖普,而且每个人都是浮光掠影地简笔带过。布鲁姆是一位在当代一直坚持高扬朗吉努斯所创立的崇高传统的批评家。公元1世纪,朗吉努斯写作《论崇高》,指出“真正崇高的文章自然能使我们扬举,襟怀磊落,慷慨激昂”(朗吉努斯82),所体现的是心灵的高度,“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84)随着这部手稿在近代被发现,以及法国评论家布瓦洛等人的译介,崇高不仅再度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词汇,也引发了启蒙思想家的关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和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分别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要扩充。埃德蒙·伯克将心理学维度引入崇高理论,指出崇高是恐怖引发的紧张焦灼和它的纾解带来的愉悦,是痛和快乐共存的情感: 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伯克36)。伊曼纽尔·康德则将崇高引入哲学领域,指出崇高感源于超出认知边界的审美对象造成的挑战,在崇高客体的激励下,想象力被延伸,借助理性的参与,对无法把握的形式进行有效的捕捉,是“自己超越自然之上的使命本身的固有的崇高性”(康德,《判断力批判》101)。朗吉努斯的崇高文体、伯克所言的痛与乐共存的审美体验,以及康德所强调的主体超越感,都是布鲁姆崇高论的理论基础。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追求崇高,是在“追求超越极限”(Bloom,The
Western
524)。在《影响的剖析》中,他指出崇高的作品会以美学意义上的“艰辛的喜悦”作为我们审美的回报(The
Anatomy
17)。在《神魔知道》中,他赞美崇高的价值在于“试图超越人的界限,同时又对人文主义有所坚守”(Bloom,The
Daemon
1)。显然,布鲁姆所继承的是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脉的崇高论,这也是经典崇高论的主调,人们早已习惯在这个框架之内讨论崇高的人性、超越性和审美体验。问题在于,这种崇高美学的核心词是“人性”“超越性”“美感”等具有普世意义的词语。然而,当布鲁姆用崇高性作为英美文学经典的鉴别尺度时,上榜的女作家为什么会如此凤毛麟角?我们是应该将这种稀缺归咎于女性作品没有超越性,无法体现崇高之美吗?有没有可能布鲁姆所秉持的崇高论存在某种隐形标准,不兼容女性的经验,所以女性作家才无法上榜呢?
这种疑惑也在提醒着我们,在把崇高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之前,有必要审视崇高本身的价值框架。崇高作为审美范畴,看似价值中立,具有普适性,然而,如果用性别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它,就会发现布鲁姆所继承的崇高传统,有着男性中心主义的政治无意识。这从崇高论的衍生同义词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在不同的语境下,“the sublime”可以被翻译为壮美、壮阔、雄浑、雄奇、阳刚之美……18世纪以来,崇高论衍生出诸多版本,但是这一基调始终存在。进入当代,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深入,相关的理论反思才逐步展开。
20世纪80年代末,陆续有学者对传统崇高论对女性写作以及女性艺术的美学偏见提出异议,尝试寻找、发现与定义女性崇高的特征。1989年,帕特丽莎·雅格尔发表了《朝向一种女性崇高》,该文章收录于论文集《性别与理论: 女性批评对话》,是较早的批评尝试。20世纪90年代,安妮·K·梅勒的《浪漫主义与性别》和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的《女性崇高: 女性小说中的性属与过度》两部代表性专著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随着《论蜘蛛、赛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与崇高》《女性解放与崇高: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环境》等著作的发表,学界对该论题的研讨一直在持续。女性主义与崇高论的相遇与论争,以及对彼此理论视域的补充,构成了当代诗学与美学理论领域颇为精彩的一页。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其关注少之又少,对崇高论的理解依旧沿用朗吉努斯—伯克—康德—布鲁姆一脉的经典框架,未有涉及性别政治角度的深入讨论。因此,本论文旨在呈现女性主义为崇高理论提供的新视野,辨析传统崇高论的父权权力-话语机制,探讨女性主义对崇高美学的重塑,理解基于女性经验的审美范式、主体立场以及伦理驱动是如何影响当代的概念演进,并使崇高理论更体现问题意识和时代关切的。
一
第三版的《劳特里奇美学指南》收录了美国美学家卡伦·汉森所撰写的独立词条“女性美学”。在词条中,汉森梳理了女性主义与美学的交织所带来的美学意义的扩展:“由于‘美学’可能意味着与艺术的创作、属性和接受相关的哲学分支,也可能是有关美与审美的理论,也可能是对感性知觉的研究”,所以女性主义美学可能涉及如下方面,即“通过批评实践搜寻与拯救被艺术史所排斥的女性;或者是对审美概念以及理论的男性偏见进行批评审视;或者是发展其他方案,对艺术的创作和效果进行‘以女性为中心’的描绘;或者是在感性认识的表述中加入性别的敏感度”(Hanson499)。女性主义与崇高理论的相遇也符合以上女性主义美学的总体潮流,隶属于“对审美概念以及理论的男性偏见进行批评审视”的做法(499)。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从时间上看,晚于艺术领域对女性艺术传统的探寻,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希林(Linda Nochlin)早在1971年就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文章;也晚于女性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倡导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比如桑德拉·M·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发表于1979年,伊莲娜·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出版于1982年。但是正因如此,对崇高论的检讨才在一开始就吸纳了女性主义成熟期的诸多思想,展现出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它不仅包含从理论角度的批评再审视,同时也关心对女性理论传统的再发现、对女性经验引入崇高论的新思考,以及对理论当代相关性的延伸讨论。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它首先聚焦了经典崇高论所隐藏的歧视性意识形态。这是女性主义为崇高论带来的重要视角: 反思经典崇高论的思维框架,从根本之处入手,拆解崇高美学的父权话语机制。
康德曾经说过:“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人讨厌的。”(《判断力批判》74)康德认为审美具有中立的共通感。女性主义却发现,在崇高审美的“普遍有效的规定”中,什么是“普遍有效”的标准,是由男权话语所界定的。“崇高”原来仅仅是美的杂多样式中的一种,它真正成为经典审美范畴,乃是通过与“优美”形成对比,使纷纭的美感被统摄于崇高与优美的两极,在与优美这个同属于广义之美的范畴的对比中,崇高找到了自己的参照系:“美学史上,崇高经常被看作与优美对立的范畴,对崇高的研究也常常是在与优美的比较中进行的,因此崇高的特征大多与优美相对立。”(彭峰72)这种对位关系依托具有结构主义经典意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在男权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迅速和性别政治的二元对立机制嵌合在一起。男性理论家们在定义崇高的同时,也书写着自身的性别属性。崇高区别于优美,一如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野。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崇高论的理论源头,即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来看一看他的理论是如何为其后的父权话语的介入提供契机的。
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中将崇高定义为一种修辞术,是语言能够激动人心、提升灵魂的力量。为了进行形象直观的说明,朗吉努斯将语言所激发的情感力量与我们面对壮美自然时的心理感受进行了类比,即崇高的文字对我们的灵魂冲击,类同于我们面对浩瀚江海、面对星汉灿烂或者岩浆喷涌的壮观场景时的心潮澎湃。当我们看到柔缓的潺潺溪流、燧石激发的微火,不会有激情,只能体会到温和的愉悦感(朗吉努斯114)。朗吉努斯的类比法为崇高概念的拓宽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文学与自然物的类比,使后来的理论家可以对崇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阐释。朗吉努斯关心文学文体以及政治修辞术的崇高特征,但艺术、自然、文化现象等更广泛的对象也可以引发同样的审美情感。第二,朗吉努斯将作为审美主体的“我”引入崇高性的讨论中,审美客体在“我”心中唤起的强烈情感是崇高审美的重要标识。第三,崇高在与之形成对位的优美中确立了它的审美范畴: 江河海洋在小溪的映衬下,格外波澜壮阔。小溪的清澈引发和谐之美,却无法唤起崇高的审美通感与愉悦共存的复杂体验,也缺乏恣肆丰沛的感情强度。
正因如此,17世纪后期,当埃德蒙·伯克以及伊曼纽尔·康德化用朗吉努斯的理论,探索拓展这一概念的文化与美学维度时,都借用了朗吉努斯笔下小溪与大海、燧石与星光的对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优美与崇高的概念对位。虽然伯克和康德对崇高论的关注各有侧重,即伯克强调情感与文化的重要性,康德关心理性与道德的意义,但当他们将朗吉努斯的自然类比进行性别政治的引申时,两者却不谋而合地从自然现象移向文化现象,把海洋与小溪的类比,变成了男性与女性的类比、力量与柔弱的类比。性别刻板印象的植入,帮助男性气质与崇高性挂钩,女性气质被界定为优美。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就是这种话语机制对女性经验的贬低和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
首先,在这种话语机制中,女性与男性的差异被放大了,进而形成优美与崇高的审美两极。男性与女性身高、体重、体力、皮肤等生理性差异被赋予了不同的审美属性,女性柔弱、温和、重情感等与文化塑形有关的特点也被进一步固化。朗吉努斯—伯克—康德一脉的崇高论的共性是对强力、高度以及庞大体积的推崇,男性的生理优势变成了他符合崇高审美标准的例证,继而又被用来印证他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成为男性从自然属性到精神力均优于女性的证据。
埃德蒙·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形容道:“崇高的事物在尺寸上是巨大的,而美的事物是娇小的;美的事物应该是平滑、光亮的,而崇高的事物则是粗糙不平的;[……]美不应当暧昧不明,而崇高则倾向于黑暗和晦涩;美应当柔和、精细,而崇高则坚固甚至厚重。”(伯克106)小溪—燧石—女性,她们同享娇小、平滑、光亮、柔和、精细的属性。海洋—星空—男性,他们共有巨大、粗糙、神秘深度、厚重的特点。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专设一节,标题是“论崇高和优美在两性相对关系上的区别”,也沿用了女性优美的性别属性设定。女性是和“我们男性有着显著的不同”,爱打扮,喜欢轻巧的东西,“比男性精致,也脆弱”(37)。就像劳拉·朗格在《英国文学批评的性别与语言》中所注意到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杂糅,最终是要为文化定义服务的:“优美代表着光滑、柔弱、微小、和谐,是新古典主义艺术想要表达的温柔的情感和特质,体现着18世纪对女性气质的要求。”(Runge174)
其次,在经典崇高论的话语机制中,女性的力量得不到承认,被贴上优美的标签,以满足男性对欲望客体的掌控感。力量与超越性是男性气质的专利,与女性气质的分野一起被建构成社会常识,“脆弱”“娇柔”“精致”……伯克和康德用这些词汇界定女性特质,它们蕴含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承担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逼迫女性主动内化这种看似“优美”实则柔弱化的设定。
康德认为女性的脆弱性导致了精神力的不足。“每种具有英勇性质的激情(也就是激发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攻坚克难的激情),在审美上都是崇高的。例如愤怒,甚至绝望。”(Kant113)女性“多愁善感”又“慵懒”,缺乏崇高性,连负面情绪也不配拥有。伯克说:“我们臣服于我们所敬慕的,却都喜爱那臣服于我们的,在前一种的情况下,我们是被控制的,而在后者我们则满意于其温顺。”(伯克96)男性敬慕崇高的自然,喜爱温婉可人的女子,这种喜爱难掩轻视。所以,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将女人与宠物归于同类。在“娇嫩”一节中,和优美女性作类比的是小灰狗、塘鹅、阿拉伯小马等。男性的隐喻动物则是獒犬与战马。在“平滑之美”一节中,伯克写道:“漂亮的鸟类和兽类,身上那平滑的皮毛;美丽女人身上,那光洁的皮肤。”(97)在“渐进的变化”一节中,他赞叹鸽子作为鸟类的完美线条,继而赞美女性的身体也同样顺滑:“请来一位最美丽的女人,细细观看她的脖子和乳房: 平滑,柔软,线条流畅。”(伯克98)
伯克的三个例子,尤其是最后两个,有着男性中心主义欲望驱动的赤裸目光。劳拉·普威在《十八世纪的审美与政治经济: 性属在知识的社会构成中的地位》中提醒我们,伯克的美学审视受到了18世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支撑。男性在婚姻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是审美主体:“女性是‘性’;男性是文化,是女性的甄别者。[……]将女性与身体相捆绑的歧视都是这样一个系统所造成的效果。”(Poovey96)
第三,在经典崇高审美的话语机制中,女性经验得不到认可,男性主体性成为现代性主体性的唯一模板。康德是启蒙时期最关注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生成问题的哲学家。但是,他对女性的主体能动性保持怀疑。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中,他宣称如果女性擅长希腊文,也会思考物理学中的力学,那可是了不起的成就,“简直就可以因此而长出胡须来了”(Kant37)。这种论调被剑桥英文版《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编者帕特里克·弗雷尔森和保罗·盖伊批评为“带有厌女症的倾向”(xxix)。但是康德的刻薄话不只是为了浇灭女性追求知识的热情,他是在质疑女性是否具有学习知识所需要的理性。理性匮乏,又如何能驾驭审慎的道德反思?照此逻辑,学不好希腊文和力学的女性,是连道德自律都成问题的。然而,女性的日常经验在反驳着他的论述: 在生活中,女性往往更善良,也更有同情心。可是康德认为这只能说明女性有好心肠,不能指望“这个优雅的性别能够有道德原则”(39)。
康德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西方世界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让位于世俗世界,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这使天赋人权观逐步成为社会共识。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也在激励着身处其中的女性的启蒙与觉醒。康妮利娅·克林格注意到康德在此历史时刻高扬崇高论,“这不是一个历史偶发事件。它恰恰发生在性别关系产生变化的时代”(Klinger194)。康德用区别两性关系的优美与崇高的二分法,将审美与文化和性别与父权制机制融合在一起,以普适性的审美合法化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在体力上柔弱于男性,在精神意志方面也缺乏能动性。她只有自发的道德情感,没有理性的协助,无法实现对庸常生活的超越。男性相比而言缺乏天生的道德情感,但他更具理性,有冷静的判断力,能够恪守道德律令。他有坚韧的勇气,能够征服自然,为自然立法;也能够借助理性、想象力和实践的多重力量,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因此,他是崇高的,这种崇高体现了“人类自由以及理性的成就。[……]将人与自然相区别,让他独立于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Klinger196),也凌驾于“自然属性”的女性之上。新诞生的现代性主体便是以这样的崇高男性主体性为范式。它成为“在自然影响面前坚持我们的独立性的一种强力[……]绝对的伟大只建立在他(主体)自己的使命中”(《判断力批判》109)。男性得到了理性与力量的完满承诺。女性无法谈及主体,又何谈能动性,故而她们拿不到超越性崇高的资格认证。
二
在辨析伯克以及康德所奠基的经典崇高论的性别压迫机制之后,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将思考的视角转回了自身: 自18世纪崇高概念进入西方美学领域,成为核心范畴以来,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崇高论默认男性主体性立场,反映男性经验,推崇男性气质。女性作家是否曾经尝试争夺审美场域的话语权,对男性理论家的女性歧视进行抗辩呢?她们是否感受到崇高论的评估体系的压力,曾经有意识地思考过应对策略呢?
当代学界对女性主义发展史的全面梳理,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位18世纪英国女性思想家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她曾经以英国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的妻子、小说家玛丽·雪莱的母亲、诗人波西·雪莱的岳母、政治理论家托马斯·佩恩的朋友而闻名。在建构女性主义理论谱系时,她被溯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思想家。20世纪后期,在深入研究她的理论贡献时,人们才意识到她同时是一位美学理论家,作为埃德蒙·伯克和伊曼纽尔·康德的同代人,她曾经参与过有关崇高论的论争,并从女性的角度,对以伯克为代表的男性崇高理论家提出了挑战。
沃斯通克拉夫特对崇高论的兴趣源于她的政治诉求。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激进革命抱有友好的态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0年11月,埃德蒙·伯克出版《反思法国大革命》,表明自己支持既有制度的保守主义立场。一个月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人权一辩》,作为阅读伯克一书的回应:“(伯克)的复杂论证唤起了我的愤怒,时时让我坐立不安。按照自然情感和普遍常识来看,(伯克的观点)有很多问题。”(Wollstonecraft3)《为人权一辩》的行文形式是致伯克的一封信,实则是尖锐的批评檄文。伯克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交锋在于如何理解法国革命,再往深处看,是在于如何理解人权、人性和道德。伯克承认革命存在合理主张,但是他对人性善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社会的积弊在于人性之恶。激进革命无法成功,是因为它无法改造人性,革命暴力却有巨大的破坏性:“唯见断头台。”(Burke66)为此,他提出良好的社会秩序依靠社会成规的约束性力量,这种约束之力就是道德。沃斯通克拉夫特则认为人是有内在的道德感和理性的,所以人性向善。她认为社会之恶,恶在制度,既有的君主制维护贵族权益,漠视平民利益,这是对天赋人权的违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理念主张理性与平等,反对压迫与剥削。在《为人权一辩》中,她期待法国大革命能够推翻贵族统治,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共和国。
基于同样的天赋人权以及人人平等的立场,她反对伯克等男性理论家的审美体系对女性的贬低和排斥,并在《为人权一辩》中加入了自己捍卫女性审美权利的辩护,批驳了伯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的性别偏见。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反对伯克所提出的崇高和优美的审美范畴二分法,但是她反对伯克将女性摒弃在崇高审美之外。她发现伯克将男性形容成强者,因其有勇气、有力量,所以崇高;而将女性刻画成弱者,使得柔与美成为同义词,女性只能顺从男性对她的定义,乖乖待在优美的审美领域。
为了驳斥伯克的崇高审美排斥女性的荒谬性,她决定以伯克之矛,攻伯克之盾。在《为人权一辩》中,她采用了“翻转战略”(Wollstonecraft14),强调自己品格中的沉着冷静与严肃真诚。她笔下的伯克虚荣、胆怯、琐碎,喜欢大惊小怪,行为方式恰恰如伯克所鄙薄的女性。伯克惧怕革命、墨守成规,何来崇高的勇气可言?他表现出的不正是所谓“女性化的软弱”吗?沃斯通克拉夫特将自己塑造成伯克的对立面: 她拥抱变革的力量,不畏惧新生事物,用理智指导行动,富有道德感,比伯克更符合崇高的标准。
沃斯通克拉夫特捍卫女性在崇高审美中的基本权利。为此,她把审美上升到神的赐予的高度:“沃斯通克拉夫特相信个人良知,将对神的敬畏融入她的崇高观。”(Bromwich634)她提出崇高来自理性和道德的双重加持,它不是男性的专利,而是上帝惠赐给每一个人的力量。在《为人权一辩》中,她写道:“我畏惧崇高的(神的)权力,它创造我的动机一定是智慧的以及良善的。我依赖于他,所以我严格遵守自己的理性总结出的道德法律。[……]对上帝的畏惧让我尊重我自己,是的,先生,我看重诚实的名声,与有德之人的友谊,但是它们都远远不及我对我自己的尊重,这是一种启蒙的自爱。”(33)沃斯通克拉夫特视上帝为崇高的最高形式,看似持有一种反启蒙的立场,事实上,她的崇高观从敬神入手,实现的是对自我的肯定。“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Mallinick9),女性和男性在神的面前一样平等,一样有理性,有资格进入崇高的审美领域。
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为人权一辩》时,没有提及康德。但是她认为崇高审美与理性有关,这一点和康德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康德认为女性没有理性,无法实现崇高,对此沃斯通克拉夫特绝不会同意。如果沃斯通克拉夫特读过康德的《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看到会希腊语的女性是要“长出胡须来”的论述,应该会和康德展开一辩。她很可能还会和康德展开另外一场辩论,原因是他们在如何认识女性情感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康德认为女性的道德情感是自然之力,比理性劣等。沃斯通克拉夫特则认为女性之美包含情感之美。她不反对伯克为女性贴上优美的标签。优美审美中的情感力量可以促进美德,令人向善,只有过度的柔弱和多愁善感不值得鼓励。她的审美观突破了伯克以及康德的崇高/优美所划定的性别禁区。理性与情感、崇高与优美,都集合在女性身上,她们有着和男性同样的精神世界。所以克里斯汀·斯科尔尼克指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致力于“让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属脱钩”(Skolnik208)。珍妮特·托德认为这种性别观念反映出沃斯通克拉夫特具有“双性同体”的思想(Wollstonecraft14)。
然而,无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多么超前于她的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 她的讨论始终停留在男性理论家框定的概念领域之内。她反对同时代男性理论家的性别偏见,肯定女性的力量,但是只要不修订崇高性的标准,崇高论对女性经验的漠视和压制就始终存在。崇高论歌颂强力,女性的生存现实是她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崇高论歌颂自由,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却一直被束缚在家庭的方寸之地,被鼓励要做“家中天使”。在文学领域,女性作家的创作被批评为格局太窄,话题缺乏崇高性。连女性写作本身都要遭受非议,在男性眼中,她们是一群“涂鸦女人”。以沃斯通克拉夫特本人的经历来看,她试图与同时代的男性思想家比肩,积极参与崇高理论的辨析与论争,自觉运用崇高修辞进行文学实践,然而,她在美学史上长期被忽略,影响力无法与同时代的伯克以及康德相比。她有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从男性手中夺取话语权的理论自觉,但其主张中不乏对男性话语的依赖,这说明了女性寻找独立美学价值体系的艰难。
三
有没有可能让崇高审美表达女性经验,对崇高论进行重新定义?有没有可能建立女性崇高的评估体系,用新的审美标准来重新解读女性书写传统?这是近三十年来女性主义批评家们的努力方向。伊莲娜·肖瓦尔特在梳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时,将这一传统命名为“她们自己的文学”。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者对崇高论的修正,则可以理解为对“她们自己的崇高”的探索。
崇高审美此前一直默认男性主体为理想审美主体。1989年,帕特丽莎·雅格尔撰写《朝向一种女性崇高》,率先对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她指出男性崇高是“唯我独尊的帝国主义”模式(Yaeger192),主张征服他者,是一种互不相容的垂直思维。女性崇高则是水平式的,更有包容性,“向他者延伸,将自己延展向复数性的存在”(191),保留自我的边界,同时拥有探索主体间性的乐趣。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释这种差异性的成因: 传统崇高建立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上,充满自我与他者的对抗;女性崇高是前俄狄浦斯式的狂喜,是对他者的向往(209)。雅格尔的文章篇幅有限,对女性文学诗学特征的分析不够充分,但是它开启了对女性崇高的理论探索。
如果在崇高论中加入女性的经验与立场,用它重新思考文学史传统,是不是可以发现被此前的崇高论所遮蔽的女性崇高的文学史风景?1993年,安妮·K·梅勒出版了专著《性别与浪漫主义》,就是要回应女性崇高文学传统的问题。她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崇高论影响力最大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她认为浪漫主义研究不应该局限在享誉最多的诗歌领域,只关注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等男性诗人。能够展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复杂性的综合考量应该把1780—1830年的文学通盘纳入研究视野。如此一来,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得以浮出地平线,也凸显出男性浪漫主义和女性浪漫主义的差异: 它们在“主题关注、形式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定位等领域”都有所不同(Mellor2)。男性浪漫主义的成就集中在诗歌领域,作品反映了现代性主体在巨变时代的多样化体验。崇高审美源于男性对主体性的坚决捍卫,大写的人站在宇宙中心,是意义的赋予者。面对壮美自然,华兹华斯式的孤独者体会到灵魂升腾,外界回应着对自我的肯定;自我包容了整个世界。柯勒律治式的想象者将自我看作一种空无,空无的灵魂与神性之间搭建起永恒的关联,消融了他者的特异性,将它收纳入神性的大我之中。两种立场的地基都是“想象力、视野性以及超验性”的男性化视角(1)。女性浪漫主义所青睐的文类是小说创作。男性浪漫主义的崇高英雄进入女作家们的笔下世界,变成了哥特小说中的父权制暴君。他们为世界立法的狂妄、为所欲为的自大、不受控制的力量,是邪恶的源泉。
该如何铸造有别于男性崇高传统的女性崇高?梅勒发现女性浪漫主义的选择是承认崇高客体的异质性特征,以女性经验对它进行接纳。所以“在女性浪漫主义传统中,崇高与优美结合,产生的不是几位男性浪漫主义诗人寻求的孤独的幻象性的超验体验,而是把不同的两个人连在一起的共通感”(Mellor103)。女性亲近崇高自然,在自然的启发下,人与人缔结纽带,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梅勒称这种女性崇高是“家庭化的崇高”(103)。
显然,梅勒想让女性崇高反映浪漫主义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让女性所珍重的家庭价值、情感价值为崇高审美添加新维度。然而,当她使用“家庭化”(domesticated)这个词汇时,不知道是否考虑到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即“驯化”。将崇高性引入家庭生活,是在驯化它,让它变得可控。经过软化的崇高是否会丧失它应有的力量?这和男性想要通过优美审美控制女性的力量,让她们安居家庭空间的策略有什么不同?经由驯化调和过的崇高还是崇高吗?抑或是它已经滑向了“优美”的范畴?
其实,这些问题可以简化成一个问题: 男性崇高强调“力的崇高”,女性崇高是不是需要用力量的弱化来体现其与男性崇高的差异?女性批评家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在《女性崇高: 女性小说中的性属与过度》中给出了坚决的否定回答:“反对将崇高进行驯化。”(Freeman3)弗里曼认为康德式的崇高隐藏着怯懦的内核: 惧怕挑战,所以强化主体建构,以压制差异;畏惧崇高客体的力量,所以对他者实行征服和控制;畏惧越界,所以强调安全的距离。经典崇高主体对客体保持警惕,以防止引发狂喜、越界、入迷,而狂喜、越界、入迷其实也是深具崇高性的审美体验。
女性崇高所珍视的正是这种被男性崇高论视为危险的崇高力量。它是偏离了标准的力量,是对男性崇高论的基本逻辑的颠覆,即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对身份认同的僵化建构,主张与绝对的异质性的相遇。这种无法被语言与文化的象征秩序所收编和压制的绝对的异质性,是无法被身份政治所锚定的存在,挑战着父权制表征体系的极限。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托尼·莫里森《宠儿》中的幽灵“宠儿”,他们身上就闪现着这种异质性。释放异质性,拆除藩篱,让生命力流动起来: 因此女性崇高追求边界美学,关注“边界的建构与破坏(这些边界可能是美学性的、政治性的或者是心理性的)”;持有流变的身份观,关心文学文本如何表达“身份的建构与解体”;承认表征的有限性,努力探索它的边界,让文本敞开,听语言言说其不可言说之意(Freeman6),从而带来阐释的多重性和意义的漫溢。
在弗里曼看来,凯特·肖邦的《觉醒》就是这样一部体现女性崇高性的文本。小说结尾,艾德娜·蓬特利尔夫人在大海中溺亡。这是一场事故,还是有意为之的自杀?如果是自杀,那么艾德娜是在海中游泳,感到脱力后,一刹那对生命的倦怠感涌上心头,所以放弃了求生,还是早有此意,顺势而为?对于这些问题,文本只提供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线索,而没有清晰的解释。在艾德娜溺亡后,再追溯她的生前,艾德娜在渴望着什么、在欲求着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只能靠文本的蛛丝马迹去揣测。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异质性的含混,这含混源于婚姻、母亲的身份、友情、身体的欲望、经济独立的愿望等众多力量对她的拉扯。但是,她也有一种异质性的决然。那是一种破釜沉舟、不甘为父权制所钳制的能动性,是一股不肯安于现状、拒绝被驯化的力量。凯特·肖邦的女性崇高式的写作,也很好地展现了这种含混与决绝交织的复杂性,开放的结尾更使文本的意义总在延宕,不肯终结。类似的作品还有伊迪斯·华顿的《欢乐之家》、简·里斯的《早安,午夜》等。
总结这一时期女性崇高论的不同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共性: 反对父权体制和男性主体观,质疑二元对立思维的合法性,肯定女性经验的意义,提倡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将跨越边界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作为女性崇高论的力量源泉。这也是为什么批评家们在讨论女性崇高时,避免过激论断,不愿将男性排除在女性崇高之外的原因。安妮·K·梅勒认为在浪漫主义诗人中,约翰·济慈的写作就有女性浪漫主义的特征。芭芭拉·克莱尔·弗里曼指出她的著作之所以不谈论男作家,不是因为女性崇高是男性的禁地,而是因为她要集中精力讨论女性的社会困境(Freeman6)。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属不是女性崇高的先决条件,女性崇高“不愿意将崇高直接等同于女性化”(5)。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策略会违反女性主义介入崇高论的初衷。因此,当她们提倡“女性”崇高时,“女性”一词不定义性别本质,而只是一种斗争工具和书写策略,用以与崇高诗学传统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相区别。
四
女性主义对崇高论的再审视始于20世纪80年末,在21世纪之前的十年时间里,“女性与崇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诗学与艺术美学领域。随着21世纪的到来,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化批评学者也展现出了对这个议题的浓厚兴趣,他们从政治美学、性别差异、伦理立场等多种角度,对已经被融合进当代社会文化肌理的崇高审美进行深入分析。
崇高论研究的女性主义视域拓展在出版于2001年的《论蜘蛛、赛博格和神圣存在: 女性与崇高》中已现端倪。在这部著作中,乔安娜·赛琳斯卡像梅勒、弗里曼等学者一样关心女性主义崇高诗学。她将它推进一步,探索崇高风格的女性表达,进而发现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以及海伦娜·西苏等倡导的“女性书写”符合女性崇高书写的特征,具有开放性、异质性、流变性。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写道:“我们如狂风骤雨;我们的自身若有部分脱离,也不会让我们畏惧虚弱[……]。笑声从我们的所有的口中溢出;我们的血流淌,我们延伸着自己,永无尽头。”(Cixous349)这是典型的女性崇高文本,表达着女性的经验与存在: 复数的“我们”中有一个个“我”,也包含着可脱离自身的“非我”的异质性,身体与精神、有限与无限同在。这里的言说方式也是流动的,意象化的文字带来诗情和复义性。
然而,赛琳斯卡研究崇高诗学,不是为了用它指导文学批评实践,而是因为她发现崇高诗学内嵌政治-伦理立场(Zylinska69),诗学同时也是伦理学以及政治学。赛琳斯卡指出,女性崇高是“新旧交织的话语”(38),“旧”是传统之旧,它建立在对传统崇高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新”是立场之新,借鉴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后现代理论,也吸纳了当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所以,女性崇高论将传统崇高论的“有所畏惧”——即崇高感来自对死亡、虚无、自我的解体等恐怖的规避或征服——改造成了“无所畏惧”——即女性崇高“放弃了伯克式的安全距离以及康德式的安全位置”(34),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恐惧,接纳愉悦与痛苦的混杂,不畏惧生与死的可通约性,认可自我的流动性。由此,一个新的政治-伦理向度在女性崇高的维度上敞开: 经典崇高论将陌生的他者的异质性视为危险与威胁。女性崇高诗学中的“我”,自身就有异质性,面对他者不会因恐惧而退却,能够承担起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倡导的“对于他者的绝对的伦理责任”(Hand56),这也是一种政治立场。
如果说赛琳斯卡的著作预示着崇高诗学研究介入伦理以及政治议题的野心,那么在“9·11事件”后,审美与政治深度地交织在一起,凸显出女性主义崇高研究介入当下现实的必要性。2001年9月11日,塔利班恐怖主义极端分子驾飞机冲向美国资本主义文明标志物的双子塔,造成数千人的死亡。“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框架。”(齐泽克6)9·11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事件”,它是重大的历史拐点,西方世界的自我认知与想象自此改变,西方世界突然感知到了恐怖和危险,陷入了妄想症式的焦虑,每一张陌生的中东人面孔都暗示着一名潜在的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崇高美学强势回归。美国及其盟友随后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 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海湾战争。战争动员、媒体宣传、部队部署、战斗场面展示,都伴随着对崇高美学的征调。因此,2006—2007年,两部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崇高美学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它们都探讨了恐怖暴力与崇高美学的深层关系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看《崇高、恐怖以及人类差异》一书。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作者是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克莉丝汀·巴特斯比。巴特斯比在序言中指出:“现代政治恐怖的表征无一例外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方式和崇高的概念相关联。”(Battersby3)在“9·11事件”后,有音乐家宣称他从飞机撞击双子塔的壮观场面中获得了创作交响乐章的灵感。他的言论招致了舆论的大力谴责。但是,“9·11事件”后,人们反复观看电视台播放的恐袭场景回放;阿富汗战争以及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常常能登上CNN等美国电视台的头条——这些暴力场景带动出的审美快感,符合伯克与康德的崇高定义: 我们体会到危险与威胁的迫近,又隔着安全的距离,可以进行审美观想。而最终将实现某种征服与超越。如果音乐家不应该对“9·11事件”进行审美解读,观看美军作战的电视观众的审美体验是否也应该受到质疑?是否要首先问责媒体为何在煽动崇高的视觉欲望?是否需要反思为什么当今社会有这么多暴力场景可供观看?此时,让我们再回到崇高审美的讨论中——崇高审美与暴力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是巴特斯比想要回答的问题。为了寻找答案,她决定回到18世纪崇高美学经典化的源头进行考察。她发现崇高美学自启蒙时代起就携带了暴力基因,它感应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主张在混乱与恐怖之上建立超验的秩序,必要时可以动用强力。它歌颂人类勇气,而勇气是彰显男性气概的重要品质,其激情源自“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攻坚克难”,所以勇气允许展示力量,允许为了抵抗恐怖而诉诸武力。在此前提下,康德这位“永久和评论”的支持者承认战争这架暴力机器可能引发审美感:“如果战争能够按照秩序和对平民的权利的尊重而展开,是具有一定的崇高性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433)按照这个逻辑来判断,9·11的恐怖袭击不符合崇高美学。但是,以消灭恐怖分子为名义的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能进入审美领域。西方军队装备精良,来到蒙昧的东方土地,如同天神般将愤怒降给蝼蚁般的敌人,这是具有崇高性的。
问题在于,在这种崇高论中,被施以暴力压制的生命是被客体化了的抽象生命,他们无面目,无个性,只能以一种可怖的异质性集体身份存在着。他们是西方人眼中长得都挺像的穆斯林人。崇高论的主客体分离切断了道德共情的纽带,也阻断了伦理责任的承担,使审美愉悦没有了负担。它推崇力量,启动征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了暴力和冲突。为此,巴特斯比认为崇高论的传统中埋藏着今日世界冲突的影子:“不宽容、全球争议以及价值冲突,当今世界的这些纷争都有审美的参与。”(Battersby206)崇高审美不是社会暴力泛滥的根源,但是,它在渲染着恐怖,对差异化的生命进行着压制,激发出暴力,甚至会造成它的升级。
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女性解放与崇高: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环境》一书中,邦尼·曼同样在讨论后“9·11事件”的政治美学,她关心的是国家和媒体如何共同征用了崇高审美。“9·11事件”后,美国“用暴力和权力的奇观化”来包装主权国家形象,以期震慑敌人,让他们感到敬畏,“重新向我们俯首称臣”(Mann, Women’s Liberation176)。媒体则迷恋力量的展示和视觉的奇观化,渲染毁灭与恐怖的崇高。观众的感官被一幕幕崇高场面震撼到麻木,无暇思考,无暇质疑。
为此,邦尼·曼认为应该抛弃男性崇高模式,从女性崇高论中寻找新的政治美学方案。弗里曼在《女性崇高》中将女性崇高比喻为交界地带,自我和他者在边界相遇,接纳杂糅,有脆弱的易感性。这种易感的脆弱和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生命观有吻合之处。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 哀悼与暴力的力量》中指出,人们生活在人世间,相互依赖,同时也容易受到彼此的伤害:“我们都如此脆弱,易受他人伤害的弱点是我们有朽之躯的组成部分[……]。认识这一弱点有助于人们以此为基础探索非暴力政治解决方案,而沉湎于制度化的统治妄想及否认这一弱点则会招致兵戎相见。”(Butler28-29)所以邦尼·曼将承认脆弱性的女性崇高视为男性暴力崇高的解毒剂。在女性崇高中,勇气不是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而是承认肉身易朽,爱惜生命珍贵,坚韧地承受精神以及肉体的痛苦,不逃避绝对的伦理责任。“崇高要求我们面对那些我们严重伤害过的他者(以及那些可能伤害过我们的他者),承认我们休戚与共,至少我们同在一个地球共居一方空间。”(Women
’s
Liberation
177)正因为缺乏反思,这种生命伦理一直无法建立,相反,崇高论的男性模式却一直在被强化。所以,2014年,邦尼·曼专门撰写了《主权男性气概》这部著作,来解释作为国家主权集体形象而存在的“自我”是如何与这种崇高美学相重叠的“主权男性气概”一起为美国的国家形象建构服务的(174)。这种建构的本意是用优势性的实力和英勇无畏的气势对抗恐怖,驱逐恐惧,但造成的后果是崇高审美堕落为无底线的暴力宣泄。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如何理解这两组关系,是区分男性崇高与女性崇高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男性崇高审美中,自我/他者、主体/客体,它们形成二元对立,分列清晰的界墙两端,这座界墙依靠强力维持,其力量体现在秩序的建立中。在女性崇高审美中,自我-他者、主体-客体,它们是共生关系,身份可以流动转换,其力量体现在包容、越界与宽恕中。2017年,厄林·斯皮思在《性别与主体间性: 福克纳、福斯特、劳伦斯以及沃尔芙的崇高》中重回文学领域讨论崇高诗学,对这两组关系的可能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当主体不再将他者视为客体,不再借助他者来进行自我认定、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怀疑,会发生什么?”(Speese11-12)通过对威廉·福克纳、E.M.福斯特、D.H.劳伦斯以及弗吉尼亚·沃尔芙的作品进行分析,她发现随着主客体模式的放弃,“一种互惠的、共情的、主体间性的崇高就会在两个主体的互动之中涌现”(4)。在《到灯塔去》中,丽莉·布里斯库想为拉姆齐夫人画像,却不愿意也没办法用艺术家客体化艺术品的方式来捕捉她的复杂性。十年后,拉姆齐夫人去世,丽莉感悟到夫人的关怀依然感召着她,通过设身处地的共情,理解了夫人的主体性,随之顿悟,画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画作,“她在极度疲倦中放下画笔,心想,是的,我已经有自己的视野”(Woolf211)。当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客体化的策略会失效,唯有关怀伦理能够给主体以力量,使其超越自身的封闭经验,抵达崇高。
自此,让我们回到开篇,重新回顾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剖析》《神魔知道》等作品中提倡的崇高论。显然,布鲁姆所继承的崇高美学传统是具有局限性的。空泛地谈“激情”“超越”与“人性”,却不愿意讨论超越的标准中隐藏的性别限制性条款,这是在制造一种男性话语权的乌托邦。而且,这种崇高忽略了历史的阴影和当下的复杂性,阻断了抵达崇高的其他路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近三十年来,女性主义在哲学、文化、政治、艺术、文学诸领域对崇高美学进行全方位再审视的原因。如何让崇高美学标准能够与女性经验和女性传统相契合?如何站在女性立场,为崇高美学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如何秉持女性主义主体观,行践对他者的崇高伦理责任?……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正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一种跨越边界、尊重情感、拥抱异质性、提倡主体间性的新的崇高美学主张正在形成中。这是女性主义为崇高美学的理论场域带来的新动能。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ttersby, Christine.The
Sublime
,Terror
and
Human
Difference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Bloom, Harold.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a
Way
of
Life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he
Daemon
Knows
: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 New York: Harcourt, 1994.Bromwich, David. “Wollstonecraft as a Critic of Burke.”Political
Theory
23.4(1995): 617-634.埃德蒙·伯克: 《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郭飞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10年。
[Burke, Edmund.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rans. Guo Fei.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10.]- -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 Ed. Frank M. Turn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Butler, Judith.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 London: Verso, 2004.Cixous, Hélène. “The Laugh of the Medusa.”Feminisms
. Eds. Robyn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347-362.Freeman, Barbara Claire.The
Feminine
Sublime
:Gender
and
Excess
in
Women
’s
Fictio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Hand, Seán.Emmanuel
Levina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Hanson, Karen. “Feminist Aesthetics.”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 Eds. Berys Gaut and Dominic McIver Lop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499-508.Kant, Immanuel.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and
Other
Writings
. Eds. Patrick Frierson and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伊曼纽尔·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 - -.Critique
of
Judgement
.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Klinger, Cornelia. “The Concept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in Kant and Lyotard.”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Immanuel
Kant
. Ed. Robin May Schott.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191-212.朗吉努斯:“论崇高”,《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章安祺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7—132。
[Longinus. “On the Sublime.”Translations
on
Aesthetics
by
Miu
Lingzhu.
Vol.1. Ed. Zhang Anq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8.77-132.]Mallinick, Daniella. “Sublime Heroism andThe
Wrongs
of
Woman
: Passion, Reason, Agency.”European
Romantic
Review
18.1(2007): 1-27.Mann, Bonnie.Sovereign
Masculinity
:Gender
Lessons
from
the
War
on
Terro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Women
’s
Liberation
and
the
Sublime
:Feminism
,Postmodernism
,Environmen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Mellor, Anne K.Romanticism
and
Gender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彭峰: 《西方美学与艺术》。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Peng, Feng.Western
Aesthetics
and
Art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Poovey, Ma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lace of Gender in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Aesthetics
and
Ideology
. Ed. George Levin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79-105.Runge, Laura L.Gender
and
Language
in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
,1660-179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Skolnik, Christine M. “Wollstonecraft’s Dislocation of the Masculine Sublime: A Vindication.”Rhetorica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21.4(2003): 205-223.Speese, Erin.Gender
and
the
Intersubjective
Sublime
in
Faulkner
,Forster
,Lawrence
,and
Woolf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Wollstonecraft, Mary.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d. Janet Tod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Woolf, Virginia.To
the
Lighthouse
. Ed. Mark Hussey. New York: Harvest Books, 2005.Yaeger, Patricia. “Toward a Female Sublime.”Gender
and
Theory
:Dialogues
on
Feminist
Criticism
. Ed. Linda S. Kauffm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191-212.斯拉沃热·齐泽克: 《事件》,王师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
[Žižek, Slavoj.Event
. Trans. Wa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6.]Zylinska, Joanna.On
Spiders
,Cyborgs
,and
Being
Scared
:The
Feminine
and
the
Sublime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