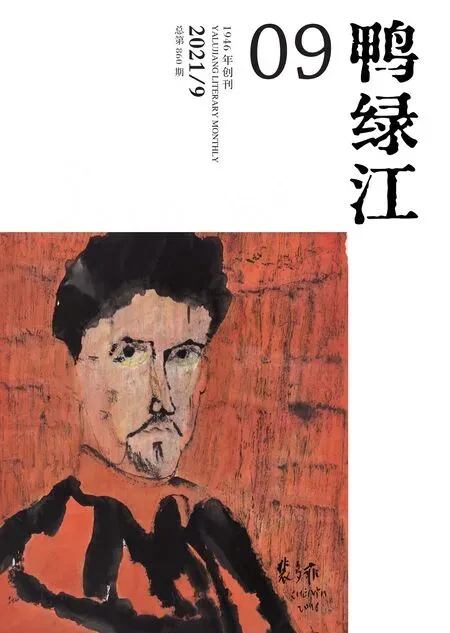我想书写一些具体的东西(组诗)
2021-11-11任白
任 白
我想书写一些具体的东西
我想书写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一棵树,和
老街旁斑驳严肃的墙面
比如你的粗呢子大衣,和
窗台上的洋甘菊
比如一个微笑里隐藏的
柔和清澈的阴影
比如一杯被蛇麻子
蓄满阳光般刺痛的啤酒
我想它们都如此贴心
如此仁慈地出现在一些黄昏
或被大雨反复淘洗的晚上
或被轮回绊倒的绵绵春路
出现在你和优美和聪慧
达成忠实盟誓的那些年
即使被人贬损和诟陷也不能动摇
作为历史的一瞬
那种难以言说的完美机缘
是的,你脸色微红
并和它们一起发光
成为明亮的釉彩
为时光降福
意外之事
整整一天,我都在刷手机
疫情时远时近,但一直在眼前
沸腾,一万个幽居者会聚于此
争吵和抚慰
从不同的世代和族群
派出一些翅膀
在广场上盘旋缠斗
生命从来没有这样激越
没有这样惹人注目
好像一下子和每个人都有了瓜葛
好像爱情终于住进了自己的院落
一丛丛花草给了我们可信可爱的细节
是的,疾病是一个坏天使
她从天而降
用尖叫和血痕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一些像视网膜一样无法被看到的事情
一些灰尘一样的好人
一杯水,当它不再在水管里等你
一通电话,当它不再在那些网络微弱的地方
艰难地搜索你的号码
一个眼神,当它的晶体发出冬天深处的芒刺
——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之事
而我们在这些意外之外
活了很多年
烟火
那些晚上
时间把胸腔胀满
它里面是空的
所以我也是空的
我点火,制造舞动的烟雾
用我的骨头,和
虹膜里的干花
像一场声势浩大的烟火
冷艳的魂魄严肃而又深情
但还是无济于事
几十年过去了
这场烟火还未将时间燃尽
这场烟火还未将我燃尽
初一
牛年初一早上
我盯着阳台上的植物出神
绿色的叶子硕大油亮
好像仍在热带故乡
安居乐业
外面还有零星的鞭炮声
一场十几亿人共谋的狂欢
正处于间歇时段
这真的非常奇幻
好像大海的潮汐
正在一只汤锅里假寐
对自己再次沸腾非常笃定
所以它的安静里
连破灭的泡沫都是幸福的
它知道下一刻自己一定会醒来
还会撑起一个个小小的穹顶
短暂而又欢欣
启示
当你目击一场雷电
鞭打倾斜的地平线
你必须从中得到启示
所有恶意都是可以溯源的
所有电击都是由于
寻仇的两极迎面相撞
但它也可能是一次焊接
用疤痕把沟壑填平
把孤悬之爱锁死
用那些白色的芒刺
装饰永世的伤口
工作
一个诗人的工作
就是在白磷般爆燃的太阳下
用一支黑瘦的榔头
敲打那些词句
看看有哪些会发出声响
清越,或者深厚
或者哀伤到像一只灾难之钟
但是终究没有碎裂
没有假扮可怜
没有要求世人无条件地爱她
没有委屈地抽泣
这时候你应该用凶狠的喙
去啄食她的腐肉
和多余的衣饰
以便她能通过那道窄门
因为从这里出去
她就将站在星空之下
自毁的太阳已经落山
它将升上天空
成为一个值夜班的星座
降落
零点三十五分
我在等一个消息找到自己的终点
此时有很多消息在盘旋
在无数半醒和假寐的魂魄之上
其实所有消息都是灰尘
我只是找到一个和自己更为相像的
灰尘,灰尘,灰尘
等着它落地
就像等待死亡降临
其中唯一的区别是我的等待
充满渴切和规劝
祈盼灰尘再想一想
你降落,但要保持郑重
保持一份和死亡同等重量的承诺
如果不能接引未来
我们只好长睡不醒
此去经年
这一年就要关闭大门时
我要带走些什么
所有东西随意拣选
还可以修改名字
仿佛某种从未有过的物种
光洁的心肌和脸庞
光洁而又懵懂的能量
对的,那些经书
并不是蓄电池
它只是一些密匙的寝宫
但我已经越来越记不住那些暗语了
我担心此去经年
在某个遥远的路边
我不得不把它的硬壳砸烂
随即在一场爆炸中
去了一个我的记忆尚能抵达的地方
花魂
我总是在那些有香味的花朵前踟蹰
我会蹲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
听见有些魂魄正在聚集成风暴
它们旋转,发出嗡嗡的响声
我长久地盯着花丛上方
但一直没发现那些动机藏在哪里
花心里的所有露水,和
叶面下隐忍的筋络
都不足以用这种迷狂和伤心混杂的方式
表达幽然和真切之爱
并从灵魂深处拥抱你
春天路过
每当春天路过的时候
我的骨头都发出解冻的声音
和年轻时略有不同
现在它们不再伸展和生长
而是把自己摊开
让骨缝里的冰水流出一些
交春天带走
而留下的部分
会静静地等着下一个冬天
准备好与历史重逢时
所应准备的一切
致新年
新年的第一天
我发现自己毫无新意
只是因为跨年熬夜
眼袋像两只黑色的贻贝
泛着海沟里蓝灰色的光芒
我猜想真正的变化是时间本身
它在变轨时身体内部不易被看到的部分
一些气泡和裂痕悄然出现
那是一些语言找到了嘴巴
一些惊惧开始舞蹈
而一些深邃的执念正在发出嘎嘎的响声
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我想看看这个人和他身后
多少场战争在抢夺战场
而多少战士不知生死
我在书桌前坐下来
打算和时间软磨硬泡
并且使劲拍打那些脆薄的书页
想知道哪些字句会散落出来
哪些事情应该被遗忘
信件
我想写下两行字
作为信件,给赶路的人
和他的下一段旅程
假扮体贴的锦囊
并且在简朴的餐桌旁等他
来和我一起吃米饭和酸菜汤
汤的热气是一道福音
我甚至充满感激
感激它愿意作为礼物
在冬天的腹地为我们筑城
向他和别的需要取暖的人敞开城门
这可真好,我们在桌边坐下来
嘴唇哆嗦着喝汤
幸福地叹气
我想把那个字条送给他
告诉以后的他,餐桌将摆在哪里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个骗局
那些饥寒交迫的地方
总该有些东西等他
在冬天里转来转去
他一定会迷路,失忆
忘了曾有一碗热汤
抱着他,冒着热气
宛若天堂
我看见自己在一家商场里踟蹰
巨大的天井,几十部扶梯无声转动
把那些无声的人送往天堂
那么多天堂在闪光,闪光
而我在矮化,像一个习惯仰望的人
把惊叹卡在喉咙里,形同密语
我看见自己在一些店铺门口
压抑全部热切和躁动
探视那些华丽的应召者
那些渴望被唤醒
并引发山洪和雪崩的部落
我想大喊一声,让他赶快逃走
但我只是个影子上帝
我的声音是一团雾
是一簇善意而又慌乱的哑语
横在夭折的天堂之路前面
失去嘴唇和喉咙
也没找到耳朵和眼睛
羞耻的花纹
每个人都有很多破绽
隐形的,或者被记录在案的
羞耻的花纹
为此我们习惯了圆舞
习惯了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
吃力地找到节奏
把比较光滑的一面朝向光源
那是一个赋形者
一个为世界说出边界的
制造和传播分裂的人
我们躲开他
躲开不可承受之疤痕
而勇气藏在另一面
或许那不是勇气
只是一点捂住面孔的力气
早春的山坡
早春的山坡上
大片野蒿草在阳光下肃立
它们早被冬天烧焦了
干裂的籽种里
集结着一个亡灵军团
所有溃败都被它们记录下来
在基因编码里反复默诵
你碾碎它,解放它
一次无声的核爆
周遭残火里
到处是
赴死的啸叫,和
芬芳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