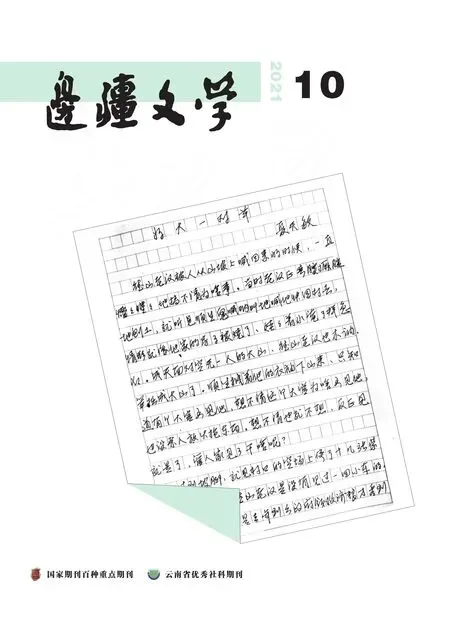浮士德与梅菲斯特 随笔
2021-11-11刘文飞
刘文飞
浮士德和梅菲斯特是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两个主角,这两个人物就像两根高大的圆柱,支撑起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史诗巨著《浮士德》。
浮士德(Faust)的形象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名叫浮士德的人,他生活在16世纪初,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也是一位江湖医生和吹牛大王,他博学多才,通古识今,无所不能,人们因此认为他可能暗中得到了魔鬼的帮助。这些传说后来被人记录下来,进入文学作品,早在1587年,德国就出现了一本题为《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的书,叙述浮士德与魔鬼交易、漫游世界、享尽欢乐,最终死于魔鬼之手的故事。到歌德写作《浮士德》时,欧洲已有很多浮士德题材的故事和戏剧。而梅菲斯特(Mephist),就是圣经传说中的魔鬼,“梅菲斯特”这个称谓虽然并未在《圣经》中出现,但“魔鬼”“撒旦”“堕落的天使”等无疑都是他的别称。在读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后我们不难看出,歌德对这两个人物原型都进行了重大加工和改造,在他们身上添加上新的性格内涵和行为逻辑。
《浮士德》用诗剧形式写成,全书共有12111 行,鸿篇巨制。这是一部超题材、超体裁的作品:从内容看,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容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等为一炉;从形式看,它集诗歌、音乐和戏剧等为一体,把叙事诗、抒情诗、民谣、合唱、古希腊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寓言剧等体裁因素合成起来,并几乎采用了西方诗歌的所有格律形式。可以说,《浮士德》既是人类智慧的合成体,是人类关于自身的庄严颂歌,同时也是人类文学艺术形式的集大成者。在欧洲,有人将《浮士德》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并称为五大古典名著。
作为这样一部思想深刻、形式复杂的文学作品的主角,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就注定要成为那种“全能型的”主人公:他们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思辨、争论和阐释;他们是诗人和艺术家,因为他们需要一直用诗人的语言来说话,用歌手的声音来歌唱;他们是科学家和幻想家,因为他们不仅要在浮士德的书斋和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的实验室里工作,还要穿越时空回到古希腊,去与作为美的幻想之象征的海伦结合;他们是政治家和实践者,因为他们曾辅佐朝廷,最后还在浮士德获得的海边领地上进行改造自然的壮举。如此一来,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也像他们的塑造者一样,都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物在他们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取长补短”,梅菲斯特在陪伴浮士德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思想,而浮士德则因为梅菲斯特获得了上天入地、穿越古今的魔力,获得了观察生活的新角度和新体悟。这两个人物相互借鉴,相得益彰,随着《浮士德》的叙事推进,他们都与故事情节一同逐渐丰满起来,最终步入人类文学史上最为丰富、最为深刻的文学形象的画廊。
《浮士德》的故事情节建立在两个赌约的基础上:一是天主(即上帝)和梅菲斯特的赌约,赌的是人的进取心,是人类的本质和可能性;一是梅菲斯特和浮士德的赌约,赌的是浮士德的灵魂,即人是否会因为种种物质诱惑和现实利益而出卖灵魂。
在全书开头部分的《天堂序曲》一章中,天主与魔鬼梅菲斯特就人类的本质问题产生争执,天主相信人的向善本性,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念,坚信人类具有永远向上的进取精神;梅菲斯特则认为人间糟糕透顶,人在本质上是卑鄙的,任何诱惑都足以使他们步入歧途。于是,他俩决定用浮士德来打赌:
梅菲斯特:您赌点什么?您肯定会输掉,如果您允许我把他慢慢引上我的大道!
天主:只要他活在人世间,你要试一试我不阻拦。人只要努力,犯错误总是难免!
梅菲斯特:那就谢您了;因为我从不愿同死人纠缠。我最爱丰满鲜嫩的颜面。我不会在家里接待一具尸骸;它之于我,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天主:好吧,随你去吧!去诱引那个灵魂脱离他的源头,只要你抓得住他,就把他随身拽上你的歧途,到你不得不交代的时候,你就会含羞带愧地承认:一个善人即使在他的黑暗的冲动中,也会觉悟到正确的道路。(绿原译文,下同)
得到天主的首肯后,梅菲斯特便降至凡界,变成一条鬈毛狗钻进浮士德博士的书斋,与浮士德签下了《浮士德》中的第二个赌约:
梅菲斯特:在这个意义上,你不妨冒冒险。签个契约吧!这几天你尽可高高兴兴,领略一下我的法术,我要让你见人之所未见。
浮士德:你这可怜的魔鬼又会给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在高尚奋发之际,又几曾被你们这些家伙理解过?你可有让人吃不饱的食品?你可有像水银一样不停地从你手中流走的赤金?可有一场从来赢不了的赌博?可有一个在我的怀里山盟海誓、同时向邻人频送秋波的情人?可有美妙极乐像流星一样消逝的荣誉?让我看看什么果实还没有采摘就腐烂了,看看什么树木每天重新发青?
梅菲斯特:这样一张订单吓我不倒,我正可以拿这些财宝来为你效劳。可是,好朋友,我们把安静当作美餐品尝的时辰也快到了。
浮士德:如果我安静下来,游手好闲,虚度时光,那就让我马上完蛋!如果你能谄媚我,诳骗我,使我自得其乐,如果你能用享乐把我哄弄——那就算我的末日来临!我争这个输赢!
梅菲斯特:一言为定!
浮士德:奉陪到底!如果我对某个瞬间说: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那么你就可以把我铐起来,我心甘情愿走向毁灭!那么,就让丧钟敲响,让你解除职务,让时钟停止,指针下垂,让我的时辰就此完结!
其实,这两个赌约为同一个赌局,因为其中都有梅菲斯特参与,也都赌的是浮士德,赌的是浮士德的灵魂。在浮士德的有生之年,梅菲斯特愿听浮士德差遣,满足浮士德的一切愿望,条件是浮士德死后,灵魂归梅菲斯特所有。梅菲斯特现身之时,浮士德正处于对知识和生活失去兴趣、急于开始新的尝试之际,他于是答应了梅菲斯特的条件。那么,这个赌局的最终结果如何呢?换句话说,在这场赌局中到底谁输谁赢了呢?
浮士德看上去是输了,因为在小说接近结束的第二部第五幕的《宫中宽广的前厅》一场中,他毕竟道出了“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这句话,说完这句话后,浮士德就倒地而亡,他的灵魂也就落到了梅菲斯特手中。但是,浮士德绝非简简单单的输家,因为他呼吁其停下的那个美妙瞬间,并非他个人幸福的顶点,而是他在感受到为人类造福的壮举之伟大时发出的由衷感慨;而且,在道出这声感慨时的浮士德已经100 岁,他眼瞎耳聋,错把为他挖掘坟墓的声响当成了移山填海的劳动喧嚣,他的感叹其实出自他的错觉。总之,他最终道出那句话,并非是梅菲斯特诱惑的结果,而是浮士德本人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歌德这样的安排,大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构浮士德的最终失败,让人感觉到浮士德虽败犹荣,明输暗赢,因为他的内心始终是不屈的,他的意志始终是顽强的。
与浮士德相反,梅菲斯特看上去是赢了,他经过长时间的引诱和期待,终于等来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浮士德倒地时,梅菲斯特似乎已生出恻隐之心,他说道:“任何喜悦、任何幸运都不能使他满足,他把变幻无常的形象一味追求;这最后的、糟糕的、空虚的瞬间,可怜人也想把它抓到手。他如此顽强地同我对抗,时间变成了主人,老人倒在这里沙滩上。时钟停止了——”他赢得了浮士德的灵魂,却开始钦佩浮士德的精神,赢家和输家的位置因此便开始相互转换了。更何况,他的“战利品”很快便被夺走:“天使们升天,带走浮士德的不朽的部分。”梅菲斯特看似赢了,却是输家。
同样,天主也既是赢家又是输家。他输给了梅菲斯特,因为浮士德终被梅菲斯特所诱惑,而且,天主还是一个不诚实的赌家,他并未信守诺言,最后派天使从梅菲斯特的手中抢走浮士德的灵魂,让其升入天堂。但是,天主这样行事自然有着他的逻辑,他的逻辑也就是歌德本人的逻辑,即浮士德最终并未放弃追寻和求索,他在历经种种诱惑和磨难后依然保持执着的进取心、崇高的爱的力量和不懈的创造精神,这说明天主起初关于人类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浮士德的灵魂最终升入天堂,就是对人类的赞美,对人类的奋斗精神的讴歌。这场赌局,原本就是天主利用梅菲斯特对浮士德进行的一场试探,就是他针对人和人类的一次道德测试和精神检阅,最终,获胜的是天主对于人和人类的信心。
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也构成一种主仆关系,一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等。在赌约达成之后,梅菲斯特就成了浮士德的助手、旅伴和仆人,可换一个角度看,他又是浮士德的导师、引路人和守护者,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谁主谁仆其实很难确定。他们两人的行程历时数十年,足迹遍及皇宫和贫民区,书斋和监狱,人间和地狱,山谷和海洋,甚至古希腊,他们的行程就是浮士德思想求索之路的外化和象征,而梅菲斯特的陪伴始终,就是为了与浮士德的形象构成呼应,形成互动,就是为了和浮士德的精神构成对话关系,形成复调结构。
《浮士德》全剧分为上下两部,分别描述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两个世界,即“小世界”和“大世界”的求索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浮士德先后经历了五大悲剧,这五大悲剧其实就象征着人生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知识的悲剧,也叫“学者悲剧”。刚出场的浮士德满腹经纶,久负盛名,却对长期的学者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不知应向何处去。学术上的成就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思想的线索已经断头,知识久已使我作呕”。理性和感性在这里发生激烈冲突,极端的迷茫和苦恼状态下,浮士德想到的第一种解决方案竟然是自杀,但是,复活节的钟声突然响起,这使他忆起天真的童年,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就在这时,梅菲斯特走进浮士德的书斋,两人达成协议,由此开始了诱惑与反诱惑的庄严斗争。
其次是爱情的悲剧,又称“格蕾琴悲剧”。浮士德在与梅菲斯特签下契约后,借助后者的帮助,喝下女巫的魔汤后返老还童,追求少女格蕾琴,这场小市民女子和贵族青年的爱情却给格蕾琴带来悲剧:为了能享受爱情的欢乐,格蕾琴用浮士德交给她的安眠药让母亲沉睡,不料因药量过大,毒死了母亲;浮士德因幽会受阻,在决斗中杀死格蕾琴的哥哥。格蕾琴悲痛欲绝,竟然发疯,无意识中溺死了她与浮士德的孩子,最终身陷囹圄。浮士德前来劫狱,却遭到格蕾琴的拒绝。所谓“格蕾琴悲剧”是《浮士德》中最哀婉动情的篇章,格蕾琴就像《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娅,她的柔情,她的歌声,一如她的不幸,她的疯狂,都很动人。浮士德不可能止步于他和格蕾琴的爱情,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的精神探索的终结,就此而言,他们的爱情就注定是一场悲剧。但是在第二部,面对浮士德和格蕾琴的爱情悲剧也心有不忍的歌德,又让死后的格蕾琴再次现身,化身天使,把浮士德的灵魂护送至天国。
知识的悲剧和爱情的悲剧构成《浮士德》第一部,即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小世界”中的经历,是浮士德在世俗层面的求索过程。在第二部所描写的“大世界”中,他又先后经历精神层面的三次悲剧,即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为了让浮士德施展他宏大的政治抱负,梅菲斯特把浮士德带到一个小王国,让他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朝廷“从政”。浮士德和梅菲斯特通过发行纸币,使这个王国暂时渡过财政危机,赢得皇帝信任。皇帝得知浮士德精通幻术,便令浮士德让古希腊美人海伦的幻影重现,在梅菲斯特帮助下,海伦果然应召现身朝廷,可是眼见海伦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谈情说爱,浮士德妒意大发,用魔术钥匙击打帕里斯,引起爆炸,海伦消失,浮士德自己也被炸死,灵魂化为一阵烟雾。浮士德的政治抱负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在浮士德的政治悲剧中,歌德其实写进了许多他本人在魏玛公国朝廷任职时的体验。
梅菲斯特让浮士德死而复生,把他送回他的书斋。对政治大失所望的浮士德转而追求古典美。梅菲斯特帮助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造人,造出“荷蒙库罗斯”(意为“人造人”),荷蒙库罗斯引导浮士德穿越千山万水,来到古代希腊,终于见到海伦的真身。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生下一个孩子,叫欧福里翁,欧福里翁不受约束,无限制地向天上飞翔,最后坠地而亡。见儿子坠亡,海伦悲痛万分,她对浮士德说:“一句古话不幸也在我身上应验:福与美原来不能持久地两全。爱的纽带断掉了,生命的纽带跟着也要断;我为二者悲叹,痛苦地道一声再见,再一次投入你怀抱之中。”海伦在最后一次拥抱浮士德之后形骸消失,只有她的衣裳和面纱留在他的怀里。这一场景无疑是富有寓意的,即美的实质是难以捕捉的,所能拥有的只有美的外在形式。最后,“海伦的衣裳化为云彩,围裹着浮士德,将他浮入高空,带他一同飘走”。这美的悲剧表明,以古希腊美为象征的一切,也不是浮士德最终的归宿。
最后,是事业悲剧。浮士德随梅菲斯特回到现实,他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事业,就像他之前在翻译《圣经》第一句话时,把“太初有道”翻译成了“太初有行”。这时,王国内发生动乱,梅菲斯特暗中帮助浮士德,让浮士德帮皇帝平息内乱,浮士德因此获得海边的一块封地。站在高山顶上,俯视浩瀚的大海,浮士德的心头涌起一个宏伟的计划:移土填海,筑坝造地,造福人类,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乐园。他感到:“事业就是一切,名望不过是空幻。”“我要获得这昂贵的享受,把专横的大海从岸边赶走。”浮士德踌躇满志,要继续大展宏图,为了建一座瞭望塔,他命令魔鬼赶走海边的“拆迁钉子户”——幸福恩爱的老夫妻菲勒蒙和包喀斯,不料梅菲斯特却放火烧掉老夫妇的茅屋,还杀死两位老人。一阵烟雾从茅屋飘来,烟雾中出现四个妇人,即“匮乏”“过错”“困厄”和“忧愁”,其中只有“忧愁”得以“从钥匙孔钻入”,对浮士德吹了一口气,使他双目失明。梅菲斯特见浮士德来日不多,就让小妖们来给浮士德挖掘墓穴,雄心勃勃的浮士德听到这挖土的声音,还以为是人们在挖土填海,于是发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感叹和欢呼:
一片沼泽在山下向这边漫淌,污染了已经开拓的所有地皮;还要把臭水坑加以排放,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的业绩。我为几百万人开辟了空地,虽说不上安居,倒也行动自由,生活写意。田野葱绿而丰腴!人畜两旺,在这片新地上过得舒舒服服,立即定居在那堤坝之旁,那可是勤劳勇敢的民夫挖的土方!堤内是一片乐土,堤外则是海浪向边缘猛冲!一旦它贪婪成性,猛冲进来,大伙儿会齐心协力,奔赴现场,把决口一一堵封。是的!我完全坚持这个主意,它是智慧的最后演绎:只有每天重新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配有享受二者的权利!那么,即使这里为危险所包围,也请这样度过童年、成年和老年这些有为的年岁。我真想看见这样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那时,我才可以对正在逝去的瞬间说:“停留一下吧,你多么美呀!我的浮生的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消退。”——预感到这样崇高的幸会,我现在正把绝妙的瞬间品味。
说完这段话后,浮士德就倒下了,梅菲斯特这一次不会再让他死而复生了,因为他这一次能得到浮士德的灵魂。
相继经历了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这五大悲剧的浮士德,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吗?就像他在与梅菲斯特的赌局中虽输犹赢一样,经历过悲剧人生、并最终死去的浮士德却不是一个地道的悲剧英雄,因为他作为人类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之象征,他最终其实战胜了梅菲斯特,也就是说,战胜了他自己内心里阴暗、消极、否定的一面,他因此是一位胜利者。他在倒下的时候是满怀信念的,相信自己是在为人类造福,是在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这样的结局是英雄主义的。与歌德同时期的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就说过:“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浮士德就一直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他的每一次失败,每一场悲剧,都使他向真理靠近了一步。在每一个具体的悲剧事件中他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失败者,暂时的失败者,但在完整的生命历程中,他却是个胜利者,因为他从未停下探寻的脚步,就这一意义而言,《浮士德》不是一部悲剧。但是,歌德本人却坚持认定《浮士德》是悲剧,他还把“悲剧”二字作为副标题写在封面上。歌德的这一体裁界定,可能既指书中相继出现的五场悲剧,也指浮士德的求索之路却始终离不开魔鬼梅菲斯特的陪伴和掌控这样的可悲宿命,也更有可能是在暗示作为本书主题的“浮士德难题”和“人类存在悖论”,即人不可能停止追求,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绝对,而绝对又是永远难以企及的目标,人若停止追求,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此一来,浮士德的所作所为,乃至整个人类的所作所为,就成了一件无比悲壮的事业。即便如此,作为悲剧的《浮士德》依然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是一曲关于人类生命力之旺盛、人类精神之崇高的壮丽颂歌。
一般认为,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虽为主仆,却分别代表两种性格,两种人,或曰人类的两种类型,他们构成善与恶、爱与怀疑、肯定与否定、行动与毁灭、乐观与悲观等人类的两种本质或两种世界观之对立。但是,读了《浮士德》之后,我们会感觉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他们似乎都是双重人格,其性格中都有着深刻的矛盾性。
浮士德作为整个人类的象征,作为被天主寄予厚望的人,无疑是一个“正面人物”,他在求索中体现出的求真、克己、坚韧和遂行等品质,都是人类赖以存在的人性前提。但是,浮士德的求索又恰恰是他与魔鬼、与自我不懈斗争的一个过程,他始终处于知识和信仰,科学和艺术,理性和感性,疯狂和理智,禁欲和纵欲,甚至善与恶的激烈搏斗的战场。在尝试自杀时,浮士德有过这样的自白:“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想从另一个挣脱掉;一个在粗鄙的爱欲中以固执的器官附着于世界;另一个则努力超尘脱俗,一心攀登列祖列宗的崇高灵境。”浮士德的自杀念头,他在返老还童后想占有格蕾琴的情欲,他是杀死格蕾琴母亲和哥哥的凶手,他对格蕾琴的始乱终弃,他让梅菲斯特赶走海边的老夫妻并导致这对老夫妻的死亡等等,都是浮士德内心之恶的种种显现。原来,浮士德的内心里原本就存在着一个梅菲斯特,梅菲斯特可以说是他的“第二自我”,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与其说是在与梅菲斯特打赌,不如说是在与他自己的另一半打赌,他与梅菲斯特的一拍即合,原本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梅菲斯特就是浮士德性格中恶的一面之外化,他与梅菲斯特的不断冲突也就是他内心激烈冲突的外在化体现。《浮士德》的中译者绿原先生写道:“事实上,在浮士德身上亦即在人类身上,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斗争——可以说,梅菲斯特就在浮士德本人身上,二者的斗争始终贯穿着一股躁动不安的向绝对真理追根究底的精神力量,不断抵抗着梅菲斯特陷人于满足、怠惰和堕落的种种诱惑。”
和被诱惑者浮士德一样,诱惑者梅菲斯特本身也是一个性格矛盾体。梅菲斯特在与浮士德第一次见面时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永远否定的精灵!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发生的一切终归要毁灭;所以什么也不发生,反而更好些。因此,你们称之为‘罪孽’‘破坏’的一切,简言之,所谓‘恶’,正是我的原质和本性。”但是就在这句话之前,梅菲斯特已经脱口说出了另一种自我认定:“是总想作恶、却总行了善的那种力量的一部分。”天主当初之所以同意魔鬼去试探、诱惑浮士德,除了他对人持有信心这一点之外,他也是为了让浮士德、让人类经受一次考验:“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他很快就爱上那绝对的安息;因此我愿意给他一个伙伴,刺激他,影响他,还得像魔鬼一样,有创造的能力。”魔鬼是具有创造力的,恶是具有矫正功能的,“否定的精神”是有可能产生“肯定的效果”的。在引诱浮士德下降的过程中,梅菲斯特也不时体现出他的恻隐之心和正义感,比如他对浮士德公开在大街上调戏格蕾琴的反感,他在朝廷里针砭时弊,他看不惯古希腊人“几乎个个都是赤身裸体”等。更为重要的是,梅菲斯特所行的恶并非绝对的恶,而是一种激发浮士德永远向上、不断求索的动力,是“黑色魅力”和“魔鬼之美”。恶的存在及其活动,在客观上为人和人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言及的“恶的历史作用”,所指也正是梅菲斯特性格的这一功能属性。堕落的天使也是天使。
范大灿先生在《德国文学史》中关于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善恶行为做过这样的归纳:“浮士德是在行善中有恶,梅菲斯特是在作恶中行善。”善与恶的相互交织和转换,这是人类性格的辩证法,也是人类存在的悖论逻辑。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两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两人的合体才构成一个整体,才是真正的人,才是真正的人类,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既有浮士德,也有梅菲斯特。
歌德自25 岁起写作《浮士德》,到82 岁才最终完成,从1774年至1831年,他写了将近60年,《浮士德》几乎伴随着他成年后的所有时光。在《浮士德》完稿后的次年,即1832年,歌德在魏玛去世,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更多的灯吧!”这句话让我们动容。我们知道,“梅菲斯特”这个名称源于古希腊语,意思就是“不爱光的人”。那么,歌德是在临终时再次遇见他塑造的梅菲斯特了吗?他是要用“更多的灯”驱赶那个“不爱光的人”吗?很有可能,弥留之际的歌德不仅再次遇见了梅菲斯特,他还再次成为了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