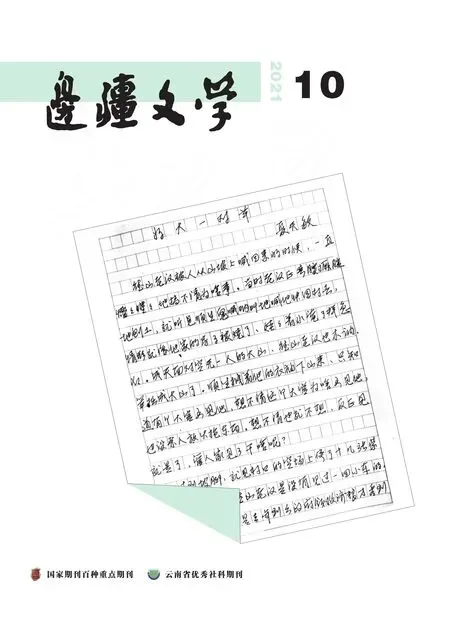你好,辛工
2021-11-11周勇
周勇
有的人你永远也想不起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好像早就认识了,没有第一次。而有的人你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相见的所有细节,时间、地点、甚至当时的表情。这里没有哪种更好的意思,只是人和人之间细微的感觉。
辛工属于第一种。第一次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伸过手来,你好周勇。你好辛工。于是就认识了,就无话不谈了。没有任何铺垫和过渡。只是在认识辛工很长时间后我仍然误以为辛工是“辛公”的意思。当时只觉得可能民主党派机关尚存民国遗风,年龄稍长者便以“某公”称之。直到我调到机关后才知道,辛工早年在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摩托车厂当厂长,高级工程师。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辛工,而不叫他厂长。后来到党派机关任秘书长、专职副主委,大家无论当面或私下仍叫他辛工,而不叫他的职务。一次聊天时我把这事告诉他,他说这也没错嘛,本来就是公的嘛,又不是母的。旁人插道,照这样说三八妇女节也可以叫三八母人节了。辛工大笑,不可引申,不可引申。
一直到他去世后,认识他的人偶尔聚在一起回忆起他时,还是称他辛工。
辛工是东北人,很小就随父亲举家来到云南。辛工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因而你不可能听到关于他的相对完整的家族往事。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会透露一些极琐碎的信息。比如,五十年代初他父亲被发配云南。“发配”一词说明父亲是犯了错误的。因而在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辛工的父亲是在那一场著名的运动中和几百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然后开始长达几十年背井离乡的流放。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的错误比当时几百万人犯的错误严重,是反革命罪。他父亲曾是吕正操将军麾下的一名师长,性情刚烈,拒不认错,被革职发配云南之后又以反革命罪送到昆明郊区的劳改农场。二十多年后他父亲的平反也与吕正操将军亲自打招呼有关。只是那时他父亲已疾病缠身不久于人世。
到劳改农场探望父亲肯定是辛工童年最难以释怀的记忆,因而他的讲述相对详细。他说当时劳改农场附近有一个货运的火车站,每天有拉煤的火车经过。因为没钱买票他便偷偷爬到拉煤的车厢上。时间久了,每次劳改农场大门出现一个满身煤屑的男孩就知道老辛的儿子又来了。他说,除了眼睛全身都是煤屑,往煤堆里一躺就跟煤堆融为一体没人能发现。他说每次到劳改农场,父亲或父亲的狱友就打水让他洗脸,脸盆里的水全是黑的。后来他还获准和父亲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
那个劳改农场后来迁走了,不知去向。再后来那地方通了地铁叫大板桥站。辛工每次叙述时表情平静,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说,要是现在我就坐地铁去看老爹。相视大笑。
辛工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干净优雅的女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90 岁了,一头银发,行动利落,说话轻声细语。这个当年的大家闺秀很少回忆她年轻时的生活。偶尔问起她只是淡然一笑“那都是从前的事了”。这一点辛工像她母亲,几十年的颠沛流离似乎并未在身上留下痕迹。老人喜欢清静不愿意跟儿子住,一人住在原来的单位宿舍里,独自买菜做饭。辛工也不勉强。辛工中午在九三省委机关吃饭,下午到母亲那里陪母亲吃饭,几成惯例。辛工说其实母亲早就把饭做好了,他是吃现成的。一次我和辛工到九三中央开会,他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里他母亲抱怨现在的菜太贵“两根排骨就20 块钱”。辛工说不错了,20 块钱就买两根了。一次他母亲跟辛工说,她已经三十年没去过西山了。于是我和辛工开车陪老太太去了西山公园。老太太年纪大了走不了太多的路,一起坐在华亭寺长廊里说话。老太太说她年轻时会唱评戏,于是轻声哼唱起来。只唱了两句就不唱了“记不住了,全忘了”。我对她说你年轻时候肯定很漂亮,即使现在你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老太太。她说“老了”。说话时一脸羞涩,像小女孩一样令人怜爱。
老太太抽烟,几十年只抽一种牌子的烟,云南产的红山茶牌香烟。每天抽一两支。老太太抽烟的姿态像极了民国时期上海月份牌上的招牌画,无比优雅。那是一种骨子里的优雅。
老太太有一个姐姐在辽宁老家,独身,是辛工的姨妈。辛工想把姨妈接过来和他母亲住一起,这样两个老姐妹也可以互相做个伴。这个想法得到了家里所有人的赞同。于是辛工就去东北老家把姨妈接到了昆明。两个90 岁的老姐妹在阔别几十年后又生活在一起。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的各自的生活经历已经使两个亲姐妹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无论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还是世界观都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吵架甚至肢体冲突经常发生。每次冲突后只有辛工才能让两个90 岁的老人短暂地和好。在又一次冲突之后,辛工的母亲对他说了一句狠话“你不把她弄走,我就把她杀了”。之后,辛工就把姨妈送到养老院。
辛工的姨妈我见过,典型的东北老太太。很难想象她和辛工的母亲是一母所生。姨妈嗓音高亢,是那种浓浓的东北口音。喜欢到处走动。即使到了养老院也不安分,常常一个人跑出养老院,然后就迷路了。养老院找不到人只好打电话给辛工。辛工就发动家人到处去找。有好几次是被好心人送回来。姨妈不以为然,对所有人说“我只是出去跟人唠嗑”。辛工说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姨妈突然想回辽宁老家看看,于是悄悄来到昆明南窑火车站。居然还稀里糊涂地上了火车。就在所有人都在大规模寻找姨妈时,成都铁路局派出所打来电话,要亲属到成都接老人回来。于是辛工的妹妹迅速赶到成都将姨妈接回来。姨妈说你们着什么急嘛,我去老家看看就回来。
那次辛工做胰腺手术我们去医院看他,一干人坐在病房里说话时,一个护士领着一个老人来到辛工床前,是他吗?辛工的姨妈居然从养老院来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找到了辛工。姨妈见到辛工的第一句话是,你让我找得好苦。然后就抱着辛工老泪纵横。她对所有人说,我心疼我家辛华呀。护士说这个老人在院子里转了半天,逢人就问辛华在哪里。护士就带着老人一个科室一个科室打听辛华。辛工当即给养老院和他妹妹打电话,他说他们肯定也在到处找失踪的姨妈。后来辛工埋怨妹妹不该把他生病的事告诉姨妈。辛工的妹妹说她去养老院看姨妈,姨妈问她为什么辛工好久没来看她了。她说出差了。姨妈不信,执意要跟妹妹回家看辛工。情急之下妹妹说漏了嘴。等妹妹走后,姨妈就偷偷溜出养老院。让所有人不解的是,昆明那么多家大医院,姨妈居然找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还是已经到其他医院,最后才找到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一个90 多岁的老人。
两个生前水火不容的老姐妹在一个月内相继离开。起初是辛工的母亲感冒,他母亲不愿意到医院,说自己吃点药就好了。母亲本来就是医生。辛工执意要让她到医院。于是就到了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我到病房看她时,老太太看上去精神矍铄全然没有生病的样子。老太太坚持要出院。她说本不必来医院的,在家吃点药就好了。只是辛工一定要让她来。我告诉她观察两天再出院。她悄悄指着辛工说,我怕累着他。然后拿出点心让我吃,让同室的病友吃。看得出同室的病友很喜欢这个老太太。据说当天晚上她很早就睡了,睡前还和同室的病友们道了晚安。一夜都很安静。直到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测体温时发现老太太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了。享年94 岁。
一个月后她的姐姐,辛工的姨妈也走了。无疾而终。
机关里的人都知道辛工好吃,而且食量极大。如果有人给他带盒饭,他会反复叮嘱要两份。时间久了大家自然知道给辛工买盒饭要买两份。有一次辛工问我,你说人最难受的感觉是什么?我一时语塞,他说最难受的感觉是饥饿。他说他什么都能忍,就是忍受不了饥饿。我说他是童年饥饿后遗症。他说是的,那时饿得眼冒金星最大的梦想就大吃一顿,死了算毬。因为好吃每到一地他就去寻找当地小吃,乐此不疲。他甚至比当地人还熟悉小吃店的分布和位置。他告诉我他可以画一张昆明或云南小吃地图。
有一天他叫我不要在机关食堂吃饭,他带我去一家新开的面食摊。我跟着他来到马街一家路边的排档。门口立一个汽油桶改成的炉子上面架一口大锅,锅里煮着牛骨头热气蒸腾。面条捞到碗里便从大锅里舀一勺汤,然后自己去放佐料。店太小食客太多,只好坐到人行道边的小桌子旁。辛工吃得大汗淋漓。问我味道如何?我说环境太差了。他说管它呢好吃就行。一次九三中央来人,辛工要我找一家饭店接待。我说你是美食活地图,在你的地图里找一家就行了。他说我地图里的都不上档次,怎么能让他们去那种地方嘛。
辛工好吃众人皆知,可是辛工还是一名资深音乐发烧友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九三省委有一个副主委周浙昆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常年在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辛工说他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外,三分之一在昆明,还有三分之一在野外考察。有一次他从国外给辛工带来几张堪称专业级的唱片。我说这唱片好像国内也有嘛。辛工说那太不一样了。周浙昆告诉我,你不知道辛工是专业级的发烧友。九三中央组织部文文部长和辛工有相同的爱好。两人的差别是,文文歌唱得好,退休后去了合唱团。辛工五音不全。我在一次酒后听他唱过歌,真的不忍卒听。我说那么多好音乐你都听到哪里去了。他说都到肚子里了。每次到九三中央开会,文文部长就提前电话告知他近期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安排。我说他不是去开会,是去听音乐会。他说革命、生产两不误嘛。美食、美声人生有两大乐趣夫复何求?我说还有美女嘛。他说那是年轻人的事了,老夫已无福消受。然后他表情神秘地问我,如果我误入女厕所会是什么结果?我说肯定是在老流氓的骂声中落荒而逃。他说人家肯定不会骂我流氓的,只会说这老头眼神不济。我不禁大笑辛工却不笑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机关里至今流传着辛工的趣事,一是他指挥别人倒车,他说尽管倒就是,撞到了会响的;一是机关工会到一个温泉活动,辛工在泳池游泳,有人问他是热水还是冷水,辛工说是热水。别人一头扎下才知道上当了,是冷水。
辛工臧否一个人的标准很简单,他说这个人没意思,张嘴全是文件和报纸上的话,一套一套的,让人生厌。以后见到这人他总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侃侃而谈很少搭腔。
现在想来,2009年辛工的腰痛预示了他后来的命运。那阵他总说腰疼,活动活动反而不疼,坐着不动就疼。起初以为是腰椎或是腰肌的问题。于是拍片、理疗、贴膏药,那段日子辛工浑身散发着膏药的气味。只是并不见好。辛工索性不管,照样游泳、散步。后来查出是胰腺肿瘤。那天他打电话给我,老弟判决书出来了,胰腺上长了一个东东。那时他已经住进医院。
手术是唯一的选择,辛工却表现出少有的固执。医生和亲友的说服在辛工的固执面前毫无办法。辛工用沉默来对抗所有人滔滔不绝的道理。实在没办法时,他就说好不容易才长出来的东东就留着吧。此时辛工的幽默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人理会他的幽默。随着劝他做手术的队伍不断壮大,包括我也极力劝他立即手术。越早越好。当然这是医生的意思。辛工终于妥协了。其实辛工比我们所有人都清醒,他私下跟我感叹,都是因为管不住嘴啊。那些日子辛工在百度上获得了大量关于胰腺癌的知识。我后来明白辛工当初拒绝手术的原因,他说他看到诊断书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去西藏,走到哪算哪。他还没去过西藏。那一直是他的一个梦想。我说回不来怎么办?他说回不来就回不来了嘛。那是命。我当时想辛工的这个梦想估计很难实现了,因为有个专家告诉我,辛工是胰腺癌,这是癌中之王。她估计辛工还有半年或者一年时间。此后辛工的生命虽然大大超出专家的预期,只是他的头上随时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每天他都要面对死神的降临。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知道辛工在最后的日子里的真实想法,他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包括他的家人。每天早晨的日出对于他都意味着可能是最后的日出。所有人看到的只是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达观和幽默。
手术后是绝对禁食的。这对于辛工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他于是在病榻上不停地回忆各种美食。只是这种回忆让他更加痛苦不堪。他说如果他是当年的革命者根本不用严刑拷打,只要饿他几顿再用美食诱惑,他就全招了。
手术后辛工腹部放了一个引流管,用来引流胆汁。分泌的胆汁从引流管里流到他衣服口袋里的塑料袋里。从2009年到2020年辛工开始了他生命中的插管人生。
辛工手术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迅速消瘦,原来身高一米八身形魁梧的男人,突然变得形销骨立。只有声音和笑声依然洪亮。尽管如此他对美食的兴趣并不比手术前有所减少。他有更多的时间坐着地铁或公交四处寻找美食。他的昆明美食地图肯定又比从前有了极大的丰富。有一天他来我家,闲聊时他告诉我,在距我家不远处有一家小锅米线味道不错。这家米线店我经常路过却从未光顾过。我说辛工你是死不悔改啊,他嘿嘿笑着,不敢多吃只是尝尝。不然人生太无趣了。他有时因为嘴馋多吃了一口,胆汁分泌多了致使引流管堵塞,于是就全身发黄。于是就到医院冲洗引流管。然后黄就随之消退。医生再次叮嘱不可多食。辛工连说好的好的。下次又去,医生问他是不是又吃多了?辛工说这次没有这次没有。后来,连护士在病房见他也说,辛大爹是不是又吃多了。我两每次见面,我说他现在不黄了,他说刚从医院出来,如果再黄就彻底黄了。彼此大笑。
去医院冲洗引流管的次数多,辛工学会了自己冲洗。他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他带上塑料管、生理盐水、一次性注射器独自开车四处游荡。刚开始时他还不敢走太远,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越走越远。每次外出的时间也越来越久。大约有几年的时间,辛工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云南高原漫游。觉得哪里好就停下来住几天,然后继续。最长的一次他在外面游荡了两个月才返回。他专走那些县乡之间的便道。他说高速公路没意思,云南乡村公路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跑到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富宁县下面的一个村庄。那里距离广西百色已经不远了。出于对身体的担心,他的旅行基本限制在云南境内。那天他坐在一个小山坡上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村子太漂亮了,你以后一定要来。然后他决定在这个村子里住几天。这个村子平时少有人来,看到辛工便问他找谁,辛工说我谁也不找,就找山找水。
那次他来到墨江县的一个乡镇,准备到一家路边的饭馆吃饭。老板告诉他有刚从河里打来的鱼,他让老板煮了一锅鱼。老板又说,师傅我看你的样子可能会喝点酒,我有自家酿的米酒,辛工又要了一盅酒。酒足饭饱后辛工突然感觉不对劲了,立马开车去墨江县医院。县医院让他住院观察,他说了两种药名,问县医院有没有。县医院的医生说从没听说过这种药。于是他到附近药店买了生理盐水在车上简单冲洗后迅速赶回昆明。没有回家先到了医院。
那段日子他几乎跑遍了云南最遥远的县乡。家里人也劝不住只好随他去了。有时早晨睁开眼睛他突然想起蒙自的过桥米线,于是匆匆洗漱后就驱车到300 公里外的蒙自。他的车里随时备有旅行所需的所有物品,无需准备说走就走。有一阵昆明降温,他告诉家人他要去一个暖和的地方,寒流过后再回来。于是他就开车到河口。那是云南海拔最低处,与越南接壤,也是云南平均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没想到寒流是从广西而来,平时酷热的河口那几日也和昆明一样寒冷异常。他在常年酷热的河口冻得瑟瑟发抖。
现在想来,让他的亲友们感到幸运的是,手术后的辛工没有在病榻上而是在云南高原各处乡村旅行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快乐时光。
在他的漫游中有两次特别的经历。那天他在中缅边境的孟连县,路上突然出现几个穿警服的人拦住他的车,是缉毒警察。盘问他为何到孟连。辛工懒得过多解释便说去看儿子。问他儿子在孟连干什么,他说当兵是武警。检查完所有证件后警察提醒辛工,路上不安全要小心。另外拿出几张照片说如果路上看见这几个人就立即给他们打电话。
还有一次是在一条林区公路上,几个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人拦住他,辛工不敢熄火,也不下车。他说如果情况不对他就加油逃跑。结果还是缉毒警察。他们奇怪的是一个老头开着昆明牌照的车在边境林区公路上绕来绕去。查完证件后就开始仔细检查车辆。在后备箱里发现了塑料管、生理盐水和一次性注射器。于是盘问和检查更为细致。辛工索性撸起衣服让他们看。警察们感动了,只是奇怪一个人跑到林区里来干什么。辛工说退休没事随便转转。后来警察请辛工吃饭,告诉辛工以后尽量少来,这里不安全。辛工问他们,我像贩毒的?警察说不像,但是像探路的。每次说起,辛工就笑得一脸褶皱。
日子久了,大家似乎渐渐淡忘了辛工是病人的事实。偶尔想起便不由感叹,奇迹啊奇迹啊。每次聚会都会想到他,他也从不践约。我和浙昆与他相约一起到处走走。一直到他离开也未能成行。殊为遗憾。
他的旅行是在他去世前一年逐渐中断的。那一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和家里度过。有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消瘦得更厉害了。他说突然就跑不动了,快了快了。那天是中午,强烈的阳光从窗户照到他的病床上。我说不要乱想,等你好点我们还要一起出去走走。他没说话只是黯然一笑。辛工其实比所有人都清楚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已经越来越近了。“我的表快要停了。”辛工说。那是我和辛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论死亡的话题。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和儿子聊天,他说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老爹是怎么死的,你就说是吃死的。我说那你以后的墓碑上可以这样写:辛华因吃医治无效于某年某月去世。辛工眯着眼笑了好久。
现在想来,那是辛工最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