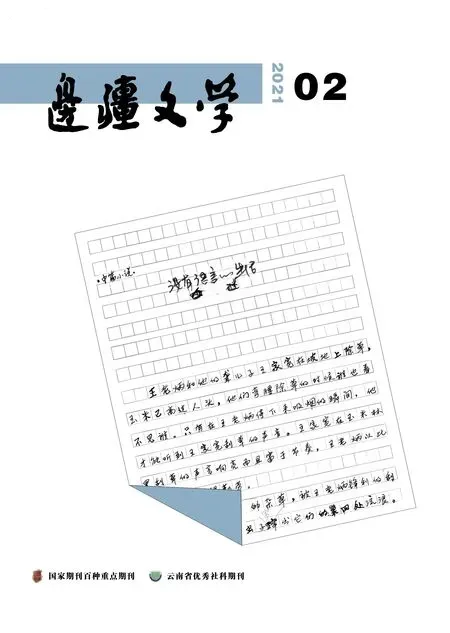1975年的冬天 短篇小说
2021-11-11
母亲早上一起床,就忙着把棉袄棉裤晒在院子里。她把依旧要穿的棉衣挂在一边铁丝上,把要改小的棉衣挂在另一边,心里盘算着哪件棉衣单薄了,要衬上一些棉絮。我家无论是单衣还是棉衣,都是大改小,——大人穿不上了,改给伢子穿。哥哥穿不上了,改给弟弟穿。
清晨的太阳刚从云缝里钻出来,似乎没睡醒,软绵绵的没有力气。风吹在脸上冷飕飕的。我穿好衣服站在后门边,望着母亲挥起一根竹篙,扑打着挂起的棉衣。随着竹篙的扑打,阳光里便飘荡着闪闪烁烁的细小尘埃。院子很窄,窄得栽不下一棵树,只能紧挨着牵出两根晾衣服的铁丝。母亲仰起脸,阳光从衣裳的间隙里透过来,照在母亲脸上,深深浅浅的。我看见母亲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有一绺头发垂下来,遮在眉眼间。“愣着干什么?盛碗粥吃了,去东头草市上买一担稻草来。”母亲没回头,继续扑打棉衣。
一阵北风吹过,有几片枯黄的树叶落在棉衣上,没落稳,磨蹭了一会,又歪歪扭扭地飘落在地上。院墙外是邻家,挨墙种了几棵泡桐树。我转身的时候,树梢上,不,蓝天上,一队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向南飞去。
我家住的这条巷子叫草巷口,这里的房屋错错落落,多是些手艺人家,做小生意和卖苦力的人家。巷子一头连着西大街,一头向东,越过一条小河通向田野,十几里外就是浩渺的高邮老湖(当地人称高邮湖为高邮老湖)。镇上的人称这片田野叫东乡。每天清早,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东乡的汉子们就挑着柴草担子行走在蜿蜒的田埂上,过了小河上的石拱桥,把柴草担子顿在纪大奶奶家门前的大滩上等待售卖。开草行的纪大奶奶瘦瘦长长的,穿着黑色对襟大褂,一把枯灰色的头发挽在脑后盘个髻,口里噙着一管旱烟,手持一根与人齐高的秤杆,早已站在屋门口了。纪大奶奶家门前的大滩不是临水的滩涂,而是一片开阔地,早先这里长茅草、荻草,后来周边有了人家,草被割净,地被踏平,东乡的人来此卖草,渐渐形成草市。不知为什么,当地人一直称这片开阔地叫大滩。纪大奶奶父亲开草行,家中就她一个闺女,父亲去世,她就接过了这杆秤。
大滩那边,纪大奶奶家门对面,有一家理发店、几户住家和一家豆腐店。豆腐店西山墙外通向一条弯弓形的巷道,向里去头一户是磨坊。从早到晚,这家磨坊的一盘大石磨不停地磨,磨面粉,磨玉米粉,春节前磨糯米粉。一条黑驴被蒙住双眼拉磨盘,拉累了,黑驴就立住腿,不拉了,打也不拉。这家磨坊的老夫妻这时就解开黑驴,让它自个颠颠地跑到小河边,打个滚儿,啃草,饮水,自己去推磨盘。巷道西侧有一家澡堂,一个偌大的院子里面有两排相连成“T”字形的房屋,这两排房屋青砖小瓦,木雕门窗,飞檐翘角。院角有棵石榴树,每年秋天里,树上都挂满了咧开嘴的红石榴,望着人傻笑。院墙下堆满树枝柴棍。此刻,天大亮,豆腐店已磨好豆子,卸了磨的花驴拴在窗外,正可劲地埋头吃草料,豆浆在大铁锅里烧开了,咕噜咕噜冒着泡,豆香味飘出来,引得正敞开怀擦汗的卖草汉子们肚子咕咕着响。
街上行人渐渐多了。这时一阵“欧啊,欧啊”的驴叫声传来,人们见豆腐店的花驴还在低头咀嚼草料,原来嘶鸣的毛驴是磨坊里的,正在拉磨。它是不是饿了?还是累了呢?豆腐店的花驴很响亮地打个喷嚏,也仰起头来“欧啊,欧啊”嘶鸣,它在应和呢。从河坡上走过来四五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他们排成一列,肩上围了披肩,裤腿挽起,穿着草鞋,哼着“吭唷”“吭唷”的号子,正挑着水桶朝澡堂走去,身后洒下一路水珠。系木桶的铁链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我的目光越过几担柴枝,盯住一头稻草一头干草的担子。干草也是稻草,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稻草。收割稻谷时,这些稻秆不是脱粒机轧的,而是人工一把把甩在石磙上脱粒的,是专门用来编草鞋、搓草绳或盖草房用的。纪大奶奶放平秤杆,我踮起脚尖起脚尖和卖草汉子抬起一头担子过秤,又称了另一头。我算好账,松开紧攒的手掌,掌心里有一把零碎钞票,已被我攒出汗了。纪大奶奶抽走一毛钱佣金,卖草的汉子仔细收好钱,挑起草担跟我走。身后传来纪大奶奶的夸奖声,十来岁的伢子会买草了。
我把草担子带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坐在门外洗山芋,一个大木盆里盛满水,山芋泡在里面,全是红皮的。进了秋冬时节,母亲每天烀山芋卖。烀山芋,红皮的香甜,口感好。黄皮山芋淀粉含量高,母亲把它们拣在一旁,积多了,等父亲拖去磨坊里磨了,回来滤淀粉。
那汉子把草担子顿在我家门外,收好绳索系在扁担头上,然后扛起扁担大步走向西大街。十字街头有两家面食店,一家炕烧饼,一家下面条、炸油条。许多年来,这两家从不互抢生意,出售的面食不混杂,你卖你的面条、油条,我炕我的烧饼。卖草的汉子先下碗素面,没吃饱,站在摊旁,就着面汤接着吃了两根油条。喝完最后一口面汤,很满足地打个响嗝,又买两根油条,用几根稻草缠绕在扁担头上,带回家给妻儿吃。
我听从母亲的吩咐,把倚在门外的一捆捆芦苇摊开,把稻草打成绕子,一根根缠在芦苇上。芦苇缠上草绕子,等父亲中午下班回家,把它们排列在两间房屋的间隔处。我家临巷两间正房,后院一间厨房。两间正房的间隔一直是扎的芦苇草绕子。芦苇草绕子一根根挨着立好了,两侧糊上掺了谷壳的泥巴,泥巴外刷上石灰水,刷两遍,草绕子墙被刷得雪白。这面墙过几年就朽了,要重扎一次。重扎,多在秋末,扎好墙过冬,暖和。
晌午时,母亲和我把“锅腔子”抬到门外。“锅腔子”是一种用黄泥巴糊的灶。母亲把洗净的山芋堆在铁锅里,堆得高高尖尖的,外面盖上十几层干荷叶。每年入秋后,我都会带上弟弟去东乡的荷塘里釆摘荷叶,回来晒干了贮存起来。母亲坐在“锅腔子”旁烧火,先用大火把铁锅烧开,再用余火慢慢烀。烀到下午三四点钟,直至渗出糖稀,火候就到了,这时候的山芋吃到口中,绵软香甜。其间,母亲时而朝“锅腔子”里内添根柴,时而上下翻动锅内山芋,让山芋均匀受热。
小火慢慢烀时,“锅腔子”四周先是热气升腾,接着一股特有的山芋清香在空中弥漫开来,引得路人咽口水。没等“锅腔子”抬到西大街十字路口,陆陆续续的食客们就围拢过来,一个个伸长脖子望着铁锅,等着母亲揭开荷叶,买一块两块三四块烀透的山芋,撕一块荷叶包了,就着荷香吞咽起来。那些腹中正饥的人,一块山芋几口咽下肚,身上竟微微沁出汗来。
“锅腔子”抬到十字街口时,卖麻花的,卖馓子的……卖锅贴的,几家“锅腔子”顿在街口几户店铺的屋檐下,都向外冒着热气和香味。
傍晚时分,父亲从县城回家了。父亲在镇上合作饭店上班,难得去县城一次,今天去,是为店里购买猪肉猪油的。区政府的一位区长调到城里肉联厂当厂长,父亲去了能买到猪肉猪油,这些原本是要按计划凭票证供应的。父亲曾在区政府里当过炊事员兼马夫,为这位区长做过饭,饲养过马。父亲顺便为家中买了几斤价格低廉的碎肉。这会儿,他从墙角拎出一只小缸,洗净了,把几斤碎肉腌进缸里。这个冬季,隔三岔五的,我们全家人就能吃上雪菜炒肉丝,或是黄芽菜炒肉丝了。
晚饭吃的是红豆大米粥,就着咸菜丝。母亲熬粥的时候,我把煤油灯罩擦干净了。粥碗端上桌时天已黑透,母亲让我点灯。晚饭后,母亲洗好碗筷,端出一只小箩筐,里面盛着旧衣旧祙针线头,就着灯光,坐在桌边缝缝补补。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在矮凳上搓草绳。之前,我把早上买来的干草一把把摊在一个结实的宽凳上,用木槌锤软绵了。这会儿,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一根拫抽出干草,压在屁股下搓绳。草绳越搓越长,我们把绳头卷起,草绳慢慢卷成球,越搓球越大。
搓绳的时候,是父亲最轻松的时候。父亲在饭店当“白案”师傅。“白案”是相对于煎炒烹炸的“红案”,专做面食的。父亲每天黎明即起去店里忙活。天亮街上有行人时,父亲和其他师傅一起做的油条、面饼出锅了,包子、馒头也出笼了。每天晚上,他擦着汗水,在店里和好一盆盆的发面才回家。平时父亲言语不多,这时话匣子打开,竟有些滔滔不绝。许多年以后,当我有了儿女,当我的儿女陪着我时,我会想起那年的冬季,每天晚饭后,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搓草绳,在昏暗然而却又是温暖的灯火下,对我们侃伉侃而谈的情景,体会到父亲那时安逸而满足的心情。
母亲静静地坐在桌旁,时不时停下手中针线活,细眯着眼,抬头把目光落在父亲身上,接着缓缓地举起手,把穿着长线的针头在头皮上挠挠,又把目光温暖地落在我和弟弟身上。
父亲告诉我们,我们的老家在泗州,就是那座位于淮河与洪泽湖交叉口的古城。后来有一年,——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黄河泛滥,占了淮河水道,大水淹没了泗州城,这座城就陷到洪泽湖底了。我们的老祖宗当时是守城的武官,城被淹了,老祖宗就带着一家人流落开了,一代代的后人散枝开叶,直至你们的祖父祖母带着我来到草巷口,在这块巴掌大的地皮上搭建了这两间房屋,总算有了存身之地。父亲说到祖宗曾是泗州的守城武官时,双目炯炯有神,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自豪感。讲述到后面一家人四处流落时,不免连连叹息。父亲告诉我们,我们和大滩那边开澡堂的李家是宗亲,当初搭建房屋时,这家人出了力,堂屋的两扇门就是那年冬季你大爷家送来的,要不,我们怎么挡得住一个冬季的寒风呢?这两扇门禾木硬料,柏木膛子,油光乌亮,上半截镂空雕花,下半截实木浮雕,雕的是梅兰竹菊四君子。走来过去的人都觉得这两扇门与我家的房屋不相匹配。这时,我才知道这两扇门的来历。
父亲有时说古,说我们居住的古镇的来历和传说,还说过神仙鬼怪的故事。说得最多的是他随着祖父祖母“抗战”时期“跑反”的事,祖父祖母和父亲那时受了不少惊,吃了不少苦呢。有时不知不觉夜深了,弟弟搓着搓着草绳,忍不住张开嘴打哈欠。父亲的肚子咕咕叫了。肚子叫似乎会传染,我的肚子也咕咕叫了。母亲问我,肚子饿了吧?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道该说饿还是说不饿。母亲起身洗几头山芋,切成段,盛在一只小瓦罐内,架起两块板砖,搭成一个简易的灶,顿上瓦罐燃起稻草。山芋炖熟了,打瞌睡的弟弟来了精神,睁大眼睛盯住盛山芋的碗。母亲从糖罐里刮了些白糖粒,撒在弟弟碗里,收回勺子时,又向我碗里抖了抖,然后盛一碗笑眯眯地端给父亲。
我想起母亲盖上荷叶烀的山芋,又香又甜,比这炖的山芋好吃多了,可我和弟弟很少能吃上。我们忍住不吃,是让母亲多卖点钱。
临上床休息时,母亲注意到后窗空出一个格子,蒙在上面的一块塑料布不见了。原来我们教室的窗户缺了几块玻璃,老师鼓励同学们自力更生,我就偷偷揭了这块塑料布钉到教室的窗户上去了。母亲问清事情原委,没有批评我,她卷起一团稻草塞进空格子里,寒风被挡在屋外,屋里顿时暖和了许多。
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搓了一个冬季的草绳,开春备耕时卖了,卖的钱够我和弟弟上学交学杂费。
每年大雁南飞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就来了。
他们夫妻俩是拖着一辆架子车来的,车上层层叠叠堆满扫帚,这些扫帚是用红高粱杆扎的。他们的家在淮河边一个叫“河桥”的小山村里,那里盛产高粱。每年秋后,夫妻俩扎了扫帚,就拖到我们镇上来卖。他们起个大早出发,赶到我家门前时天已经擦黑了。我站在门前台阶上,望着他们把架子车傍墙停好。巷道很窄,两辆架子车相向而行时,双方要擦墙才能错过。他们挥起扎在头上的白毛巾弹弹身上的灰尘,然后从车上取下一捆高粱杆,铺在我家屋檐下,又铺上一片麻袋,夫妻俩并肩坐下,舒舒服服地喘口气。夜里,他们将倚在檐下围着棉被入睡。他们从黄布包里取出一张面饼,撕成两半,一人半张吃起来,这就是他们的晚餐。我跑进屋内为他们倒一茶缸热水。妻子接过去喝一口,抬起头来望着我微笑。丈夫从车把上解下一只水壶,水壶的外壁磨光了,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他拧开盖子,仰头呷一口,咂咂嘴,一丝红晕涌现在脸颊上,壶口飘逸出浓烈的酒香,原来水壶里盛的是烧酒。他又从布包里摸出一头蒜,掰下一瓣,慢腾腾地剥了皮,递进口中嚼起来。我望着他满足的神情,竟有了品尝一下壶中之物的冲动。这是一个魁梧的男人,阔身板,大脑袋,脑门禿了,亮晶晶的,一双眼睛特别有神,炯炯地盯住过往的行人。喝了酒,他掏出装烟丝的荷包,卷支烟,眯起眼,有滋有味地起吸起来。
母亲告诉过我,他们是我家的远房亲戚。“抗战”时期,祖父带着一家人“跑反”,曾在他家住了些时日。那偏僻的小山村庇护了山民,也庇护了我的祖父祖母和父亲。不能亏待他们,我们欠人家的情分。母亲多次叮嘱我。这几年,他夫妻俩年年来卖扫帚,每次来,母亲都请他夫妻俩进屋铺稻草打地铺睡,这样暖和些。我家吃晚饭时,都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喝粥。他们不肯,坚决不肯,怕给我家添麻烦。每次来,都睡在屋檐下,吃饼时只喝我家一缸热水。
许多年以后,有一次我路过河桥,因贪恋淮河风光,小车开上河滩,陷进泥淖里。这时,有几个山民帮我把车推出来。我看见其中一位老人,高大的身板,硕大的脑袋,顶谢了,脑门亮晶晶的,似曾相识。我想问问他姓甚名谁,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我已不记得这对夫妻的姓名了,而我的父母亲早已作古。
这对夫妻一大早就推车沿街售卖扫帚。一天,二天,有时三四天,卖完了,他们就拖着车回去了。临走时,他们悄悄丢下那捆高粱杆。母亲舍不得拿来烧锅,用这捆高粱杆扎了十几把扫帚分送给左邻右舍。母亲的这手活计,就是这家妻子教的。
他们在街上售卖扫帚的时候,街上有淮西人拖着架子车来卖长条萝卜干。有淮河南边的人骑自行车来卖桌凳。这些卖桌凳的人一人一车,几人一列,每辆车上桌凳都叠架得高高的。他们车技真牛,像杂技演员似的,车子骑起来只见桌凳不见人。到了集市,每辆车上的桌凳卸下来,都铺了一大片。比他们更牛的是河东人,他们从家乡出发,划船经过高邮老湖来卖盆,卖缸,卖瓦罐。船靠码头后,也是一人一车,车上垒起盆、缸和瓦罐,用几根草绳绑住。盆、缸和瓦罐垒得比人高。我有时恶作剧地想,要是路中间有个土坷垃怎么办呢?真想听听瓦盆、瓦罐摔地的声音,然而一直没见他们摔倒过。
天气越来越冷了,可街上做买卖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西山里有人用“三蹦子”拖石灰、石子来卖,河东人家挑了水芹菜、白藕和剥了皮的菱角米来卖。河道里一只只帆船逆流而上,有人在岸上拉纤,那是下河人运来一船船青砖、青瓦来卖。返程时,他们运走一船船木材和毛竹。这些木材和毛竹是顺着长江放排放来的。最好玩的是有个老头牵几只猴子在集市上耍。几只猴子一会老老实实地表演,翻跟头,朝行人作揖。一会耍沷,抢小伢手中的零食吃,吓得伢们号啕大哭。老头像天上的大雁一样,年年这时候来,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又要到哪里去。旁边还有一对苏州来的中年夫妻,摆张长条桌卖梨膏糖,一边卖一边唱歌,歌唱得软绵绵的。有几个山东来的妮子每天下午上街卖糖串葫芦。她们穿着花棉祅,扎着红头绳,扛着插满糖串葫芦的毛竹竿,挤在穿着灰色、黑色、蓝色、黄色和杂色棉衣的人群里,分外引人注目。
西伯尼亚寒流来临了,这是广播里播报的。草巷口和西大街一样,街头巷尾都拉了广播,一只只架在木柱上,每天三次定时播报时政新闻和天气预报。我们听惯了广播,早上听着广播里高亢激扬的歌曲起床,中午听着现代京剧吃饭,晚上广播声停了,我们上床钻进被窝。
这股寒流来得突然,说来就来。那天早上我是被冻醒的,被窝里没有了热乎气,人像是掉进了冰窖里。睁开眼时,见窗外天色阴沉,才记起夜里西北风在屋外呼啸。想到上学不能迟到,我咬牙掀开被窝。弟弟怕冷,哭着闹着不肯起床。母亲端来一个瓦盆,抱来一束稻草在瓦盆里点燃了,把弟弟的棉祅棉裤举在火盆上烤热,穿在弟弟身上。火熄灭了,袜子没来得及烤,弟弟又哭了。母亲把弟弟的袜子塞进怀里,焐热了,取出来帮弟弟穿上。
母亲把早饭端上桌时弟弟又哭了。今天早饭熬的是玉米粥。玉米是粗粮,难以下咽。我家大米不够吃,母亲娘家在西山,那里多产旱粮,一斤大米能换二三斤玉米,母亲换来玉米才够一家人吃到月底。我转着碗吸净玉米糊,碗底被吸得干干净净。母亲从腌菜缸里掏出一把黄灿灿的腌菜,洗净切碎,盛在盘中滴几滴香油,哄弟弟吃下一碗玉米粥。
每年霜降后,街上家家户户腌青菜、萝卜干。镇南郊有个蔬菜大队,这个队只种蔬菜不种粮食。每天清早,菜农们挑着粪桶穿街走巷倒马桶,到了腌菜时节,又沿街逐户送青菜、萝卜,算是回报。这时,家家户户都忙着晒青菜,洗青菜。洗好的青菜沥干水,一层菜一层盐码进缸里。萝卜洗净切块,下盐暴腌,又翻出来晾晒,算好日头晒好,用开水烫了,再晾晾,拌了椒盐下坛。这个时节,街头巷尾,凡是能晒到阳光的地方,不是晾晒着青菜、雪菜,就是晾晒着萝卜干、萝卜条。腌菜是霜降后各家各户的头等大事,一家老老少少,全凭缸里坛里的腌菜下饭,才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呢。
腌菜时,母亲挑出一些又嫩又大的青菜棵,一棵棵晾在厨房的屋檐下做“风菜”。晾些时日后,青菜棵干巴了,取下来洗净,开水烫了,切丁,拌一小把虾米,洒几滴香油、醬油,菜丁吃在口中格嘣嘣脆。
母亲每年腌一缸菜,才够一家人吃。凉拌咸菜,清炒咸菜,饭锅头上蒸咸菜……咸菜熬汤。一个冬季,一天三顿全是咸菜打滚。咸菜烧豆腐、黄豆炒咸菜,就是打牙祭了。
天气真的寒冷,太阳却出奇地亮,天空也出奇地蓝,蓝得没有一丝杂云,更让人觉得清冷。我们放下棉帽上的帽檐出门,耳朵还是冻得疼。随便哈口气,便在眉毛上凝成白霜。我们一路上流着清水鼻涕,跳着蹦着去学校,脚趾和脚后跟还是冻得疼,后来渐渐冻麻木了。早上起床时,母亲见我穿的塑胶底单鞋没鞋垫,怕我双脚冻坏,揉好两小团稻草垫进鞋窝里。弟弟戴好棉手套滚着铁环一路小跑紧随着我,到了教室外,他的手指已冻僵了。路上行人稀少,我们见到两个卖草的汉子,裤脚束了稻草绕子,腰里束根草绳,把草担挑进西大街,弯了腰双手捂住耳朵立在屋檐下等待售卖。草市上没人,不少人还赖在被窝里呢。母亲买了半担草,晚上要用这半担草铺床取暖。
下课的时候,班上同学分成几组,或“斗鸡”——抬起左腿相互撞击。或“挤油渣”——在墙角排成一队朝前挤。女同学三三两两的踢毽子。有两个调皮的男同学偷偷跑出学校到小河边溜冰。夜里,小河悄悄结了冰。正溜得开心,冰面裂开,这两个同学掉了下去。幸好河水不深,仅湿了他们的裤子,他们艰难地爬上岸,朝教室跑。进了教室,人已经冻得讲不出话了,班主任老师慌了神。我想到这时候全镇最暖和的地方莫过于澡堂,便提醒老师。班主任老师又喊来一位女老师,两位老师一人背起一位同学朝澡堂跑,我们几位男生跟在后面。没跑多远,女老师跑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这时,侉子正好打狗路过。他丢下死狗,接过女老师背上的同学。
侉子四十来岁的年纪,黝黑精瘦,披一头长发,操着一口南腔北调旳口音。当地人把南来北往的外来人口,不管是侉子还是蛮子一律都叫成侉子。侉子不怕寒冷,成天穿一身油浸浸的黑衣裤。到了冬天,他就穿上夹祅。不过,那件夹祅也是薄薄的。他一年到头穿草鞋,再冷的天气也是光脚丫子穿草鞋。他以打狗为生,常年扛一条枣木棍,棍头上挂一团拇指粗的麻绳,游荡在东乡的坟地和杂树林里。他打了狗,剥皮,吃肉。冬天里打了狗,他有时背到集市卖了,换点钱——本地人只在冬季才吃狗肉。天长日久,他宰的狗多了,身上有股煞气,有时路过村庄,狗狗吠成一团,吓得躲进屋里。待他走远,又钻出来远远地朝他嗷嗷嘶吼。侉子孤身一人,初来时睡在小河边的“二帝宫”里。这时的“二帝宫”已没有了香火,墙倒殿塌,夜不遮风。我那开澡堂的两位堂哥舍不得他,让他晚上睡在澡堂内。他饱一顿饥一顿,有时肚子饿了,跑到父亲的饭店里。父亲下一碗面条给他吃。面条碗里撒了胡椒粉、蒜末和葱花,还抹了一团猪油,香喷喷的。侉子吃完面条,不走,在灶下帮父亲劈柴、烧火。
当这两位同学旳家长赶到澡堂时,见他们家的小调皮正坐在浴池内的宽木凳上披着棉被喝姜汤。浴池内暖和和的,放寒假时,我和小伙伴们一早上常钻进来玩游戏,讲故事,澡堂到午后才上客呢。这两位同学身上暖和过来了,脸色红润润的,而背他们的两位老师和侉子还瘫在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等侉子缓过劲来回去捡狗时,死狗还在地上躺着,冻得硬邦邦的。
这一天滴水成冰,不少低年级同学在教室内被冻哭。老师不授课了,带同学们做广播体操。
晚饭后,母亲不像平常那样坐在灯下缝缝补补,而是掀开两张床的铺盖。我家东头屋里一张床,父母亲睡,厨房里靠墙搭张床,我和弟弟睡。母亲在床上铺了稻草,铺平展,盖上麻袋片,麻袋片上又盖上垫被,再在垫被上盖一床被子。我们睡觉时,把棉祅棉裤都压在盖被上,母亲睡前还为我们灌了“汤婆子”。
母亲铺好两床铺盖时忽然愣了神,口中喃喃地说,可怜小扣子家鸡窝里都没一把草,他爷俩怎么挨过这个冬天呢?小扣子是我家对门那家人的孩子,和我弟弟一般大,他从小母亲就跟人跑了。他父亲是个剃头匠,人又笨又懒,每天挑个剃头挑子给人剃头,一天下来剃不了两三个头,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家养一只母鸡,鸡要下蛋了,就用爪子在地上扒个窝。逢年过节时,母亲没少接济他家。
我们母子俩每人夹一捆稻草敲开小扣子家门,他父子俩挤在床上正冻得发抖。我们把稻草捆解开,母亲指挥他们在床上铺好稻草。
整个冬季,是澡堂的旺季。每天午后,澡客们陆陆续续就来了。有的人是来洗澡的,有的人是来泡澡的。泡澡的人多是一些上了岁数又有点钱的闲人,他们要泡到晚上澡堂外的木柱上升起桅灯时才回家。步出澡堂的时候,他们往往掏出一两个硬币,在桅灯下的零食摊上买一包椒盐花生米,讲究的人再掏点钱,到卤菜摊上切些猪头肉或是剁只五香兔胯,揭张油纸包了,回到家喝两盅老酒,才钻进被窝里。
晚上七八九点钟是澡堂生意最忙的时候,澡池里人挤人,人挨人。后来的人插不进脚,就蹲在池外,用毛巾抄水朝身上浇,等前面的客人走了才能入池。
澡堂是李家大老爹二老爹合伙开的。这家人与我家是宗亲。大老爹是位盲人,生下来就瞎眼,一辈子没见过这世界是个什么模样。他成年后娶了乡下的一位盲女,即我的大婶娘。大婶娘是后天瞎眼的,瞎眼后脾气特别急躁。我瞎大爷脾气也急躁,他拄根铁棍上街——是铁棍,不是木棍或竹篙。不小心与人撞了,瞎大爷就抡起铁棍,我瞎你也瞎啊?当然,他是吓唬对方的。但我瞎大爷从没对大婶娘发过火,家里家外总是逗我大婶娘开心。身为盲人,他知道盲人的苦,作为先天瞎,他知道后天瞎尤其苦。我瞎大爷眼瞎心不瞎,人特别聪慧。他从小拜师学艺,吹拉弹唱,评话,口技,样样精通。后来,县上编县志,“民间艺人”这一章里头一个记载的就是我瞎大爷。我大婶娘又瞎又麻,从小害了天花,但模样正,身板好,嗓音脆。婚后,夫妻俩四处卖唱,瞎大爷拄根铁棍在前面摸索着走,大婶娘右手搭在瞎大爷肩上,左手抱把月琴。瞎大爷背的乐器就多了,二胡,笛子,笙,箫……除了表演说唱,瞎大爷还掌握盲人谋生的独门技能——算命,“打时( 打卦占卜之类)”。当地人相信盲人打卦占卜时通神,灵验。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自古以来明眼人从不抢盲人这饭碗。东乡里庄户人家丢失头牛崽,或是跑了只猪秧子,都请瞎大爷“打时”,都说“打”得准。
我二大爷命运就顺得多了,家里本来就不穷,读了几年私塾,又坐船去扬州上了几年新式学堂,能写会算。他人又长得齐整,年轻时跑码头做生意,见多识广,赚了些钱。后来结识一位富家女,那女子死活要嫁给他。这位富家女成为我二婶娘时,她娘家砌了这座澡堂做嫁妆,轰动一时。当时高邮老湖西北岸四乡八镇就我们镇有澡堂。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不舍得花钱花功夫来洗澡,只有临过年了才来洗把澡。这座澡堂建于“抗战”胜利那年,院墙上至今还有“光复”“胜利”的字样,是一座只供男性顾客洗澡的澡堂。建国后,地方政府干预,说男女平等,女同志也要洗澡。后来到“三八妇女节”这天,澡堂不接待男顾客,专让女同志洗。当然,服务员换成女性了,她们全是澡堂男员工的女眷。
二大爷心疼瞎哥哥,怕他年老了吃不上饭,就哄大哥,说兄弟俩合伙盖澡堂,让大哥掏出卖唱攒下的几个钱。澡堂开业后没两年,二大爷就把他瞎哥哥当初掏的钱以分红的名义给退回去了,以后年年让他瞎哥哥分红。等到瞎大爷二大爷老哥俩上了岁数,两家各由一个儿子——瞎大爷家是我二哥,二大爷家是大哥,兄弟两接管了澡堂。两家的其他几个兄弟早年参加了华东野战军,他们主动放弃了对澡堂的继承权。
这澡堂原是我瞎大爷二大爷家开的,后来“合作化”了,但仍由我大哥和二哥负责经营管理,我和弟弟就沾了光。这年的冬天特别冷,每天晚上我们都去蹭澡。掀开门帘进去时,见我大哥,那位戴着眼镜,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门边噼噼啪啪打算盘记账,卖“筹子”——两寸来长的刻了印记的竹片,是付了钱下池洗澡的凭据。
跑堂的小伙是我二哥。二哥人长得像我大婶娘,身板正,模样好,皮肤白皙,当然,他是个健全人。二哥为人开朗,整天乐呵呵的,客人一进门,不管二哥在忙什么,都抬头笑脸相迎,亮开嗓子喊一声:来客啦。请客人落座后,把客人上装叉上墙。墙上端立着一排木楔,衣服叉上去,防盗,又不打褶。客人脱光衣服,二哥递过来一条白毛巾和一双木屐。待客人穿上木屐,不忘提醒一声:慢慢走——他怕客人滑倒。客人出浴时,身上不断浸出热汗。二哥麻利地折一叠毛巾,浸在滚水里,提出来拧干,左手托着这叠热毛巾,右手抓一条,飞快地在客人的前胸后背擦汗珠。前排的客人要热毛巾,二哥右手托起一条,热毛巾打着旋花飞出去,正好落在客人怀里。澡堂分外间里间,里间又称雅间,一律是躺椅(外间一律是座椅)。客人出浴后,喜欢躺下,请二哥敲背。二哥手法娴熟,力道不轻不重,敲得客人筋酥骨麻。敲着敲着,客人就打起呼睡着了。一觉醒来,客人排出几个硬币来,二哥递过去一盏红枣姜汤。客人吃了枣,喝了姜汤,浑身上下热乎乎的,穿衣回家。
就在滴水成冰的这天晚上,二哥被人打了一顿,打他的人是公社治保组长。这人酒后来泡澡,进门时,二哥正低头拾掇木屐没看见他。治保组长见没人理他,气不打一处来。下了浴池,他轰出池里的人,用木杠顶上门,一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池内泡澡。光屁股的澡客一个个在外边冻得打颤也下不了热水池。大哥是个斯文人,干着急却说不出话来。二哥上前在门外赔笑脸,恳求治保组长高抬贵手。治保组长开了门,叉开双腿让二哥跪下。二哥瞪圆了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可望望身后一众冻得哆嗦的澡客,垂下头来扑通跪下。治保组长左右开弓连抽他几个耳光。
来年夏天,有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徐州人歇在澡堂内(夏天卖给谁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澡堂歇业。这位徐州人是个武把式,膀大腰圆的,热衷于摔跤,每天早晚在院子里锻炼。他锻炼的方式与众不同,一口大缸里盛满黄沙,他光膀子抓住缸沿,把缸掀起半边来转来转去。这时他臂上的,腿上的,后背上的疙瘩肉都鼓起来,令人羨慕。有一天,他和二哥喝了几盅酒,两人都有些醉意,说要切磋一下。我们几个小伙伴围着他们看热闹。二哥的家就在澡堂的大门旁,一明一暗两小间砖墙草顶的房子,澡堂的院墙就是他家的前沿墙。他从家中拎出几只大小不一的石锁,也光了膀子。我们见他一身腱子肉,白渗渗的,身材上下匀称,如果纹了身,活脱脱就是一个《水浒传》里的浪子燕青。他抓起那只最大的石锁,反手扔过头顶,另一只手接着,又反手扔过头顶,右肩接着,右肩抖一抖,石锁跳上左肩……自始至终,二哥的眼里一直含着笑意。那位徐州人提了提石锁,朝二哥拱拱手,顺了眉眼,讪笑着走到一边去了。
我后来问二哥,那位治保组长打你时,为什么不还手呢?二哥的眼里射出两道精光,攥紧了拳头,瞬间松开手掌,转脸对我一笑,那么多人要泡澡,厮打开了,还泡得了澡吗?
晚上洗了澡回家时,见老舅来了。老舅是借匹骡子骑来送大米的。我家没有牲口圏,骡子来了没地方拴。老舅说拴在院里,给它披件棉被就行。母亲递把刷子给我,让我给骡子刷毛。她掰了掰骡子的牙口说,不行,它牙口嫩着呢,会冻坏的。让我把它牵在堂屋里过夜。老舅在西山的一家石矿上当矿工,他是干重体力活的,硬是从牙缝里省下些口粮送来,怕我们饿着。
我们在骡子旁边的地上打了稻草铺让老舅睡。我和弟弟来了兴致,巻了床上铺盖过来,和老舅挤在一起。
这一夜大雪。
天明时,雪还没停,纷纷扬扬地下。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了亮晶晶的冰挂,屋顶、路面全被大雪覆盖,天地间一片白茫茫。东头大滩上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很快又被飘落的雪花覆盖。雪地上顿了几担柴草,一会工夫,柴草担子被白雪覆盖了,像一个个雪堆。卖柴草的汉子们缩头缩脑地躲在纪大奶奶屋檐下避雪,不停地哈着手指跺着脚,却不见纪大奶奶开门。早饭后,有几户人家来买柴草,还不见纪大奶奶开门。
母亲不时站在门口朝大滩望去,满天飞舞的雪花里,整条巷道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寂静得让人心慌。母亲匆匆来到纪大奶奶家屋外拍门,屋里没人应。母亲推开门,见纪大奶奶躺在床上已僵了,一床破棉被被蹬在床下。
母亲哇的一声哭开了,纪大奶奶孤身一人,走了都没人知道。母亲心疼得不行。
开澡堂的大哥和二哥,还有打狗的侉子……开磨坊的老夫妻,来到纪大奶奶家料理后事。他们翻了半天,米坛是空的。一只木箱里装了几件旧衣裳。掀开锅盖,锅里有半碗山芋干子粥,已冻上了。二哥想抽下房梁拆了门板为纪大奶奶钉口棺材,房梁又细又弯,还有两根房梁是毛竹,开不了料。房门是柴火棍钉的,外面蒙张油毡。二哥蹲在地上叹气。
父亲扛出两根木材,这两根木材是我家准备打张床的用料。我和弟弟睡的床是几块木板拼的,砖块垒的床腿。我们渐渐长大了,父亲一直张罗着要为我们打张床。父亲出门时,提上老舅刚送来的半袋米,犹豫片刻,又放下米袋。母亲提起米袋对父亲说,背上吧。邻里帮着下葬大奶奶,这冰天雪地的,不吃口饱饭,哪来的力气呢?说完,母亲红了眼圈,转过身去。
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纪大奶奶下葬时,我带几个小伙伴正在米厂的仓库里玩。澡堂对面,紧邻着纪大奶奶家有座青砖青瓦的老宅子。父亲对我说过,这座老宅子是纪大奶奶家祖上的,传到他父亲手里败了家,他父亲就持杆秤开了草行。前些年,院里建了所大房子,安装了机器,机器每天轰隆隆开起来加工稻米。仓库里的稻谷堆得高高的,我们溜进仓库在谷堆上干仗。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小芹子对我撒了把稻谷,我一把推倒她,抱着她打滚。正干得热闹,小芹子母亲来了,是来喊小芹子回家吃饭的。见我压在小芹子身上,她妈不由分说拉起我,揪着我耳朵到我家告状。我母亲听了,拿过扑衣裳的竹篙就抽我。刚抽两下,芹子妈瞅着小芹子的神态,拦住了我母亲。母亲抽我一下,小芹子的嘴角就咧一下,似乎抽我比抽她还疼。芹子妈笑着说,不打了,不打了,以后两个小冤家真好上了,倒要跟我结仇了。母亲一听,也乐了。后来我见了小芹子脸就红。母亲有次见我脸红,手抚我头顶,望着小芹子背影说,我儿长大了。
转眼过年。过了年,我十三岁了。开学时,我去初中一年级报名。刚开学,我收到一封信,信是从北方一个海滨城市寄来的。小芹子的父亲是位石油工人,在这个城市的海滩上开采石油,小芹子随母亲去了这个城市。小芹子在信上说,等到春暖花开时,她回来看我。
雪,一天天融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