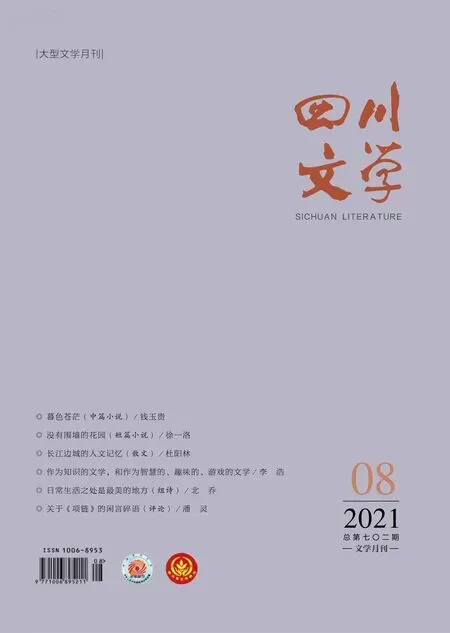烛燃烛灭
2021-11-11鄞珊
□ 文/鄞珊
一
白昼落幕,家汇街亮起了鳞次栉比的灯火。冬夜,寒风驱赶着收工人的脚步。一天劳作后的晚餐可以坐下来慢慢享受,灯火和炊烟、家里的杂语是冬夜的热炉。吃饭的时候,冷不防半掩的门被小心推开,有人站着,敲着手里的碗:阿婶,给点饭吧。这声音不用问就知是乞讨的,隔三岔五,几乎饭食时分都会有的。要饭嘛一般就是要点饭的,有时也给他一点钱——这里的乞丐叫“乞食”,顾名思义,很简单。
他站在门口,一根竹竿当拐杖,竹竿顶着一个麻布袋,就是他的全副家当了,他手里的碗伸进我家里,并且顶开了挂正门的竹帘。我们就看到他的碗和手,还有后面暮色掩映的影子。来晚了,我们刚收拾好饭桌,剩饭已经放在后面灶台上。外婆说:等一会儿。铁锅里的剩饭吃到后面差不多就凉了,何况已经洗干净了锅。外婆把装在盆里的剩饭又用小锅装起来,开了风炉,把饭热一热。热好了,倒在他碗里,他忙不迭地道谢:谢了啊!外婆说,先别走,再加点萝卜干吧。我忙往后面灶台跑,帮外婆先把萝卜干拿了一个,外婆撕开一半,放在他碗里的粥上。
加热的饭,把他的心头给热到了,他站在门口,眼泪汪汪说:你们心肠真好!
这话语让外婆受到鼓舞,连连说:“饭要趁热。”我也顿生兴奋,我们平淡的粥此刻翻腾起美丽的波澜。若我们围着饭桌吃饭时他们倚在门口乞讨,给盛上一碗粥他们是不肯罢休的,只有把盘里的菜分点给他,一家人不由得赶紧加快了筷子的速度。因为,吃饭时分要饭的来得特别多,他们同样需要吃饭。我们再慢吞吞吃饭,恐怕菜盘里的菜都没了。我们有饭菜,没有理由不分给站在门口等候着的他们。
卑微的人不经受夸奖,夸奖之后的外婆,她的头一下就变大了,外婆在乞丐面前慷慨大方,不仅给饭,还拼命掏钱,看有没零钱可以给,所有的口袋都掏遍,有点掘地三尺的坦荡,一定要掏出一个钢镚给门口等候者。
带着孩子的要饭者,不会空手而过,我们家还有些不要的旧衣服,完好的。我们会找出这些给他。外婆甚至会跟乞丐搭讪,问是哪个乡,为啥要出来要饭。他们会如实告诉我外婆,是哪村哪镇的,有的还拿着公社大队的证明,因为壮汉出来乞讨,有好吃懒做之嫌,他们需要找出证明自己乞讨的原因。
看着要饭的汉子跟外婆搭讪,他身边的小男孩盯着我家局促的客厅,好奇地探看我的作业。我突生悲悯,从铅笔盒拿出了私藏的一块糖,“给!”他伸出手,边抬头看了他爸,紧紧地攥在手里,我告诉他:“要剥开纸,才能吃。”
他怯怯地看着我,把手里的糖攥得更紧了。
家里要没啥东西,那吃饭时就得把门关住,不然乞讨者站门口,让我们挺为难的:要知道,食物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盈余的,衣物也是。我们的日子是在度量着钱、米、煤炭这些具体实在的东西,月底紧巴巴了,还得艰难地熬过余下的一段日夜轮换的时间。
可是关住门,却无法关住跟外婆要钱要东西的亲戚。外婆周遭有很多双向她伸过来的手,外婆好像是取之不尽的源头。殊不知,她在竹器社领到手的退休金,顶掉旧债,再除三去四,仅仅过了半个月工资告罄了。
我和外婆刚从竹器社领了工资到家,阿城舅已经坐在我家里等候。我一看就来气,我不跟他打招呼,直接甩给他个横脸就“噔噔噔”爬上楼,而他根本不在意我的脸色。我知道他算得很准——外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间他算得比竹器社都准,三十来岁的阿城长得人高马大,本是种田插秧的一把好手,可既然有一门小城镇上的亲戚,理所当然地就该给他点什么。
外婆是他姑妈,这便是至亲的义务了。外婆现在却不给,因为十多天钱前阿城才来过。
“你肯定去赌博了,赌输了!”外婆一说就来气了。一语中的,阿城不语,把头垂低了足足一分钟。
他转而哀求说:“阿姑,我赌钱的债得还清,还欠三块五。”
外婆今天拿了工资,光天化日之下的钱,是逃不过阿城的赖皮。轮到我外婆不语,坐了有半个钟头,只有拿着包着的布包,走到里面房间,这么多钱是不能给阿城看到的。
外婆拿了两块钱出来,豪气地甩给他说:“去!这钱拿了去还债!让我知道你再去赌,我不再给你一分钱的!”
阿城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就拿着一笔不小的钱,随即写满笑意,连招呼也不打,掀开竹帘走了。
隔天,阿城的哥哥阿憨也闻讯而至。吃番薯长大的阿憨同样五大三粗,一身力气,他倒是老老实实干庄稼活,可惜的是,老婆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撒手人寰,家里面少了一个干活的娘们,两个孩子没人管,生活过得有一搭没一搭。嗷嗷待哺的孩子没娘养,让我外婆一直心疼,他每每来要钱,外婆一般都舍得给,可阿憨拿了钱是不会给孩子买吃的,钱一到手他就沽酒喝,喝个酩酊大醉打起孩子来。
一看到阿憨,说来说去,不外乎从孩子说到庄稼,他能把庄稼伺弄得有各种收成,这倒是让人放心,但阿憨说到最后还是离不开这动作——伸手要钱。这下外婆啥话都不用说,还能说啥呢?阿城都给过钱,能不给阿憨吗?外婆又掀开布帘折回房间,一阵“沙沙沙”老鼠翻东西般的声响过后,她拿着5块钱走了出来。
阿憨拿着钱溜出门,外婆还在后面不停叮嘱着:“看好孩子,不许喝酒!”
阿憨的大孩子阿吉才五岁,一个人拾荒,拾到我家门口来,在我家斜对面的垃圾堆里翻翻找找,希冀拣出可以卖钱的东西。我赶紧跑回屋里告诉外婆:“阿吉在那里!在垃圾堆里掏东西!”
外婆走出门朝阿吉喊:“来,阿吉,过来!”阿吉怯生生不敢过来。外婆掏出两毛钱,准备叫住阿吉塞给他。
阿吉都不敢叫一声“老姑”,他不敢看我外婆,阿吉就是不敢来我们家。外婆走到垃圾堆边,低头哄着他:“阿吉,怎么出来了?”外婆跟阿吉说了好多话,阿吉就是不吭声,低头看着垃圾,最后他拿了外婆递给他的钱。
阿吉拾荒竟然攒了5块钱,这么大的一笔钱可惜阿吉还不懂藏着掖着,他不知道亲叔叔阿城虎视眈眈呢,阿城哄骗他:借阿叔一下,马上还给你,阿叔跟你爸说好了。
阿吉的5块钱成功地进入阿城口袋。
这个镇没有围墙,这消息似水流渗到家汇街的每一户人家。叔公他们摇着头叹息,我都瞪大了眼睛——读小学的我已经觉得这狼叔叔匪夷所思。我把自己的储钱陶罐捂得紧紧的,藏到床铺底下的旧衣服堆里面。外婆在家里发了很久的呆,她在阿城又一次来要钱时,对着他大发雷霆!
那把老藤拐杖恰到好处地派上用武之地,这是戏曲里才有的拐杖,是佘太君端坐舞台中间发怒之威的道具,看来外婆的潮剧没有白看。外婆积聚平生的火力朝阿城开炮,她用拐杖敲敲地板,用那有力的手指点点阿城的额头。她丹田十足,咬牙切齿,眼里喷发出怒火:“这么个没娘的娃!没个人照顾,没饭吃,你还拿他的钱!”
外婆手里这把黄藤拐杖,配合话语,一句一敲地砖,让我很是担心这地上的红砖不经敲,今天就委屈地砖遭罪了。外婆说到气处拐杖飞起,就快敲打着阿城的头颅了!外婆这种杨门佘太君的气派,倒不是来自姑母的身份,而是来自平时被掏的腰包。
“你还有脸见人!说!把孩子的钱拿到哪里去了?”阿城支支吾吾,平时伶牙俐齿的他此刻语言极度贫乏,他不断狡辩,声音却被外婆大分贝的话语和拐杖的敲击声掩盖了。
“我要把你老婆也找来!”外婆把阿城轰走了,这次他甭想在我们这里掏到半个铜板。
小阿吉的钱是甭想从阿城那里要回来,早被他花掉了。我们安慰着外婆,母亲也掏出几块钱,我们一块凑给了阿吉。阿吉可是比我还小三岁的表弟啊,我妈看着也心疼不已。
阿城阿憨他们兄弟居住的大宅院,里面基本是外婆娘家的人,每个家庭占据大院子的一角,或是一两间屋子。院子里辈分最大的是婶辈的文婶婆了,唠唠叨叨的文婶婆是院子的看门人般,看着各家的喜怒哀乐而跟着或喜或忧。
矮小的文婶婆从村庄来,她每天起早贪黑,忙完了庄稼地里、家里的,好不容易有空出来卖完菜,偷空来镇里找我外婆控诉,话题自是阿憨他们兄弟俩。说起阿城和阿憨两兄弟,文婶婆直摇头,都是三十左右的年轻汉子,就是这副德行!说实在话,阿憨就喜欢喝酒并且偷懒而已,还不像阿城那样招摇撞骗违背良心。
“最可怜的就是阿憨那两个没娘的孩子啊!”文婶婆说到这,一把鼻涕一把泪,她只有用衣袖擦了。
在那个宅院里,只有文婶婆弄点吃的给这两个孩子,可气的是阿憨,“一点都不看顾孩子,就知道喝酒。”只是文婶婆自己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操心多了。她不断感叹自己:“我劳碌命!”人有多善良就有多少挂心,有多少挂心就有多少负累。
文婶婆回去了,阿憨却不停地来,自是跟外婆要钱,他从没空手而归。他的背后是那两个小孩子,亲戚们看着就心软:阿憨就是眼睛小点,那眼睛还有胆怯的神色,特别是开口要钱的时候,话题总是得走过几里路,才不好意思地进入钱的门槛。给完了钱,外婆照例叮嘱道:看好孩子!你有吃的要给孩子吃。
母亲也不忘给表哥阿憨些钱,阿憨却在我母亲面前显示出了忸怩局促,毕竟拿的是表妹的钱,于他好像有些良心上的坎。我发现血脉的亲与疏,极其有趣,一棵树长出的枝丫,各自的分叉,隔一层就是一层的疏离感。阿憨在表妹面前,究竟不比自家姑母那般亲。
外婆开始叮嘱他,要让孩子读书。
二
阿吉突然到我家,却是来送喜糖。
从门口闪进来的高大身躯,却有一张透着稚气的圆脸的阿吉,甚至不好意思跟我这个表姐打招呼,照面一个腼腆的微笑,直接就到里屋找我妈——表姑母去了。
这一闪的身影,我发现他竟然比我高很多,从小学到初中竟然是一个身量的飞跃,才读完初一的阿吉,心智也跟身量一样早熟:他要结婚!阿吉的对象是一个大他三岁的初二女同学,阿吉有点忸怩而又掩盖不住兴奋,在我妈面前有问必答,介绍着自己的婚事。
我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知道很多失去母亲的男孩子,喜欢找比自己大点的对象,并且对家庭的渴望显得更为迫切,哪方面欠缺,愈是需要在哪方面弥补。此刻正冲刺中考的我们,“结婚”这名词的嵌入真是觉得匪夷所思,何况他还是比我们更小的年龄。
这喜讯甚至冲掉了“结婚”里面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包括母亲的担忧。可惜外婆已经作古了,我妈为阿吉这比一般人提前了许多的婚姻感到欣慰不已。
跨越了腼腆的阿吉,原来也伶牙俐齿,他一口气说完了安排:“已经选好日子,下个月的初十,几位姐姐和阿姑都要来喝我的喜酒啊!”现在他的喜气冲出了心理重围,转向了我们这几位表姐。
他的大婚自己安排,下聘礼、选时择日、喜席的地方、位次的安排……我没想到他那么熟谙传统的礼节,竟然层次分明,说得头头是道。
“我那女同学家,他们要我先通知我们这边长辈。”他只能管他的对象叫“女同学”,这里没有大城市“女朋友”的叫法。
虽然阿吉读书慢,且有一搭没一搭地上学。“阿吉,你比我小几岁?”我突然冒出了一句,其实我只是想落实他究竟比我小2岁还是3岁。
阿吉有点虚张声势,他知道我们在乎他现在结婚的年龄,他扬起脸说:“我都15岁了。”我随即回应:“不对的,姐姐我没那么大了啊!”阿吉只好把年龄又往回走,说:“是14了。”
我计算着这年龄也不那么吻合,但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阿吉显得比我更有主意,他铺展着自己的前途:现在不读书,结婚。然后在舅舅那里打工,他舅舅刚开了个颇有规模的手工作坊,生活好转的舅家对他兄弟俩一直关照着。
阿吉提前进入的婚姻生活一时安慰了很多关注着他的亲戚,这样尘埃落定的幸福日子快得就像猝不及防的雷阵雨。我外婆从没想象到阿吉成家这样令人宽慰的未来吧?!只是外婆在阿吉来报喜之前已沉溺病榻三年,刚刚先一步走了。
当外婆一头栽倒在里屋门口后,床铺成了困住她的地方。躺卧床上的外婆慢慢干瘪下去,高大的身躯萎缩得像失去水分的橄榄。
病榻上的外婆身体越缩越小,思维也缩回时光的那头,夜晚她不停地敲着床铺,敲得手都烂了。我匆匆起来,打开灯:“阿嫲,什么事?”我看着她,她神志清醒,眼睛有神,她说不出什么事。近八十年的人生有多少往事需要诉说?多少结未曾解开?
阿公阿嫲在客厅
客厅通地块
通到后院花园边
花园开花白披披
人人来到姆敢摘
秀才来到摘一枝
外婆在自己病痛的煎熬中度过她人生之残年,那样的日子,她越来越退化,退化到只有人生的本能:吃喝撒拉。外婆离开世界前的时光,她的灵魂被囚禁在这肉躯中,动弹不得。这个“中风”的名词是如此可怕,它像巫婆的扫把,对她的血脉一代又一代地逡巡着。外婆的灵魂渐渐暗淡,暗淡的灵魂很低,低得看到阴间的事物。
生命的油耗完了,接受洗礼不久,外婆这盏灯就熄灭了。
父亲借来了手推板车,外婆的身体被裹上了草席,像包裹搬到了板车上。父亲用力推,我紧随着,双手把着外婆这个像婴儿般的包裹不要掉下。
父亲和我用板车把生命潮汐已退的外婆推进外公那个祠堂里,都说人死前必须进祠堂,不然灵魂在外面游荡无所依,要趁没断气前就进入门槛。我和父亲终于在黑夜里赶到了这个大公用厅。
把外婆放在临时的木板上,我坐在她身边,小祠堂堆满稻草,属于外公的那一角耳房紧闭着,门楼内的几户近亲紧闭着门,唯恐死人的晦气跑进去。可旧式的木门还是泄出一线屋里的灯光,我借着这点亮光捻着手里的念珠,为外婆送终。
外婆的身体只剩下点温度,没有气息,生命的潮水退了、退了,她的痛苦也离她越来越远了,最终回归于安息。那个大宅院所有的人家都紧紧关着门,他人的生死别离却是自己的恐惧和忌讳。外婆不时会回来跟看望这“门楼内”的三亲四戚,可现在外婆的离去别说没有人愿意陪伴,连看一眼都怕,像躲避瘟疫。
父亲叮嘱我看紧外婆的遗体,不让老鼠靠近,他必须连夜赶去异地传报凶信。父亲母亲半夜三更分头去通知舅父姨妈,病榻三年,虽然都是我们伺候着,可人一死,男女之别便分出来,她是属于儿子的,我们得尊重属于她宗祠的人,一切后事儿子说了算。
现在只有我一人在她身边,父亲母亲分头去通知舅父姨母。
我摸着外婆的身体,还有温度。我跪她身边,手里数着念珠念痛苦玫瑰经,我戴着念珠,刚才慌乱之中我还是记住这个物件,一路上把手里的念珠攥得紧紧的。现在,各家躲进厢房里,天井连着大厅,四周空荡荡的,老祠堂改成的房子,一边放满稻草,梁上黑乎乎,特别是后院,有井,连接一片竹林,夜在这里体现它的幽深和惊悚味道。以前我晚间不敢进后面打水,而此刻,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得看护好外婆,不让扰乱的魔鬼和老鼠靠近。
左边厢房的阿婶灯光还亮着,透过紧闭的门缝歪歪斜斜把黄色光亮隙漏了过来,让我能看清楚外婆沉睡的身子——原来长眠就是这样了。我知道,今晚过后,我就再也触摸不了她,当她换上寿衣、整个成了硬邦邦的尸体,那不是她了。我念完了所有能念的经文,摸了摸发麻的腿,继续念。
外婆的灵魂渐行渐远,身体却像睡觉了,越来越冰冷,我用手触摸她的鼻孔,一直没有鼻息,此刻她沉沉入睡,就像没摔倒前那般,那样宽松悠闲的状态。
夜越深,她的手脚越冰凉了——
我摸着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这具熟悉身躯的灵魂即将离开我了。
我从出生后便跟着她,她油亮的头发、她的宽大耳垂、她手上的老人斑,她的大脚趾丫上的趾甲裂痕我都熟悉,她的呼吸从什么时候变得喘重,伴随着身躯的沉重,老牛拖车,却力不从心,越来越拖不动车了。
在这座旧宅一侧的厢房里,我随在她身边睡觉,半夜醒来,看着她熟睡的身躯,想她会不会沉进另一个世界醒不来?于是我偷偷用手探外婆有没有鼻息,没有呼吸人便是死了——这是我最初始的科学知识。我害怕外婆离开我,我再三探她的鼻息,她睡得很沉的鼻息沉重地冲击着我的手,热气拍打我的手指。
现在,气息和灵魂离开了她的身体,她真正离开我了。寂静的夜,此刻只有我守护着她。
第二天,她遗体僵硬。厅堂上人来人往,各色人等突然而至。
外婆的遗体任由人们摆布了,人们给她换上可怕的寿衣:头上扎着白帽子,身上整套白布衣,三年不着鞋子的双脚给穿上了一双崭新的布鞋。
这不是外婆的模样。
她应该戴着她那顶羊绒编织的褐色帽子,帽子中间有个金灿灿的如意扣,这如意扣既能端正帽子,也映得外婆神采奕奕,让我以为人一当上外婆便是这般穿戴。这种白色宽布衣外婆没穿过,她生前只穿黑灰色斜扣如意钮的大同服,或是短袖对襟衫。外婆一直干净利落,清清爽爽。
这个家族的小祠堂在第二天的阳光照耀下很快热闹起来。丧事跟喜事一样都是一门热闹的事情,有许多角色浓重登场了!
大妗矮胖的身躯带着洪亮的声线一下杀入灵堂,她一把掀开外婆身上盖着的寿被,大声责备外婆:你的钱哪里去了?!怎么一点钱都没有了?!
闹哄哄的大厅一下肃静了,众人的声音全部回避起来。大妗的声音足够覆盖整个祠堂,连同堆叠得高高的稻草都被压了下去。
大妗继续怒斥着被放在棺材里的外婆:你每个月的退休钱,在哪里?我们三年前过年时还给过你四块钱,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
我那性格倔强的母亲此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的眼泪哗哗哗地流淌!我不明白母亲平日里的硬朗和心直口快的语言怎么突然卡住了。母亲多少的委屈,除了我们所知的,还有多少我们未知的,外婆卧床的三年,作为儿媳的大妗来看过她一次,就是拿四块钱的那次,大妗在门口打住了,皱着眉头说:“有股味道。”她用手捂住鼻子,不停地用扇子驱散味道,最终没进里屋。
外婆的床榻是有股味道,再怎么清洗,也无法消除没晒阳光、屙屎屙尿的酸臭味。这股味道让儿媳妇退避三舍,再也没来过,包括外婆一直惦念疼爱的孙子孙女。
大妗继续大闹,整个祠堂安静极了,外婆应该也听到了,她的灵魂应该还没走远,会不会在梁上看着我们呢?
阿连婶偷偷地对四姆说:“她这样,不好,不好的。”旁边七老姨和陈婶眼睛不约而同地瞄了过去。七老姨自是倚老卖老,自个儿喃喃道:我姐这辈子不用吃饭呀?!你告诉人家是不是喝西北风就能活呀!我看着母亲流泪,想冲过去,告诉大妗,外婆的钱是怎么花的!我的衣角被阿连婶拉住了,昨晚她家的灯火亮着,她今儿才出来。她唯唯诺诺地说:你一直给外婆端屎端尿,阿婆知道,阿婆知道。
唱功德戏的已经齐整,他们一帮人端坐灵堂前,开始敲起锣打起鼓,就着几盏拉得透亮的火油灯,一字一顿唱将起来:
听念三世因果缘
因果报应非小事
若人深信因果报
同生西方极乐国
父母一生深恩情
儿女需要尽孝道
不孝儿孙下地狱
阿妗的声音被他们洪水般的说唱漫过,熄灭在锣鼓声下。
功德戏的男声高亢,唱给死者听?不,唱给生者看。功德戏的老者拖长尾音,颤抖着手里的长三弦:“今生——来世。”
领唱的中年男声又突然飙起高音:
养儿育女,备受艰辛;年老体衰,儿媳床前;子女成人,理应孝顺。不孝不顺——
老者紧接着喊:“善报——恶报——”
一整天的功德戏完,锣鼓声戛然而止!
三
父亲再一次去外婆娘家的村庄,阿憨家的大宅院里空无一人。
父亲迈进大门,左边厢房找了几间,右边都坍塌了,院子里的破杉木椅断了胳臂,和稻草堆一块,看出已经烂了好久没人理会。大厅没门了,剩下了两个凹槽,告诉人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大院里本来住那么多户自家宗族,搬进搬出,现在几乎都搬走了。但父亲听说阿憨一直都住这里,现在看这个荒废的样子,门都没有,里面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
天井里荒草丛生,油麻石的砖缝隙冒出葱绿的草儿。父亲犹豫再三,想往回走,可又踌躇,毕竟专门来了一趟,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被淹没的老宅。即将离世的阿憨还能在别的地方吗?父亲不甘心被这荒宅所吓退,只有顺着花巷,一间一间黑暗的房子找。
父亲边朝每间黑屋子找,边喊着阿憨的名字:“阿憨——阿憨——你在吗?”
踩过一堆横放的门板,走过五六间无人的屋子,后厢房那里终于传来一声极其低沉的回应。
父亲一喜,赶紧朝声响的方向寻去。
阿憨在黑暗的那头,回应着父亲的叫声。
父亲的脚步声渐近,黑暗的角落以渐渐明晰的视线迎接着他。大厅后面,花巷右转,后巷子一头那昏暗的角落里,有床铺,有脸盆,有人的生活痕迹。后厢房已经没有房间的样子,只有屋梁和下面几处象征房间的老杉木骨架横斜着,靠着外墙。有屋顶的厢房,连着门的木板已经拆掉了,角落有一个床铺,一个身影躺在那里——应该是阿憨无疑了。
父亲多年没见他,现在亲人已经不多了。辗转而来的信息:阿憨病得快死了。别离是至亲所牵挂的,父亲辗转找到这老宅,没想到阿憨竟是这样一个人躺卧在这里!
若死了怕是没人知道的。父亲心里面咯噔了一下,首先产生出顾虑。
见到父亲,阿憨很高兴,空荡荡的房子边上有几个空瓶倒在一边,巷子一边有个炉子,锅碗瓢盆萧条地躺在那里。父亲皱了皱眉头。虽然阿憨基本无法进食了,可这整座破落的院子里就阿憨这残留的气息在苟延着。
有谁来帮你吗?父亲问。
“我妹他们晚上会来一趟,看我有什么需要没有。”阿憨说,“阿武媳妇也会来一趟。”阿武是他的小儿子,即是阿吉弟弟,阿憨也说不出他在哪里打工。儿子成了家总归了却一宗大事,至于儿子的家,他从没建设也就不敢索取。
“不过,生病了儿媳妇有时也回来看看。”阿憨满足地说。
两个老亲戚,从共同的亲人聊起来,回忆是一剂最好的安慰剂。
父亲刻意回避谈阿憨的病情,阿憨撑起右手,用枕头垫背,父亲帮他把棉被也垫上,这样可以坐起来说话。
说到阿武和儿媳妇,这些现在时的人和事不构成记忆,也平淡无可聊起。渐行渐远的阿吉却是父亲阿憨绕不过去的话题。
阿憨“唉”一声开启了回忆的模式。
“那时我被通知去上海,阿城和我同去,两人咋就不晓得要求赔偿呢!”阿吉在舅舅工厂做工,工厂业务扩大,他随即被派到上海负责业务。后来自己单飞做生意,把舅舅踹了,正因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阿吉却再也没有回来,据说在那里也有了女人,老家这边的家庭一直凉着,阿吉不再回来了。
“本来若是跟家人有正常联系,失踪也会知道的。”阿憨叹息着。
阿吉去收款时被对方预谋杀害后,人世间没有谁发现这世界少了个人。直到公安局破案后,通知到村里。作为父亲的阿憨,在弟弟阿城陪同下,第一次到大城市,却不知道是领儿子阿吉的骨灰盒回来。
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啊!父亲也是道听途说,才得到第N手的消息。这些口口相传的消息,梳理了脉络,便是两句话:阿吉丢下老婆孩子一直在上海,阿吉死了好久都没人知道。
“我们在上海那里,就是不懂提赔偿的事。”阿憨还是这句话不断地重复着。
“我和阿城回来后,很多人都说,应该要求赔偿。可惜了,本来应该赔偿好多万。”
阿憨无不惋惜,这个赔偿,按村里人的说法,下半辈子够吃够喝的。想不到,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就那样没了,连一分钱赔偿都没有。儿子生前也没给他半个子儿,在老家的阿憨一直期待儿子在大城市的发达和以后的富贵,哪想到人却一下没了。
阿憨一直给村里的工厂看门。“看门好,有地方住,有了工钱还可以喝酒。”现在喝酒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不愁没肉下酒,养阿吉兄弟俩时,就是因为连一点下酒的菜都没有,火辣辣的酒直接进入肠胃,硬生生把胃肠给烧坏了。
阿憨总结说:“就是那时候给搞坏的胃,现在就得了这绝症。”阿憨还是惋惜那时候酒中没肉,连素菜都没有,其实园子里的菜都在烂掉,青菜有什么稀罕?又没有油。
父亲陪他坐了一会儿,环顾左右,怎么烧开水呢?想问阿憨要不要喝水,看到缺角的长木几下面有热水瓶,我父亲问他:“这个里面有水吗?”
阿憨这才想起需要招待客人,不好意思地连连说:“你要喝水吗?连杯水都没招待你。”
父亲说:“不了,我就看你需要不,我帮着你。”
阿憨看着热水瓶说:“也好,里面还有水。”
父亲拿起热水瓶,在茶几上拿了他的碗,倒出水,发现水都是凉的。
阿憨说,没事的,这是昨天我妹过来烧的。阿憨凑过嘴,拿过父亲递过来的碗,呷了一口,就没再喝了。阿憨又感叹表妹——我的母亲走得太早了。
人走着走着,发觉都走丢了。
父亲留下几百块钱给阿憨用来买吃的,晚上他妹妹会来一趟,让她买些想吃的东西,话必须这么说,皮包骨头的阿憨生命力那么坚韧,按科学说法,这么多天不吃东西都维持不了生命的。
这老屋子,好像也在等着他这盏将灭的灯火熄灭。
几天后,阿憨妹妹来向我父亲报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