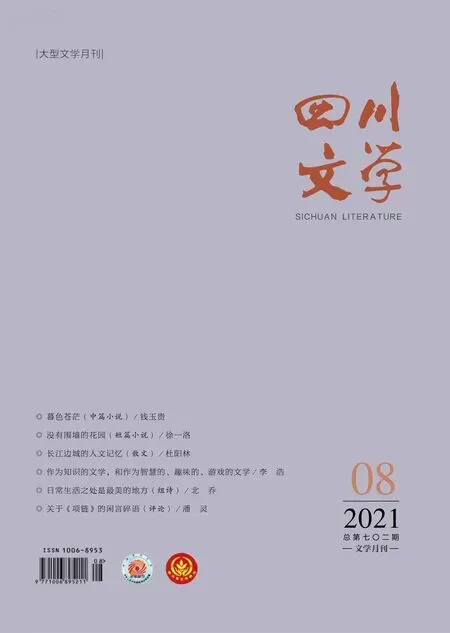江边
2021-11-11王晓燕
□ 文/王晓燕
她每天都出门去,打算自己找点事做。几次迷路之后,她不敢再走太远。午后离黄昏到来之间的那段时间显得很长,令她最不好过。走出小区的大门,沿着两边的马路来来回回地走,至今她都搞不清那些站名和路线。有一回坐过了站,搞不清方向,她新婚的丈夫在手机里导航了一阵,她哭起来了,他只好放下工作开车过去接她。拐了个弯,就已经看到她常走路的那条街了,看她气急败坏的样子,丈夫说:“我只管你这一次。”她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在生气。
她是在夏天跟着丈夫到这个城里来的,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有种到了世界另一边的感觉。
她想尽快融入这个全新的世界,丈夫答应会帮她找一份工作,仿佛是为这个,她才跟他结婚的。好多天里,她隐在窗帘后面,看那些下了班匆匆赶回家去的女人。丈夫会在十二点准时出现在他们暂时借住的房子里。他紧紧地拥抱她,好像他们已经半个世纪没见过面了。这种时候,一切都像是曾经梦想过的样子。
“我们可以顿顿吃食堂,只要你开心就好。”
嫁给丈夫之前,她的脚几乎没有踏进过厨房。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嫂嫂,除了在自家的超市里卖东西,她的手没干过别的。她的丈夫在一个外国人投资的公司里工作。同事都喊他朱总,朱子俊只是个部门经理。
“可我想出去工作。”
“这个。不急。”
朱子俊在老家娶了她,在村子里庆祝了整整两天。又在公司办了一次婚礼,她穿了婚纱,有摄像机追着拍她。影楼将她的照片做成了巨幅广告牌,悬挂到街上去,朱子俊差点跟那伙人打一架。朱总的同事都以为她是个模特。
“不幸得很,因为我太小气,使我的妻子没能成为模特。”
这话引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跟我妻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上学时,我就追她。”那是朱子俊第一次那样称呼她,有点骄傲,还有点不自然,然而,他应付自如,她感觉自己欣赏他这点。
“你看别人的眼神差点就像个妓女了,像什么话。”
朱子俊笑着说的,她便没有生气。
慢慢地,她才知道,丈夫不是一般的小气。他常常冲她又吼又叫,只允许她待在房子里,若有人看她时,她必须得低下头。
“你是我老婆,我管哪门子礼貌。”
她再也不敢提想要出去工作的话,她只有在丈夫上班后才敢走出房子。她从未经受过这般炎热,像有一个环形燃烧的火炉四面围着炙烤,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可炎热丝毫未退,不过,海风随时带来湿润,人的面颊、衣服成天潮乎乎的。她撑着阳伞,穿着一件长裙,凉拖啪嗒啪嗒拍打着她的脚底和地面。这条街上,只有她一个人,经过的车辆都很少。西边,环着几栋高楼。东边,是个破破烂烂不规则的玻璃房。从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传来类似于风铃般若有若无的响声,在这无边的空旷里很是诡异,不像是起自她处身的这个世界。暗旧的招牌上,看不清写着什么字,白天,玻璃门上一直挂着锁。马路那边,是几家酒店,海鲜店的门大张着,有点杂乱。那天问路时有人告诉她,这片地方是军区,属这个城市比较偏远的地方。她还从未走过大桥那边去。
“你是说火车站啊,那你得过江去哎。”
在某个午后,她从桥底下穿过去,来到江边,滔滔江水奔涌向前,向着故乡的方向。江面上漂着一两艘船。她从未坐过船。
朱子俊出差了,这天她没去食堂吃午饭,而是吃了一堆小孩子吃的零食。这些日子,她和朱子俊真的天天到食堂去吃饭。遇上朱子俊那些男同事的目光,或是稍有些过度的调侃,她总是不合时宜地低下头。她还做不到在食堂里自如地取餐,她担心放在盘中的食物会有人盯着惊讶地看。她感觉难以应付那些眼光和嘴巴一样刻薄的女人们,尤其当她们聚在一处时。相比,那些男士对她更热心,也更善意得多。但再没有人敢随便帮她什么了。她很想加入女人们的圈子,只是还未学会端着餐盘坐在她们之间空出的一张椅子上恰如其分地说上点什么。
若有若无的风铃声一直追着她。她感觉,秋天不是在这个世界里,而是从她内心里开始的。
一间没有家具的空房间,谁也不知道它是在期待运进家具还是想把它清空得更彻底。她感觉受了欺骗。
A
杨林啪啪拍打窗户时,她还睡着。开了卷闸门,她去洗头,杨林跑出跑进将烟酒牛奶洗衣粉一样样从那辆小货车上搬到超市里,再一样样地替她摆放在货架上。清早的风从树梢也从庄稼地里吹来。
“要不要把窗户打开。”
她垂着一头湿发说,随便你。她从发缝里瞧见杨林的胳膊和双手,并没有在夏天里晒黑,淡蓝色的血管清晰可见,他的衣服总是很洁净,鞋子不像是在这遍地黄土的地方走过。
杨林一个人住在对面山尖尖上,两间破房子孤零零地立着,随时都会被一阵大风吹跑的样子,杨林的父母还给他留下几亩田地,别的什么都没再给他留下。自打父母去世后,杨林再没往地里种过一粒种子。
杨林在她洗过头的水里洗了手,将水洒在外面的土路上,再拿一把扫帚哗哗扫了过去,他挥着扫帚时,腰像那扫把一样直,两只手臂起劲地舞动着。她的几个哥哥和母亲说,杨林看上去,不像个会吃苦的人。杨林扛着扫把返回来时,她吹干了头发,太阳正朗朗地照进了超市,照在她身上。有人走进来买东西,跟杨林大声地说着话,她坐在里间的镜子前往脸上涂面霜,再涂了一层粉,衣架上挂满了衣服,一只化妆盒里装着几只耳环,她挑选了半天,最终将一对金光闪闪的穗子戴在耳朵上。
杨林已经打发走了三个在半路上停车走进店里来买烟的顾客,收来的钱放在玻璃柜台上。她看了一眼,没有将它收进装钱的盒子里去。
“今天多拿了些花露水,”杨林说着打开一瓶往屋子里喷洒。“闻到这个,人们就晓得夏天快要到来了。”刚才他就卖出去了三瓶。“对了,差点忘了。”杨林往外走。她开了一瓶酸奶,喝了一口,甜得让人反胃,猝然之间,浓郁香气兜脸扑来,一捧鲜花伸了过来。
她开心极了,眉眼间漾开不由自主的笑意。
“那个花店,刚开张,全是新鲜的。人得为自己寻开心。”
“你咋知道我不开心。”她的眼睛与他刚进来时不一样了,她从架子上拿过花瓶,将里面还未枯掉的几枝芍药扔掉,将那捧玫瑰百合满天星插进去。芍药是她从家中的花园里摘来的。
“我就知道。”杨林低着头,背靠着货架,双手支在上面。
她嘁了声。
“你干吗不往土地里种庄稼。”
站在超市门外,可以看见在庄稼地里劳作的人,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土地。
“我将来要到城里去,等我攒够了钱。”
“就凭你给人送货?”
他抬眼迅速看了她一眼。
她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晓得。但她的眼睛,看他跟看别人时不一样,就因为这个,杨林天天都起个大早,将小货车开进县城时,几家店铺才刚刚开门。有时,他只拉了几袋洗衣粉来敲她的门。
“一会儿我要去给二哥拉水泥去。”
“哦。”
“给你带双子镇上的乔粉吃,晚上等我。”
她的眼皮一下翻上去。他又说,“别吃晚饭,等我。”
他的脚搁在门槛上。
“你适合待在城里。”她大声说。
他的脚抬起来,迈出了门槛。太阳一下照射下来,刺目的亮。他往前走,低头往前走。她早早穿上了那件束腰的白裙子,腰带恰到好处地衬出她的细腰长腿,他想,那双腿,在期待着去哪里奔跑,而不是被困在这里。
“你是个有心人,城里的姑娘一定会喜欢你的。”她走出来,背靠着窗台,对着他的背又说道。
杨林停住了,转过身来,盯着她看了几秒,跨着大步又走回来了。
她想逃。她喜欢他身上洗发水的味道,他洁净的样子,他懂她的样子,偶尔,她感觉他懂她。
“只要你说一句,你会等我,我今天就去城里找活干。”他的脸贴着她的鼻尖。
他将她心里的焦躁抚平。他也会让她的期待落空。一阵风吹来,将她额前的卷发撩开,她的目光越过远处的树梢,在终于回落到他脸上时,那眼里讥笑的意味就深了。她几乎跟他一样高。他是个高个子,眼睛会探测人心的小伙子。
他将她一把拽进了屋子里的阴影下。她被挤到墙上。
“你疯了吗?”她猛一下将他推出去,货架上的糖果方便面往地上掉,他跌坐在地上。他将一只火腿扔出去,不知哪里响了下。
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脸颊上化的妆花了,赶紧补妆。她需要躲在那下面。
小货车发出一阵轰响,她坐在那里听着,在那条车道上,杨林不知留下了多少刹车的印痕。
这一整天她过得没滋没味的,不断有人走进来喊着她的名字,在一排排货架前寻来探去一番,将要买的东西放到她面前,她懒得称呼他们一声。她是个藏在浓妆后面的女孩。
“你小时候,是个机灵鬼。”他们一边拎走了装在袋子里的食盐和醋,或是烟和牛奶,一边盯着她的脸说。
杨林没给她送乔粉来,马路上不时有车开过,她听着那声响,也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吃乔粉。三嫂电话过来,说要上山来换下她回家去吃饭。她说吃了方便面和鸡蛋,还喝了一罐八宝粥。三嫂说,看小心长胖了。她听出来三嫂有些失望,哥哥们在改造房子,准备建成度假村,加上干活的人,一次得做一二十人的饭,想起来都熬人。三嫂只不过是想出来放松下。几个嫂子里头,数三嫂最有头脑,度假村就是她的设想。其实玄麻村里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夏天凉快,三嫂在快手上晒了玄麻村里的风光,有人向她打问,能住宿不。三嫂怂恿弟兄们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接下来的规划,是将村里的河水围成一个湖坝,如果老天成全,每天都猛下暴雨的话,就有望在湖坝里养鱼划船。
小时候她脾气很坏,村里人都不敢惹她。她没干过农活,也没做过家务,有空就抱着乱七八糟的闲书看,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找到工作。她的嫂子们私底下认为,她已经被全家人宠坏了,不知天高地厚,不过,她倒不是坏心眼的那种女孩。
没有人来请教过她那些关于书的事。她读的,尽是些没用的,无以回击他们对于现实的疑问。
她的哥哥们建了很多房子。她和父母住在果园旁边的四合院里,大哥在县城当老师,几个哥哥在城里都有房子,为的是小孩上学。从村小学后面才修起来的马路上走上去,就能看见杨林的破房子。
站在公路上,也能看见杨林的破房子。超市开在公路旁,两条公路在超市前面汇合,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经过那里。她哥哥本来要卖化肥的,可村子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就开了超市。父母不许她出门去寻找理想之事,只想把她嫁到朱家去。
黄昏慢慢到来,金色的光不断地从窗玻璃和柜台上撤退、消隐,她早早开了灯,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无聊地张望,白天,她在电脑上看了十三集美剧。她是村子里唯一的剩女。那些从外乡嫁过来的小媳妇,哪个是哪个,她都对不上号。她们在田地里嬉闹耕作,或在雨天聚在一处做针线活,只有买东西时,她们才来找她。
半夜里,她听见下雨了,沙沙的雨声罩着她,无尽地罩下来,她越睡越清醒,开了灯,翻看手机,杨林没有发消息给她。平时,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她发很多逗笑的话,就算她一个字也不回,他还是发。
明天几点去县城,我也要去。
给杨林发微信的同时,她想起来了:明天朱子俊要来。
天微明,杨林拍门。
“我想我去不了了。”她隔着窗子对他说。
“你不会开心的。”
她分辨不清自己是不是听到杨林说了这个。在很久以后,她想起这句话,就像是一声诅咒。一阵马达声,她感觉自己的心已随着它去了。
站在杨林的破房子上头,可以看见朱家山,那是玄麻村里的富人区。那里的人或靠做生意或被朱氏兄弟带出去做工赚到了大钱,每家人的房子建得都像一个庄园。可惜的是,庄园越来越空,年轻人都跟着朱子俊走了,只剩下些老弱病残守着房子。
几年前,朱子俊邀杨林一同去远方谋生活,杨林打算留下来。朱子俊每年回乡两趟,每次都备了厚礼去见她的父母和兄长。朱子俊也会到山上杨林的破房子里去。
“如果你想跟我走,就收拾下行李,我后天离开。”
杨林没说话。
“我要去小麦的超市买点东西,一起去吧。”
两人出门,下了山,过了河沟,再爬山,上到高处。
朱子俊拿出一只礼盒,让她打开。小麦看了眼杨林,杨林看着她。
她没有打开盒子。不久,她穿上了那件白裙子。杨林知道是那只礼盒里装的。
朱子俊这次回来,想跟她把婚期定下来。
很多事,都已经变得跟从前不一样了。她说。她一面化着妆,一面把脑子里的一些东西掩埋掉。
朱子俊只会说那一句话:“我喜欢你,没办法。”
自那天清早起,她后来再没见过杨林。在她跟朱子俊的婚礼上,杨林也没有出现。婚后第二个礼拜,她跟着朱子俊去了南方。在南方,她穿上了婚纱,与她的丈夫又举行了一次婚礼。
她的哥哥在电话里说,杨林把她的超市盘了下来。
B
有人说,我们似乎逃不开命运的枷锁,总像是走在命定的一条路上。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总是平淡无奇。也有些时候,会有那么些意外。
那天清早,听着一阵车子的马达声远去,她将脸扑到一堆衣裙上,听着雨滴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今天将要度过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沉闷无聊的一天。想到这个,她跳下床。
“等等我,请回来接我。”
她飞快地梳洗,换衣服。一条丝巾上落满了灰,她捉起来,看到丝巾下蒙着一摞书,心里一阵暗涌漫流,那辆车子的马达声再次响起时,她正戴上那条丝巾。她记起了一些事,但车子的马达声一下就淹没了那些事。
杨林一只脚踏在门槛上,掏出一支烟,他一直盯着她看着。
当他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罩到她身上时,她感觉自己方才被那些探头探脑的事搅动得心安静不下来。锁了门,她又要打开去取雨伞,他脱下上衣,罩在她头上,把她推到了车上。
他知道她想逃跑。
杨林的眼睛俯在她眼睛上:“坐好了,听话。车子就启动了。”
上学时,她住父亲单位的宿舍,宿舍对面就是图书馆。只要父亲出差,她就躲在房子里看书。
“你考不上大学,居然是因为书看得太多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杨林大笑。
那几年,他们三个都在县城读书,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杨林和朱子俊骑自行车,轮换着将她载在车子的后座上。
“还记得我们在这赌钱的事吗?朱子俊总有办法赢钱。”车子盘旋了一阵,来到平坦之地。
“今天你怎么交代。”杨林直视着路的前方,他不想听她回忆过去。
“没想好,你告诉我,我要怎么说。”除了父亲,她谁也不怕。所有人都晓得她要订婚了,除了她自己,朱子俊是和她的父母哥嫂商议这件事的,唯独没有跟她商量。
“你只是在跟他赌气。”杨林瞪了她一眼。
她没说话。
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到了县城。
他要去吃牛肉面,她想喝一杯咖啡。最后,他们坐在咖啡店里,她点了一杯美式咖啡,他吃了一碗面店伙计端过来的面,他们打量着街上走着的行人,一切跟他们上学时不一样了。
直至这时,她才感觉乱无头绪,她不知道要来这干什么。
杨林打了几个电话,把今天要干的事都推到明天。她则把手机调到静音上,它一早上已经响了很多次。
在服装店流连了很久,她什么也不买。经过一家金店,他带她走进去,指着玻璃柜台里说:“选一个吧。”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那就拿出来看看吧。店员热情地把里面的镯子都取了出来,她选了一个最小的。他将那只镯子戴到她手腕上,用现金付了款。她觉得他把存款都带在身上。
后来,他们一起去看了场电影。杨林将她拥在怀里亲吻,她没有踢打也没有推开他。
电影院里出来后,他们一直牵着手。
雨时落时停,她穿着他的外套,他们去看了学校,她父亲原来的单位搬迁了,那里如今是一片商品楼,县城拆建得乱七八糟,没有了他们上学时那种古朴而沉静的美。
在一个小商店里,他们买了把雨伞。撑开雨伞的时候,她想到,那会不吉利。
走进公园,她脱了身上的那件外套,杨林只穿着件衬衫,肩膀上被雨淋湿了,她给他穿上外套,杨林将她包在外套里。他心里知道,回去后,她又会反悔。虽然此刻她对他从没有过的好脾气,还有爱,真真实实的爱,从她的肩膀、脖子,那双手上传递过来。
天光渐渐变暗,出了县城,山间的路浓雾环绕,她头枕在他的胳膊上,一会儿又挪到他腿上,他缓缓地开着车,一只手臂伸过去环抱着她。行到山顶上时,她睡着了。
那天晚上,她父亲大发雷霆,她和杨林在县城乱转的事,早在玄麻村里传开了。她没有吃晚饭,一个人回了超市。三嫂子上来陪她,告诉了一家人的决定:
虽然今天没有参与,她也已经与朱子俊订婚了。正式婚期定在下个月。
朱子俊回南方去工作了。朱家不时有人过来,跟她父母商议有关婚事的诸多事项。
离定好的婚期还有一个礼拜,她的哥嫂轮流去超市值班,换下她在家中准备嫁妆。
没有杨林的消息,她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她不知自己在期待什么,也不知要跟谁说点什么。她感觉对每个人都很抱歉,尤其对自己,什么也不做,每天昏睡不起。
有天午后,三嫂子进来看她,唤了几遍不见反应,三嫂子发出一声惊叫。
她被送去镇医院,杨林赶来时,大夫已为她洗了胃,她把抽屉里杂七杂八的药片全吃了。她的胳膊上缠着一圈纱布,她举给杨林看:
“太疼了。没勇气割下去。”
“我可以去城里挣钱,如果你只是嫌我太穷。”杨林抱着她哭。
“我不是真的想死。我只是很迷惑。”
“迷惑什么?”
她盯着胳膊上的纱布没说话。
杨林去城里打工挣钱了。
她父亲一边叫骂一边要帮杨林修房子,她母亲则想让女儿女婿结婚后住到四合院里来。
半年后,她嫁给了朱子俊。
C
当然,生活总会以别的方式呈现。以我们难以预料的面目。
如今,人们越来越追求实用。那些看上去没用的,在这个世上越来越少了。再少有人留恋家乡,也再没有人会在纸上为自己的恋人写字,漫长的等待,经受考验,或只是享受缓慢。
朱子俊为她写过很多封信。就在得知她差点割了手腕、差点喝了药而死之后,他依然在为她写信。他始终如一地记着他们一起上学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她感觉自己极为庆幸和感动,当有人从镇上的邮局为她取来信件,她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眼眶都湿了。可是,当她站在林子里,看着公路上的车子一辆辆经过,当她感觉到阳光晒暖了皮肤,心里升腾起一阵空茫的愁绪,朱子俊写给她的那些字,正如那林子里的雾气一样不可靠,难以触摸到她心里。
当听见杨林的卡车远远地驶近来,当他的目光布满她周身,她总能从那空茫的愁绪里挣脱出来。然而,她到底也不能跟杨林亲近。杨林只适合近看。远视,她会失去方向。她感觉现实竖起一块木板,将她和杨林隔开。很多时候,杨林的目光,以及朱子俊的文字,到达她这里时,似隔着花玻璃的那瓶玫瑰百合满天星,它们是那般的娇艳,可她总难以马上闻到花香,她得提醒自己,那是玫瑰,那是百合,玫瑰应该散发出这种味道,哦,是,这才是百合的香气,不,它有香气的,仔细辨别,你就会闻(想象出)得出来。总得这样,那些妖艳的花,总不能直接朝着她散播它们该有的芬芳和香气。
中午,她关了超市,下山去家里吃午饭。杨林和村里的年轻后生坐在他们搭建起来的门框上抽烟,远远看见她,他们像是受到了惊吓。背地里,他们会相互打趣,谁娶她做老婆,他们一点也不羡慕。他们的记忆里,总是残留着她凶恶霸道的样子。
“杨哥,去跟她说句话呀。”
“我从不巴结谁。”
那些后生大都已有了两个小孩,杨林比他们都要大几岁。
那天在医院里,杨林问她:“我娶你,好不好?”
她没说话。
杨林说:“好吧。就当我开玩笑。”
那天后,他就再没跟她说过话。他拥着她亲吻的那些瞬间,总在她的记忆里闪现。有时候,她想马上告诉他。她感觉这村子里空极了,她哥哥们建度假村像是在建造一个神话,或是坟墓,很多人离开了。
超市后面的那片林子里,生长着几棵核桃树,秋来时,有人拿着蛇皮袋子在林子里打核桃,他们伸着长长的竹竿,孩子们欢笑着,他们的后备厢里,很快就装满了核桃和蘑菇,她感觉那有意思极了。忍不住走过去帮他们捡核桃。
“你住在这里真好。”他们跟她说。但也有人问她:“你不寂寞吗?”
很快,冬天到来了,她在超市待的时候越来越少,度假村的房子已建起来了,太阳好的时候,她跟干活的人一起拿着一把刷子往木头上刷油漆,贪婪地吸油漆的气味,她觉得油漆的味道跟木头的一样好闻。
“这个丫头,从小就是个怪人,肠子跟人长得都不一样。”
她的嫂子们现在觉得,她可真是蠢。
“你究竟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为什么非得嫁人,难道你们怕我分你们的家产啊。”她说出这个,就没人敢再问她那个问题了。
不时,会听见山那边有人受惊似的喊她的名字:
“小麦,有人要买货啦!”
有时候,是她的一个嫂子替她过去为那人卖货,有时候,是某个堂弟去。他们很快就又跑回来了。
那是自家的房子,开不开,卖不卖货,都无关紧要。她晓得父母跟哥嫂都早已商议过那个超市的未来了。
过年时,朱子俊又来了。她约他在超市里见面。
“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朱子俊的个头没有她高,看着她时得仰着脸。他有点发胖,有着城里人那种难以言说的精明。她往他的眼睛里望去,杨林的眼睛,跟朱子俊的不一样,跟任何人的都不一样。
她叹了口气说:“我看不懂你在信里说些什么。”她记起,朱子俊在信里说了无数的情啊爱,可她连一点都没感觉到。那是为什么,她差点就问他了。
“对不起,我仔细想了下,我不可能适应城里人的生活。我喜欢乡下。”
“你说什么。在这种节骨眼上你说这个,让人怎么看我。”
“哦。反正你在乎的只是这个。”
他走出去后,她告诉自己,你期待过。如果他说,我就是喜欢你,我想娶你,我就收回我说过的话。可是,他答错了。
这个冬天没有落雪。一个暖和的早晨,她走进了杨林的破房子里。
没有婚纱,没有嫁妆,只有杨林的几个哥们矜持地嬉闹了一小会儿以后,漏风的房子里,就安静下来了。
有几个月,她没有回过一次娘家。家人因为她的选择而丢尽了脸面。尤其是父亲,一辈子没受过这等侮辱,他是这么说的。
她哥哥让她继续开超市,收入归她和杨林。很多时候,她和杨林住在超市里。头一年,她和杨林过得很开心。杨林总会有办法令她哈哈大笑。隔几天,他们会去县城转半下午,把她想逛的地方都逛遍。杨林在县城的工地上干活,每个礼拜还继续为镇上和村子里的商店送货。第二年,杨林去了大城市做工,到年底才回来。那时,他们的儿子已有一岁了,他们没有翻修房子,只往超市旁边另盖了两间平房。他们梦想有一天会住在城里。为此,她和杨林拼命赚钱。
“为了你,我什么苦都能吃。”
每当杨林说这个,她都会流着眼泪拥抱和亲吻他。他依然能把她心底深处的柔情搅动。
她把杨林父母留下来的几亩地里的荒草清除,哥嫂帮她种了庄稼。辛苦一年下来,她收获了大豆玉米和小麦,也累了一身病。
儿子三岁的时候,她把他托给母亲。已经没有人来超市买东西了,人们开着自己的小车一会儿就到了县城。风吹日晒中,房子渐渐破败,连林子里的树都没那么密了,核桃树上也不再结核桃。
一个表嫂回乡探亲,顺道过来看她。表嫂吃惊极了:“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吗?”
表嫂比她年长十五岁,看去却像比她小十五岁。表嫂讲的那些事,令她意识到自己心里某个角落已蒙了太厚的灰。
三天后,她跟着表嫂离开了村子,坐上去往南方的高铁。她不知道自己出去能做什么。她坐的车开往与杨林做工的城市相反的方向。
表嫂在一户人家侍候两位老人,将她介绍给另一家,那家人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孩,她的工作就是在主人上班后照看那个小孩。
开始的几天,她抱着那孩子哭,那是个只要睁眼就哭闹的小家伙,她尽量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她越用心去爱护他,那孩子越是不怕她,举着一把水枪把她赶到门外,她快被折磨得垮掉了。钥匙锁在里面,她可怜巴巴试了数种办法也没使那孩子将门打开。
那是个炎热的午后,出了小区,她缩在那些高大建筑的阴影下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她浑身都在冒汗,拖鞋磨着她的脚,她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来。街上空荡荡的,她想拦住过路的人,借个手机给主人打个电话。
有人从一辆车子上下来,冲她猛挥手。
“小麦。”
她向来讨厌自己的名字,但在那个瞬间,这声亲切又满是疑问的呼唤令她一下抽泣起来。
“真的是你!你怎么在这?”
朱子俊的手臂很自然地环上她的肩。她哭了很久。
朱子俊开车送她回去,有什么需要,一定给我说。我手机没变。朱子俊说了又说:“真不敢相信,你会出来做这个。”
礼拜天上午,她坐上朱子俊停在楼下的车子,他载着她拐来绕去了一阵,停在一个白色的建筑前面。
“天啊,那天看见你,我才知道,我一直没能忘了你。”他们坐在车子里,朱子俊将手按在她手上说。
她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他身上那股精明气更重了,现在,他是个彻底的城里人了。
以后的每个礼拜天,朱子俊都过来等她,带她去很多地方,吃各种海鲜,她爱上了喝啤酒和红酒,并在看孩子的那家人家里也喝,她让那个小男孩也尝一口,为此,两人友好了许多。
那几天下雨,他们在一个酒店的房间里待了一天一夜又一个早上,中午,朱子俊回去工作了,她一个人又待了一个晚上。
“看见你这么辛苦,我的心都痛了。”“是这样的。”她给自己说。朱子俊说这个时眼睛是湿的,她才跟着他进了酒店的房间。
朱子俊许诺要在他的公司里为她谋个事做。也许,根本她就没在等,她并不真的想去他的身边工作,一点也不想,那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时是夏末,直到冬天,那也还只个许诺。朱子俊跟她联系得越来越少了,她从没主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或是直接去他的公司里找他,她从没那样想过。尽管如此,不可避免的,她感觉自己还是沦为了她所厌恶并不屑成为的那种人。
春节来临,那家人说,她不必一定要回乡下去。那家的女主人很欣赏她,觉得她带小孩很有一套,并且,打扮起来,她的长相和身材满足了女主人的虚荣心,邻居们可雇不到个像模特的女人来当保姆。男主人,哦,当他的眼睛注视着她时,她就避开了,他对她很照顾,他容忍和掩盖了很多因为她没有尽心或是贪杯而留下的残局。
一个细雨飘洒的早晨,男主人开车送她去车站。她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你。”
他再次地问:“非得走吗,你还会回来吗?”
“也许不会了。”
他回头看她,她完全与刚来时不一样了,她的眼神也不像初来时那般迷茫。
他找话说:“谢谢你照顾我儿子。”
“我也有个儿子,比你儿子大半岁。”
他感觉没有理由挽留她了。
“你会是一个好母亲的。欢迎你带他来城里玩。你们那里下雪了,注意保暖。”
“谢谢你。”
※
她无意间听说朱子俊曾经谈过好几个女朋友。
她心里没有任何感觉,只庆幸她们都有办法离开了他。
炎热的午后,她在房子里待不住,阳伞抵挡不过烈日的炙烤,她望着江水流去的方向,想起杨林像曾经以往的她一样,如今整天站在门外晒太阳,期待着公路上会有一辆车停下来,车上的人会走进超市,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上点外边的什么事。
海风从竹林那边吹过来,那阵声响,一会是玻璃的敲击声,一会又像是瓷的叩击声,有一瞬,那响声错落散乱,忽一下叠加,清晰有力,像是一种召唤,吸引着她,走进那个歪歪斜斜的玻璃房子。
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张厚重的木桌上,摆放着一些纸,轻漫单调的诵唱声,似乎从远古时代弥漫而来,太阳也从那里照射下来,她向里走,有人迎面而来,不知所措间,她已站在那人面前了。
“你来了。”
忽而声泪俱下:
“请告诉我吧。”
“该怎么办,你自己知道啊。”
阳光的缘故,她看不清那人的脸。
“说不出来的,就请写下来吧。”那人推过来一支笔、一张纸。
炎热令她虚弱,一阵眩晕,她感觉自己终于病倒了,她的脸从浓妆里露出来,她想说声抱歉,不知道要道给何人。玻璃是茶色的,她刚才走过的街道像在另一个世界。这里,流淌着某些记忆里无用的东西,刹那的错觉,她跟那个世界之间,并非一块玻璃,而是一道深渊,她看见了一面被丝巾遮挡住了的镜子,她想拂开那丝巾,她的手指马上要触到了,那番挣扎,扭曲她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