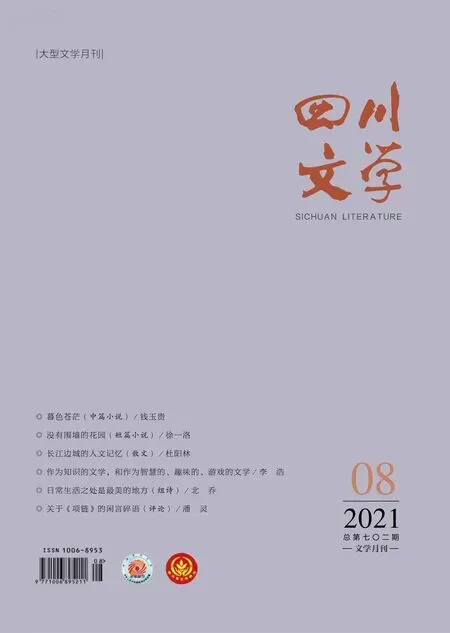没有围墙的花园
2021-11-11徐一洛
□ 文/徐一洛
一半脸黑一半脸白,那只阴阳脸的猫蜷在窗台上,古铜色的瞳孔时浅时深。推开窗,玻璃撞击着它无骨的身躯,它在空气中摇坠,来不及留下半句遗言。关上窗,所有的天空向我涌来,大地像一口深井。密不透风的新房内,处处盈漫着看不见的灰尘。
那天,是我18岁生日,喜事铺天盖地。父母20周年瓷婚纪念、父亲荣升为正厅级干部、母亲获准提前退休、我收到了某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此,父母特地选在这一天乔迁新居。180平方米的新房里,六喜临门。
父亲赠我一只金属手镯,手镯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H”,像一道密密丛丛的栅栏。父亲拉过我的手,又捋了捋我的衣袖,准备将H戴到我手腕上时,我缩了缩手,一条十厘米长的文身暴露在他眼前。他愕然,又果断地将H套到我手上。我摸了摸这一圈冰冷,将手藏到身后。母亲愧疚地说,没有给你准备礼物。我耸了耸肩。
父亲还变出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捧到母亲面前。母亲接过礼物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一条明晃晃的项链、一枚沉甸甸的金锁吊坠,亮得刺眼。父亲细心替她戴上,母亲抚着金锁,嗫嚅道,出了门就不能戴了,容易招来歹人。父亲不快地吼道,和平年代,哪会这么乱?母亲的身体一颤。父亲轻言慢语道,这个花园小区的业主非富即贵,物业也是一流的,你们就安心地住、放心地戴。父亲将手自然地搭在我肩上,我一躲。父亲说,我家的女人,绝不能受半点委屈。
花园似的三层蛋糕上,曳曳烛光随风荡漾。父亲冲母亲使了个眼色,二人向我的脸颊袭来。我迅速闪开,父亲的吻眼看要落到母亲脸上了,忽然停滞住。他扫了我一眼,尴尬地将一个生硬的吻掠过母亲苍白的脸,母亲以极快的速度抹了抹被沾湿的地方。
父亲启开了一瓶碧尚男爵干红,以优雅的姿势倒了三杯酒,我举起高脚杯正要干杯,杯子毫无征兆地碎了,裂成几瓣,差点割伤我的手。父亲说碎碎平安,母亲忙查看我的手心手背,又手忙脚乱地收拾。饭后,父亲拿出一把崭新的水果刀,替我削了一只红苹果,说是吃了就会平安。
微弱的烛光中,幸福在摇曳。
第二日,欢乐戛然而止。父亲依旧忙碌,一天仅回来睡个觉,或者接连几天不归家。母亲一退休,便报了一个旅行团,她自由了,解脱了。偌大的家又仅剩我一人。我穿着宽松的黑睡衣,在空房子里四处游荡。
新房太大了,像一张掉光了牙齿的豁嘴。一堵无形的墙,逼仄地禁锢着我,墙里的花儿鬼魅地开着。灼人的灯像一张张舌头,舌头不说话,它永久缄默。我在房子里东张西望,房子同我面面相觑。慎重的防盗门上有一个黢黑的猫眼,它无时无刻不在窥探着我。我试图走近,又止住脚步,一股恐惧的力量攫住我,拽住了我的双腿。我逃回卧室,平躺下来,大口喘气,许久才平息。这是我的新家,父亲说它很安全。
天黑了又白,白了又黑,我晨昏颠倒。无聊地打开手机讯息,17岁的男孩与母亲吵架跳桥身亡,丈夫为了房产肢解妻子,男子酒后抢劫一元钱获刑三年……无趣,关机。我吃了两颗安眠药,睡了长长的一觉,睡得极不安稳,噩梦连连。梦里有人抱走了我的腿,劫走了父亲送我的H形栅栏,甚至偷走了我的梦。这个梦让我很生气,醒来后同自己赌气。
疼。痛。从床上坐起,赫然看到床边站着两条腿。莫非是我梦中遗失的腿?我摸了摸自己,腿还在。那两条腿正缓缓移动。我慌忙用被子将自己包裹起来,裹成一只残破的茧。
你是谁?
你以为我是谁?
腿在说话,腿会叫唤。腿上生出两只手,其中一只握着一把水果刀,又将冰凉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昨天,这把刀曾替我削过一个平安果。
别叫,叫就杀了你。
那两条腿绕到我的腿前。那张脸裹着一只蓝口罩。浓重的南方口音,同握刀的手一起战栗:我以为你家里没人。
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请不要伤害我。我的声音同双腿一起战栗。
那两只手从身上挖出一根绳子,开始捆绑我的手脚,边缚边说,你家我已经来过三次了。
我天天在家,怎么没见过你?你撒谎。
我是小偷,不是骗子。他认真地说,第一次来,你家正在装修,我上了个厕所,顺手带走了你爸的一个进口打火机。
我怀疑地看着那两条腿,裤子的两个破洞对我虎视眈眈。
第二次,你家刚装修完,你们还没搬进来,但你爸来了,还带来了一个人,你猜是谁?
一个女人?可我没有说出来。此刻,恐惧是我的盔甲。
不等我回答,他就主动揭开了谜底:一个3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我不解地望着那双寒光凛冽的手。
我还拎走了你爸的名牌皮包,你猜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又是猜谜。我没好气地说,男人皮包里除了钱还会有什么?银行卡?名片?
再猜。我像超市里待售的螃蟹,努力揣测即将进到哪一只滚锅里。
笔记本电脑,烟,打火机,耳机,充电宝,眼镜,钢笔,合同,照片,安全套?我一口气说道。
很接近了。你反应很快,只是你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细节:那个小男孩。
所以,小男孩同皮包有关系吗?我斗胆问,同时试图趁机解开手上的绳索,但无济于事,我被他打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你绝对猜不到,是——一份亲子鉴定书。
我直视着他的双眼,身体仿佛被冻僵了。
被鉴定者是一个3岁的男孩。他盯着我,似乎要将我的脸盯出一个洞。我将目光胶着在他青筋蜿蜒的腿上,父亲的羊皮拖鞋掩住了他的脚。
我陡然将被捆缚的双手伸向茶几。他警觉地一把抓过水果刀。
我笑了,我只是想喝口水。他将茶几上的一瓶水拧开,递给我,我艰难地喝了几口。他开始在我房间里翻找,不到五分钟,就将我的房间扫荡了一遍。
就这些?
就这些。
我长期过着断舍离的生活,房间里所有的物品不超过30件。就连这些,我都觉得冗余。口罩背后的他审视着我,像看一个怪物。他将水果刀对着我,问: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我又笑了,这些年我有几百次都想死,最后都没死成。
想死是吧?我成全你。他用水果刀在我手腕上划了一刀。
几滴血珠涌了出来,它们穿过我手腕上的一串字母,又滴落到地面。
他抓过一团纸巾,递了过来。你的文身是什么意思?
每一次缝补也会遭遇穿刺的痛。我一字一句地说。
缝补?痛?你真的想死?他一脸狐疑。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城里的富家小姐活得比蜜还甜呢。也对,你爸有一个3岁的私生子,你和你妈肯定过得不好。
我们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可以骂我,但不能骂我妈。我怒道。一口水呛在喉间,我剧烈咳嗽起来。我干脆夸张地咳嗽着,咳得胸口绞痛,却没有人能听到。
我转过身,递给他一个清冷的背影。他将水果刀在玻璃茶几上划拉着,发出嗞嗞嗞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似乎划到我的皮肤上。在我的血流尽之前,我鼓起勇气问他:你第三次来我家是什么时候?
他放下刀,如实相告:就是前几天,只有你妈在家,你猜她在干什么?算了,反正你也猜不着。
我扬起头,看到了他头上有一处斑秃。
你妈拿着一张纸发呆,面无人色。那张纸你绝对猜不到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
咦,这回你猜对了。他抠了抠毛发稀疏的头。
想起来了,那天我到客厅倒水,母亲一言不发,一见到我,立即慌乱地藏起什么。
我还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没想到你比我还可怜。
面对他的幸灾乐祸,我轻轻一笑。心放松了,身体也不那么紧张了,被缚住的手脚不再疼痛,而是麻木。我问他:你看上去也不像坏人,为什么要……
为什么当小偷对吧?你去过农村吗?吃过存放了七年的陈米吗?过过一下雨屋子里可以撑船的日子吗?有过走12公里的山路去上学的经历吗?尝过作为扶贫对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怜悯的滋味吗……
他紧攥着刀,恶狠狠地说。
你以为我天天生活在温室里?每年暑假,我都会去五山乡支教两个月,还资助过一个叫覃韦南的孩子。
他拿刀的手抖了一下。我一个激灵,问:你不会就是覃韦南吧?
他撇了撇嘴,又不是小说,哪有那么巧?
你喜欢读小说吗?
喜欢。家里穷,买不起书,也上不起学,我读完初中就到城里来打工。没有文凭,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天天在工地上混,白天抹灰、砌墙、刷油漆,晚上在满是汗臭、脚臭、尿骚味的工棚里,听人吹牛、喝酒、谈女人。他们用辛苦赚来的钱去找鸡,还想拉我一起去。
你去了?我戏谑道。
不去,脏。工地的月收入总共也就不到2000块,一大半寄给家里,除去吃穿用度,剩下的都来买书。
这个小偷勾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疑惑地问:你都看过哪些书?
马尔克斯、莫言和高晓松的,也读西川、欧阳江河和里尔克的诗。还有一个作家叫陀思妥也夫,不对,斯托夫,野夫司机?见鬼!
我无意纠正他,莫名的同情在看不见的缝隙里滋生。我激动得差点要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套精装台版《金瓶梅》送给他,不料,他已经毫不客气地将价值5000台币的《金瓶梅》从书架上取了下来。他看了看我,冷冷地说:盗亦有道,贼不走空。
我沮丧地问,你干这行多久了?
就今年。这幢房子就是我们建的,每一块砖、每一堵墙我都认得。
那些砖和墙的主人认得你吗?
他两眼空洞地望向前方,颓丧地说,这个城市有好几幢房子都是我建的,却没有一套属于我。而你,住着这么高级的套房,爹生妈疼。同样是人,凭什么我们只配做打洞的老鼠?
我没有回答,我不敢告诉他我刚拿到了某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张通知书被父亲带到公司去炫耀了,他的亲朋和下属的孩子没有一个比我考得好。
很快他又自我安慰:你爹妈一离婚,你就是个孤儿了,你爹还在外面找了个小三,生了一个私生子,你比我还惨。我一没钱,二没读多少书,但至少还有一个完整的家。他得意地笑了。
我平静地说:你放心,他们离不了,他们都舍不得钱。
他的面目开始变得狰狞。下来!他厉声喝道。
我打了个寒战,慢慢地将身体挪到床沿,捆缚的双脚先落地,随后晃晃悠悠地站立。我幻想我因失血过多突然昏厥,但我贫瘠的血液在手上断了流,凝固成一道褶皱。
过来。他压低声音命令道。我蹦跳着来到阳台上。阳台很阔绰,上面种满了花草,像一座孤独的花园,花园里花草枯靡。三扇巨幅的玻璃窗张着大嘴,随时准备将人吸进去。父亲还没来得及为这套安全的房子装防盗网。他推开了窗。我哆嗦着,闭上双眼,准备一了百了。爸,妈,对不起,我们三个人一直都在演戏,这场戏该剧终了。
你看,他指着对面的一栋楼说。我睁开眼,发觉自己还活在人间。
3楼的男人喜欢打老婆,平均一周打两次;5楼的女人天天打骂孩子,一个8岁的男孩天天挨揍、被吼,我真希望3楼的男人打的是她……
我循着他的手指,贸然闯入一个奇异的世界。他继续指引:9楼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夜夜看黄片、自慰,还穿着女装跳舞,一会儿跳迪斯科一会扭秧歌,他退休了,儿女都在国外;20楼住的是一个房地产商,在同一幢楼买了三套房,分布在不同的楼层,他的糟糠老婆和包养的两个年轻女人都住在这里,一三五陪小三,二四六陪小四,至于周日,当然陪原配咯。还有……
我咯咯地笑起来。我不会告诉他,我时常躲在这座没有围墙的花园里,用望远镜偷窥目光所及的人家。除了他说的八卦,我还见到过一个赤身裸体在家鞭打男人的女人,一个坐在轮椅上唱歌的孩子,每周带不同的男人回家的迟暮妇人,一年365天只唱同一首歌的鳏夫……
我不可抑制地笑着,他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得我心里发毛。我用缚紧的双手抹了抹眼泪。他惊惶地说:你别又哭又笑的,我怕,我妈也经常这样。
你妈她?
她已经疯了二十多年了。
他已全然没有方才的骄傲,像阳萎一般,在我面前迅速垮塌下来。须臾,他又还原成一个自负的人,抖擞着说:你看,那些有钱的、有脸的还不是活得一团糟,家暴的离婚的外遇的变态的,有几个真正幸福的?
月亮黯淡,星星稀疏,夜风拍打在脸庞,凉飕飕的。有外室的父亲今晚不会回来,飞出囚笼的母亲,应该也回不来了。柳枝随风摇晃,弯成一个大大的问号,又扭曲成一个惊叹号。
有些冷了,我连打了三个喷嚏。他说,回屋吧。天空骤然雷声轰隆,我们是两只惊飞的鸟,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晃动。
我重回床上,茫然地望着天花板。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吊灯,像一个缺氧的病房,里面住着两个黑沉沉的人。盯天花板的时间长了,竟出现一个椭圆的霉点,严肃地注视着我。
他掏出一盒烟,在身上摸索了半天,又叹了口气道:你爸的ZIPPO打火机我放在家里,舍不得用。我拿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一样也舍不得用。你说,我把它们拿回来有啥意义?
他仍未释然,愤愤不平地说,起初,我对这些花里胡哨的品牌一无所知,我在老家只能买到山寨品牌,什么瓢柔王老古康帅傅等,来这个小区后,才发现你们同我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们天上有许多我没见过的东西,每发现一件好东西,我都会查一下价格,也因此记住了很多品牌。通常形容坏人都是用“穷凶极恶”,我唯一具备的就是第一点——穷。
我一笑。有些人只具备后两条。
他有些气馁,我现在难道不是正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你凭什么嘲笑一个努力的人?
他定定地看着我,恼怒地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我明明就是个小偷,是社会的渣滓,是盲流,是流氓!
他凶相毕露,一把将我推到床上。
我冷冷地说,你刚才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样我就不用自杀了!我抑郁症3年了,想死都死不成。
抑郁症?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打开那个相框。我看向书桌上的全家福,上面的一家三口笑得春风荡漾。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他抓起相框,打开背板。一张某医院精神科的诊断书掉了出来,白纸黑字写着:疑似中度抑郁。
他将这张诊断书看了许多遍,又反复检验我的脸。这应该是你们城里人的富贵病吧。你要啥有啥,还抑郁什么?
我怎么告诉他,我天天生活在黑洞里,被一只黑狗拼命追赶,我想逃出来,却逃无可逃呢。
他抱着头,低沉地说,我有一个妹妹,今年16岁,跟你一样,成天不出门,不上学,也不出去工作,经常离家出走,还寻死觅活的,打她、骂她都没有用。可惜她是小姐脾气丫鬟命,我爹娘养不起闲人,准备给她找个残疾的或者死了老婆的男人随便嫁了。你命比她好,生在有钱人家,你爹妈可以养你一辈子。
我又不是宠物,为什么要人养?
你成天被关在这么大的笼子里,跟宠物有区别吗?他讥讽道,你们城里人把猫儿狗儿当儿子女儿,我们这些下等人却活得猪狗不如!他亮出左腕上的一块手表,激愤地说,这块帝舵手表价值3万多块,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我们一家五口不吃不喝,三年也赚不到3万块!
他的眼神如野兽一般,撕咬着我的自尊,他的嘴角带着血腥,咬牙切齿地说,生活并不公平,我又何须公平!他钳住我的手,向我扑来。我脖子上的心形项链横亘在二人中间。我来看看这是什么大品牌。他一把扯下项链。啧啧,这根卡地亚项链至少值15000多块,大小姐,你生得这么荣华富贵,凭什么抑郁?凭什么!
我抚着脖子上被勒出的一道印痕,回避他灼灼的目光。
他的嘴唇和双手开始放肆地在我脸上、身上游走,我不知所措,如同电在身体里短了路。
他剥开了我的内衣。
他的手滑向我的鼠蹊。
我的呼吸急促而又恐惧。我已做好了赴死的决心,正当我心一横,准备束手就擒的那一刻,脑际倏忽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亲子鉴定的结果是什么?这个3岁的小男孩是谁?我的亲弟弟?我是公主,而他呢,一辈子都只能活在阴影里,一出生就被戴上了一个“私”字号的紧箍咒,私货、私奔、隐私、私情、私欲。父母会离婚吗?他们一离婚,我便成了那个二手的私货,一个落单的流浪儿,我和那个小男孩,注定只能有一个人幸福。他也会抑郁吗?不,他同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但他活着注定是个悲剧。这个孩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个卑鄙的我。
黑色睡衣被解开了,我的凹凸袒露无余。我注意到,他解扣子的胳膊有些异常。你的手怎么了?他起先将左臂藏在身后,随后又拿出来,恨恨地说,8岁那年,我一个人爬山去砍柴,不小心摔断了胳膊,我娘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帮我接骨,那个庸医接反了,结果……
我见到了一只往外拐的胳膊肘。这真像小说情节。
他恨不得嚼穿龈血:拿到第一笔工资,我就去大医院拍片子,医生说本来是普通的骨折,但现在关节处已经陈旧,无法再复原。这十几年来,我不敢上体育课,怕被人笑话;不能干重活,因为畸形的胳膊会酸痛。我被同学取笑、被工友歧视,我恨!我这辈子都记得那个耻辱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让那个庸医尝点苦头。我朝他家里扔过石头,泼过鸡血,塞过破鞋,丢过死蛇,往他地里倒过开水,在他家唯一的宝贝儿子头上揉过苍耳,披块白布半夜装鬼吓他儿子,吓得他的宝贝疙瘩住过几次院……我只是想吓唬他,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我仔细查看了那只变了形的手臂,上面缝了十多针,像一只丑陋的蝎子。它羞怯地躲藏,便向外弯曲成120度。他趁势抱住了我,我挣扎,我推脱,却被他搂得更紧了。他试图吻我,我迅速将脸别开。他仍坚持不懈地咬住我的嘴,执拗地吻了上去,笨拙而慌乱。
他腾出一只手,开始解他的衣裤,衬衣开了,纽扣也掉下来一颗,裤子却半天解不开。他懊恼地试图拉开牛仔裤拉链,手一抖,拉链卡到了他的肉。他惨叫一声。
我望着他裸露的裤裆,忍不住嬉笑起来。世上还有一个同我一样不爱穿内裤的人。他狼狈而痛苦地用眼神乞求我。我蹲下身,将左手放到他那一根上,它有些硬,我又将右手放了上去。我用不太灵活的双手试探着,一点点解开他的锁。那一根时软时硬,每拉一下,都会发出惨痛的叫喊。
我忽然生出一个恶念,右手准备狠狠往他微硬的一根肉里一拉时,手却止住了。
他被解封了,肉上破了一小块皮,他迅速将它藏进裤子里,又轰的一声,将自己放倒在床上。
他双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
我同他并排躺在床上,一起望向天花板。上面,有一道巨大的圆影。突然,那个影子咣当一声,碎了。
四条腿破门而入,两双戴着臂章的手,牢牢地控制住他,又强行扭住他变形的左臂,他无望地挣扎了几下。
临出房门的那一刻,他在离我不到一米处停了下来,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他轻声说:覃韦南是我弟弟,我叫覃韦东。他即将消失于我的视野时,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刺痛了我。
覃韦东离开了,他没有拿走我的《金瓶梅》,却顺走了我去年的生日礼物——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巴掌大的迷你水晶鞋,并且只拿走了左脚的那一只。
一名保安将覃韦东扭送到派出所。另一名保安告诉我,我触动了家里墙上的报警开关。父亲没有骗我,这个高档小区的确很安全。
我仰躺在床上,上面尚留有覃韦东的余温,他拖着一条扭曲的手臂,哀怨地盯着我,企图将我的身体盯出一个洞。我惊魂甫定,取出父亲送我的新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却显示忙音。我又准备打给母亲,想了想,挂了。
次日,一位自称某派出所警官的男人敲门,起初我不敢开,他提到覃韦东,我才放了心。
徐警官说,覃韦东于今年春节期间,趁住户外出旅游、探亲之机,在本小区利用住户大门上安装的猫眼,反向观察室内的光亮,再结合在门口听声的方式,判断住户家中是否有人。他通过反复踩点,断定其中一户家中无人,就在这家住下了,吃喝拉撒,还穿着男主人的衣服,时常在小区里出入,就连物业的保安也以为他是业主。
可是,他是怎么行窃的呢?
这个小区总共有四栋楼,他自第一栋开始,从顶层30楼偷起,每天只偷一层楼。行窃时,他戴着帽子、手套、口罩,遮挡住面部,来到之前踩过点的单元和楼层,使用撬锁工具,采取破坏锁芯的手段入室盗窃。
他总共偷了多少家?
18家,你家是最后一家。这个小偷很奇怪,不吸烟不喝酒,偷来的东西都收藏起来。被盗的住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有的甚至连干什么工作、姓什么都记得,都写在一个本子上,真是胆大心细。他的字也写得非常清秀,像是练过的瘦金体。徐警官感慨地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贼,我抓了这么多年的贼,头一次见到这么文艺的。他偷过一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支派克钢笔,一副猛犸象牙雕刻的国际象棋,还有一套女式性感内衣,叫什么黛安娜,不对,黛安芳?
我纠正他,是黛安芬。
徐警察继续道,他还偷过一把电吉他,一副望远镜,一块浪琴男士手表,还有两瓶88年的茅台酒,他准备带给父亲,他那面朝黄土的老父亲一辈子只喝过不超过十块钱一斤的酒,有一次喝到假酒,吐血,再也没有醒过来,他准备带着这两瓶酒去上坟。他还偷了一套阿玛尼的白西服,这套西装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想象有一天当新郎,和一位身穿洁白婚纱的女孩一起步入教堂。他还顺手牵走了一台数码相机,他起初偷的是一台单反相机,因为不会用,便换了台数码的。他每光顾一家,都会用相机拍下屋内的场景,正是这台相机,记录下他入室盗窃的罪行。
我半晌无语,陷入长久的沉思。徐警官突然问,你懂音乐吗?
略懂皮毛。我如实答道。
覃韦东偷了一台进口的音响,以及二十张进口CD。每天晚上,他都会听着圣桑舒伯特门德尔松的音乐入睡。他在别人家提前过上了倾慕已久的生活,他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住上这样的花园洋房。
我打断徐警官的话:覃韦东会被判多少年?
其实他偷的其他东西价值都不超过5万元,唯独这套音响价值300多万,正是这套价值不菲的音响,有可能导致他判重罪。
我若有所思。高考前夕,母亲扔掉了我所有的CD,理由是担心影响我的睡眠。
他来自乡下,当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穷,父母逼他辍学,也许他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他渴望城市生活,羡慕城里人,也恨城里人。你没遇害,算是万幸。对了,你知道他用望远镜观察对面的楼层这事儿吗?
我惊惶地说:不,不知道。
通过踩点和望远镜,他将小区里住户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且只挑选喜欢的东西“收藏”。在你之前也有人报案,失物很奇怪,丢了三只鞋,都是左脚的。那些鞋都是昂贵的奢侈品牌,丢了一只跟丢了一双没什么区别。报案的是个女人,她最喜欢的一双鞋丢了左脚的一只。
他为什么只偷左脚的鞋?
我也正在研究这种畸形的心理。
可是你刚才提到他还偷了名酒、手表、进口音响之类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报案?
你要知道,这个小区里住了很多当官的。你还年轻,没走上社会,还不懂得这里面的玄机。好了,我得回去处理案子了,你以后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警官,我可以提一个要求吗?
只要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都可以。
请不要告诉我爸妈,我怕他们担心。
徐警官点了点头。
走出警察局时,我左手拿着一支徐警官用过的水性笔。
我生日的第三天,母亲回来了,第五天,父亲回家了。他们争相对我嘘寒问暖,百般示好,我也摇身变成一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孩子,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共进晚餐时,天花板上有一块椭圆形的霉点正窥视着我们。那个斑点,是黑暗,虚无,还是光亮?
占据了二分之一面墙的电视上,本地的新闻联播里一片歌舞升平,我正想关掉这噪音,画面上意外地跳出一则新闻,说某某小区里发生了十几起盗窃案,小偷已被抓获归案。母亲指着电视说,那不就是我们小区吗?母亲停下筷子,父亲放下了碗,二人脸色都有些异常,却极力掩饰。他们关切地问我是否听说过此事,我轻描淡写地说,听说了。是一个矮个、清瘦的小偷吗?母亲追问。我说可能是吧。父亲凝神地听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将头埋进青花瓷碗里,猛扒了几口饭。
母亲沉默了许久,才说,其实那个贼来过家里,你爸不在家,我怕吓着你,就没跟你们说。
父亲忙问,没丢什么东西吧?
没有,他看到我在家,什么都没拿就跑了。
父亲缄默了半晌,说,房子刚装修好时,那个贼也光顾过,房子里是空的,什么都没丢。即使丢了什么也不要紧,只要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
父亲说话时,我始终盯着他的脸。他说得那么自然,仿佛那个3岁的男孩从未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