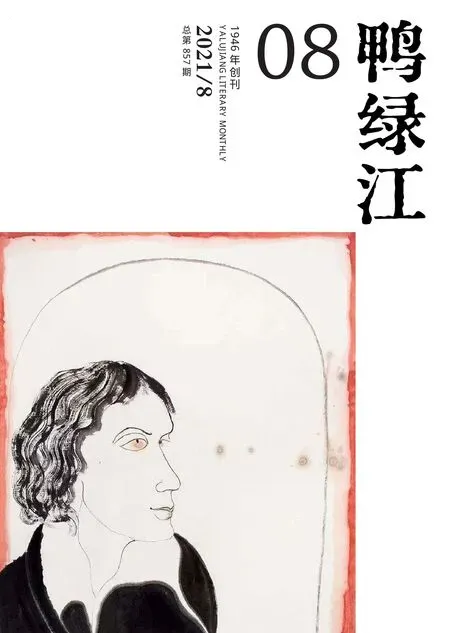乡土世界的精神文本
——读孙惠芬的乡土系列小说
2021-11-11丁颖
丁 颖
1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鲁迅提倡的“侨寓文学”的示范下,以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用真诚的笔触描摹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雏形状态。自此之后,许多拥有土地情结的作家在乡土文学这面旗帜下集结,依托生活和眼界,用丰沛的情怀和深刻的乡土叙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乡土中国的生动范本。在沈从文、萧红、赵树理、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阿来这些大家笔下,湘西、呼兰河、晋东南、高密东北乡、商洛山地、白鹿原、嘉绒藏区等地成为醒目的意象,引起世人对这些“别一世界”的注意。作家们用近乎“地之子”的痴情,不倦地书写,接续地努力,逐渐将乡土文学发展为影响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学书写题材,中国乡土文学终于作为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学力量,在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里发挥了主干的作用。
在这接续传承的队伍里,就有孙惠芬。诚然,作家在创作之初,不大可能有明确的文体意识,更不可能体会到,在一个少女个人化的沉思默想与涌动着变革浪潮的大时代间会有怎样的微妙关系。作品是创作者精神的徽章,作为为数不多的执着于乡土写作的女作家,孙惠芬以不徐不疾的叙事姿态,逐渐显现出不俗的创作实力。她斩获过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女性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入围过茅盾文学奖提名等。她用全部的生命体验精心建构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在赓续乡土写作传统的同时,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乡土文学再续新章。她立足于辽南乡土社会,用朴素晓畅的艺术化文字完成对变革时代辽南乡土心灵的精神凝视,在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里,深植民间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在对乡土社会式微的深忧隐痛中,从不放弃对“精神故园”的建构和探求。她的乡土小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
罗丹说:“艺术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孙惠芬的乡土想象发端于她记忆中的故乡,那些有着辽南地域特点的粪场、东山岗、场院、夹地、土街、小山坳,让作家看到了“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那个挓挲着两个朝天锥似的辫子、房前屋后没命疯跑的小女孩,没有顺从命运堕入庸常,反而在故乡和家族的根脉中汲取了特别的乐观和勇气,将故乡的山水与人事化为审美的对象。在四十年的创作生涯里,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孙惠芬悲悯温情的目光逡巡于进退失据的故土乡亲,从未停止过对它们和他们的牵挂思考,在深忧隐痛的精神探索中,写出了《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后上塘书》《寻找张展》等长中短篇小说近400万字,在勤耕不辍中,完成着创作的“可持续性”和“生命的最佳样式”。
2
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直言:“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番文学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探讨,孙惠芬是否读过不得而知,但她却以自己的文学实践,暗合着“地方与文艺”的关联。她的创作领域集中在乡土世界,这与作家人生最初的体验有关,也与乡土社会的鲜活、丰富与复杂性有关。
故土的悲喜哀乐滋养了作家的文学感觉,生命中长久的积郁助燃着文学的想象,在尺牍之上方寸之间,孙惠芬一丝不苟地书写着乡土社会鲜少人知的幽微世界,在“心灵的历史里寻找高地”,建构自己的“天高地远”和文学理想。孙惠芬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默默观察和度量身边人事的本领,也就是说,我在身体上跟母亲走着一条狭窄的只在院子里往来的道路的同时,心里头却走着一条漫长又宽广,通往别人心灵的道路。”书写心灵和精神世界,是孙惠芬乡土创作一以贯之的涉足领域,她饱含深情地细细打量乡土大地上发生的故事,揣摩乡民们的眼神、心事和命运,乡里乡亲、家族人物、左邻右舍经由艺术的想象,在作家笔下便有了意象的意味。无论是她早期的还是中后期的作品,心海泛浪、心有千千结,永远是她笔下多数主人公的精神特质。1982年,孙惠芬在《海燕》第5期发表了她的处女作《静坐喜床》,这篇由“压抑而生成的想象”之作,源自作者辍学务农回乡的生活日记。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要嫁到小镇上的农村姑娘,她静坐在喜床上,看着前来贺礼的人们热闹欢喜,看着忙碌人群里的婆婆和新夫,心里充满了喜悦、惶恐和不安。心情的抒写是这部日记体小说里最牵动人心的地方。恰似平静的水面吹来阵阵清风,眼前从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在这个姑娘的心海里掀起了一波波涟漪。作家抓住她在“静坐喜床”的半天里真切细腻的心理活动,呈现出一个新嫁娘幽秘深邃的精神世界。
孙惠芬曾明确表示她对心灵精神世界的看重:“从平庸中发现光彩,这需要精神的提炼,所有的事物,没有精神,就会沦为平庸,所谓素常人生中的素常心情,就是指素常人生中的精神世界,这世界不管多么微小,多么短暂,都闪烁着金子一般的光芒,‘微妙’和‘瞬间’,其实只可能发生在精神世界里。”《小窗絮雨》也是她早期的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刚刚迈进文学门槛的农村少女。作者从她的寂寞、愁闷和回到乡下家中的种种不适写起,让她心绪不宁的是那份欲罢不忍、欲爱不能的两难情结——是和等了她四年的乡下男友完婚过日子,还是不顾周围的闲言碎语而专事写作,到外面的世界去体验更大的精彩?新与旧的摩擦,爱与怨的交织,让少女的心弦震颤,充满了惶惑和挣扎。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心理描写的线索延伸到少女身后的世界,那不可忽视的以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为代表的家族伦理的影响,将这份热闹熏染过的矛盾心绪扩展开来,使其显得格外真切动人。
孙惠芬长于洞幽烛微,往往在人们习见不察之处,勾连起人物细腻丰富的精神世界,连同她的疑虑和苦痛一并纤毫毕现地呈现给读者。《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潘桃和李平是两个新婚后马上独守空房的农村媳妇,外出打工的丈夫离家后,留给她们的是乡下单调、重复、沉滞的生活。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由开始的敌对到后来的认同,一点点走近,渐渐理解信任,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她们在稀薄自由的空气里建立起来的精神同盟,很快被离间被摧毁,各自只能又回归到传统的规约和既定的生活轨道上,脆弱的友谊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小说最富神采的部分,是两个女人在寂寞独行中找到知己最终又失去彼此的精神历程。她们心灵深处每个瞬间里每一份希冀的懊恼和幻灭,都是看似静默的生活之流里“最奇崛的波澜”。
孙惠芬一直保持着心理写实的热情,乐于表达内心深处的波澜壮阔。她尤其着意于人际关系的平等,她坚信乡下人的人格尊严和精神世界同样独一无二且色彩斑斓。《秉德女人》被孙惠芬看作是“一次黑暗里的写作”,而“在这黑暗里,我携带的唯一的光,是心灵,是贴近人物情感的心灵”。作者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秉德女人,这位乡村女性的心灵风暴意趣盎然,她跌宕起伏的一生与元气淋漓的内心世界相得益彰。乡下女人努力讨生活的坚韧、乐观和不屈从命运的个性,她的宽容、大气以及努力朝向外面的世界探光景的地母品格,极容易攫住读者的心。孙惠芬钟爱秉德女人,通过秉德女人的心灵,“照亮”了作品里更多人的心灵,进而书写出一个家族的心灵史,一场跨度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史。
乡村女儿的身份、沉静坚忍的个性以及长期的乡土生活经历,使孙惠芬与其笔下的人物几无疏离感。对心灵世界的重视,让孙惠芬的乡土世界充满了意味和生机。她尤其善于捕捉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致力于书写人的心灵和人性的困惑。她带着亲昵的感情,精心抚摸每一道心灵的褶皱,以同理心和悲悯的情怀长时间地审视乡土世界的苦乐人生,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到乡土世界流动的心灵,倾心书写或丰饶或贫瘠或闭塞的精神内部,让她笔下的生命在文学的天地里焕发神采,让她笔下的性格和命运从“幽黑”的隐秘角落走向敞开的“光亮”天地。
3
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也是中国传统伦理关系孕育和形成的基本单位。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坦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对人伦思想有过形象的比喻:“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伦通过“差序结构”一层层地发挥着作用,家族中的血缘关系作为强有力的脉络凝聚力,在差序结构中是最活跃的元素。对家族伦理关系的书写是了解乡土社会、反映乡土中国的重要维度。
孙惠芬来自辽南农村,在一个讲究家教和家族观念的大家庭里生活了很多年,对人与人关系的敏感,对血缘和地缘的重视,形成了她的情感路线和审美方向。那些让她不能释怀的早期生活记忆,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她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成为稳固的深层的情感记忆、审美意识和价值判断。乡土伦理写作几乎占据了她大部分的生命和时光。家族的存在感是鲜明的,血浓于水的亲情,让记忆复苏,使久别重逢的人迅速找到沟通的路。孙惠芬立足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文化理想,在家族这座艺术的高地上纵横想象,续写传统伦理关系的绵密与悠长。
孙惠芬惯用第一人称向外敞开的方式,引领读者走进辽南乡村的家族世界。众多的家族成员,被一件件小事所牵扯勾连,聚拢起来。申家、翁家、张家等形象活泛在作家的笔下,不仅出现在单篇作品里,还在其他作品中连续出现,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线索清楚的家族谱系。作为不同的意义载体,在家长里短、爱恨纠葛、利益计较中融入家国情怀和个人的精神诉求,以家族兴衰际遇透视历史变迁和社会演化。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境况的性质。”作为“处境的存在者”,孙惠芬那些对乡村伦理关系的真切体验,引导她将人物纳入群体和社会之中,在时代的嬗变中表现家族成员的命运起伏,呈现家族的荣耀、伤痛、衰败与希冀。在作品中倾注伦理本位与深情书写,这和孙惠芬自幼建立起来的家族意识关系密切:“家族荣耀感,我想是真的有,这跟我的家族在当地影响有关,也跟奶奶这个人物在当地的威望有关。很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家族与乡村其他家族的不同。这荣耀感不管是不是好事,它确实是我创作的源泉。”
《来来去去》《伤痛故土》《岸边的蜻蜓》等作品里的大哥,是家族的主心骨,是“顶天立地的柱子”,他讲求信义、重视礼仪,自小就立下了为家族崛起而奋斗的理想,用主事议事、开会号令建立权威和责任感,在家族中享有最高的威信。但今非昔比的种种失落,也常常伤害、挤压着他,可他依然挺起坚实的脊梁,在命运的纠缠和抗争中,带领家族重拾信心。而《歇马山庄》《飞翔之姿》《致无尽关系》中叔叔和侄子的形象,则代表了外边和远方,他们往往知书达礼,不卑不亢,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好的艺术修养,与家族洼地里的乡民们区别开来,展现着家族通向省城、通向国家的风光。《歇马山庄》中的翁月月出生于歇马山庄最有名望的翁氏家族,在外人眼中翁氏家族“祖上有德行有教养,讲求礼节”。在月月的眼中,家族是她心底的一种“无形的依托,无声的骄傲”。孙惠芬用细腻的笔触,书写着带有崇仰感的家族意识,呈现着传统儒家思想在宗族乡间的作用力,在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让一个个素常的日子于暗淡之中泛出神采,更透视出家族荣光给乡民干涸心田带来的慰藉与力量。
随着时代变迁,向往自由和追求个性的思潮逐渐改造了乡下人的生活伦理,传统的家族关系也悄然地发生了变化。《盆浴》开篇这样写道:“老家是大户村落,在一洼恍如澡塘盆池一样的黄色盆地里。就是这么一个澡堂似的雾蒸水润的地方,住着我们近百人的申氏家族。”申氏家族庞大,成员众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家规异常严格,在辉煌灿烂的家族史册上,记录着誉满辽南的秀才和任过国民党少将的二伯。然而,发生在堂二哥传江和本家二嫂之间的婚外情,却让久负盛名的家族“蒙羞”了,它强烈冲击了申家的家族伦理关系,动摇了家族本位思想。但人们可以接受李家的豆腐房、张家的粉房,甚至可以容忍堂二哥“强奸”傻圣子媳妇,却坚决视堂二哥和本家二嫂的恋情为洪水猛兽,情投意合的爱情在固化的家族观念面前,注定结不出喜乐的果实。孙惠芬在新与旧的冲突中诠释时代的多元变化,以阡陌交织的方式,写出了家族儿女的迷失、痛苦和寻找。
《四季》里写到的“我们申家家族”,“是澡盆子样山乡里靠经营山野田地为生的农民的后裔”,作者饶有耐心地书写着另一个家族故事。一奶同胞的血缘关系,使申氏姐妹近距离地感受到嫁到小镇给大姐申传扬带来的名望,由“十三间房子的店铺和四亩半地的菜园”建立起来的迥别于乡下人的生活光景,助燃了她们急于往外奔逃的心。在大姐的一番引导下,姐妹们怀着投身新生活、改变旧命运的美好愿望,从泥泞的田埂走进奇异新鲜的小镇,并因受雇于大姐在小镇的店铺而开始新的人生。然而让她们始料未及的是,摆脱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之后,却要面对新的泥沼。而其中大姐传扬着手于“光宗耀祖”,将几个妹妹嫁给了与她们绝不般配的城里人,改变了亲堂姐妹四人的生活,在根脉谱系间生成的罅隙和产生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亲情伦理滑向生存伦理的现实选择,是一首秘而不宣地氤氲在申氏姐妹心间的田园挽歌。
关于家族生活历史感的书写,更多出现在孙惠芬后期的长篇《秉德女人》中。出生于辽南小镇书香家庭的大小姐王乃荣,在传教士的儿子影响下,用绸缎刺绣世界地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扬帆远航去往远方,却阴差阳错地被匪胡子掳走成了秉德女人,从此被践踏在阴沟里,遭遇了纷至沓来的各种磨难和打击。她不断寻求存在的机会,依靠不屈服的生命本能,拉扯一大家子在无数次逆境险境中死里逃生,用顽强的生命意志和饱满的家族责任,书写了“由她繁衍的一个家族在国家百年政治变迁中的命运历史”。
孙惠芬喜欢素朴,她不热衷于小说写法和技巧的新奇,而是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执着地沿着乡土伦理的阡陌沟壑向纵深处寻觅。那些充满人情味和苦涩味的家族生活,那些时代变迁之下乡土伦理关系的嬗递,始终属于她的乡土创作的“永恒”叙事。她以感性细腻的写作方式演绎自己的思考,即便是世风日下、众声喧哗,即便是乡土题材一度式微遇冷,孙惠芬依然坚定地立足于她的故土家园,书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写出他们的情感、意志和希望。
4
孙惠芬是一个长于感悟属意抒情并勇于探索的作家。故乡作为心灵的栖息之地,安放着她刻骨的思恋、深度的思考和永不止歇的追求。她对乡土世界的守望不仅表现在执着于忠诚的书写态度上,更在于在自觉的精神凝视中,她能将现实的情境引向心灵的情境,发掘出人心的幽暗与光亮,写出时代变迁中的躁动与困顿,在质询中召唤意义。孙惠芬坚守民间立场,立意突破,在“伤痛故土”的传统主题上不断翻新,以救赎和追寻,作为她新乡土写作的重要姿态。
在商业化大潮的裹挟冲击下,贫瘠土地上的生存日显粗粝与艰难,城乡差异不断扩大。孙惠芬笔下的辽南乡村地处沿海,很早就与外面的世界有贸易往来。当外面的世界逐渐敞开,孙惠芬不再满足于描写个人的情感潮汐,而更乐于带着清明的理性,以反思精神描写乡民的心灵躁动,深刻揭示农民对“现代化”的渴望与追求。乡下人进城不仅是改变生存处境的手段,也激荡着生命自我实现的渴盼与挣扎。在她的系列乡土小说《春冬之交》《来来去去》《四季》《民工》《歇马山庄》《秉德女人》《吉宽的马车》中,几乎每篇都有乡下人离乡进城打拼闯荡的身影,一批闯荡者离城返乡,又一批仰慕者踏上征途,在朦胧的憧憬与坚硬的现实的对峙中,出走与回归都由焦灼写就。
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始终交织着伤痛故土与伤痛城市的不和谐变奏。对此,孙惠芬曾感慨道:“我身边的乡村人在困境中挣扎,寻找和世界关系的入口。他们以为生活在外面,在那个充满文明和秩序、在他们看来与国家强大肌体的主流血管水乳交融的外面,他们以为只要进入那个世界,生活就能得到改变。”《春秋之交》中的小兰是孙惠芬笔下最早的一批出走者,也是最早的一批闯荡者。在城市文明难以抵御的诱惑下,她卖掉嫁妆,抛弃乡下的男朋友,毅然决然到城里棉织厂当一个临时工。她的离乡进城涌动着饱满的激情,也掺杂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盲动:“她被一个城市人占有,从此她就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城市人了。”思想认知的偏误以及生存法则的坚硬,注定了小兰被抛弃的命运,即使为此费尽了心机失去了贞操,城市还是没接纳她。失败而归的小兰得到了男友和家人的接纳,但乡情的抚慰并不能熄灭她对城市的恐惧与渴望。得不到的永远在躁动,生存的两难始终困扰着现代人。
《歇马山庄》中的小青是第二代离乡进城者,她是新的时代观念涤荡冲击下的青年,她与小兰一样拥有着留在城里的强烈渴望,只是她更有目的性。小青主动向50多岁的卫校校长献出自己的处女之身,希望借此留在城市。她受到了一定的教育,洞悉城市的游戏规则,了解人情世故,似乎更有能力在城里站稳脚跟。可她还是失败了,伤痕累累地回到乡下。小青与买子的爱情悲剧,与其说是为了还原歇马山庄姑嫂石篷的凄美传说,毋宁说清楚地演绎了以小青为代表的城乡游走者的生存困境。此外,翁凡书是《歇马山庄》中的返乡者代表,他受聘于古建公司,深得族人拥戴,而他耿介的个性与利益驱动的时风格格不入,他的荣贵之旅,最终也成了败兴之旅。故园失去了昔日的安详和宁静,城市的浮华和喧嚣又无法安放灵魂,家在何处呢?在孙惠芬笔下,乡土世界呈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时代意蕴,凸显着现代的乡下人彷徨无助的精神困境。
《致无尽关系》中,女主人公申玉贞在“年”的吸引下,在“三百里外整个一个家族热盼等待的目光”中,带着归心似箭的心情,急三火四地返乡过年。牵引她的“真正的钢绳”当然不是年的团圆,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这里保存着欢畅自由的童年,这里是熟稔亲切的乡情寄托之所,乡恋不需要刻意捕捉,即可如潮水涌来一般的淋漓,只不过,相伴而来的还有“巨大的亲情之网”以及烦琐的乡俗礼节所带来的无尽烦忧。“事实证明,你与家的关系只在想念里,不在现实里”,作者在对家族亲密感和疏离感的细致描写中,呈现了进退失据的现代人在无尽关系中的精神苦闷。
对于存在方向的寻找,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属于城市,属于乡村,属于所有的人。它是一种存在感,是来自生命的原动力,正如一棵树向往天空,一条河仰慕大海。在《吉宽的马车》《后上塘书》中,孙惠芬以精神还乡的主题,为中国乡土写作探索出了一条救赎和寻找的精神之路。《吉宽的马车》中懒汉吉宽身上寄寓了作家古朴乡村慢生活的诗意气质,即使主人公现实化地趋同了城市规则,学会了投机和以次充好等等,但作品中始终吟唱的吉宽体,回荡着的还是田园故土的美好牧歌。在城里,吉宽将农村的景观用于黑牡丹酒店的装修创意,让他赢得了城市的喝彩,这包含着作者对乡土方式的认同。吉宽的来来往往和多次返乡,根底是对美好爱情的坚守,是对自然的无伪的精神生活的守护。《后上塘书》是距离《上塘书》十年之后的作品,主人公刘杰夫作为成功者的代表,在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庭的悲恸中,以丧礼和灵魂回归的方式重返故乡,重新建立了与故乡的精神联系,在忏悔成功之路的过程中,完成了精神的救赎和灵魂的还乡。
孙惠芬不厌其烦地书写“熟人社会”,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常”与“变”,通过城乡的差异时代的变迁展现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殇,锲而不舍地寻找与世界的对话方式和反思与世界的意义关联……我想,这里边定然有着丰沛的理由,但其间的基础性答案,应该只存在于孙惠芬自己那真诚而又质朴的表达之中:由于“我在乎眼前这一切”,因而,“永远跳不出这种生活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