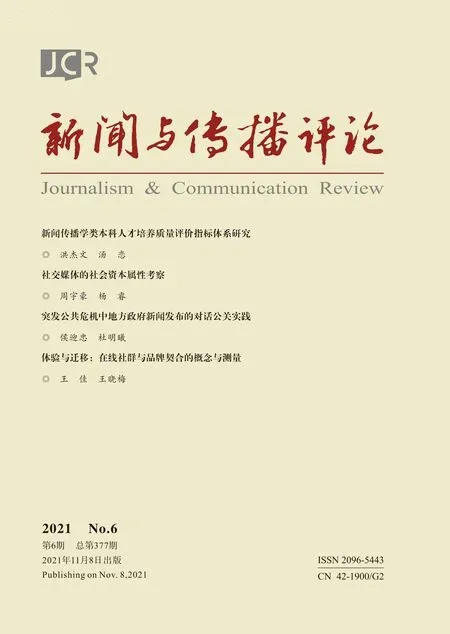2020年西方公共关系学术前沿
2021-11-06陈先红秦冬雪
陈先红 秦冬雪
在进入21世纪的20年里,深度联结的全球政治经济带来资本、人口、贸易、知识的全球流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全球性、多向性传播模糊了社会文化差异,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创造出看不见的、广泛的、快速的和爆炸性的变化,曾经的“地球村”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存空间”[1],公共关系是这一共存空间中的个体、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最短路径,对作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事业”的公共关系的构想已不仅仅是公关学者与从业者所期盼的,更是日益多元化的公众所向往的神秘之境,瞬息万变的全球生态与国际关系不断呼吁这一领域的完善,这需要从公共关系领域的研究现状的探察开始。
本研究主要关注2020年刊载于西方9大学术期刊中的公共关系学研究,由两位作者参与文章的收集与筛选,具体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收集公关界最权威的2本SSCI期刊(PRR、JPRR)和另外2本专业期刊(PRJ、PRI)官方网站上的2020年度的全部论文;其次以公关趋势研究和专题研究最常选择的5本学术期刊(JMCQ、CCIJ、IJSC、JCM、MCQ)为样本源,以其专栏标题、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包含“public relations”或“public relationships”或“PR”为筛选标准进行收集。总共获得集中在9本学术期刊(1)9本样本来源期刊分别为:Public Relations Review(PRR)(SSCI),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JPRR)(SSCI),Public Relations Journal(PRJ),Public Relations Inquiry(PRI),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MCQ)(SSCI),Corporate Communic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CCI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IJSC),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JCM),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MCQ).上的151篇公关学术论文,从“问题-理论-方法”研究三视角进行主题分析,爬梳出西方公共关系研究的七大热点议题,以期为公关研究提供最前沿的学术参考。
一、对话与信任
对话(dialogue)是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哲学讨论的重点话题,苏格拉底式对话由两个参与者之间的一系列询问和回答组成;到20世纪,以巴赫金、布伯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延续了这一经典哲学,认为对话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参与者之间进行的双向交流。在公共关系领域,格鲁尼格与亨特最先提出在双向对称传播中,组织与公众进行对话;皮尔森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维护组织和公众之间关系的道德沟通过程;关系范式的兴起使对话与公关的关联性得到扩展;随着互联网技术带来传播领域的深度变革,公关对话理论被发展为通过网络指导关系建设的战略框架;直至2002年,肯特与泰勒才进一步明确公关对话的真正内涵:有助于组织在实践中与公众接触的导向,并提出公关对话五原则:相互性(mutuality)、接近性(propinquity)、共情(empathy)、风险(risk)和承诺(commitment)[2]。在之后的20年中,组织-公众对话(organization-public dialogue,OPD)成为公关领域十分有影响力的研究议题,新的理论突破来自“参与”(engagement)概念的引入,以指导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3]。对话理论在西方公关学界引起研究热潮,并逐渐吸引中国学者对其进行情景化探讨,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公共或私人组织只是将对话沟通作为一种工具来提高公众的反应或参与,而未充分挖掘其对组织和公众的战略意义。“强制对话”(mandated dialogue)、“竞争性对话”(agonistic dialogue)等新型对话概念研究者关注到对话产生共识的能力是有限的,对话双方的权力不平等注定了沟通过程中差异、冲突、分歧和多元声音的存在。对话理论与中国阴阳哲学的共同结合衍生出了积极公共关系理论(a positive public relations theory)[4],该理论依托于积极心理学,反思“坏情况”的叙事范式,强调正向价值传输[5],与西方新兴的“建设性新闻”异曲同工。
早在1977年,“信任”(trust)就被当作组织-公众关系(OPR)的研究成果之一进行探讨,信任被定义为“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程度和向另一方敞开心扉的意愿”,包括正直(integrity)、可信(dependability)和能力(competence)三个维度[6],这只是指代一种基于认知的信任(cognitive foundations)。此外,还存在基于情感纽带的信任(affective foundations),其始于对合作伙伴的真正关心和相互之间的情感互动。相比较于“不信任”,信任对对话沟通、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评价产生更高的感知影响[7],在携程应对虐童丑闻危机的过程中,公众对组织的不同信任程度使其表现出六种不同的沟通行为:合作、劝说、信息寻求、威胁、动员和不回应[8];而与特殊群体如LGBTQ公众之间的对话需要从四个方面培养信任:文化能力(关注群体特征)、组织一致性(组织内部制度与其外部多元包容努力之间的匹配)、真实性(真实沟通、真实接触)和利益相关者授权[9]。在未来,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参与动机、对话预期、线上线下对话融合、对话网络化与数据化测量、社会责任背景下的公共对话、对话与信任中的权力等主题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倾听、透明度、真实性等关键维度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信任测量可能需要跳出相关关系、因果关系的测试,致力于模型框架的开发,为对话公关实践提供理论的指导。
二、政治公关:公民政治参与、组织倡导与公共外交
公关通过公共话语促进社会共识,是制造认同的国家艺术,是一种政治,个人、组织、国家乃至国际社会都在践行着政治公关的哲学。在个人层面,“公民政治公关”(citizens’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概念在加纳和平建设的背景下被提出;中国情境中的“政治化消费者行动主义”(politicized consumer activism)群体身份得到确认,即经济资本适中但文化资本相对较低的群体[10]。出于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对话中重塑话语权的需要,组织层面的企业政治倡导(corporate political advocacy,CPA)和企业社会倡导(corporate social advocacy,CSA)得到关注,它们都指向组织在有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以表明与关键公众的共同承诺[11]。不同的是,CPA被看作企业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追求可能有利于部分利益相关者的规范信念;而CSA采取更加工具性的方法,更加关注此类活动对公司的财务影响。不同的企业倡导动机会导致不同的公众反馈,如价值驱动动机、战略驱动动机能够促使个体形成对企业的积极态度和行为意图,而利己主义动机、利益相关者驱动动机传达的是操纵性、被动性意图,只会导致个体的消极回应[12];从公众视角来看,细化程度(elaboration,个体参与议题思考的程度)[13]、倡导契合度(advocacy fit,即企业业务与其倡导的社会问题之间的一致性)、企业信誉和共识启发(consensus heuristic,即个人根据他人的评估做出判断)影响着公众对组织倡导议题的参与和态度变化[14]。
在国家层面,中国语境下的政府沟通能够增强制度信任,网上政治信息寻求(而非网上政治表达)正向调节了政府回应对公民信任的影响[15];此外,“垂直社会资本”(与监管当局的关系)使中国企业有更多机会澄清哪些是可谈判的信息,发现并抓住机会影响决策者[16]。冲突后的北爱尔兰,通过创造社区对话和尊重辩论空间来建立“善意”信任[17];美国背景下的“政治组织-公众关系”(POPRs)则受到媒体偏向、党派议程框架、候选人特征等因素的影响[18]。在国际层面,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外交研究强调公关在建构、合法化、加强和改变权力和共享意义中的作用,公共外交路径从信息导向的单向沟通逐渐转变为关系导向的对话式沟通,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价值共享是公共外交的核心,今天的国际舞台早已成为参与者及其信息在公众关注和公众支持之间进行激烈竞争的场所,经济关联性(而非政治文化接近性)极大地影响各国政府对某一国际事件议程的采纳[19]。针对两种不同的国外公众——声誉关系群体(reputational relationship group,即只有东道国二手经验的群体)和行为关系群体(behavioral relationship group,即与东道国发生行为关系的人),需要制定差异化公共外交策略,如符号性单向形象流与双向沟通互动[20]。
虽然西方研究者探讨了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政治公关,但仍然没有对这一概念形成统一界定,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对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媒介体系、组织类型等宏观“硬”元素的影响关注更多,而忽视“信任”“对话”“透明度”“参与”等微观指标的影响与测量。组织层面的政治公关以“倡导”为关键词,但忽略了对非利益组织、公众主体的倡导行为的关照,倡导战略的使用已被验证是在Facebook上进行病毒性传播的重要预测因子,“倡导内容组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组织促进社会变革[21]。公共外交强调关系导向,但如何在国际层面进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建构、维护与测量仍然是公关学者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三、公关历史:国家建设、运动宣传与公关先行者
历史是一种积极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力量,但公共关系学科的历史呈现却被有选择性地作为一种表面的合法化功能,尽管许多教科书口口声声谈论古代和现代晚期公共关系的“根源”,但根源本身被视为历史偶然事件,从而与公共关系真正“是什么”脱节[22]。在美国的报刊宣传运动源头之外,公关作为国家建设、民族认同进程、非殖民化或自由斗争的一部分而演变:暹罗(今泰国)拉玛五世国王通过在国际社会展示暹罗文明形象、传达改革信息、监督政治新闻报道和影响国际舆论,使暹罗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的国家[23];英国殖民者以发布新闻稿、召开记者会、组织展览等公关活动,推动马来西亚的锡、橡胶以及棕榈油等原材料的国际化贸易[24];在塑造民族认同方面,公关却并非一定带来好的结局:新西兰政府赞助的广告、品牌、电影以及民族文学催生了更广泛的身份阐释,却塑造了疏远非巴基斯坦裔新西兰人的种族主义[25];在哥伦比亚的国家和平建设中,竞争性、双赢性、第三方调解和原则性这四种公关策略被应用到当地政府与武装力量的谈判中[26];阿联酋在国际与当地公关机构的助力下推动了国家的政治建设(影响他国政府和全球公众的意见)与经贸拓展(贸易、旅游等经济现实对声誉的极度需求)[27]。早期的公关运动通常使用手册、海报、传单、新闻报纸、广播、发布会、电视等宣传工具,帮助组织实现筹集资金、招募人员、建立合法性、鼓动支持以及鼓吹反对等目标,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公关办公室)、英国法西斯联盟分别运用公关手段推行“开放外交”(open diplomacy),宣传不同于其他法西斯主义的“和平”主题[28];而20世纪50年代,美国财政部和英国计划生育协会以相似的公关策略分别推进了大规模征税在美国国内的合法化,以及节育知识在英国大众中的普及化[29]。作为“爱尔兰公共关系教育的伟大先驱之一”弗朗西斯·泽维尔·卡蒂(Francis Xavier Carty)在其25年的执教生涯,撰写了诸多公关著作与教材,“告别炒作”是他的公关宣言[30];而1944年在纽约开设全女性代理公司的梅布尔·弗兰利(Mabel Flanley)和萨莉·伍德沃德(Sally Woodward)为公关职业中的女性开辟了一条道路,她们是种族、族裔、性别多样性、群体包容性举措的执行先驱[31]。“法国公关先驱”马扎林(Cardinal Mazarin)强调通过外在形象管理、主动沟通、取悦公众、赞助、预防危机、虚假承诺等手段建立强大的声誉,保证权力的维持,对其分析有助于理解西方政客(如特朗普、约翰逊等)的主张:表象和操纵真相是获得权力的有效合法手段[32];
公共关系的传记历史总是过分关注个人而忽略制度或结构权力,运动史通常局限于单个案例与策略的解析,国际发展史往往缺乏全球视野与整体观,研究者从被忽视的历史细节中挖掘出的珍贵资料似乎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引人深省的作用。举例来说,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方案被用来表现企业的良好道德,但其出现可能由于历史上的剥夺和剥削模式,或来自风险制造行业的普及而引发的公众反抗,历史正义的不平衡被用来美化企业行为。故而,公关实践需要历史化,公关历史更需要超越“事实”的表述,揭示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游戏和道德困境[33]。
四、公关战略角色:大战略、战略与战术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卓越公关项目研究成果的问世就为公关和沟通管理的战略方法铺平了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们开始讨论“战略”概念的重要性,强调从战略角度思考如何进入主导联盟;2007年,《战略传播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的创刊为战略与战略传播研究开辟了前沿阵地;2011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国际传播学会-战略传播预备会议则直接将公关战略研究推向白热化。美国公关学者卡尔·伯顿对公共关系中的战略进行了划分:包含“大战略”(grand strategy)—“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三个层面[34]。大战略属于政策层面,是一个组织对于目标、联盟、道德以及与公众的关系和环境中的其他势力所做的决定,例如香港、澳大利亚、加纳从业者对市场导向关系战略,冲突生态学战略框架、对称的关系性公关路径的坚持。战略层面涉及资源安排和调配以及组织实施大战略论据的传播活动,在防灾减灾的公关战略研究中,学者分析了信息告知(informational)与参与(engagement)这两种信息传播战略中存在的“正面悖论”(即过分强调正面信息可能会产生错误或误导性含义),提出需要统筹传播政治信息与“共享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y)意识,要将社区伙伴关系作为必要条件,加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抵御能力[35];而灾后恢复的公关战略则需要跳出声誉、危机、议题管理的框架,着力于“社区恢复力”(resilience)建设,包括更好地了解社区属性与文化环境,促进社区内关系网络与抗灾机构网络的形成等战略的使用[36]。英国的公关战略家们以精心组合和公式化的公共话语改变民众对战争的文化理解,将无人机描述成一种公正的“远程干预”技术,为其战争部署赢得广泛的公众支持[37]。在正面宣传之外,澳大利亚公关学者季米特洛夫强调了公关的另一职能——避免负面宣传,提出了“战略沉默”(strategic silence)(包含策略性沉默和非策略性沉默),认为沉默构成了中断、折叠和转换的链条,其中也传达着某种信息,不能直接说的内容间接地变成了一种解释模式[38]。战术则指向具体操作层面,在虚假参与和虚拟社区的时代,从业者正在寻找基于真实性、准确性和连贯性的长期关系,个人声誉、所涉主题的相关性和在线共享内容的质量是从业者识别“新把关人”——社交媒体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s,SMI)的主要策略,影响力分析指标(如社交距离、互惠性、情感价值、权威性、中心性、模块性以及连通性等)也逐渐被纳入其中[39]。
在“实践”的研究视角之外,研究者关注到作为话语的战略,即关注“战略做什么”而非“从业者如何使用策略”,从而更好地理解战略话语如何促成和制约战略工作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具体而言,战略话语使传播实践者能够将自己描述为“战略家”,而战略家的“指导”和“促进”功能使从业者获得更大的组织内权力和对他人的权力[40]。作为文化的战略将公关从业者定位为“文化中介”(cultural intermediary),即品位的塑造者和新消费主义倾向的灌输者——他们致力于战略性地制作和传播叙事,使其客户的身份和体验对大众切实可见;必须翻译真实的经历,创造出媒体能够传播并与主流受众产生共鸣的故事,他们被赋予一种解释性和代表性的战略功能[41]。
五、危机传播:类型、变量与策略
危机传播研究是公关领域的一个范式,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IRT)和库姆斯的情境危机传播理论(SCCT)是该范式下的主流理论。在过去一年的危机公关研究中,学界延续着将前者包含的形象修复策略(规避、否认、道歉等)与后者的理论工具(如道歉与责任归因)放到不同国家情境下进行检验的传统,文化差异是讨论最多的影响因素。此外,非传统形式的危机得到探讨:“未遂事件”被证实与实际危机产生消极结果和消极认知的方式大致相同,“调查中的危机”需要组织采取“承认并等待”策略,并做好准备随时应对危机责任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更为独特的危机认知来自“社会建构危机模型”(social constructionist crisis model),该模型从事件、文本、意义和情境(cause,text,meaning,context)四个维度分别强调了危机的记忆共建性、语言复杂性、意义丰富性以及情境独特性[42]。在危机中,组织与内部公众(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和对称沟通能够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问题感知,而员工的能力、心理信念和积极沟通行为有助于为组织创造一个恢复力系统[43],“信仰者”作为一类特殊的利益相关者被证明能够成为捍卫组织声誉的重要平行力量[44],消费者的道德判断、信任与不信任、危机距离感知、口碑动机、与组织之间的先验关系规范等都影响着他们对企业危机的反应。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具有更高的交互性和更广的传播范围,在降低危机责任感方面更有优势,信息指导、共情、系统的组织学习和有效的组织修辞可以提高社交媒体公众对组织危机的积极情绪[45],然而它们如何共同或独立地影响危机传播,以及信息传递和媒体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危机恢复,都需要从传播效果的广泛变异性展开研究[46]。“信息审查”(vet information)步骤被加入社交媒体危机传播模型(SMCC)的危机信息传递之前,扩展了公众对信息内容的判断和选择阶段[47]。危机传播中的威胁信息被认为会增加危机责任归因,进一步损害组织声誉,而以提高公众自我效能为特征的信息内容有助于保护组织声誉[48],故研究者进一步构建了自我效能信息(指导信息和调整信息)质量量表[49]。具体到危机应对策略,研究者多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特定危机情境下,不同危机策略的有效性。例如,事实阐述和员工支持策略被证明会直接影响危机应对效果,信息质量感知在纠正性沟通中起到中介作用[50]。在数据泄露危机中,组织表达悔恨、承认责任、承诺忍耐和提供赔偿策略都有助于公众对组织道歉的认知[51]。针对叙事说服(narrative persuasion)策略,不同的研究者揭示了其固有的矛盾性:一方面,根据叙事参与理论(narrative engagement theory)对故事有效性的阐述,讲故事的危机应对方式被证明可以增加对组织信任,降低危机责任感知[52]。但另一方面,尽管道德叙事比非道德叙事更具有效性,公众却更喜欢发言人直接提供非叙述性信息而非故事来处理媒体关系[53]。此外,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危机的案例研究检验了七种利益相关者危机应对策略:信息寻求、说服、咨询、威胁、动员、合作和无回应的有效性[54]。
六、内部沟通:变革、领导力、渠道
“内部沟通”是管理相互依赖关系并在组织及其员工之间建立互利关系的艺术和科学,是公共关系和沟通管理学科中增长最快的专业领域之一。自2012年以来,与内部沟通相关的公关文献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研究者多引用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大众与组织传播理论(如媒介丰富性理论、组织传播构成理论)和领导理论等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理论框架,研究内容多涉及对内部沟通的特征、功能和模式的描述性研究,并逐渐关注内部沟通如何影响员工与组织关系,如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参与、组织认同、发声、员工倡导等主题的研究,关于公众关系、组织文化、媒体与技术、领导力、变革管理、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增加。变革给员工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焦虑和压力,学者们提出通过对称的内部沟通建立开放、透明和信任的氛围,降低员工负面情绪与消极发声动机,激发员工对变革的参与、情感承诺和行为支持[55],而变革中以愿景(envisioning)、激励(energizing)和赋能(enabling)为特征的魅力型领导力沟通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水平、变革开放度、变革行为支持[56]。在非变革时期,领导者也需要经常面对员工“发声”(voicing)所带来的挑战,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对语言使用的权力结构、位置和环境的强调为内部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领导者需要坚持动态性与开放性,衡量员工建议性质及其所处的组织内外环境,使用特定修辞策略,开展互动式沟通[57]。组织内部有价值的沟通还取决于选择适当的信息,并以方便员工的方式发送。媒介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强调减少不确定性和歧义对成功的信息处理的重要性,面对面的交流被认为是最丰富的媒介,数字媒体其次,书面媒体最简要,有效的传播需要将媒介丰富性与任务模糊性水平(如数据、消息、符号等不同信息类型)相匹配来选择合适的媒介组合[58],使员工在沟通中获得最大的满意度。随着内部沟通的数字化发展与渗透,内部社交媒体早已超越一种平台或工具角色,成为员工人际沟通与战略沟通管理之间的纽带。研究表明,员工使用内部社交媒体越多,越能感到参与其中、越能感知组织透明度,随着对组织的基本价值观、愿景、目的、战略和活动等信息的充分了解,员工更有可能发现自身与组织的共性,进而增强对组织的认同[59]。作为一种“由内而外”的传播方式,“员工倡导”被视为一种跨越边界的功能,一种组织公民行为,其本质是自愿。员工倡导的信息传播渠道(面对面与社交媒体)和信息效价(valence,即正面与负面)通过影响外部公众对组织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感知,调节公众对组织的认知和行为意图[60]。积极的员工倡导可以帮助组织获得客户,吸引高质量人力资本,进行议题管理以及塑造声誉[61]。
总体观之,内部沟通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出发,充分考虑了领导者与员工的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并不断探究媒体环境、商业环境、劳动力动态带来的多重挑战,促进了其学术身份在公共关系中的发展与合法化。但公关如何能有效而道德地代表内部公众的利益,如何为他们寻求福祉?不同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如何影响与塑造组织的内部沟通实践?内部沟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历史性的纵向变化?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文化效应、方法多样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七、社会经营许可:亲社会与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经营许可(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SLO)一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采矿业,最简单的含义是指利益相关者和更广泛的社会对企业应如何经营持有的一系列要求和期望[62]。作为一个隐喻性的术语,SLO指向一种无形的和不成文的“许可”,逐渐被用来表达对组织及其实践的信任和合法性,SLO的生成取决于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相关文献探讨了SLO概念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亲自我观点”(a pro-self perspective),这一观点认为SLO是一种“交易性”资本,需要持续的投资和监控,对公众意见进行战略性管理,以维护组织声誉[63];另一种是更具参与性和道德衍生性的亲社会观点(a pro-social perspective),将SLO定位为一种“关系”资本,强调互利的“协作、关系建构过程”,其特征是信任、合法性和可信性[64]。满足公共利益、利益相关者参与方法通常可以帮助获得、维护和修复SLO。但是让个人参与亲社会议题可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主动沟通行为(信息前导、信息倾向和信息寻求)与被动沟通行为(信息允许、信息共享和信息参与)可以预测不同形式的亲社会行为(经济支持、志愿服务和政治支持),主动沟通可以预测更高水平的志愿服务,而被动沟通行为更可能导致政治支持[65]。此外,研究者强调了作为一种合法性建设功能的SLO能够促进企业参与社会议题管理:有意识地选择需要进入的对话、采用的参与方式以及使用特定的策略、表现和议题框架,从而为社会变革做出有价值的贡献[66]。
企业社会责任(CSR)被视为SLO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经从“社会义务”框架转向“社会回应”框架,以保持合法性并与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责任是一种社会结构,公众对其认知取决于责任的归属,企业的自我责任形象与公众认知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距。同时,今天的公共领域已经不是人们进行理性争辩的场所,而是一个用图像和热情的回应来表达情感诉求的、密集的、不断变化的、重叠的“野性公共网络”(wild public networks)的集合。CSR必须采用新的话语策略,注重产生情感运动而非连贯的意义,甚至需要拥抱具有象征性和争议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悖论[67]。“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CSV)受到欢迎,它强调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要改善其经营所在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68],企业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建设性对话以有效地创造共享价值比其说服工作更重要[69]。
SLO的关系方法反映了西斯提出的“充分功能社会”观点和霍姆斯特伦的“公关反思范式”观点,为证明公关不再是“宣传术”和操纵性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这一概念有潜力成为公关中有影响力的研究传统。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一直在扩大和成熟,但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始终未得到正面的审视与回应,这一特定视角下的组织-公众关系研究也有待深入。
八、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2020年西方公关学术期刊上的151篇研究论文进行聚类与文本爬梳,呈现了对话与信任、政治公关、公关历史、公关战略角色、危机传播、内部沟通、社会经营许可这七大热点议题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公关历史与危机传播历来都是西方公关学术期刊上的热门专题,随着研究者对文献的纵向追溯与横向挖掘以及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而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政治公关、公关战略角色与内部沟通三个新兴议题的增加,源自企业与政府组织在世界国际关系格局剧变、各个国家民主建设推进、国际经济贸易激增的宏观环境中进行自我战略更新的需求;而对话、信任、社会经营许可这三个关键词在学界引发的热议充分展现了公关的“利他性”“亲社会”特征,公关具有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国家建设、社区发展、组织倡导、公众参与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极大潜力。
在以上七大热点议题以外,2020年的西方公关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零星的议题体现了新兴的研究方向,值得关注。例如“科学公共关系”(science public relations)研究的两篇文章一方面比较了公关与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轨迹的异同,明确提出“科学公共关系”(science public relations)的概念,探讨如何以建设性和道德性的公关方式促进科学与组织、公众之间的共同目的感和认同感[70];另一方面以增强疫苗可信度为研究个案,提出战略传播和公关修辞的工具箱包含许多有利于科学传播的见解和方法[71];对“权变组织-公众关系”(contingent 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s,COPR)的研究分析了在冲突环境中的六种关系模式(包括竞争关系、回避关系、投降关系、中立关系、通融关系和合作关系)[72];公关领域的自我反思从未停止,研究者既反思大数据兴起所形成的霸权对社会制度与权力的强化,探讨公关应如何通过大数据的生产、复制、使用,帮助创建“充分功能社会”[73],也反观公关污名化对从业者本身的人际关系与职业关系的困扰[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