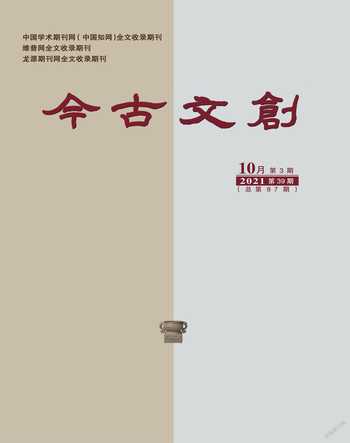唐陵神道石柱的多棱空间研究
2021-10-26郭继锋鲁阔刘兰兰
郭继锋 鲁阔 刘兰兰

【摘要】唐代列置于帝王陵园、贵族墓地神道两侧的大型石柱,是唐陵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标识作用,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唐陵石刻造型艺术风格、艺术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对于唐陵神道石柱的多棱空间研究,有助于探讨唐陵神道石柱艺术表现形式、造型艺术特点、空间布局方式等在当代造型艺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乾陵;石柱;石刻 ;空间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104-02
基金项目: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阶段成果;2020年西安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WL226)成果。
神道石柱作为帝陵标志性构筑物,长久以来人们将其称为华表。根据《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①2002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的唐昭陵111号陪葬墓石柱题记“蒋王故妃元氏墓·石柱一双显庆元·年十一月卅日葬” ②唐人将其称呼为“石柱”。石柱及其他石刻的制作,在唐代由甄官署专司其职,《新唐书 百官志三》中载:“甄官署有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供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敕葬则供明器。有监作四人、府五人、史十人、典事十八人。” ③该类石刻均为唐代官方部门甄官署负责,其“石柱”名称具有官方界定意义,也符合唐代人的称谓习惯,故本文沿用此种称谓。在唐陵神道大型石刻群中,矗立于神道前端陵墓入口两侧最为醒目位置的石柱,是神道石刻的制高点,起着标示和引导的作用,自此标志着进入陵墓的核心区域。神道石柱、石刻、阙楼、墓室等帝陵地表地下建筑、石刻构成一个地上地下一一对应、互为表里的体系,这一体系将陵域分割为天界、现实和地下。经过神道石柱,犹如通过了一扇虚幻之门,带领逝者由地下进入理想天国。
唐陵神道石柱除位于咸阳城东北三原县陵前乡侯家堡唐永康陵西侧石柱上篆刻有“唐永康之陵”,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的唐昭陵111号陪葬墓石柱题记“蒋王故妃元氏墓·石柱一双显庆元·年十一月卅日葬”之外,在其他唐陵均去除名称标榜,这也在无形当中在更大概念内扩展了石柱造型本身的空间引领作用。
唐陵神道石柱大致根据具体年代,参照陵墓石柱制度造型等各方面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期类型:献陵石柱,由南朝样式向唐样过渡期。第二期类型:乾陵,重要转折期。第三期类型:桥陵——靖陵,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长,在造型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在形成规范的粉本基础上仅有尺寸和石柱雕刻工艺上的变化。
一、空间的主宰——神道石刻群的布局
帝陵作为最高级别的墓葬,其陵墓配套设施也在数量上达到极致。以唐乾陵为例,陵墓可分为三重,内城城墙为护卫陵墓主体,东西南北各开一座門,其中在南门神道最前端以一对石柱为高点起首,后为一对带翼石马,再向北则为石屏鸵鸟,在鸵鸟与翼马之间的距离跨度远远超过其他石刻的阵列长度。鸵鸟之后置五对牵马人和石马,十对石人,一对碑刻,两组60余尊宾王石像,再以一对蹲狮收尾,形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视觉空间布局。
在平面空间构图上,石刻群前段2/3部分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并排排列,在碑刻和宾王像部分向外侧扩张空间,蹲狮回归中轴线对称布局封闭队列空间,形成空间闭合。在立体空间构图中,以石柱为制高点、依次降低高度至鸵鸟石刻,再由牵马人和石马拔高高度,至碑刻形成第二制高点,再降低高度至蹲处收尾,形成高地错落的曲线型天际线构图。整体石刻空间布局在秩序中寻求节奏,在庄严肃穆、威严崇高的皇权氛围中营造仪式感与秩序美。
二、空间的表达——神道石柱的方位空间
唐陵神道石柱在整体造型的切面分割布局中,筑基由四面组成方形,柱身为八面组成棱形,棱面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方位空间象征内涵。中国古代对方位有明确的解释,如《文选·张衡·东京赋》注:“辩方位而正则。”薛综注:“方位,谓四方中央之欸也。” ④以东、南、西、北为基本方位,以东南、西南、西北、东北为中间方位。在《逸周书·卷四·武寤解》记载:“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 ⑤此八方代表了全国各地的诸侯。唐陵神道石柱八棱面分别面向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方位,与中华民族本原文化中的宇宙观八卦示意方位有着高度的契合。八卦各方位代表自然界一定的事物或方位,如乾主天,代表西北;坤主地,代表西南;巽主风,代表东南;震主雷,代表东;坎主水,代表北;离主火,代表南;艮主山,代表东北;兑主泽,代表西。
唐陵神道石柱八棱体自永康陵起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汉魏时期的独特造型样式,棱面对应方位以及棱面仙界装饰线刻图案,更充分彰显着八棱体所蕴含的八方概念。
三、精神的释放——石柱线刻的上升空间
唐陵神道石柱矗立于旷野之中,经历千年历史变迁,面向北侧方向的棱面因受北风和阴雨侵蚀,风化现象严重。向阳一面受阳光呵护,在光影的照射下,呈现着丰富而华丽的装饰纹样。
在目前已知的唐陵石柱八棱面纹样上,“献陵为蔓草花纹;乾陵为蔓草,海石榴纹样,以及瑞兽类;桥陵枝蔓和天马类;泰陵枝蔓类;建陵瑞兽枝蔓纹样;崇陵伎乐飞天;丰陵石柱面纹样雕刻保存较好,可清晰辨认迦陵频伽,獬豸,凤,花卉,吹笛童子;端陵蔓草纹;贞陵蔓草纹饰。” ⑥由此大体可知,唐代工匠围绕柱身八棱面,通过线刻的造型艺术方式将体现丰富想象力的物象图案以平铺的方式布满整个柱体,几乎没有留下多余的留白空间。在每个棱面的构图中以华丽的云纹、蔓草纹做底,上衬吉祥瑞兽、迦陵频伽、飞天伎乐等造型,营造云雾缭绕、繁花似锦的天国仙境,将逝者引领至更为广袤的多棱宇宙空间。
唐陵神道石柱棱面以平铺满屏式构图,简洁流畅的刀法,在整体与丰富、饱满与华丽之间,创作出了和谐统一的唐陵石柱造型艺术风格。
四、空间的交织——石柱造型的多棱空间
唐陵神道石柱整体造型中,石柱高度与柱径比大都在6.2—7.2倍的范围内,柱高与柱头高度的比例均集中在3.4—5.3倍之间。
乾陵及之后神道石柱整体造型既不是完全的舍弃唐之前的圆柱造型,也不是完全的采用方形形体,而是采用方形、圆形、棱形相交织的造型处理方式,在方与圆的变化中寻求空间的完美和谐。整体造型以柱基、柱体、柱头三个主体部分组成。柱身和柱顶主要采用八面的棱状造型样式,底座基石以正四方形为基础,上附16瓣圆弧形的莲花瓣,花瓣上置八面棱柱体,莲花瓣之间中缝分别对应柱身的方棱,方棱又与柱头中仰覆莲座下的方形八棱盘相对应,上衬16瓣仰莲座,最上置圆形宝珠或桃1枚。从下至上,由方到圆,由圆至方、归圆,以方做基底,以圆封顶,方圆结合,充分体现了唐陵石刻独特的“方中有圆、圆中有方”造型观。
在石柱构图中,柱身占整体长度的2/3。柱身略带有一定角度的向上收紧,顺陵、乾陵、永康陵、兴宁陵、献陵、恭陵、桥陵等神道石柱,柱身从底向上收紧大概3°左右,下粗上细的渐变式柱体造型,更增加了直冲云霄的空间延伸感。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的帝王陵神道石柱运用了向上收分的原理,使得形体饱满有力。柱身的八棱柱体,方中带圆,圆蕴含饱满之感,方带有力量之感,所感受的力量之感由四面八方向中间集中并向上收紧,展现出像山一样的威严庄重,像塔一样的挺拔耸立,体现出古代帝王陵的威严与肃穆。柱身的凸起棱线,更强化了一个由内向外的扩张过程,赋予石柱雄浑的体块感与空间感。
五、结语
唐陵神道石柱简约饱满的八棱柱身背后所隐含的信息量最为复杂多样,深藏着唐陵石刻造型艺术的文化觀,又综合着唐代人对于“儒、释、道”的深刻理解,更暗含着唐代人对于空间宇宙的观念思考。通过以石柱为引线的唐陵神道石刻传统造型艺术研究和空间论述,对比唐代各帝陵神道石柱的空间造型特点,以新时代的视野,重新观察、体悟和审视唐陵神道石柱的精神文化内涵,更深层次地体会大唐盛世的世界观、场域观和造型观,将唐陵神道石柱的多棱空间架构理念应用到艺术考古、景区规划和艺术创作等之中,清楚地认识唐陵石刻雕塑群的位置布局所隐含的叙事、角色、空间观念,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唐代的宇宙观空间观念,从而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现当代的有效延承与发扬,为中国传统石刻造型艺术在当代中的运用提供借鉴。
注释:
①(南朝宋)范烨编撰、李贤注:《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50页
②李浪涛:《唐昭陵陪葬蒋王妃墓发现题记石柱》,《文物》2004年第12期,第83-85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撰:《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74页。
④(梁)萧统编选:《东京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⑤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武寤解》第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⑥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1页。
作者简介:
郭继锋,男,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雕塑艺术。
鲁阔,女,汉族,陕西富平人,陕西服装工程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雕塑艺术。
刘兰兰,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西安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雕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