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难得成知己战友更兼同道人
2021-10-18居其宏
居其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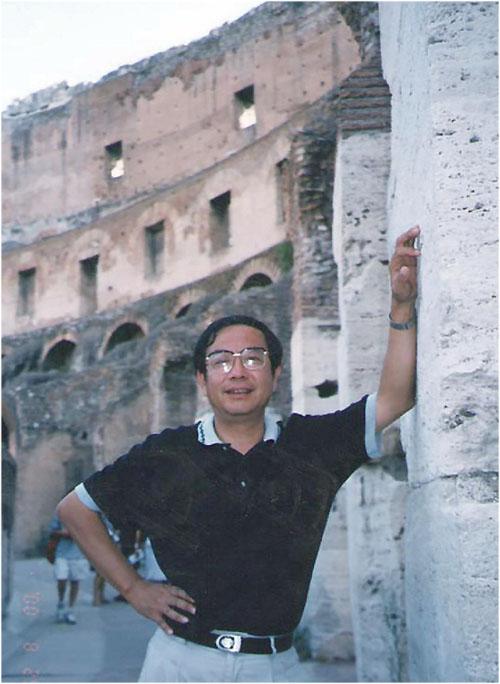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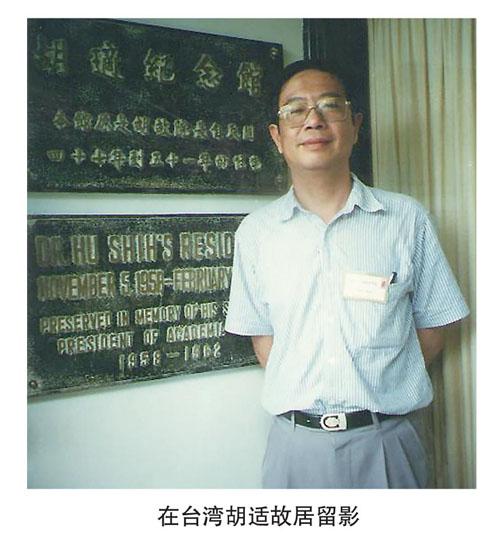
我与戴嘉枋相识且因歌剧结缘。记得在1981年至1982年间的某天傍晚,我到总政歌剧团剧场看戏,在歌剧开幕前,有个戴眼镜、面色和善、操一口浓重沪普的小伙子前来与我打招呼;由此得知,他来自上海,小我6岁,1978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时,他于同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其时正以石夫的歌剧《阿依古丽》为研究对象撰写毕业论文。正所谓他乡遇故知,又是歌剧研究同行,顿时彼此间倍感亲切;谁料想,这次偶遇,便成为我与戴嘉枋长达40年密切交往与亲密友谊的起点。
此后,在我与嘉枋之间便以家乡话打招呼——他称我“居”,我叫他“戴”,且一直沿袭至今;随着彼此接触的日渐频繁和相互了解的逐步加深,遂开启了由相识到相知、由学友到战友、由同乡到同道的历程。
说来也奇——表面看来,无论在平素生活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我和戴嘉枋属于性格迥异的两类人:我生活随意、不修边幅,为文张扬、锋芒外露;而他则慈眉善目,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文章平实厚重但绵里藏针、笔力强劲。与我对烟酒皆有所好不同,别看他的面容常常给人以酒意微醺之感,其实他生来滴酒不沾,连吃几颗蓝莓都要脸红欲醉,但其烟功却与我不分仲伯。
当然,我俩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己,绝非嗜烟之功也。从根本上说,实乃在80年代音乐界宏观语境下,他与我不约而同地步入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并在此后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中观念一致、志趣相投、彼此支持、配合默契、同声相应之故也,从中我亦充分感受到他那深深的知己之诚、烈烈的战友之情、浓浓的同道之谊。
在无私帮扶中得一知己
1983年,戴嘉枋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毕业后,当即回到家乡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因关山阻隔,我与他直接交往不多,但对他发表的文论既十分关注,也非常欣赏和钦佩——从这些成果看,始知他的研究方向和教学课程已正式转入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遂在歌剧研究之外,彼此间又建筑起第二座个人交谊和学术沟通的桥梁。此后,他的作品越读越多,愈发为之折服,故我一有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常去“上音”找“二戴”(老戴即戴鹏海,小戴即戴嘉枋)相聚,从中国乐坛大事、共同关注话题到个人研究心得,遂在海阔天空、畅所欲言中彼此了解日深,渐臻知根知底。
1988年底,我受中国音协分党组之托,创办《中国音乐报》并担任主持报社编采工作的第一副总编辑。为拓展报社的新闻报道业务,在征得社长晨耕、总编辑张非同意后,决定设立《中国音乐报》上海记者站,由戴鹏海任站长,戴嘉枋任特派记者——这是《中国音乐报》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京外记者站。二戴,尤其是戴嘉枋在一无经费、二无办公场所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完全无私而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报社发来不少有价值的报道和采访,其中一些已公开见诸报端,为全国同行及时了解上海音乐界的艺术动态和音乐家们的创造业绩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和贡献。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音乐报》在出版一年之后即停办,上海记者站也无疾而终,但就我本人而言,通过这短短一年的合作经历,令我对戴嘉枋为人做事的职业精神和无私品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92年,戴嘉枋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彼此接触更加频繁,他对我本人的帮助和扶持也更多。其中有几件事,令我没齿难忘。
其一,从1995年起,我便南下郑州,与河南大学武秀之“三结合”教学团队展开深度合作。鉴于武秀之的“三结合”实验及其价值知之者不多,支持者更少,故多年来一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苦苦支撑。我除了尽一己之力外,对此苦思无计。真是无巧不成书,又似久旱逢甘霖——1996年某日,我与已转任文化部艺教司副司长的嘉枋相遇,他问:为何近来在京老不见我?我便将武秀之“三结合”的渊源、意义及其困顿无助境况如实相告。他听罢沉吟片刻,提出一个全国艺术院校音乐剧教学三校交流的方案,真令我惊喜莫名。1997年初,在他周密筹划和精心组织之下,由他亲自率领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班、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领导和教师十余人来到郑州西郊一个叫马寨的偏僻所在,在极寒天气和简陋场地观看了武秀之“三结合”师生的汇报演出并举行座谈交流。此后又组织武秀之团队赴京观看“中戏”和“北舞”音乐剧同学的演出,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三结合”汇报演出,并邀请北京声乐界和音乐剧界专家座谈,赢得大家的高度肯定。就此,武秀之“三結合”复合型表演人才培养模式始为国内不少同行所知。至今想来,如无嘉枋这一番热情关怀和苦心组织,武秀之及其“三结合”很可能仍在那个默默无闻的马寨默默无闻。每每念及戴嘉枋这一为民解困、雪中送炭之举,总有一股暖流在我心中升腾而起。
其二,我在2002年调入南京艺术学院之后,仿照中央音乐学院之例成立南艺音乐学研究所。2004年,嘉枋告别仕途,从文化部艺教司副司长、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任上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音乐学研究所所长。至此,我俩重新成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同行。2004年他在就任之初,便由中央音乐学院牵头,与南京艺术学院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行“全国音乐研究所工作会议”,两所又于2008年在“南艺”联合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两次高层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令刚刚成立不久的南艺音乐学研究所始为全国同行所瞩目。
其三,我在“南艺”主办的一些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如2005年举行的“当代音乐学研究专家论坛”、2007年举行的“全国音乐学博导论坛”等,他非但每请必到且都精心准备了高质量的发言;其提携后进、热情帮扶之情,真让我深深感到温暖。与此同时,鉴于他在这个领域的独特见地和成就,还应邀参与我主持的几个课题的结项论证,如2005年在浙江宁波举行的《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以及《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等课题的现场或书面结项论证会。每次论证,戴嘉枋都认真审读课题全文,客观评价得失,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无论肯定或批评尽皆真诚坦率,视角独到,见地深邃,且多富建设性,对我本人帮助颇多。
其四,戴嘉枋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期间,设立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课题向全国招标,我组成“南艺”团队参与竞标,2008年12月批准立项。此后课题组又先后遭遇火灾、水祸之患,到2013年5月举行结项鉴定并以“优秀”等级通过、2013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结项,再到2014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最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举行座谈会,前后历经5年,其间之艰辛,真有不堪回首之慨。尤其令我和课题组全体成员乃至“南艺”科研领导刻骨铭心、终身不忘的是,在课题中标立项之后,作为这个课题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戴嘉枋带领郭懿和李理两位助手在课题管理、资料搜集、剧场工作、资金使用、器材购置、项目论证和延期结项、成果出版等各个阶段和每一个环节上,或亲临现场、或遥控指挥,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想方设法帮助我们排忧解难,全力以赴推动课题进展。因受篇幅所限,个中若干生动而感人的细节不及备述,但以我曾参与或主持过十多项科研课题的经历看,能如戴嘉枋及其管理团队如此暖心贴心、尽心尽力、模范地践行“领导就是服务”宗旨者,在国内音乐学界绝无第二家!对此,我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在心怀感激之余,无以为谢,乃于《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出版座谈会上,以一面锦旗当面赠予戴嘉枋、郭懿和李理,上书“学术研究开道者,课题管理贴心人”,聊表我们的薄意和寸心。
在思潮论争中结成战友
其实,我与戴嘉枋的战友情谊,始于80年代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大潮以及音乐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以及随后“回顾与反思”的思潮论战中。当时,成为中国乐坛广泛注意的焦点和激烈争论之主战场的有“两潮一史”三个领域——“两潮”者,一为新潮音乐、二为流行音乐是也;“一史”者,即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是也。作为共和国音乐发展进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又一起从事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戴嘉枋和我不约而同地在上述若干命题上秉持同一史观,跻身同一战壕,参与了这场大论战。
首先引起我瞩目的是戴嘉枋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读两本冼星海传》一文①;作者从两本冼星海传切入,实际上提出如何以实事求是科学态度书写历史人物及其得失评价命题,并对某些夸大其词的不实之论发出中肯的批评。其后不久,戴嘉枋又相继发表《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②和《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③,引发一些老前辈的不满;吕骥发表《音乐艺术应当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④一文,批评新潮音乐、通俗音乐不走“正道”而遭到广大人民群众“无声的厌弃”,对戴嘉枋以及同时期发表的我和其他学者的反思文章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指出:“音乐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摆脱党的领导,这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当时,我在创刊不久的《中国音乐学》担任副主编,一看这是在不同学者、不同艺术观和历史观之间当面锣、对面鼓地展开论战的大好机遇,于是在征得主编郭乃安和全体编委同意后,乃于《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全文转发吕老此文,并开辟专栏,提倡在不同意见之间展开平等争鸣。随后,戴嘉枋又以《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商榷》⑤予以回应,包括我在内的音乐学界诸多同行也都撰文参与讨论。
然而,这场讨论与争鸣却因一场“反资”风暴不得不戛然而止,戴嘉枋、我和其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因各自发表的“不当言论”而被当做音乐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代表,遭到连篇累牍的严厉政治批判——在中国音协1990年6月北京举行“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戴嘉枋的“音乐异化”理论成为万箭齐发的靶标之一,有发言者认为:
前些年,音乐界出现的所谓“规范”与“异化”论,其要害在于否定以聂耳、星海为代表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运动的传统,否定对“五四”以来的我国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了科学概括和总结的毛泽东文艺理论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实际上是以特殊规律来否定普遍规律的指导意义,否定音乐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并进而以特殊规律为借口,否定党对音乐事业的领导。⑥
面对如此前所未有之疾风暴雨般的批判和重大政治压力,戴嘉枋不为所动。在一次与我的私下交谈中表示,他就新潮音乐和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所发的系列论文,尽管在个别论点及文字表述上或有某些偏颇之处(这一点我比他更甚),但他确信自己的史观、立论及对音樂界极左思潮的批评经得起历史和音乐实践的双重检验,并对这场批判的结局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回到上海工厂重操旧业,再去当一名车工,而绝不改初衷!
幸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音乐界轰轰烈烈的“反资”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嘉枋担心的最坏结局并未出现,但在风声鹤唳的当时,听罢此言,直令我心潮澎湃、血脉贲张!看他在平和文静外表下搏动着的一颗刚毅不屈之心,乃回想起他与我在音乐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及“回顾与反思”中并肩战斗、彼此呼应、同气相求的情景以及由此结下的战友情谊,不禁由衷地发出赞叹——
壮哉战友戴嘉枋,绕指柔加百炼钢!
在学术研究中引为同道
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在我国音乐学诸学科中,唯有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争议最烈、难度最大、风险最多。纵观当代乐坛历次思潮论争与批判运动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批判事件,多发生在这一领域。
所谓“同道”,乃志同道合之谓也。就戴嘉枋和我所从事、所钟爱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而论,我俩非但志趣相同,共同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和历史观,并在研究实践中努力学习和运用它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来观察、分析、评判纷繁复杂、聚讼纷纭的音乐现象、代表人物、重要作品(含理论批评作品),冷静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期服务于当代音乐艺术建设事业的健康繁荣这一根本宗旨。
对此,戴嘉枋在一篇论文中公开宣告:“笔者也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确信唯物史观是史学工作者手中锐利的理论武器,并力求以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⑦戴嘉枋长期以来的研究实践表明,他不但明言宣告,更是切实践行。
综观戴嘉枋的研究成果,涉及面很广,且凡有所论,必有新见,但其用力最勤、著述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文革”音乐研究。数十年来,其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成果《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⑧《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⑨《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⑩《复苏与再沉沦——〈战地新歌〉中的歌曲創作》?《动乱中的喧嚣——“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的音乐》?以及京剧“样板戏”音乐改革、“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在掌握大量确凿史实、史料基础上,对具体现象、事实、作品和人物等做了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的分析,既不虚美,更不隐恶,是则为是,非则为非,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坚持学术定力,从不对某些时论随波逐流,亦不被特定语境强势裹挟,充分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音乐史家应有的科学态度、理论风骨和超拔见识,从而在“文革”音乐研究这一极具挑战性的敏感领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我敢断言:迄今为止,其结论无人撼动,其成就无人可及。
至于说到他对我的帮助,其中有一个细节令我难忘——我在一本著作中论及“革命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时,仅凭我当时的听觉记忆而没有重读总谱,就对这部作品的结构和成就做了简略记述。戴嘉枋读了书稿之后,即刻指出我的记述有误并补充了确凿例证,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对其坦诚态度、严谨学风和深厚积累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还有两个涉及“二戴”的有趣细节,颇值得一提。
一是在《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结项论证会上,戴鹏海对我在书稿中将批判极左思潮仅限于音乐界表示不满,认为应提高档次,被我当场拒绝。嘉枋明确支持我,并当着老戴和大家的面批评我:老戴之所以如此,都是你惯的!弄得老戴和我只能面面相觑。
二是关于老戴主持编撰出版的《贺绿汀全集》,对书中将贺老在某些特殊语境中所写的某些跟风文章略去不收的做法,嘉枋和我都不约而同地当面提出批评。老戴辩解说,收入这些文章会对贺老形象有负面影响。对此,嘉枋反驳说,在那些特殊年代,贺老的这些文章有其独特原因,丝毫不能降低贺老的伟大人格,而且也要充分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如今将它们略去“全集”之“全”何在,实事求是精神何在?经此一问,老戴一时竟无言以对。
从以上两例亦可见出,老戴对嘉枋有师长之谊,又兼同道,二人关系极亲。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嘉枋则无论长幼、不避亲疏,坚持学理、直抒己见。
2010年,戴嘉枋担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社科重点编写教材项目《中国音乐史》首席专家。这是一项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的教材工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历史观为指导,编写好这部中国音乐通史,对于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游刃有余的戴嘉枋而言,此前虽曾涉猎古代音乐史,且有一部《中国音乐简史》?问世,但毕竟非己所长,故极具挑战性,有大量学术难题横亘在编写之路上亟待破解。
为达成这一工程的预定目标,11年来,非但戴嘉枋本人全力投入、殚精竭虑,且还邀请一些学界同仁参与进来以发挥集体智慧,共同攻坚克难;感谢嘉枋厚爱,让我也有幸忝列其中,为此不仅参加了在黑龙江伊春举行的编写工作研讨会,与大家一起为嘉枋和教材编写出谋划策,且嘉枋在书稿基本成型之后,还把其中的某些章节和最后结论发给我,嘱我一定要严格把关并上手修改——这种信任,唯有用学术研究的“同道”才说得通。
当然,既为“同道”,为不负嘉枋重托,我自当竭尽绵薄、勉力为之。不过,鉴于他的书稿已然十分成熟,以我的水平和功底,也仅能提出若干陋见并做些文字修饰而已。
教材书稿定稿之后,始进入最后的送审程序。鉴于全国通用的这部“中国音乐史”教材意义重大,教育部制订的审议标准极高,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把关甚严,故在审议与修改送审之间已往来了多个回合,对此嘉枋无不一一认真应对,字斟句酌仔细修改,精雕细刻不舍昼夜——此间,他经历的酸甜与苦辣、洒下的心血与汗水,我等纵是“同道”,也难以体察其百般滋味之二三。
古诗云:“平生颇同道,相见日相亲”,以此形容我与戴嘉枋相识40年来历久弥坚的知己之诚、战友之情、同道之谊,倒也十分贴切。尽管我与嘉枋均已退休多年,长期分居南北二京,又很少在学术活动中见面,然而偶有所遇,必如每日常见一般亲切自然、倾心相谈,毫无久别重逢略有陌生之感,而话题亦常常不离彼此共同心心念念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乐坛要闻左右。
时至今日,我已年届“望八”,嘉枋也逾古稀。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的生活阅历、个人情趣和艺术爱好比我丰富得多,对人间万事、学界风云的观察也独具慧眼、别有识见。如能将自己从“文革”时期的车工、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涯、80—90年代的教学和音乐学研究及被批判的经历、此后的入仕与回归、以及成长为真诚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如实写来,必是一部饱含人生况味、充满学术睿智的大书,连同他的诸多著述以及蕴含其中的高尚人品和深邃学品一起,必将大有益于今人和后世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
在本文行将收尾之际,遥祝我的知己、战友和同道戴嘉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中国音乐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