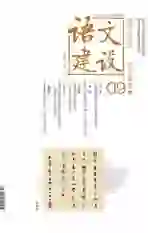心灵受难之下的精神自救
2021-10-14姚舜禹
姚舜禹
【关键词】《峨日朵雪峰之侧》,官能意象,转化重构,精神自救
昌耀的诗歌往往凝聚着个体对特定历史时空复杂的心灵体验,被选入高中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的《峨日朵雪峰之侧》体现了这一特征。对于该诗的解读,《教师教学用书》强调其与诗人生命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峨日朵雪峰之侧》写于特殊的年代,这时的昌耀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却给了他严厉的答复”。很多教师正因忽略了这种密切联系,从而消减了该诗的精神价值。
《峨日朵雪峰之侧》完稿于1962年8月2日,不仅记录了诗人面对“不公待遇”时心灵受难的真实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呈示了诗人以认知转换和精神重构为方式,进行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这需要以官能意象为切口,在整体审视文本意脉、理性分析修辞策略的基础上加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该诗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内蕴。
一、官能意象的联构:心灵受难的三维呈示及其历史关联
“昌耀诗歌中充满了对心灵受难的逼视与摹写”[1],《峨日朵雪峰之侧》便是典型代表。诗歌前十行借由视觉、听觉和触觉三重官能意象的联构,呈现了心灵受难由表及里的三个维度,并且有着深厚的历史纵深感。
1. 心灵受难的表征:“太阳”所隐喻的价值体认崩毁
视觉意象“太阳”在昌耀的诗歌中常常象征生命的价值本体,《峨日朵雪峰之侧》中太阳决然跃入深渊,则隐喻经历长期自我怀疑后价值体认的崩毁,这是昌耀对于彼时“不公正待遇”的直接感受,因而成为受难体验的表征。
然而问题在于,“彷徨许久”与“此刻”“决然”所呈现的明显矛盾应该如何理解?《教师教学用书》中所说的“不公正的待遇”到底指什么?这就需要回溯诗人的生命经历。据《昌耀评传》记载,1962年7月底,劳改期满的昌耀本应和其他人员一样被赦免,但青海省文联却因领导机构改组,而对此事毫不知情[2]。“不公正的待遇”正在于此,《峨日朵雪峰之侧》正是在这样的“此刻”写就的。昌耀对于自我价值的怀疑从1958年7月开始——当时他因《林中试笛》二首而阴差阳错地遭受非难,伴随着之后的管制与劳教,这种怀疑逐步累积与深化,直到这一瞬间,其最终超出了心理承受的阈值。昌耀正是在“此刻”感到“新星作家”的身份标定、价值体认轰然崩毁,自己依然是乃至于将永远是“受管制的囚徒”。彷徨许久的太阳在此刻决然跃入山海,正是诗人此时心灵受难最为直观可感的表述。
2. 心灵受难的隐质:“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所隐喻的精神动力溃散
听觉意象“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折射着诗人更为隐秘而深刻的受难体验——精神动力的溃散。“喊杀声”作为《峨日朵雪峰之侧》中唯一的军事化意象,看似突兀,实则与诗人更为久远的生命记忆有着紧密关联。陷入价值崩毁的昌耀,对于在朝鲜战场和河北荣军学校的经历——这段军旅生涯是昌耀精神动力形成的重要阶段——发生了记忆的置换,由认同转向了疏离。
“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生涯,对于他的确是重要的。它不但使昌耀天性中的写作冲动得到了诱发和释放,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昌耀的人生调控出了文学写作的方向。”[3“] 我的诗歌创作始于1953年秋冬之际,时在河北省荣军学校……那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时期,我的生活兴致极高,蓬勃的青春渴望爱情。渴望着云游与奇迹。”[4]昌耀身上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5]及其衍生的浪漫主义,正是由那一时期的生活经验聚合而成,并在之后成为支配行为的精神动力。
但接受劳教以来逐步累积的怀疑惶惑,不仅让昌耀的价值体认陷入崩塌,更令其对生成行为的精神动力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喊杀声”的“远去”并非石砾滑坡的机械比喻,而是诗人精神动力溃散的实体化复现。“远去”作为解释性修饰语,就意在澄清和强调由认同转向疏离的心理过程。比价值崩塌更为隐秘而深刻的是,诗人因精神动力的溃散而失去了行为支配准则,从而也就失去了重塑价值体认的可能。
3. 心灵受难的痛觉强化与本因暗示:“血滴”所隐喻的个体与现实的撕裂
触觉意象“血滴”指向心灵受难的最为隐秘的维度:个体与现实的撕裂。昌耀有一种“笨拙的试图紧贴时代的追赶欲望”[6],对攀登姿态不顾一切的维持,原因正在于此。然而悖论在于,“雪峰”作为冰冷现实的象征,既是生存的“附丽”,同时也是“牢笼”。昌耀越是试图抓紧雪峰,手指揳入的程度就必须越深,渗出的血滴就越多,痛觉也就越强。
由“渗血”所隐喻的撕裂,一方面以身体叙写强化了心灵受难的痛感,指明了持续的受难状态并非无病呻吟,因此“自救”有着充分必要;另一方面,暗示了个体与现实的撕裂,正是导致诗人心灵受难的根本原因。自罹难以来,昌耀所有的行为,几乎都与预定目的之间存在着深度错位,他越是紧贴现实,现实越是以“严厉的答复”回应他:被流放之前写《我的自白》試图自辩,却换来“火力更为猛烈的揭、批、查”[7];在若约村接受劳改时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家和干部身份,却导致“体力活暗中层层加码”[8]……这些正与“攀登”姿态的悖论暗合。也正是因为这些错位及其衍生的撕裂感,才让怀疑与惶惑层层累积,最终导致了诗人价值体认的崩毁和精神动力的溃散。
二、受难中的精神自救:认知转换后的撕裂弥合与回溯心灵原点的精神重构
《峨日朵雪峰之侧》作为昌耀的精神传记,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心灵受难的静态描摹,更在于呈示诗人进行精神自救的心路历程。
昌耀精神自救的方式与心灵受难的维度逆向嵌合。在认知层面,诗人从西部意象中汲取双重生命启迪,实现了由“撕裂”到“快慰”的认知转换,从而弥合了自我与现实间的撕裂感;在支配认知的心灵层面,昌耀回溯了作为其生命原点的爱与悲悯,重塑了更为坚实的精神支柱,并在更高的价值参照下重建了自我。
1. 撕裂感的弥合:双重生命启迪下的认知转换
在摹写受难之外,昌耀诗歌的意象选取同修辞策略,往往也介入负荷与痛感的转化。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中,与前十行“呈示受难”的官能意象相对立统一的,还有后五行拟构而成以期“转化受难”的西部意象——“雄鹰”“雪豹”“蜘蛛”,二者相承呼应才是该诗的完整意脉。教师在教学时要注重引导学生对西部意象进行探究分析,思考其与官能意象的联系,体悟诗人从中获得的双重生命启迪,在整体把握意脉的基础上分析诗人“受难—自救”的心路历程。
象征生命强力的“雄鹰”“雪豹”从形而上的层面给予了诗人启迪,即“主体精神对客观世界的超越性”[9]。雄鹰与雪豹是昌耀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如“鹰隼领有霄汉”[1“0] 神祇半狮半鹰,眼膜半垂”[1“1]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12]……其往往象征孤寂、高傲、神圣和宗教。诗人如此“渴望”与雄鹰、雪豹为伍,实际是对二者生命哲学的神往。孤寂、高傲作为雄鹰与雪豹本身的特质,拉远了个体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释放了雄鹰与雪豹最为本原的生命状态,二者本真的生命强力、自由无惧,正是在野性的飞扬与奔跑中,得到了完整的释放与展现。由此,距离所衍生的撕裂感被转化成了心理上的势能,借由这种心理势能,雄鹰与雪豹实现了主观精神对于客观现实的超越,彰显了更为坚实的生命内核。
昌耀以全诗仅有的一个语气词“啊”来凸显这种渴求的强烈,其中还包含着认知转换后的彻悟与解脱。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采用朗读法引导学生仔细品味,加深对诗人行为的理解。诗人在渴望中已然顿悟,个体因现实际遇所产生的撕裂感与孤独感,可以从西部风物的象征与隐喻中觅得更为高贵的精神因子,即“意味着澄明、镇静、无惧”[13]的神性与宗教式力量。面对与现实之间的撕裂,肉体无法挣脱客观现实的框囿,但主观的精神可以在追求澄明、镇静的过程中获得跃升,从而将撕裂感转化为精神上的超越感,使更为本真、劲健的生命力量得以勃发。
象征生命宁静与沉潜的“蜘蛛”,从形而下的层面给予了诗人启迪:以无言默对苦难,方能将苦难转化为生命的滋养。昌耀的所有诗歌中,只有《峨日朵雪峰之侧》一首出现了“蜘蛛”这一意象,但很多教师的关注却远远不够。教师应当从“蜘蛛”的生物属性切入,以具体特征连通抽象内涵,引导学生探究其中蕴含的生命启迪。蜘蛛,小得可怜,而且先天缺乏发声器官,故而静止无言是其恒常的生命状态。正如《教师教学用书》所言:它的出现,它的沉默,使一切自以为是和虚张声势都失去了力量。蜘蛛与诗人一同见证了太阳跃入、石砾滑坡以及诗人受难的絮语,但它却以一贯的默然沉潜提醒着诗人:“屈辱诸多。进退维谷。唯大智无言”[14]。这是极富宗教意味的生命哲学。
在双重生命哲学的启迪之下,诗人实现了认知的转换。“快慰”二字独立成行,便是最为明显的精神标志。在此时的昌耀看来,雪峰不再是生存的囚笼,而变作宗教式的修行之路,之前那些不公待遇和严厉答复,皆化作富有宗教意味的心灵历练,成为通往更高精神层次的媒介。
2. 精神支柱与自我确认的双重重塑:回溯生命原点后的精神重构
在认知转换的背后,昌耀的精神自救还潜藏着更为本源的心灵支配力量——爱与悲悯。这是诗人矢志不渝的生命原点:“他把爱奠基为人生的本体维度”[15] 直到今天我仍然信仰诗是生命化育……这样的诗人必具有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与生俱来的生之悲悯”[16]。诗人正是借由对爱与悲悯的心灵复归,完成了精神的重构。
一方面,昌耀凭借爱与悲悯造就了更为坚实的精神支柱。在如此巨大的困境之下,诗人依然渴望与雄鹰、雪豹为伍,依然以悲天悯人的姿态亲近了蜘蛛,这正源于爱与悲悯的精神支撑。进一步而言,与其说诗人是从西部意象中“汲取”了生命启迪,毋宁说意象中包蕴的更高精神价值是诗人以爱与悲悯所建构的,因为“任何可能的世界图像的形成,都取决于爱和旨趣行动的建构”[17]。这便是昌耀精神支柱重塑的印证,这时的诗人将爱与悲悯奠基为支配行为的准則,因此才能使内向的生命意义开掘与外向的现实认知深化并轨而行,在爱与悲悯的感召之下与意象发生精神共振,敏锐地知觉“雄鹰”“雪豹”“蜘蛛”所包蕴的生命启迪。这是撕裂感弥合的深层心理机制。爱与悲悯从支配认知经验的心灵层面,调和了行为与目的之间的错位,并让诗人拥有了不断更新生命意义的可能,因此是比单纯经验层面的“动力”更为坚实的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昌耀借由爱与悲悯,在心灵中重建了价值参照系,从而在更高精神维度上重塑了自我。“价值及其秩序是隐藏在我们心灵之中的先验事实,是由‘爱自发地依据其本性构建出来的”[18],《教师教学用书》中所言“更是找到了一个新参照”,正在于此。雪峰变作苦修之路,撕裂感萃取为快慰,其本质原因是诗人身份认同的转换。这时的昌耀,已经不再纠结于外在给定的“作家”或“囚徒”身份,而是发自内心地成为宗教式的修道者。这种身份转化的根本力量,正是爱与悲悯的价值观照。在这种观照之下,诗人以更高的精神维度重构了价值参照系:生命意义的内核不在于一味乞求社会与历史的认可,而在于不论身处何时何地,都对生存的现实施以最大限度的爱与悲悯。此时,对于“修道者”昌耀而言,血滴渗出成为以自身精华反哺现实的爱之行为,而“快慰”的本质内涵则是因此获得的精神充盈,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得到以爱为准则的重新确认之后,所生成的满足感。因此,只要作为参照的爱与悲悯持续存在,诗人就能不断地探索生命的价值,更新生命的意义,永葆心灵与精神的自足感与充盈感。
三、余论:略谈《峨日朵雪峰之侧》的文学史意义
昌耀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中构筑的修辞景观及倾注的爱与悲悯,不仅让这首诗充满着丰实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同时,也使得这首诗具有了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从纵向来看,之于昌耀个人的创作历程而言,这首诗所呈示的“自救”,标明诗人在面对现实、转化苦难时发生的根本变化。这首诗之前,逼仄的现实与昌耀之间往往呈现不可调和的对立,诗人转化苦难的方式主要是寄希望于外在神祇式的力量,如《群山》中盼望山峰变为向生活长啸的太古巨兽,《海翅》中将引航的船帆描述为远古神话的复制品。自《峨日朵雪峰之侧》以降,正如前文所言,昌耀将逼仄的现实变作了心灵修行的场域,转化苦难的方式也由被动的“他救”升格为主动的“自救”,如《断章》《水手》中折射的生命意志与强力。这正是诗人在复归爱与悲悯之后的主体觉醒。此外,从《峨日朵雪峰之侧》开始的这种觉醒,使得诗人自发地将爱与悲悯作为之后创作中反复吟咏的母题,期望以此为准则整合时空与万物,在作品中呈现更为博大的诗学景观,最典型的便是《慈航》和《致修篁》。
从横向来看,这首诗的艺术成就与精神价值,要远高于同题材、同时期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整体意脉圆融完整,紧扣诗人的生命体验,并且呈示了诗人动态的心路历程。反观其他西部诗人的代表作,不论是李季的《柴达木盆地》《黑眼睛》,还是闻捷的《河边》《夜莺飞去了》,几乎都流于以重复、零碎的意象进行去自我化的抒情。此外,自1962 年起,“诗歌创作特别强调政治意蕴的开掘,而缺乏基本的审美意味”[19]。在郭小川等写出《战台风》《青松歌》这样缺乏审美余韵的诗歌时,昌耀依然关注着生命的内在景观,坚守着诗歌最为基本的美学尊严与思想价值。
以文学史的视域观照和把握《峨日朵雪峰之侧》,是教师在备课和教学时不应忽视的。《教师教学用书》明确指出了学习昌耀诗歌对普及当代诗歌史的作用。教师在备课时应阅读了解“十七年”诗歌的整体风貌以及昌耀的人生经历,在教学中以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构建参照系,引入与这首诗相关的作品和史料,开辟自由的言说空间,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有理据地、个性化地理解和鉴赏这首诗,并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性思辨,评价文本的价值内蕴与作者的精神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