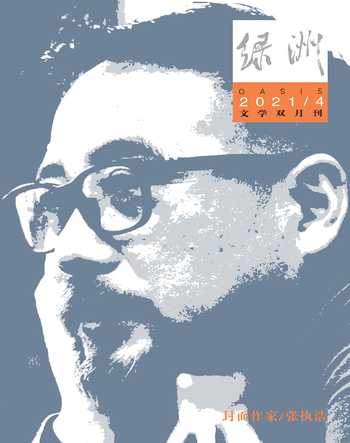涉世书
2021-09-13刘星元
刘星元
1
拿上毕业证,我拖着自己有限的行李,来到了户口所在地的这座城市——沂城。在沂城的人力资源市场里把自己抛售了多日,我终于找到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在此之前,因为囊中羞涩,无法去住价格不菲的宾馆,我已经在城中村一家名叫聚合的小网吧里窝了一个多星期了。这一个多星期里,我每天都会步行去人力资源市场抄录各类招聘启事,然后再一家接一家地打电话,去公司应聘。这是一个希望渐次被磨灭的过程,刚开始我还是有选择地去求职,行业类型、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假休标准——我事先反复掂量着自己的底线,后来,这底线越来越低,我便慌不择食,只要能找到工作,这些标准就都不再刻意去计较了。
夜晚,我就在网吧里休息。偶尔会在QQ上和同学聊聊天。聊天内容无外乎是求职之类的话题。有几个同学已经找到了工作,不出所料,都和自己的预期相差甚远。更多的是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他们叙说着这些天来的所遇和所感,抱怨着社会的不公,却又在抱怨过后相互鼓励,期待明天会有阳光一扫阴霾,前途一片光明。网吧里烟雾缭绕,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无忧无虑,他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嘴里叼着香烟、喊着脏话,眼睛直勾着屏幕上的游戏页面,消瘦的脖颈支着脑袋,似乎要钻进屏幕里,手却一刻不闲地在键盘上猛烈而迅疾地敲击着,在一轮游戏结束之后,他们或旁若无人地放肆大笑,或用拳头愤愤不平地砸向桌面,或如泄了气的皮球疲惫地靠在椅子上发呆。偶尔也会有人在这里下载被赋予某种特殊颜色意义的视频,边下边看,毫不避讳。那些充满诱惑的声音肆无忌惮地在凌乱、昏暗的空间里持续迸发着,让人既冲动又反感,既血脉偾张又茫然无措。整个下半夜,我便在这各种音像混杂的环境中半醒半寐,日复一日。
连续在网吧住了一个多星期,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物流公司。说是物流公司,其实就是一家小小的配货站。虽说和自己学习的物流管理专业相符,但从学校里学来的东西完全用不上。公司共有四辆货车,分别跑两条专线,货车开进来,大家便都来卸货,货物被工人从数米高的车上抛下来,也没有人在意是否损坏。等卸完货,大家便再将这一天收到的货物装上车,目送货车开走。卸货之余,我平时的工作是分拣货物——或是把别人要寄的货物分类堆成小山,或是在卸下的堆积如山的货物里跳出某件货物,或抬或扛或背地带到前来取货的顾客面前。
既干装卸工,又做分拣员,的确很累,但尚可勉强支撑。让我受不了的是这里的脏。因为怕浸湿货物,地面上不能洒水,那地面便积了一层尘土,一有风吹,地上的尘埃便开始飘荡。不安分的尘埃到处钻,简直无孔不入。打个喷嚏,鼻子里便冒出一股黄烟;吐口唾沫,唾沫里就包裹着一堆沙尘。忙完一天,去墙角处打开水龙头洗洗脸,脸上的灰尘便和自来水一起顺着指头流下来,再用手摸摸头发,头上便黏糊糊一片,手上则像涂了一层药水。
就在我坚持不住想要辞职的时候,赵勇飞也应聘来到了这家公司。当老板把赵勇飞领到灰头土脸的我的面前时,我们俩同时愣住了,各自尴尬地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知该说些什么。赵勇飞是我隔壁班同专业的同学,在那所我们刚刚毕业的高职学校就读时,他曾担任系里的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因为宿舍卫生方面的问题,我们宿舍还曾和他有场不愉快的经历。那时候,我们绝对都没有想到,毕业之后的某段时间,曾经的“仇人”竟成了相互支撐的好友。
赵勇飞的到来,让我单调的生活有了一丝生气,每天,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有时,晚上还会在附近的大排档炒上两个小菜开开荤,边吃边聊上学时候的糗事,互相“挖苦”。然而,如此过了半个月后,我们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聊天的内容了,日子又重新跳入波澜不惊的镜面里。
终于有一天,赵勇飞对我说,他想要离开这里。之所以下决心离开,是因为我们的另一位同学蒋一维给他打了个电话。蒋一维告诉赵勇飞,他在另一座城市里找了一份好工作,包吃包住,底薪三千元,年底还有不菲的提成,他说公司正缺人手,正在大量招聘员工,怀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思,他希望赵勇飞也能过去和他搭伴儿。这个电话让赵勇飞喜出望外,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他决定第二天就辞职。赵勇飞离开的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找了个借口向老板请假送他去车站,等他刚进入候车室,我便迅速转身,向距离汽车站最近的站牌走去,我在站牌下等了二十多分钟,那辆载着赵勇飞的车就开走了,它从我身旁穿过,一刻也没停,快速闯入了前方茫茫的细雨中,最终远离了我的视线。此后,我就和赵勇飞失去了联系,几年之后,我从另一位同学口中得知,蒋一维把赵勇飞拉入了传销团伙,他俩被传销团伙洗了脑,他俩的亲人又被他俩洗了脑,最终被骗得倾家荡产。
从汽车站回来,我也递交了辞呈,重新回到了借住网吧的日子。
我想找同学聊聊天,倾诉我心中的伤悲,却发现,才刚刚个把月,气氛好像就不一样了。刚毕业时,几乎每天都有同学打电话、发短信或在QQ上留言,说辛苦,谈希望,相互勉励,互相支撑。而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彼此遗忘了。我查看了一下手机,最近的一个短信是二十多天以前一位同学向我哭诉他和我们班班花分手的事情,而我的回复也异常简短:好好的。那时候,我正在给货物分类,把相同属性的货物放置在一起,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复。现在回顾我发出的这三个字,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想要去表达什么,我不知道同学是否以他独有的思维解读出了这三个字的含义,反正,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信息发来。
我当时尚未想到,同学之间的关系还将继续疏远。如你所见,再后来,我许多躺在QQ里的兄弟姐妹们,时而亮一下头像,又总匆匆下线,为了各自的生活奔波着。手机里储存的名字依旧还坚守着自己的位置,但联系却越来越少,我不敢确定这些曾经熟悉的号码还有几个人在用。就像某年某月某一天接到的一个电话,他说:猜猜我是谁?陌生的号码,陌生的属地,陌生的声音,却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可是,他究竟是谁呢?
2
从本地的一家网站上搜索招聘信息,发现有一家文化公司招聘采编人员,于是便去面试了。那时候,我已经在一些小报刊发过几篇小稿件了,似乎是这些小豆腐块起了作用,老板对我很满意,当即便录用了我。工资标准是实习期八百元,实习期过后一千五百元。虽然工资不高,但这次的工作毕竟和“文化”搭上了边儿,所以心里还是挺知足的。
老板姓朱,四十多岁,面目清秀,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在他的办公室,他眉飞色舞地给我和其他几个新员工展示自己与市领导的合影,并倾吐自己要在文化行当里闯出一片天地的雄心。这座北方城市,是王羲之和颜真卿的故里,或许是因为先贤的庇荫,书画之风向来繁盛。作为生意人,我的老板从中窥见了把文化转化为经济产业的门道,他承包了一家省级网站的地方频道,以文化活动家的身份把自己装扮起来,做起了书画生意。
我的工作是以记者身份采访本城的一些书画名流。其实,所谓“采访”不过是掩人耳目,实际工作是借助采访和宣传之名,向书画家们收取一定的宣传费用。朱老板明确指出,宣传费只要现金,不能用书画作品代替。在我的意识里,书画家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他们高高在上,以翰墨指点人间,想采访他们,难度大概不小。一位比我早半个月入职的同事指点我,从一些书画网站上搜索本城书画家的联系方式,然后打电话询问,询问内容无非是“看到您的书法作品如何如何,想对您进行一次专访,并把访谈信息发表在省级网站上”之类的话。没想到這一招竟然屡试不爽,只要打过去电话,书画家们无一例外,全都爽快地答应,并且比我还急迫地约好了访谈时间。
第一次采访的是一位书法家。这位书法家似乎比我更清楚我的工作,他先是拿出各类贯以“国际”“华夏”“中华”名号的各类会长、院长、理事、会员或杰出贡献奖、终身成就奖的荣誉证书,让我们欣赏,以示自己名副其实,然后再步入正题,回忆艺术生涯,提炼创作心得,顺带着也品评一下当代艺术作品。至于他的作品,他不拿出来,我也没有执意要去看。临走时,我还没张嘴向他索取宣传费用,他便早已笑着从怀中抽出一个红包,交到了我手上。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在这座小城,书画界的大师真是比比皆是,用时下的段子来说,从楼上抛下一块板砖,也能砸倒一群大师。或许是有了免疫力,时间长了,再见到一些大师,竟然不再诚惶诚恐了。甚至,还有些书画名家主动给我打来电话,把价钱讲好,也不用去实地采访,他们就把自己的事迹发给我,嘱咐我在网站上发出来。当然,他们发来的稿件,除了修改一些错别字,其他诸如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的记录,是不可以删减的。
这样干了大概一个月,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老板召集我们说,最近资金链困难,下个月再发工资,并且鼓励我们要带着情怀去工作,要把它干成事业,而不是简单的工作,如果干得好,下个月涨工资。听完老板的话,我们一扫心里的阴霾,浑身又充满了干劲。
第二个月该发工资的日子,老板又召集我们说,公司决定要办一场书画展览会,前期需要投入一定费用,等展览会结束后,公司早已挣足了资金,到那时,前两个月的工资和第三个月的工资一并发放,而且,还要给每个人发放额外的奖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终究还是没说出来,于是便根据老板的吩咐,联系场地、布置会场、邀请书画家……终于把展览会操持起来了。看到那些书画家一个个将人民币交到公司会计手里,我们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然而,老板还是没有发工资。我们一群人敲开老板的办公室大门,再一次向他讨要工资,他态度很好,说马上打电话安排人员去银行取钱。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我们的工资,而是一群胳膊上刻着文身、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的小痞子。小痞子们刚把我们控制住,老板便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数落我们的不是,不是说这个工作态度不认真,就是说那个业务能力差,致使公司业绩下滑乃至亏本经营,将我们批得一无是处。一位女生借去厕所之名在厕所里拨打了报警电话,我们才得以脱身。事后我们才知道,这家公司已经利用同样的方法忽悠了好几批初涉社会的学生为其免费工作。
三个月的辛苦就这样打了水漂。我们有些气不过,便向一些部门投诉,却无任何作用。我们心灰意冷,不愿再就此浪费时日,便各自散去了。那天夜里,我与在这家文化公司工作时最要好的两位同事——谭友和公雨林一起聚了个餐,其间聊起对未来的打算。谭友决定回他们那座小县城,他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有教师资格证,他想先去当地的私立学校就业,为以后考取公办学校的教师做准备。艺术院校毕业的公雨林说,小县城没有艺术专业的用武之地,他决定留在这座城。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却不知道何去何从。深夜时分,我们就在那家小餐馆门前彼此挥了挥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从此之后,便再无联系了。我想,所谓的萍水相逢就是如此吧。
几年后,我的一位厨师朋友在他的朋友圈晒出了一张荣获本城特色餐饮店的牌匾,同时转发了某个行业协会以这座城为名的公众号推出的关于这次评选活动的新闻。我点击进去,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依然显得那么文雅的朱老板。几年不见,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意从书画文化行业拓展到餐饮文化行业了。我用自己的经历小心提醒朋友,朋友却说:用八百块钱买个口碑,值。
3
刚到那家文化公司就职的第二天,我就在附近的城中村租到了房子。
城中村藏在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的某个角落,与这座城市呈现给世人的面貌不同,它是一处“藏污纳垢”的所在,所有与高速发展的城市不相匹配的人、事、物,都被不可知却又无处不在的力量用不同的遭遇赶到了此处,譬如露天垃圾堆、用金属和塑料搭建的简易棚、修自行车的老摊位……狭窄的小巷像一条曲死的蛇,不知道最终要将身躯探到一处怎样的所在。墙上到处写着画圈的“拆”字,因为风吹雨打和日晒尘磨,字迹都黯淡了。
我租住的那座小院,一共两层。第一层是原始建筑,房主自己家住;第二层是临时加盖的,它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觊觎政府的拆迁补助。因为是加盖,又因为加盖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拆除,所以便显得随意,只用一层红砖简单地垒起来,有了房子的样貌。楼上一共三间房,我居最西边,月租一百五十元。另两间则分别租给了一对情侣和一个中年男人。
情侣的关系总是反复无常,这几天还甜甜蜜蜜的,那几天就开始打打闹闹了。有时候,房主怕打扰四邻,就沿着摇摇晃晃的木排梯爬上二楼来劝架。也有劝不好的时候,房主就将他们一起撵出去,等到再回来的时候,竟然又手拉起手来了,脸上全然不见吵架时的凶狠和狰狞。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体会到,所谓争吵就是把对方最为不堪的伤疤揭开来给别人看,正是通过他们的争吵,我窥见了他们各自的伤疤。我试着从那些谩骂之词中先抽丝剥茧再查漏补缺,还原他们的经历:他们是从老家逃出来的,女子本是有夫之人,而那个男子,则是女子丈夫的同学。这男子常来同学家玩,一来二去,就和女子搞在了一起。两人决意私奔,最后就躲避到了此处。
爱情固然是美好的,但冲破道德的藩篱之后,如何生活,显然他们都还没有深思熟虑。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需要一场抉择来表明接下来要走的路。最后,是女人为他们的爱情做出了让步的举动,女子开始晚出早归,连周末也不休息,听男子对房主说,女子似乎是在某家商场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自从女子从事了所谓的售货工作后,便开始精心打扮起来,脸上涂抹着厚厚的脂粉,身上穿着露骨的衣衫。男子的说法和女子的举动都让我感到疑惑:难道从事售货工作需要昼伏夜出,需要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疑惑归疑惑,既然人家那么说,我们也就姑且那么信了,都是萍水相逢,没必要刨根问底。男子却依然游手好闲,不但游手好闲,他还借着女子出去工作的空隙,隔三岔五地领回来不同的几个女人。这对情侣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争吵也越来越激烈,甚至有几次,与女子迎面相逢,我会看到她脸上或深或浅或红或紫的伤痕。每当我的目光瞥到她脸上的时候,她便慌乱地将脖颈扭向别处。
如此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突然想起,已经很多天没有听到那对情侣的争吵声了,满腹疑惑地向着那房子望了望,才发现房门前空空如也,平时晾晒的衣服之类的东西,已经不知所踪。看来他们是已经离开了,然而他们是一起走的还是彼此分开走的,是萍水相逢之后再萍水散去还是轰轰烈烈之后继续轰轰烈烈,恐怕永远都是个谜了。
至于中年男子,虽说在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但我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屈指可数。与那对情侣相比,他的生活平平淡淡的,几乎没有任何波澜,穿着虽不时髦,但是很得体,一身休闲西服或者夹克,恰好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特点。他开着一辆旧夏利,早出晚归。听房主说,他好像在什么企业任部门经理,至于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他不说,别人也就不问。
有时候,迎面相遇,他会递上一支烟,我摆摆手,表示不会抽,他也不在意,就自顾自地抽了起来。虽然没有接过他递过来的烟,但我却看出,他一直抽的都是二十元一盒的泰山。他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不间断地抽,我在心里悄悄计算了一下,他一个月大概就要抽掉我几乎一个月的工资,按理说,以他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租一套公寓的,不知为何屈尊与我们这些勉强糊口的人住在这样破败的地方。
有一次,我又一次被生活撂倒,迷茫的我徒步穿过这城市一角的某个喧嚣的广场,发现一个乞丐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地半卧在水泥地板上,用颤颤巍巍的臂晃动着手中的宽口白瓷茶缸,茶缸表面的瓷已经掉了三分之一,露出里面黑黝黝的金属色泽,人们三五成群地从他面前掠过,并未因他的存在而迟疑片刻。由彼及己,我忽生同情,走过去,从口袋里摸出打算坐公交车的那枚硬币,弯下身,将它安放在他的茶缸里。
他听见响动,抬起头,刚说了个“谢”,另一个字还未出口,就愣住了。那一刻,我也认出了他——那个住在我隔壁的中年男人。我们彼此都尴尬了起来,尴尬过后,我们又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向着对方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从此之后,我们见了面就不再说话。
又过了些日子,他从小院搬出。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他。
4
冬天到来的时候,我又一次辞了职。
那是一家售卖保健品的公司,我的工作是到那些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旧小区里和老人们聊天,并以开授健康讲座的方式招徕他们购买保健品。这份工作没有底薪,全靠售卖商品赚取提成,随便一款产品,只要贴上“两千八百八十八元”的标价牌,就可用“亲情大减价”“回馈爸和妈”等名义售出八百八十八元的价格。而这八百八十八元,我们可以抽取四分之一的提成。
我的搭档是公司里的明星销售员,我跟着他穿梭于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家庭,唯一相同的是,这些家庭都是空巢家庭,家中只有孤独的老人。爷爷、奶奶、干爹、干妈、大叔、婶子……在不同的老人面前,搭档口中的称谓灵活转换,对于产品功效的宣传也越来越让我惊疑,我既佩服他又隐隐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妥。我说出自己的疑惑,我的搭档嗤之以鼻,用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蹦出了两个字:愚笨。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或许真得好好谢谢我的愚笨——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先知先觉,我辞职了。在我辞职的一年多后,我在本地的报纸上看到了查处这家企业的新闻报道。
再次失业的我学会了抽烟。无数个黄昏,我沿着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漫无目的地游走,偶尔停下来,点上一支五块钱一盒的白将军,烟草与火相遇,浓烈的气味迸发出来,呛得我直流泪。我想起和我同居沂城的诗人邰筐,想起这位诗人的一首短诗:
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听不到抽泣声/他只是在无声地流泪/他看上去和我一样/也是个外省男人/他孤单的身影/像一张移动的地图/他落寞的眼神/如两个漂泊的邮箱/他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和我一样/老家也有个四岁的女儿/是不是也刚刚接完/亲人的一个电话/或许他只是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为即将到来的漫长的黑夜哭/或许什么也不因为/他就是想大哭一场/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他动情的泪水/最后全都汇集到/我的身体里/泡软了我早已/麻木坚硬的心/我跟在他后面走/我拍拍他肩膀关切地/叫了声兄弟/他刚刚点着的烟卷/就很自然地/叼到了我的嘴里。
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这首诗。在边抽烟边默念这首诗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像诗中的“我”一样注意到了我,有没有人也跟在我的身后。我只知道,没有人拍拍我的肩膀,也没有人喊我一声兄弟。跨河大桥上车来车往,它们经过我,又绝尘而去。一路上,我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抽烟,似乎只有在烟雾缭绕中,才能感受到这人间烟火的温暖。
那一年春节,是我唯一一次在外面过年。除夕那晚,失业的我蜷缩在自己租住的小房子里,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无非是说些工作忙不能回家过年之类的话语。话还未说完,我就匆忙挂掉了电话,我怕若不挂掉,下一刻,鼻子就会抽泣起来,眼中的液体就会流出来。
面對那一面白色水泥墙面上零散点缀着的几颗灰色斑点,我什么也没想,只是静静地发了一会儿呆。这座院子里,那些被生活逼入死角的人,他们都陆陆续续越墙而走了。甚至,连房主都撇下了这座院子,去省城与自己的儿孙团聚去了。偌大的一座院子,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本来,房主也是要撵我走的,我说了诸多好话,并且把身份证押在他手里,他这才勉强同意让我在春节期间继续住在这里,并替他守着这座院子。
太闷了。尽管北风呼啸着从墙缝间钻进来,还是太闷了;尽管烟花的身姿从玻璃窗上散下来,还是太闷了;尽管别人家团圆的欢声笑语从隔壁涌进来,还是太闷了。
我想要出去走走。关上门,沿着晃晃悠悠的木排梯爬下一层,打开院门,跨出院子,再转身锁上,然后再从巷子里左绕两次,右绕两次,就来到了大街上。平日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也没有几辆车,就连沿街的店铺也都关闭了。只有路灯以百米行距森严地站在马路两旁,兀自亮着,渲染着这座城市的虚假繁华。头顶的天空中,偶尔有烟花展开,又迅疾地熄灭。迎着寒风,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着,我如阿Q附体,突然觉得这人间的灯火和烟花都是我一个人的。想到此,我挤了挤嘴唇,微微地笑了笑。
那一夜,时光似乎被无限拉长了。在漫长的时光里,我就这样一直走啊一直走啊,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走向何处。
责任编辑车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