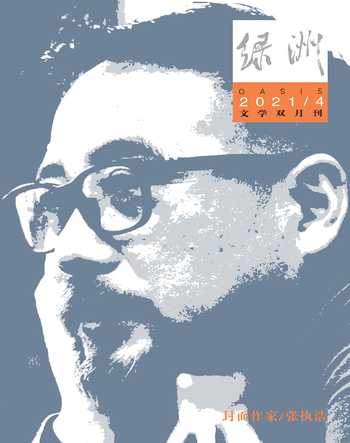嫁到郴州
2021-09-13朱小平
朱小平
1
我嫁到郴州已有二十年。
婆婆家住房傍苏仙岭下,依郴江河畔,近百年来,老房子虽经几番修葺,却从未迁移
郴江,一名黄水。据史书《太平御览》49卷引盛弘之《荆州记》曰:“黄箱山一名黄岑山,在东南三十里,其山郴水所出。”
北宋词人秦观,1097年三月被贬阪居旅驿郴州时,在郴州旅馆写下名词《踏莎行》,下片结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我在苏仙岭“三绝碑”摩崖刻字上,读到此词的第二个版本:“幸自”改成了“本自”。古人作诗词,也多是反复推敲的,“幸自”也好,“本自”也罢,反正秦观在旅馆视线所及的郴江,只可能是我们家现居的苏仙岭脚下这一片河面流域。
郴江全长75.7千米,系湘江支流,也是郴州市区的母亲河。她发源于南岭之一的骑田岭之巅,冲出江口峡谷,穿行在郴山丘冈间,然后一路向北投入耒水的怀抱,终源汇聚于湘江。依此看来,我想“本自”应该更为确切吧。
刚来时,听闻郴州有句流传甚久的民谣“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有些触痛,好似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山水荒芜的绝地。
公交车缓慢驶过繁荣的商业街文化路,报出义帝陵站台,才知公元206年,徏义帝沿水道迁都于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郴州竟是一个舿舟载来的城市。
唐宋时期,那些被贬谪到岭南、海南的京朝官员,千百年前就曾涉水郴江。隋朝薛道衡《入郴江》有“扬帆溯急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至郴江赠张署》有“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三转疾于飞”。
翻开《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那时的郴江商业交通兴旺景象,有文字為证:“南货北往,北货往南,悉上此经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坊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清明上河图》,莫非北宋画家张泽端也曾来过郴州?要不然,我怎么会感觉汴河上有郴江的影子?
2
当我从郴江历史追溯中回神的时候,四楼窗前的桂花树尖上,传来婆婆邀约我散步的召唤声。
我们平日里走得最多的路,是郴江白鹿洞桥至石油桥这一段游道。早上从鳌头湾出发,沿河岸走半公里到白鹿洞桥边市场买菜,傍晚反向石油桥,绕两桥一圈归家,婆婆的手机计步显示六千余步。她玩手机比我溜,网购、头条新闻、全民K歌、微信运动,无一不通,无所不能。
婆婆偶尔兴奋得像个孩子,向我炫耀她又占领了朋友圈运动打卡封面。我知道她的好友并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但我没说,怕扫了她的兴。
这狭短的六千余步游道距程,却纵贯了婆婆漫长的七十多年人生印迹。
婆婆出生于新中国成立的那年春天,有好几个未曾谋面早夭的哥哥,她应该算是其父母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孩子。她的第一声啼哭飘落在郴江白鹿洞桥与石油桥之间的河面上。
每每行至河道某个路段,她就会翻出记忆库中的往事片段,讲述我没有见证到的——她的青春以及个人情感。讲完总是重复发出苦尽甘来的感慨:“那时,哪能想到有今日的好生活啊!”
3
婆婆说,她的整个童年几乎都泡在郴江里。
站在六中北校围墙外的游道护栏边,俯瞰郴江河水面,隐约可见几方不太规整的天然大石头,石头上布满毛茸茸的浅绿苔,小鱼儿摆个尾,也能搅出一圈浑浊。
原先的河水是澄澈清亮的。母亲牵着幼儿小手,挎一篮衣服,来到这个洗衣挑水的码头,小心缓慢地踏着石阶一步一梯下河,幼儿坐在最后一级临水的石梯上,小脚丫子在水中晃荡,母亲的捶衣板带着节奏敲击在平滑的石板上,那是世间最美妙动听又最铿锵有力的摇篮曲。
码头右前方有座裸露在郴江河中间的荒草洲。婆婆童年时期还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老是觉得胃空,对一切可食物品都充满向往。趁大人忙碌没空看管她,偷偷溜下挑水码头,划拉几招“狗刨”,游到荒草洲上找吃的,揪冬茅草芯生嚼,越嚼越甜;掀开石头捡螃蟹、挖团鱼蛋,煨在灶火里,满屋子香喷喷;冬季用筲簊在河沿黑草丛下一撮,就有一海碗小河虾,多鲜的味道啊!就算什么也不做,夏季泡在清澈的河水里找凉爽,心情也是惬意畅快的。
我喜欢成熟丰收的秋季,想起故乡洞庭,平阔的湖面上,布满密匝匝的绿叶红菱,它们点缀在金灿灿的稻田与白水鱼塘之间,构成一幅永恒的暖色系画面。
苏仙岭后山卜里坪辖区张家湾在河对岸,是外公(婆婆父亲)的故乡。每年秋天外公从家山采摘一担茶籽,光着干瘦的膀子,气喘吁吁挑过河,身上尽是荆棘刮刺的痕迹。“哎哟,怎么把衣服搭在扁担上?”路人这么问过外公。
“衣服烂了要买布补,皮刮烂了会长好。”外公穷怕了,把钱看得比命重要。
茶籽铺在老屋坪场晒几天,晒到茶籽壳裂开,外公摸搓着茶籽粒咧开嘴笑,当时年幼的婆婆极少见外公如此开心,只有腊月年关,外公在煤油灯下舔着口水,一遍遍数着手里那几张薄钱时,曾经闪现这样的笑。
茶籽一身是宝,茶籽壳引火煮饭,易燃耐久火力强;茶油炸出米面美食套环、兰花根、烫皮、瓜片,揣着这些年礼,花五毛钱,买一张承载着婆婆的诗和远方的火车票,去栖凤渡外婆娘家走亲戚看风景;茶圃(茶籽榨过油的茶渣)熬水洗出来的头发柔滑黑亮,还是闹鱼(毒鱼)的上好佳料,闹死的鱼放心大胆吃,安全无毒。
不知道是不是怕人哄抢,外公每次闹鱼都在夜晚。天擦黑时,外公蹑手投几块茶圃在郴江河,年少的婆婆屏气凝神等到半夜,她要负责站岸上打手电筒给捡鱼的外公照亮,其时河面浮起一层白花花的鱼,鳞光泛滥,她的作用只是在岸上看守那一大脚盆没死彻底的鱼,不再蹦回河里,并协助外公抬回沉沉地大脚盆。
闹死的鱼适合做熏干鱼,嗜酒的外公,有了下酒的好菜。
酒,水一样的流液,悲喜交织,有时是药,有时是毒,变幻莫测。外婆讨厌酒,夫妻俩经常在餐桌上当着两个女儿“开战”,相互嫌弃仇视,婆婆的耳朵里灌满了他们的谩骂声:外公喝到面红耳赤,骂外婆“扫帚星”,生不出儿子,还克死了他的儿子;外婆则指桑骂槐地喊天,说老天没开眼,不该收了好人,哭求大眼睛菩萨,收了眼前的恶人。
比婆婆小七岁的妹妹还不谙事,只顾着笑哈哈抢鱼吃,她天性乐观胆大敢闯敢拼,后来走上仕途,性格决定命运不无道理。婆婆则常被这样的场景吓得不敢上桌,饿了,就去郴江河里找生食祭牙口;愁了,就去郴江河岸打水漂(斜着丢小石片在水中,溅起水面一波三折)扔烦恼。婆婆一生扎根在郴江河畔的土地。
婆婆是靠郴江滋润着长大的。
4
每逢中元节,邻家祭祖烧冥币纸钱是在自家屋门口,而婆婆却要带着晚辈沿河道走到石油桥,选定第三个河栏墩,才点燃香烛郑重开启祭拜仪式。
我当了书法老师之后,婆婆家祭祖的冥钱白包由我执笔。照着婆婆纸条上的姓氏辈分誊写,她一再提醒:千万别落下了给唐伯的那封白包。我很纳闷:婆婆的父亲是河对岸卜里坪张姓,母亲是栖凤渡李姓,姓唐的伯伯是谁?
唐伯就是外婆一生恋恋不舍的前夫。
外婆1914年降生在以鱼粉闻名全国的郴城栖凤渡,李姓盐商家的二小姐。十四岁得了一场风寒,问诊吃药不见好转,其父请来算命巫师施法,法师开示:速嫁人冲喜,方可救命。
外婆的父亲长期从事食盐买卖,跨过很多桥也走了很多码头。他挑着空篾箩筐与镇上几个小商贩搭伴而行,自栖凤渡步行郴州歇一夜,次日再步行去广东坪石进货,回来时,几个人合租一辆骡子板车,货物载在板车上,人紧跟在后面,一个来回大抵要七八天。来来去去的征途,结识了在郴州铁路工作的唐伯,虽比女儿大了十岁,但相貌周正,为人和善,询问得知唐伯尚未成家,当即把女儿许配给他。
唐伯家住处正是我们家现居位置。他家祖山在郴江边四普庄山后,民国时期唐伯家境何等富足啊,为了便于祭祖临时歇脚,竟买下三进三间大房。外婆嫁来一直住在这,土改时分出去左右两进,仅剩一百多平方米地基。据外婆说,唐伯一家待她如同己出,夫妻万般恩爱,婚后她的病真的奇迹般好了。
也不知是何种怪病,外婆婚后接连生了六个儿子,养到七八岁,莫名其妙突发晕厥不醒,一一夭折。
我问正在上医学院的大崽,他根据症状分析,外婆的那些孩子,患的有可能是某种先天性心脏病,现代医疗技术可通过手术治愈。
1943年,外婆又染风寒,带着最后剩下的幺儿,回栖凤渡娘家休养,唐伯留守在家。他不是舍不得满屋的财产,是怕外婆回家找不到他,就没有躲进山里防空洞,有天在郴江河码头洗袜子,日本鬼子见他头上戴着铁路上的帽子,以为他是抗日兵,残忍地在他身上连刺七刀,尸体随着红色河水冲到石油桥河段,被一块石头挡住,过路的好心人,找来铁锹铲子,把唐伯埋葬在郴江河滩上。当天,日本鬼子在白鹿洞村杀死三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唐伯是其中之一。
一个月后,外婆才从乡邻口讯中闻此噩耗,因当时铁路已炸毁,她踉踉跄跄拖着病体赶到郴州,跪在河滩上的一堆新坟冢前,泪流成河……若不是身边的幺儿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她真想纵身跃下郴江河,追随亡夫而去。
短短三十天,外婆承受着人非物也非的悲痛,家被洗劫一空,徒留四壁空泥墙,幺儿巴巴地望着她,从未下过田地干过农活的外婆,开始挖土犁田,种菜种粮。
时间制造伤痛又疗愈着伤痛。
河对岸卜里坪张家湾的外公,1939年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三年后逃亡回来,妻子跑了,儿子丢在同族人家中寄养,养得瘦骨嶙峋,眼睛鼓起老大,说是患了“疳积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外公,有幸得媒人牵线搭桥,父子双双入赘外婆家里,算是有了落脚营生之地,可惜他视为珍宝的儿子与外婆六岁的幺儿,一年内先后因疾病不治而去。
外公重男轻女的思想,嵌入骨子到死未改。外婆生下婆婆时,他叹一声气,多年后看到自己的大外孙女时,他还是一声叹气,叹息声似乎更为沉重。1975年,外公因哮喘病复发去世。婆婆怀着小儿在腹中,他终究未能见到他的男丁后代,未能舒出那一口怨气。
外婆八十九岁高龄逝世,她说享到了两个女儿的后福,不枉此生。弥留之际,似乎仍有遗憾,老是对着婆婆念叨唐伯,念他的俊模样,念他的体贴,念他悲惨的命运,嘱咐婆婆中元节莫忘给唐伯烧衣烧钱,要烧在离他最近的河岸……
外公和外婆,两颗伤痕累累的心,用各自身上的疤痂磨蹉对方一生。
5
有时候,用心聆听长辈们的过往旧事,不妄自判断谁对谁错,也不失为一种孝顺。
六十年代末,苏仙岭底下有一家木棚小酒馆,用竹筒子定斤两打散酒,也有人坐在酒馆柜台边尝酒试味,爱酒的外公在这里碰上了同样爱酒的公公,酒逢知己。
婆婆还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公公的细节:他左手还燃着烟蒂,右手就取下耳朵上别着的烟点上了,手指熏得跟湘西腊肉皮一样,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屋檩条,讲话“这里嘛——那里么——”操一系列停顿思考的拖音官腔,其实只是个烧煤炭开火车的,其实那只是公公湘西方言口音。只有初小文化的公公,1958年从花垣县十八里洞苗族山村招工来郴州铁路,生肖比婆婆足足大了一轮。
从婆婆的描述,我听出了她一开始就没看上公公,这也为之后的离婚埋下了伏笔。
我见到公公时,他已是面容慈祥的老人,晚年腿脚不好,一个人住在郴江河畔机务段单位房,固执着不肯来我们家。他话语不多,知道我们要去看他,总会买些好吃的在房子里等着,碰上年节,悄悄地封好红包,塞进我们衣兜口袋。2017年,公公摔了一跤,伤得很重,在医院躺了半年,也终究没能爬起来,躺到了香山陵园长眠。
外公吃了公公从铁路食堂端来了几碗荤菜几瓶烧酒,晕头转向替他说话,语气斩钉截铁,婆婆若敢不同意,就滚出家门,他招公公当儿子。外公唱完“红脸”,外婆接着唱“白脸”,绵声柔语劝导婆婆:“工人吃香呢,月月有薪水,不愁吃穿。”
公公拎着一套换洗的铁路制服,从郴江河边机务段单身宿舍,轻松走几步把自己搬到婆婆家做了新郎。
“制服口袋里肯定有一本存折。”我这么说着逗婆婆。
“鬼呢!钱屑子都没有,他那三十三元工资,全给他自己抽烟喝酒还不够。”多年后,婆婆说起他时,仍旧悲愤交加。
河岸一侧全是婆婆队上的菜地,游道还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崎岖泥路。知情的邻居背着婆婆,窃窃告诉过我:这条路你公公婆婆年轻时的“战道”,冷战时几个月不见公公足迹,热战时两人打得灰头土脸,有次把“战道”扩展,打折了队上几块土刚结辣椒的辣椒树。
那个年代城乡差距大,公公瞧不起婆婆是农民,婆婆抱怨公公没有家庭责任感。
婆婆成了鳌头湾村史上首个主动起诉离婚的“巾帼英豪”。法院判决:两个孩子,大女归公公,小儿归婆婆。
从不后悔离婚,如果时光倒流,打死也不离,对孩子伤害太大。这是很多离婚女人自相矛盾的感悟。
法官上门调解,只要公公说一句软话:保证少喝酒,多回家吃饭。婆婆就会撤了诉状继续过,多少婚姻瓦解在一时之气。
1984年,婆婆把上段婚姻消耗的体力精力,全身心投入到劳动发财致富之路上,种菜卖菜、养鸡喂鸭、拖板车收潲水养猪,男人一样干活。次年,她攒下了建一层毛坯房的本钱,壮起胆子向银行贷款,推翻外婆的泥砖房,原地建起两层红砖楼房,楼下出租楼上自住。随着农民工蜂拥进城务工,尝到了出租房屋甜头的婆婆,又加建了兩层楼。
1994年,队上的菜地全部征收,变成飞虹路的医院、学校、菜场、企事业单位,她成了城里人。婆婆买了养老保险,坐在家里一点点拾起年轻时的爱好,看书读报,唱歌跳舞玩电脑,不让一日虚度。
没有雨的夜晚,白鹿洞桥上人影穿梭,我和婆婆闲散着停靠在桥边,轻风送来绿化丛中盈盈花香,郴江两岸七彩霓虹闪耀,透映在河面化作繁星点点,隔着红绿灯的苏仙岭福地广场,传来热闹响耳的红歌声,婆婆笑说他们调子没唱准,要在G调上,嘚,是这样唱的:“党的光辉照万代——”
我不吹牛,婆婆确实唱得好听。
责任编辑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