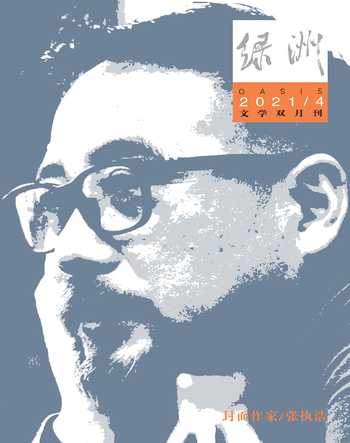洗头
2021-09-13唐新运
唐新运
记忆,如同脱发者头上的那根白发,怎么也不会掉。拔了还会长,而且比先前更茁壮。
消息,怎么挡也挡不住。它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屁,隔的布再多,还是能钻出来,照样散发出韭菜和葱花的味道。
赵得贵悄没声息进了他爹的门,他为此还有点沾沾自喜。事实上,天在上,地在下,中间还有他自己,加上他的爹,至少已经向四个地方发出了信息。
村里人早就在村子周围时刻凝望注视着他的身影,人的相貌会变,可走路的姿势一辈子都不会改。这村子周围观望者之中,就包括我的父亲,还有羊圈里一只肥壮的两岁羯羊。只是这羯羊,没有运气看到赵得贵,因为院墙阻挡了它的视线,它看到的是我父亲焦灼渴盼的表情和在院里游走不停的身影。还有,一盆清水,一把锋利的刀子。
赵得贵是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明天是清明节。
赵得贵兄弟有好几个,多得村里人记不清楚都叫什么名字,因为有用处的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的名字记住与否都不重要。反正,据辗转整理的家谱记载,他们这一辈人名字最后都有一个“贵”字,改变的只是中间的那一个字。我记得很清楚,赵得贵前面有一个哥叫赵富贵,不知道排行第几。一辈子种地,并没有富贵起来,因为富贵被赵得贵给“得”去了。所以赵得贵在省城为官,赵富贵在村里种地。不得不承认,赵得贵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村里人基本上都是孝子,每年清明,赵得贵必赶回来给母亲扫墓,不管有没有衣锦还乡和光宗耀祖的嫌疑,人,终究是回来了。
清明时节,天有些凉,草要长未长,太阳升起照在身上,有些暖洋洋的感觉,可太阳一掉下去,天马上会冷,那冷,透过衣服,往骨头缝里去。村里人一般都在清明前一天放下手里的事情,在村的周围等赵得贵回家,无论事情大小多少,多年如此。赵得贵家周围,就会比平时多出些人来,有事没事找出些话来。
赵得贵的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小的院落,离我家不远,站在墙头,就可以把院里一切尽收眼中,饭菜的香气也会串门走院。院落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但很是干净整洁,这说明赵得贵的爹——赵爷精神非常好,也同时说明他不会在这个院子里终老——房子干净整洁,将来才会卖个好价钱。
赵得贵的爹年纪称不上高寿,但在赵姓家族中辈分很大,据说他的排行不光是在村里,在全省也是最大,大到后三辈、后四辈、后五辈的人都不好称呼他,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太爷”。后面小辈中爷爷叫他太爷,儿子也叫他太爷,孙子还叫他太爷。这“太爷”怎么也得算是个七品吧,只是前面少了个“县”字。祖孙三代都叫他太爷,终觉不妥,就都含糊地称其为赵爷,直至现在,村里人基本上都把他叫作赵爷。我的爷爷年纪和他差不多,但辈分太小,除了小孩子,村里人都叫他哥。
赵爷院里有两三头猪、四五只羊、七八只鸡,除了已经养家养乖的蛆虫蚂蚁和老鼠,以及年年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一群在枝头叽叽喳喳的麻雀外,院里基本再无活物,确切地说,是能够在院里活动的东西。
一扇白杨枝叶做的篱笆门,背南面北向前走,房子恰好面南背北。前院子中有棵成熟到参天又豪情笼罩四野的榆树。推开房门,掀开门帘,迎面扑来一个硕大的土炕,差点要把人逼出门去。炕不能不大,不然怎能容得下如狼似虎的六七个兄弟。
赵爷忘了添煤,炉子苟延残喘,他蜷缩在墙的一角,裹住被子,蒙头盖脚。屋里显得阴冷,还有一个原因是屋里人太少,没有人气,更少了人的火气。人气也还是有的,不过是在远处,并不能赶几百公里来烘暖这个屋子。
赵得贵进屋捅了捅炉子,还往炉子里添了新煤。两根莫合烟的工夫吧,屋里的寒气转到门外,赵得贵的汗就冒了出来。
“爹,冷不冷了?”
“冷!”
“哪里冷?”
“我身上冷,手脚都冻得很!”
赵爷冷了好几年了,前些年他就说自己冬天怕冷,尤其是脚。赵得贵拉了一大卡车煤卸在院里。他还特别叮嘱他的爹,这煤,想烧多少就烧多少。他每年往家里拉一大卡车煤,那煤根本烧不完,风吹日晒,时间一久,手一触就破,还把石灰刷的白墙弄黑了一坨。他还在三伏天找人重新盘了炕,完全按照先前的模样,在炕的上面又多加了几条羊毛毡。他没有想到的是,爹在和先前一样的炕上躺下,会想起自己的娘。他想着,自己住烧着暖气的房子,绝对不能让爹冻着。其实,谁也不想让自己的爹挨冻。
没想到如此过去了好几年,今天爹还是说冷。一个人会不会觉得冷和两点有关系吧,一是居住环境,二是自身的耐寒能力。比如冬天换毛的畜生——狗。赵得贵想到这里,对自己的想法很不满意,差点扇自己的耳光打自己的嘴巴。牲口是牲口,怎么拿爹和牲口相提并论?说实在的,赵得贵在城里为官,在城里衣食住行了几十年,除了回到村里还用夹着普通话的方言之外,在城里他基本都说“官话”了。别说他自己就连村里人都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户口在城里,村里已经没有他的地了。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拿城里的事物和村里做對比。看到大街上年轻人旁若无人又肆无忌惮的亲热,他就想村里只有两匹马才会在树下互相啃对方的脖子,狗啊,猪啊,羊啊,才会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趴到对方的身上;看到好多时尚女子为了显其腰细长腿屁股大的好身材,三九天穿得单薄但忍不住哆嗦,他就偷偷笑了,牲口到了冬天都知道换毛,人怎么就忘记添衣呢?
赵得贵想不通的事情还很多,比如他爹老说自己的脚冻得很。
赵得贵确实是个孝子,这从他对村里人的谦逊态度和从不摆官架子就可以看出来,毕竟自己的爹还在这里生活,邻里总会有个照应。
再加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赵得贵对村里有些辈分不大但年龄不小的老人尤其敬重。人老了,自然经的事多,明白的道理更不少。他带着自己的疑问去拜访这些老人,当然也没有忘记带些廉价的烟和酒。
“你的爹年龄又不大,精神也很好,该给找个老伴儿了!”
“找老伴儿和脚冻得很有什么关系?”
“有了老伴儿就有人给他焐脚了啊!”
赵得贵终于明白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同时他又有些埋怨起自己的爹来。你是我的亲爹,我是你亲生的儿子,有事和想法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赵得贵把兄弟们请到一起,商量给爹找老伴儿的事情。赵得贵并不是家中长子,但他的官最大,日子过得最好。兄弟们分散在各处工作,有各自的家,巴不得赶快给老爹找个老伴儿照顾,所以都同意给父亲找个老伴儿。倒是赵爷,脸上有些红晕,有些羞涩。他想,这么多年来,都是自己给儿女们安排婚事,这个家庭会议的场面太过熟悉,只是换了角色。先前是自己决定,现在自己倒被别人左右。不过这种形式挺好,先民主后集中,谁说得对就听谁,反正从此以后,自己的手脚再不会冷。赵爷在村里参加的会议多了,民主、集中、酝酿、决定之类的词在耳朵上磨出过老茧来。这个家庭会,也有些许的争论,但毕竟决定了,而且,这个决定太正确了,太英明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赵爷开心得很,大事情解决了,心里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步履也显得轻快不少。他拿出酒来,还给几个吸烟的儿子发了烟。这烟酒比送人的要高档得多,就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偶尔喝上一杯抽上一支,那还得恰巧逢上赵爷有好心情。
孩子们来得匆匆,去得忙忙。清明一过,他们就被风吹落叶一样刮走了,因为先前就由风送来。院落又变得冷清、安静和寂寞,赵爷还沉浸在兴奋和畅想之中,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孩子们做出决定的那一瞬。
人,一高兴和开心就要喝酒,想助兴;一悲伤痛苦的时候也要喝酒,图忘却;平平淡淡不痛不痒的时候还会喝酒,求升温。人不可能不喝酒,没有理由不喝酒。那赵爷的酒喝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祝福、吹捧和掌声是最好的下酒菜,自己的好心情是自己喝醉的最好理由。
夜已深,赵爷却不见了踪影。是我父亲发现赵爷不在房子的炕上,但这怨不得别人。和赵爷喝酒的人,把醉酒的赵爷送回家,安顿在炕上,盖了被子,生好炉子,才放心离开。这是酒友酒徒的最低门槛,也是必需必要的酒德。
是赵爷自己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难道,是他嫌大炕烧得太烫,非要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父亲是赵爷的本家孙子,多年来照顾赵爷,久而久之,从习惯变成义务,变得理所应当。除了这些,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家也有好几个孩子,赵得贵兄弟几个,不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更是我们将来的希望和寄托。我们全家都以能和赵爷家沾亲带故感到自豪,更有人无法和他们接近而失望和嫉妒。
那赵爷喝酒喝丢了,找不到了,是谁的事情?是我们家的事情,是我们家最大的事情;是谁的责任?是我们家的责任,是我们家无可推卸的责任。谁让我们是本家,还又是近邻?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庄,几十个巷道,无数路口和墙根,数也数不完的角落,一家连着一户的棚圈,一眼看不完的树林。赵爷喝醉去的地方次次不同,这次他又会去了哪里?
我和父亲拿着手电筒,穿着厚厚的棉衣,开始搜寻。那手电筒不是太阳,无力普照,只是寒酸孤独的一小束光。晃来晃去的光点,匆匆忙忙的脚步,招惹得狗叫此起彼伏。我们父子兩人是打破别人酣梦的人。我跟不上父亲的脚步,设法在他左右,只能紧紧跟在他身后。现在也是,即使我现在走路的速度非常快。
寻找期间的艰辛和痛苦不必多说,关键是赵爷终于被我们找到了!躺在庄稼地旁的树林里的他还活着,睡得正香,抱着头,蜷缩着身子,他还在身旁树下撒了一泡尿,都没有打湿自己的鞋面和裤脚。他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们父子两人都想不通。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了,尤其醉酒之人的所作所为,姑且当作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酒吧!事是酒做的,话也同样是酒说的。
我们重新送赵爷回家,父亲背他回去。我跟在后面,看得很清楚。我们没有离开,和衣而卧,睡在他的身边,反正炕足够大,再睡几个人也盛得下。一直到他清醒。
我们没有多说话,既没有给村里人说,也从没告诉过赵得贵兄弟。因为照顾赵爷已经习以为常,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有些事情只要你做了,就有人会去说,自然人人都会知道。操心太多,会掉头发。
赵爷非常重要,在整个村里都是,非常符合“举足轻重”这个词,除了辈分大之外,关键在于他是赵得贵的爹,这是真实的。假如你要找一个人办事,有求于这个人,有时候还不如求助于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人太多了,有配偶、子女、司机、秘书等等。除了配偶,身边的人再多,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人家的爹。从古到今,中国的官员大部分都追求“忠孝两全”,忠不必说,孝肯定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形,终归是少数。这个事情,我在想,一直在想。我的父亲在我之前就在想,比我想得早,而且现在仍然在想。可我们家的邻居陈鹏举不这么想,也没有想到过。陈鹏举,不但要像大鹏一样飞起来,还想飞得很高,可他没有丰满羽毛和中空的骨头,他的身材好比一个装满大米小麦的麻袋,扎口处放了一个南瓜。身体肥壮,里面装的多是糟糠;头硕大,里面主要是糨糊。他一直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有着老鼠般的精明和机敏,事实上牛就是牛,猪终归是猪,如何超得过老鼠,自从出现生肖以来,老鼠总排在第一名,牛在后面,猪更不必说。陈鹏举是有些聪明,但这种聪明是只看到眼前的聪明,他看不到过去和将来。很都事他也想不到,他吃饱了就犯困,稍一思考就开始打呼噜。
有一年,他遇到一件烦心事,什么事情现在我早就忘记了,反正这事急着要做,还要做好。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几个大事、若干个关键处可陈鹏举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没有人指点和提醒,他居然突发奇想地背了一只膘肥体壮的两岁羯羊直接到省城找了赵得贵。赵得贵的态度很热情,来了老乡,居然还没有空手,这老乡还称得上是儿时玩伴。可赵得贵的老婆是个“吊死鬼”,脸吊得很长,除了没有吐舌头,其他和鬼差不了多少。这“鬼”见不得光,更见不得人,直到陈鹏举离开,“鬼”才露面。陈鹏举连口水都没喝上,赵得贵也因为激动和高兴吧,忘了倒水。陈鹏举送出一只羊,连口水都没喝上,但他心里仍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赵得贵答应给他办那件闹心的事情,还表示有十足的把握。事实上,这事情有多大呢,我想来想去,不会是让陈鹏举去当外国的元首吧?或者,是去当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当然,如同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常见的情节一样,生人一离开,“鬼”就会从屏风后或墙角处轻移莲步走出来,脚下没有声响,身后免不了还有影子。“鬼”出来拖地板,洗拖鞋,开窗户,洗茶杯,结果没有茶杯可洗,省下一份力气,好跟赵得贵吵架。她最厌恶赵得贵的家人和乡亲,经常来,每次来都有事情,进门之后总是忘记换拖鞋,还要抽莫合烟,把烟灰弹在地上,带来的土特产大多是瓜子、黄豆、大豆,最多是两只鸡,都不是值钱的东西,还占地方。
陈鹏举出门之后情难自已。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了快乐就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不是有句话说,“有快乐一起分享,快乐会增值和翻倍吗?”可这快乐是个“空中楼阁”,是饥饿难耐时自己画的饼,是镜中花、水中月。包子还没有蒸熟,陈鹏举就急着掀开了笼屉,这蒸汽没有乱跑,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过屋串巷就来到了赵爷的家。这赵爷虽然经常把自己灌醉,但身板硬朗,耳聪目明,鼻子还很灵敏。那时候电话是个稀罕物,赵爷穿着停当,拎着他那相伴已久的黑色人造革包出了门。村里人把人造革简称“人革”,差点就叫成“人皮”。村里人都知道,赵爷这身打扮,肯定是要上县城。可这次县城上得有些久,天刚亮的时候出门,天开始黑的时候才回来。上个城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村里人不但结伴前往,有时候还单独上城呢!大家不知道的是,赵爷上的是省城,一天一个来回。他出门的时候必须经过我家,还经过陈鹏举的家,因为我家和陈鹏举的家墙挨着墙,还有一条巷道连接两家。赵爷急匆匆走路的时候,陈鹏举正拿着一把铁锨,把牛圈里的牛粪一锨一锨地扔出圈外,他们两个人只打了声招呼,没有多说一句话。陈鹏举没有问赵爷去哪里,赵爷也没有问陈鹏举的牛粪什么时候能收拾干净,拉到哪块地里。
陈鹏举在家中静候佳音,因为当初赵得贵答应得理直气壮、豪情满怀。可是如今还没有消息,当然,噩耗也没有。到了年底,他又背了一口袋自家种的、精挑细选后准备留作种子的葵花籽去找赵得贵。那葵花籽我见过,和他一样,肥厚饱满,不要说老鼠,人见了也眼馋。赵得贵态度依旧,语气里却有遗憾,说这件事情非常难办,自己能力有限。“吊死鬼”在上次上吊的地方继续上吊,一如既往地无暇见人。陈鹏举心里透凉,也开始有一丝透亮。瓜籽留下,人回来了。他心疼他的肥羊,还真舍不得那袋可留作种子的瓜籽。我后来慢慢知道,收些乡下亲戚的土特产算上受贿,这是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
陈鹏举心里的那一丝光亮没有扩大,像灯芯,没有拨亮;似火星,无法燎原。直到多年之后,自己孩子长大成人,还进了城,长了见识,与他们谈笑间,说起当年的困惑,群策群力。终于得出结论,居然是因为绕过了赵得贵的爹。找儿子办事,居然没有让老子知道。另外,赵爷种麦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帮过忙;赵爷割玉米的时候,他也没有搭过手;赵爷喝醉不回家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找寻过。在小小村庄里他和赵爷近在咫尺,却要到几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去找赵爷的儿子办事。我觉得陈鹏举没有父亲聪明,没有父亲那么奸,如果父亲有事去找赵得贵,不管赵得贵是否愿意帮忙是否同意办事,赵爷肯定会给我们帮腔,说起父亲做过的事情,落下的好。
前面说过,陈鹏举的脑子里装着糨糊,可这糊糊,粘住的是陈鹏举的思想,并没有粘住他和赵得贵的感情和关系。要是换作我,我先自己把那一口袋瓜子炒熟了吃完,补好了脑子,再做打算。
有一年的春节。大雪。
雪厚得没过我的膝蓋,至今我没有再见过那么大的雪,可能雪确实大,也可能当时我的个头矮小。虽然我早已成年,吃吃喝喝四十年,可事实上身材既不魁梧也不高大。
一个早晨,我们都没有清扫房前和屋后的雪,只勉强清扫了自己出门的路和别人经过我们家的路,给自己方便也要给别人方便。那路还窄得可怜,勉强够两个人并排行走,两个半都不行。
全家商量好要去父亲的父亲家,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家里。按照当地习俗,大年初一,一般都要去自己的父母家里拜年,大年初二一般要上岳父母的家门。大雪把整个村子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可能只是我有这种感觉。门前的一棵榆树,不知道是忘记还是无力,树身被压得快挨到地上,也不抖动一下身体,把我着急得在房檐下不停地晃悠和抖动自己。我就想问问那树,是懒得不想动还是抖不动,那雪究竟有多大有多重,比得过“三座大山”吗?
雪掩盖了整个村子,我家去爷爷奶奶家的路,被雪连接得不留丝毫缝隙。天亮了,放晴了,再没有一朵雪花落下。因为老天爷把昨晚该下的雪,下得干干净净,一丁点的存货都没有。各人自扫门前雪,我们去爷爷家的路因此通了。事实上,如果路不通,我也可以踩着雪走过去。毕竟,雪只是没过膝盖,没能漫过头顶。人啊,是万物之灵,只要还能呼吸,总会有办法。
我们一家收拾停当,却迟迟没有动身。我知道,今年和往年一样,要等一个人。
等赵得贵。等赵得贵来看他的爹。等赵得贵看他爹的时候经过我家院门。等赵得贵看过他的爹之后光临我家。
这种等待毫无悬念,必有结果。因为只要赵爷没有死,赵得贵每年清明和春节都一定会回来,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他的“根据地”“补给站”,还是他的“疗养院”。当然,当时的我们根本无法完全体会到,只是成年后在外面打拼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时,才慢慢体味出这种感觉。才算是知道,才算是明白。
等待是一种折磨,让人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翘首期盼。不仅仅折磨我们一家人,还有家里所有喘气的活物。
是身影,是清晰的身影,还有那逐渐真切的面容。那是赵得贵一家经过我家院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房子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形和位置,将会省去很多麻烦赢得不少先机。赵爷家离我家很近,要去他的家必须经过我家。当然,如果从村西头进来,东拐西拐也能到赵爷的家,只是,有捷径的时候,谁愿意多走弯路。牛羊也知道节省力气,人怎么会做无谓的浪费。其他邻居想见赵得贵,得轮流在家门口迎候和张望,甚至一直站在风雪里,就怕丁点的疏忽和丝毫的大意,赵得贵就经过了,就走远了,就回去了。
我们全家一下都聚集在了门口,像极了撒了一把玉米麦子后疯狂奔跑簇拥的鸡。家里的狗都不叫,它认得他。羊睁大了眼睛,牛抬起了头,猪都不再哼哼,都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家养的牲口,向来和主人心意相通。
赵得贵拖家带口,来给他的爹拜年,那个“吊死鬼”也在其中。她在城里“上吊”不够尽兴,来农村感受新鲜,前面说过,赵爷院中有棵大榆树,村里的老榆树更多,还大多是歪脖子。我们满脸堆笑,迎上前去和“亲戚们”打招呼,除了赵得贵,其他人似乎都不认得我们。猛然出现的一群人,让他们吃了一惊,同样,这群人也吓我们一跳。其实,除了赵得贵和“吊死鬼”,我们也不认识其他人。
赵得贵和往年说的一样,看过他爹有时间就来我家。“有时间”“过一段时间”,“完了再说”,和官场上的“研究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把问题、困难做推手打太极最圆滑完美的托词。他轻描淡写又漫不经心的话,我们得当作大事来对待。至少,父亲相信他的话是真的。父亲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是同年同月差点同日生。赵得贵能从农民变成干部,从农村走向城市,当年的父亲可没少下功夫。赵得贵被推荐上学的选票,好多是父亲私下里通过自己的关系拉来的。父亲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上学的好材料,却喜欢给别人做嫁衣。结果是,别人现在城里在当官,自己一直在村里种地,而且还将一直种下去。
赵得贵进了他爹的院门,再没有出来,我趴在墙头,看赵爷院里的动静,一个原因是我着急着想去自己爷爷家,另一个原因是父亲怎么好意思趴在墙头张望。赵爷的院门前停靠着几辆小车。试着近前,胆怯地伸出手去,轻轻触摸那车。这个新鲜物,估计比生马驹还要厉害,生马驹别说摸它,靠近了都会用蹄子踢你。也有人不愿意围观这车,觉得让人当自己没有见识,觉得掉了身价,以围观为耻,以遥望围观为荣。你有轿车,我有马车,你在城里做官,我在村里种地,我又不会求你。其实,陈鹏举当年也是这样想的,还是这样做的。但不管怎样,那轿车总是新鲜和充满诱惑的,因此墙头和窗玻璃后面就多出些眼睛。
我们全家足足等到傍晚,等到天黑时分,终于算是把赵得贵给等来了。在等候期间,父亲还忍不住到赵爷的院里转了几次,只是在院里,没有进屋。从轿车里出来又进了屋的人,相当于古代坐轿子的人,和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农夫、一介布衣,应该没有什么能够说到一起。再说了,见了面,肯定得打招呼,点头,甚至握手,那蜻蜓点水般的轻轻一触,那微风拂面般的些微清凉,能伤却自尊无数。
赵得贵来我家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其中一个秃头矮胖子,感觉浑身就一个脑袋,头顶油光锃亮,周围毛发异常茂盛凶猛;还有一个大个子,满脸就一张大嘴,要吃尽天下,要抽筋扒皮敲骨吸髓,恐怕看相算命的也担心说话间被他一口吞下。总之,只有赵得贵看起来是个人。我们准备结结实实请个神仙,谁能想到来了一群“妖怪”,可这些“妖怪”却会说人话,不会吃人,还要吃人饭。这些“妖怪”,是赵得贵的大姐夫、二妹夫、小舅子、堂兄弟……
说是我们家里请客,但满桌子基本上没有我家的人。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活,父亲更是忙碌,不停地在桌子和厨房间来回穿梭,还时不时地使唤我。开吃的时候,更轮不到我,靠着窗户大红柜旁的榆木椅子,榆木椅子的旁边,那就是我的位置。那个地方,正好是电灯的开关所在,为了躺在炕上关灯方便,我们在开关上系了一根长长的棉线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把已经丢了钥匙再无法打开的铁锁。这绳子一直下垂,只有上炕睡觉前,才会拉到枕头旁边。恍惚间,半梦半醒时,随手一拉,免得起身下炕。好几次,就差一点,我就拉了那根绳子,让虾兵蟹将和妖魔鬼怪把饭菜吃到鼻子里,酒和茶灌到耳朵里。生火、倒茶,是我今晚的全部,上菜都轮不上我,是父亲。这么隆重的场合,这么重大的事情,父亲觉得非自己亲自出马。鱼虾全部带了醉意而来,但仍然能够吃得下去,喝个继续,这让我在成年之后想到那个晚上羡慕到绝望,我喝了酒,一口饭菜都吃不进去。后来随着我的知识渐涨,我知道了古书上说的一种吉瑞之兽——貔貅,也从来都是只吃不拉,而且还有招财进宝的意义。他们每个菜都要尝上几口,点评几声,划拳喝酒的时候,还要把满桌的饭菜用唾沫星子喷洒一遍,仿佛在阳台上浇花,又仿佛给庄稼打药。父亲在村里向来拳高量大,这个夜晚又能怎样,总归是架不住人多。他仗着酒勇,让我给赵得贵一行敬酒,我只会向国旗行少先队礼,因为我是少先队员,还是“红花少年”,而敬酒太过陌生;他又让我学着和每个人握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和别人握手,在此之前,我的手和别人的手接触,仅限于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若干年之后,我每次和别人、尤其是和陌生人握手的时候,亲近疏离,劲道尺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是不是都和这晚有关。
当我扭扭捏捏给秃头矮胖子敬酒的时候,他左推右挡,说他的肝脏不好,死活不喝酒,把我晾晒在桌子旁边,我进也不是,退也不行,我只好用眼睛向父亲求助,母亲一直在忙碌,她讨厌父亲喝酒,她对喝酒的规矩更是一窍不通。父亲的眼神比我更无奈更无助,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无能为力和无限悲哀。他涨红了脸,嘴唇没有血色,还泛起了干皮。我心里想,矬子,胖慫,你现在不能喝酒?那你的浑身酒气和满脸通红,嘴边的白色唾沫和眼角的灰黄眼屎都忘记擦去,而且一个比别人低几寸矮一尺的小个子,怎么会在人面前耀武扬威口出狂言。我心里又在想,你肯定喝酒,你现在不喝酒,那你前面喝的都是尿吗?
他不但不喝酒,还使唤我赶快给他的茶杯里加些白砂糖。那糖我们家从来不缺,我们家里种植甜菜多年,领不上甜菜款的时候,糖厂就会用白砂糖顶账。农民老实,有总比没有好,所以我家的白砂糖向来不用罐子,用的是口袋。
他非要让我在茶水里加糖,我正好可以活动,就驴下坡,我放下酒,进了厨房。我在茶杯里放了一把糖之后,没有从先前的门进去。厨房和请客的正屋是个套间,堂屋正对着院子还有一个门。就在穿厨房进院子到正屋的时候,我往杯子里吐了两口唾沫,又使劲咳出一口痰吐在里面,末了,又用把尿的手指搅和了一阵,反正矮胖子已经喝醉,他分不清也辨不明。他只是在这个时候,想要喝这样一杯茶,究竟喝的什么,他并不关心。
其实,我本来想撒泡尿在杯子里,可是我又想,这个杯子他只用一晚,我们却要用好多天好些年,就此作罢。
胖子喝了我端来的茶水,含糊不清又接连不断地说,好喝,真舒服,再来一杯!自那时开始,每次他来我家,他的茶水里一直都有我的清痰和唾沫,“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我给谁都没有说,包括我的父母。
忘记了是谁有意无意中说起,“吊死鬼”的身体不好。反正,在村里,只要是女人得病,或者身体不好,只要是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知道,乌鸡于女人而言,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强身。因为乌鸡向来很少,不显其珍贵由不得自己。一窝鸡,甚至一大群鸡,才会出现一两只乌鸡。识字那会儿,老喜欢看村里一个能治各类疑难杂症的中医写病历。只要患者是个女的,用不着望闻问切,那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赤白带下”。《本草纲目》讲道:“赤白带下。用乌骨鸡一只,治净,在鸡腹中装入白果、莲肉、江米各五钱,胡椒一钱,均研为末,煮熟,空心吃下。”赵得贵肯定给我父母说过乌鸡的事,因为此后一段时间,父母操心最多、跑腿最勤的事就是寻找乌鸡,都差点忘记了春种秋收。可有些事物就是这样,不需要的时候它老在你的眼皮底下晃悠,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就好像预先知道似的专门躲着你,让你找不到。我看到父母的可怜,恨不能让家里所有的鸡喝墨汁、吃墨汁、泡着墨汁。我的母亲也是个女人,她从没有吃过乌鸡,还生养了三个儿子。与到处找乌鸡吃的“吊死鬼”相比,我母亲能好好地活着,对她来说有点匪夷所思吧!
送他们走的时候,我们都无比诚恳和真心地邀请他们再来做客。说实话,是真心的,至少我是真心地希望他们再来,尤其是那个秃头矮胖子,再来把我的唾沫和痰咽下去。
那乌鸡最终还是找到了。只要用心,一切都有可能,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母亲把找到的乌鸡宰杀收拾得干干净净,托人带去了省城。
如此过了几年。
家里的灯泡瓦数向来很低,黑白电视也很少看,都是为了省电。有几户人家就因为省电,却多生了孩子,多了嘴吃饭,超生没地,还被罚款,因此日子过得很是紧张窘迫。
父母有一个习惯,随手关灯。现在的我也是,可当初的我不是这样。父母熄灯睡觉,我还要在灯下看书,正看得入迷,忘记了是父亲还是母亲,总要拽绳关灯,还不忘说一句“狗看星星,熬灯费油”。灯是熬了,油却没有费。屋里顿时一片漆黑,我再怎样睁大了眼睛,借那月光去看书上的字,却总是看不清。
可是有那么一天,父亲特意换了灯泡,把15瓦的灯泡破天荒地换成了100瓦。100瓦的灯泡我家每年只用一次,就是除夕的夜里。因为夜里要吃肉,说是“装仓”,把肚子像仓库一样装满。还要穿新衣服,这样在灯光下才会看得清楚,这样才能显得出崭新和亮丽。
父亲换了灯泡,又烧了热水。原来,他是要洗头擦澡。村里没有澡堂子,好像村里人也没有洗澡的习惯。村里人偶尔洗澡,是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麦收时节。麦子做的面粉好吃,可是麦秆上的粉末会钻进衣服里痒得要命。村里最大的涝坝干涸多年,再往南边去,零星有几个小涝坝,充其量是个水坑。是打了土块取土之后生出的坑。土块被用来砌墙修房,原先的地方因此就低矮下去。水不小心从地里流出来,四处漫溢,最后流进那些坑里。水只进不出,成了死水。时间久了,水会变得温热,上面生出一层浮萍。有人受不了痒和酷热,跳进去洗澡,暂时是消暑了,但走到人前,散发出浓浓的鱼腥味道。
父亲喜欢香皂的味道,如果要去县城,无论再忙再累,总会在家里洗头擦澡,换上干净衣服和崭新布鞋。农民进城,应该是种渴望和追求,父亲打扮得簇新,说明对进城的重视,好比古人祭祀,总得沐浴更衣。
父亲洗头,还要擦澡。香皂盒的下面正好有许多塑料小齿,他拿着香皂盒,使劲在头上刮过来磨过去,还要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似乎要把头上的陈年污垢彻底清除。他洗了胳膊,擦洗了前胸,后背那块有些麻烦,怎样够也够不着。我们总是看着眼前,常常忘了身后。他只好弯着腰,双手撑在热水盆里,撅着屁股,让母亲帮忙。母亲在毛巾上打了香皂,使劲给他搓背。盆里的水,颜色也并无多大改变,父亲是個爱干净的人,每天睡觉前都要把自己擦洗一遍,不然就躺不下去,也躺不倒。但这么郑重其事地擦澡,一年中也不多见。我以为父亲又要进城,问:“爸!你明天要上城吗?”父亲起不了身,背上的水正流过他的脸,睁不开眼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不上城,赵得贵来了,让过去吃饭。”背上的水和香皂沫子已经流进了他的嘴里。母亲的脸有些红,当着孩子的面给父亲擦背,我们也很少看见。
父亲洗完头,擦完澡,换了干净衣服。我发现他还穿了袜子,正是农忙时节,我们都赤脚穿鞋,除了方便凉快,更多的是怕一不小心袜子被庄稼刮破了。尤其是麦收季节,麦茬常把我们的脚腕刮破,脚腕儿常有血迹。到了暑假结束,我们穿着袜子上学。有了袜子庇护,那伤口会慢慢长好,结疤,发痒。上课的时候,忍不住伸手去脚腕儿上挠痒痒。抠挠伤疤,有回忆往事的甜蜜,有痛并快乐的愉悦。
我跟在父亲身后到了赵得贵家,其实现在只是赵爷一个人住,赵得贵的家在省城里。今天来的不是亲戚,是赵得贵的同事。赵得贵省城的同事,除了皮肤白,不像我们一般黑红之外,说话的语气口音也完全不相同。父亲在最末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有些胆怯,有些拘谨。没有我的位子,当时我还不算个人,至少他们没有当我是个人。我还是个孩子。
我小小年纪的,猜想父亲带我赴宴的目的。一个是让我来见见世面,一个是让我察言观色自己找活干,比如端茶倒水。
父亲在家里吃饭时有个习惯,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会吧唧嘴,尤其是饭菜特别合口的时候,他还会故意使劲地吧唧着嘴,发出非常响亮的声音,想证明他吃得很开心。我很烦听到这种声音,等这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不敢说破,更不敢冲撞,我就不吭声,就沉默,或者端了饭碗换个地方,可那声音实在太响亮,始终不离耳畔。父亲要是和邻居陈鹏举比吧唧嘴,真是小巫见了大巫。陈鹏举全家都是胖子,连牲口都比我家的肥壮。他家的饭菜,也做得很是粗糙。比如说把自家种的黄瓜凉拌了来吃,我家是切成丝或者片,好入味。他家是用菜刀切成段或者拍碎了就盛盘上桌,还忘不了随手将一段黄瓜屁股塞入嘴里。因为块头大,吃起来就比较费劲,陈鹏举就仰起头、歪着脖子、闭着眼睛使劲咀嚼,腮帮子鼓起好大一块。那一块疙瘩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有时候在嘴里倒腾不过来,嘴巴就向前突出来,再突出来。我在旁边看得着急,就想狠狠在他脸上打几拳,倒不是打他,只想帮他赶快把黄瓜打碎下肚,免得噎死他。
父亲长得瘦小,明明知道天生就是这类“品种”,偏偏羡慕起陈鹏举一家的肥壮。他曾有一段时间,也把菜故意做成大块,也学着陈鹏举的样子仰头、歪脖、闭眼,我实在看不顺眼,就躲远,不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眼不见,心不烦。
在赵得贵家的桌上,其实我离父亲很近,忘记了是在身后还是身边,父亲吃饭吃得很小心,也很谨慎,不但没有一丁点儿的声音,还像省城来的人一般斯文。饭菜入口,紧闭了嘴巴细而慢地咀嚼,舒缓有序的下咽。他也可能是想告诉别人,自己早已吃过了饭,并不是完全为了这顿饭而来。从那天起,我才知道,父亲吃饭,也有不吧唧嘴的时候。他也不多说话,倒是城里人看他不自在,不停地给他夹菜、劝酒。我知道,父亲不但没有吃好,而且连吃饱都谈不上,因为那厌烦至极的吧唧声,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那时候我想,父亲的吧唧声于我而言,可能是天下最美妙的声音。可恨可悲可怜的是,它一直没有出现,枉费了我的留心留意和刻意。
等有声音出现并逐渐响亮的时候,大约是在喝完第四瓶白酒的时候,桌子上的酒大多进了父亲的肚子,因为今天只有他和我是外人。赵得贵虽然在村里长大,但村里人都认为他是省城的人,至少,在这个酒桌上,他和其他人是一伙,至少,他们一起来。父亲的声音逐渐大起来,响起来,不停地和赵得貴回忆儿时往事,他们还能有其他共同的语言吗?除了回忆之外。父亲开始仗着酒劲,搂着城里人的脖子,拉着城里人的手,不让他们走,要把自家的羊宰倒,招待他们。羊,我们家有的是,常年保持在30只左右,只有贵客上门,才宰羊置酒。父亲的亲热和热情,总让城里人有些不习惯。许多年以后,我在书上读到:在同一地方工作的同事,日常交往中有一个雷区——身体不能亲密接触,比如搂肩搭背。但这是西北边陲的静谧村庄,没有人会管你,没有更多的人注视你,是非闲话更无从谈起。况且,我的父亲是洗头擦澡换了新衣来赴宴的,不会在城里人的衣服上留下乡土的味道和痕迹。
父亲的酒量不错,甚至可以说酒量很大,而且划拳划得特别好。每逢村里婚丧嫁娶,他敢一个人站在擂台桌子前打擂台,好长时间都不下桌子。村里的习俗,红事白事都要喝酒,红事喝酒更添喜庆热闹;白事喝酒,会把悲伤和晦暗一扫而光。尤其是高龄老人过世,村里人会当作一件喜事,酒就更不会缺。院子门口支一张木桌,摆上酒瓶和酒杯,父亲在桌子正中一站,手一挥,擂台赛正式开始。打擂台的人轮流上阵,父亲并不怯阵。喝酒打擂,父亲在村里算得上是个老江湖。说实话,当擂主有很大难度。划拳的时间越长,出拳就有规律可循。有聪明狡猾的打擂者,并不贸然上阵,而是旁边仔细观察,认真揣摩,快速又冷静地思考,思考如何抓住父亲出拳的规律,并牢牢记在心里。父亲划拳的本事是真高,高就高在不管怎样的对手上台打擂,他都能应付自如。如果有人连赢他三拳,他马上改变拳法,拳风也随之变幻,而挑战者拘于之前的深思熟虑,来不及变化,被杀得大败。那时候,我正在看《说岳通俗演义》,觉得父亲就像是书中的小将,手握双枪或手提双锤,杀得敌兵丢盔弃甲、哭爹喊娘、屁滚尿流。
擂台酒结束,恰是饭菜上桌。酒要连续不断地喝,才能尽兴。父亲斗志正酣,他又开始在桌子上“打通关”,就是必须和桌子上的每一个人划拳,且划赢后才会轮到下一个人开始接替。“打通关”有“红关”和“黑关”之分,“红关”就是赢了桌上所有的人,按规矩要接着再划一轮,按顺时针方向再打一关;“黑关”就是输给了桌上所有的人,一个人都没有赢,按规矩逆时针方向再划一轮。父亲总是红多黑少,赢多输少。父亲拳高量大,还能说会道,待人真诚大方讲义气,这种人在村里大受欢迎,尤其是办喜事的时候必不可少,常被主人叫去帮忙。帮什么忙,切菜洗碗蒸馍馍吗?不是,这些活女人们早就做得妥当圆满,父亲的主要任务是招呼客人、陪人吃饭喝酒。男方这边的人是“东客”,女方那边来的人被称作“西客”。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东客西客”的来历和渊源,反正我喜欢当“西客”,喜欢村里的女人嫁出去,“西客”只需坐着吃喝,自有人端茶倒水,还有“西客”桌子上总不会有“东客”桌子上没有的糖果和点心。“东客”就很辛苦,要伺候人。可是这“东客”和“西客”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有女人嫁出去,就会有女人娶进来。我更喜欢当“西客”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村里有更多的女人嫁到城里去,最好能嫁到省城,这样村里的好多女子就不会再像自己的父辈一样耕作辛苦,而且我也可以借机坐城里来娶亲的小汽车。
“东客”辛苦,所以办正事之前要“请东”,吃好喝好了好干活;正事之后要“谢东”,要犒劳这些干活的人,以解劳顿之苦。父亲是事前事后必请之人。
这顿饭是在赵爷家吃,赵爷很是重视,一直在忙前跑后,还不停地给父亲劝酒,说这酒是赵得贵带来孝敬他的,不但价格高而且味道好,他自己都舍不得喝。所有人都喝多的时候,他显得更加急促和忙乱,还有些不自然。我的眼光跟着他,身体也跟着他,他甩不动也摆不脱。他居然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把酒给换了,他把当地产的酒装在了据说是赵得贵孝敬他的好酒的空瓶子里。我没有喝酒,更不可能醉,我看得很清楚,我没有吭声,我记在了心里。
从那天晚上起,我认定赵得贵一家,不是实诚人。一直到现在,不管别人怎样说,我都不会改变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和看法。
责任编辑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