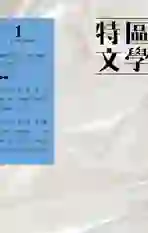夜车
2021-09-10何荣
何荣,女,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散文、小说见于各文学期刊,有作品入选“岩层”书系、《小说月报》创刊35周年的“小说新声特集”。
候车厅极大,车厢极小。
要上车了,随便买点什么吧。握一桶杯面,风衣翻出深色内里,行李箱轱辘咕吱咕吱响,她更正宗了,更像个风雪夜归人了。
列车停泊在夜的平面,是一小节被遗忘的会议室。六人座,她第一个到。车窗框出一个方形,细看,辨出一张脸。笑一下,那边也笑,好像隔了几秒。起身去灌热水,回来时对面多了一位,余光里只觉得皮肤很白。
三号是个中年男人,有一点油腻,感觉像刚从酒局上下来,正在奔赴下一场。四号跟五号四腿相对,为了方便伸脚,彼此错开。列车启动了,从车窗倒影看去,二号白皙的脸庞变成液态石油上漂浮的月亮。
车厢的震颤让所有人呈现出一种频率一致的醺醺然。列车员的制服与一丝不苟的妆容出现在过道正中,两边的乘客似乎更加坍陷。六号招手,买了一包泡椒凤爪。
杯面差不多了,就着泡椒的气味,她开始吸溜。六人座的小型自助餐厅,每个人都在咀嚼,唯有四号不动。过道另一侧,与他们并排的四个人在打牌。
二号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一种非常平滑的陌生。她发现二号的双眼皮非常漂亮,围巾的苔绿色让神态有点儿冷。五号的翻绒大头鞋上溅满泥点,和四号的阿迪达斯贝壳头交叉摆放。六号基本被挡住了,一只穿着粉色呢大衣的胳膊,从四号肩膀附近伸出。
到站之前,这个格局应该不会变了。每次坐车,都会像摇骰子一样,跟各色人凑合到一起。凭借工作、学历隔开的一些人,现在统统回来了,比如说五号。也许她应该看看窗外。
窗外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单调。飞驰而过的城市。厂房灯火通明。狗在走,脊椎骨栩栩游动。暗影里的白房子。路灯照不到的死角,积水熠熠生辉。桥身全程亮化。间或一片纯粹的黑,边沿整齐,是某块农作物。湖面极远,像朝此处涌来。出租车提示灯。独行的男人,拎一瓶二锅头。车龙。LED显示屏矗立在荒野深处。消了音的交通事故。民房的轮廓与四号的后背交叠。车身的运动迅速地取消了旧景,甩出更新的,反而是车内的陌生人们持续着陌生,值得信赖。
泡椒味已经完全闻不出来了。
她从前座的椅背抽下一本杂志,从卷边与污渍上,她感受了沉甸甸的、多人份的无聊。像之前所有的乘客那样,她把这个默认为旅途的一个标配,被迫开始阅读。
马上,她就发觉自己的注意力其实在这光滑的铜版纸上,洁白,没有印刷错误,经得起反复挑剔,一群人的接力挑剔。这是一些旅游攻略、葡萄酒广告以及自驾游路线。有人编出这个,想提醒乘客,在列车之外还有别的,就在不远处,触手可及。事后,没有人会购买广告里的葡萄酒,在货架上遇到,甚至会避开。怎么能让旅途中的趁乱偷袭得逞呢?她将高清分辨率的照片贴近眼睛,直到能辨出细密的网状小点,感到一种拆解的快乐。
四号似乎已经变成了时间本身。他的存在,箍住了六号,让她一直保持着比较端庄的姿态。
她可以想象四号购买脚上这双鞋子的过程。不探头探脑,径直入店,气氛庄重,也许肩膀上还夹着电话。他穿过打折区,不看标价签,直接拿下被神选中的一双,试穿,买单。他应该是商家最喜欢的上帝类型,预算宽松,入手迅速,限量版的主要消费对象。设计师的理念在他们身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对接,而不是湮没于满五百免一百的折扣中。他身上所有单品的购买过程,一定全部伴随着这种铁蓝色的果断。将来有一天,他会像他父亲那样,享受躬身半跪的试鞋服务,女售货员向他展示脑后一丝不苟的发髻,黑色丝袜被两个脚后跟处顶得发白。
她突然想,她是四号想要避开的那一类人吗?远看像同类,近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不管怎样,六人里排次序,她不在食物链底端。
四号高于她的又一铁证,是他面对五号的镇定。空间逼仄,四腿交插,痦子近在咫尺,他丝毫不为所苦。他右手边的六号,每件衣服都自带一段滚动播放的DV:霉味扑鼻的仓库,黑色塑料袋,江浙沪包邮,快递员小哥在公司前台大喊“兰馨月儿”。瞄一眼老板,镜头推成特写,偷偷对光确认有无明显瑕疵。跟拍,女厕所,反锁出一个带马桶的试衣间。吊牌不敢摘,巧妙地藏在后领处。在闷臭里吸气,飞快地拉上拉链,在缩水、开线及起球之前,洗手台镜子出现一位五秒钟公主。
她视线下滑,杂志上出现这么一段:
如今,商品化入侵人心。服装不再仅仅是用来遮身蔽体,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角力。再羞于承认这种角力的人,也会为某次会议上洗得发白的运动裤而不安。
她锐利地看了六号一眼,还有五号,抑制住大声朗诵的冲动。车厢过于明亮整洁。五号左脸的黑痦子成为一件被多角度打光的文物,变作这个车厢的核心。她控制不住自己,隔几分钟就要瞄一下,以确定此物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视线兜远一点,与他们并排的那一桌,牌局已经散了。被熨烫至发亮的裤缝线,黑袜子,黑皮鞋,皮鞋上一道高光。得体跟随性不矛盾呀,起码她懂得欣赏这一点。二号一个慌张的动作引起了五号的关注,三号的笑容像是横着切开了脸。
列车在黑夜里运送一截光,运送着一些被钉死在座位上的人。一位黑夹克男从卫生间出来,极其艰难地走过过道。车身震颤,他走在飓风里,一幀一帧地支撑身体,留下了无数个截面。一只巨型蜈蚣走过,一路褪下两排脚。他经过他们,奔向属于自己的、已经凝固的六人座。那人形搭建的巢穴,已经持续十分钟,或者半小时的家。你已经不再自由,随时会被邻座的乘客顺利认出。
此时,二号起身,打算去洗手间。众人进入备战状态。五号用力贴紧座位靠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四号站起来,这个动作促使他旁边的六号也站了起来。三号双手抱胸,任女性在他双腿的M形里进出,这复杂的肉体迷宫。想着等一下还要再来一次,工程浩大,四号直接站在过道里等。
机会。
她跟着起身,组成一个小分队。二号打头,迷宫似乎顺利了一点。依然有个败笔,臀部在五号的膝盖上蹭了一下,还好,时间极短,短到那恼人的弹性,最终滑向了轻松。卫生间亮起了小红灯,她得等。视角换了,她站在会议室讲台,台下是黑压压的,临时小团体。四号,双手插袋的老朋友。粉色小点是六号的手机防尘塞。两个被座椅挡住的半圆形头部,发型翘一点的,五号。他们是她不太亲的亲友团。
痦子还在。
车身呈现一种有规律的晃动,这晃动时刻都在,就连厕所这样的密室里也难幸免。她翻检保洁记录本,辨认着龙飞凤舞的字体。这一小块地方,于她来说,是列车上仅有的、未开发的区域。其它地方,她未免太熟了,连某位男列车员中式英语的发音方式都了然于心。金属把手清洁冰凉,向左扳,世界暂停。镜中,她被迫开始看自己。光腿呈现不真实的肉色,衣物堆叠至膝下,脸上带着被抽打过的神情,胸前两团恼人的软。
五分钟后,她归队了。这次她是正对着男人们进来的,五号学得很快,他不再避让,公然叉着腿。在她和二号缺席的空档里,三号和五号似乎结成了同盟。也许,他们觉得,是她和二号先结盟的?四号耐心地等她和二号坐定。六号像把折叠伞,吧嗒一收,脚背勾着腿肚子。
嗨,小兄弟!这几个姑娘,你想带走哪个呀?
终于,终于开始了。她的直觉又灵了。三号的学生时代,肯定也这样调戏过班上的某个大傻子。他眼光很毒,能在素不相识的旅伴中,精准地选中调戏对象。五号的笑是羞赧的肉红色,一双泥色大手互相搓洗。这个配合太烂熟,以致于他的笑没有卡准时间,稍微提前了。
四号浑然不觉,他是去性别的。银白耳机线源源不断地给他输液,可能是重金属,也可能是古典乐,最不济,也是台湾小清新吧。六号的透肉黑丝、劣质香水、晕开的眼线,对四号不起任何作用。这童贞之神般的面孔,屹立在六人座。
指针在洁净的密闭空间内,安全地瞄准了11点。夜行动物开始兴奋,窗外黑漆漆的世界里,蛰伏着无数被隔绝的、一闪而过的、遥远的骚动。防水布帐篷,收拢了60瓦灯泡的黄光。啜饮时喉结滑动,大铁锅爆炒时腾起烟雾,霓虹灯笔划缺失。如果她不去厕所,一直蹲守,大家继续静得像死,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人总能找出一些节点,来暴露本性。臀部那一下是导火索?她向他们展示了活体山峦,所以她也有罪?那么六号呢?
她在背包侧袋摸索,平摊一本小说,举至眼前。
反复扫描几行汉字,读不出任何数据。视线上移,停留在书页的空白处。虚掉的背景里,是可以放心观察的二号。发色偏浅,眼珠颜色淡,眼角描着上扬的细黑眼线。二号跟四号,像被同批次出产的,肤色在单元楼里捂出死人白。两人应该同时出现在某个时装杂志内页,穿着情侣款,同样的冷淡,同样的表情俭省,带着不明所以的高级感。身后是一片荒漠,抠图十分仔细,头发缝里都抠干净了。而他们身边的五号与六号,这两方手泽肥腻的镇纸,压住宣纸的新雪气味。
三号避开近在咫尺的实体对象,谈论他的心得,尺寸,以及手感。一些虚拟的女体进入了他们的谈论,可能是三号凭空捏出来,也可能是几个合成一个的精华,又或者是,道听途说的嫁接物种。相比之下,现实的人却消失了。她想知道,这些意淫对象里,她、二号,尤其是六号,各被采用了多少?显然,这语境让五号异常踏实。被吞票的紧张,女安检员的冷眼,B4检票口与A2的不同,四下埋伏的中英文双语警示牌,头顶岌岌可危的行李箱,快要压不住的烟瘾,这一系列的不安,被来自厂房宿舍的下流话安抚了,这份亲切的脏。黑色痦子被面部表情带动,像一只蠕动的黑色甲虫。他们有着奇怪的默契,嘴上功夫很足,却没有一个人看她、六号或者二号,仿佛她们是缺席的,任何一位女士只要开口反驳,就会变成主动对号入座。咣,咣咣,列车反复撞击铁轨,以往所有被调戏的女性鬼影幢幢,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予三号有力的回击,他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些被他口头玩弄过的纵容者们,现在把难题抛给了她。
设想,不具备威胁性的三号。十七岁,也可能是十八,念高中,穿着运动服款校服,宝蓝化纤裤子,侧面有两道白杠。还没有成为老手,恋着某位校花,像怀旧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要给他安插一个水性杨花的母亲吗?不然这轻浮态度的养成,也未免过于迅速。或者,一个劈腿的老婆?失婚,借酒浇愁,烟头明灭,窗前剪影,天色向晚,火烧云燎了半边天,挺动人。一定有某个时刻,三号收起猥琐,呈现出宗教式的悲剧美。这个时刻是他精神保险箱的密码,要威逼利诱才能获得。没有伤痛垫底,很难被原谅。原生家庭不在车内,可以承担起恶之源,像一个精神厕所,隔得远,没有异味。再小一点,十二岁,这是一个临界的年龄。十二岁的、临界的三号,在夜里醒来,发育的身体肿胀着,听见独居母亲房间内的异响。
她听过那异响,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十二岁。她看上去是完好的,其实已经遍布冰裂纹。真想给三号来一榔头,不然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可以顺利过女性这一关了。没有一把枪抵着,谁会痛哭流涕地承认痛苦呢?邻座产生了两位男性听众,暂时还没有加入,不过笑点踩得很准,其中一个烟鬼拿烟敲着手背。一出不能快进的好戏,现导现演,三号兴致更足了。
她无处可去。小说大概一指厚,非常涩,很密,撬不动。耳机没带。二号左后方出现一盏小红灯,极远,故意停了一会儿,咻地消失了。他们是一脸倦容的归人,驶过另一些人的梦,怎么可以内讧呢?
三号和五号已经牢不可分,只能考虑换掉四号。一个不那么冷面的四号,介于三号和五号之间,不会捉弄人,也不被人捉弄。他真的可以这么中立?那就等于多了一个看客,而且面对面,反馈及时。更有可能,他会加入这个雄性阵营,表演一种古板的正派,朝另一个方向拉扯五号,制造更高級的喜剧效果。那样的话,她连掩护都没有了。
那么,还是六号的问题,罪魁祸首,蛋上的一条缝。总有一些同类,用自身作为诱饵,击破她衔来无数细节、苦心营造的壁垒。睫毛蕾丝短裙,低胸打底衫,斑驳的玫红指甲油,这难道不是在招徕什么吗?更可怕的是,六号没有姓名、年龄、职业,只剩下性别,三号们跟着当原始人。
当然是胖一点的好,摸起来舒服!
又有人加入了,来自过道对面,笑得很内行。电光火石之间,她错过了什么。三号开始直视六号,准确说,是瞄。瞄一下,错开,再瞄。这种做派的女人不算难搞,他成功过。清点记录,有一两个甚至与她非常相似。
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六号骑跨在三号上方,不断上下起伏。宾馆的房间变作透明长方体,围坐着所有看客,甚至包括了六号与三号本人。目前,所有人,都在朝着这个指向,紧锣密鼓地努力着。也许,在二号眼中,她也不过是另一档次的二号,或者,高阶版的六号。总有一天,她会骑跨高阶版的三号。
黑色痦子是没有年龄的,十二岁也救不了。
病毒在蔓延。前座有男人探过不知情的脸。再探几回,就会知道,这里有一场真人游戏。零成本,霎时间,花样百出。
飞速前进的密室尽头,出现一位乘务员。令人期待的即兴中断,破坏了节奏。
贯穿车厢的行走,大约1分钟。制服是分量感极恰当的紫。丝巾在颈部结成一颗疣。V领是一只下箭头,指向两座得体的突起。饱满的大腿在短裙上拱出活的、瞬息万变的褶皱,张紧的丝袜绷出冷金属色。短裙下伸出两根白皙修长,浅口漆皮平跟鞋是指尖涂的黑色指甲油。手指前后交替款款行来。车厢中部有一片倒伏,无非是几个男人搭上了话,小范围咸湿,眼神里闻得见醉意,火烫的目光焊出S形身板。她走近了,越来越近,近到可以为所欲为,不等你出手,已悄然错开,永生不得相见。她走入钢铁巨鲸深处,身体的轴心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曳动,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范本意味。
休止符之后,节奏加强。六号重新登台,被追灯盯住不放。要的就是这种忸怩,就是这种多人参与的、集体开发的过程。台下烟雾腾腾,几万只男人的手齐齐挥动,庞大鱼群般的默契。
八歲的六号,和表姐在晒衣服的大箱子之间嬉戏。她们用毛巾卷成条,包娃娃,一根毛线勒出脖子,另一根勒出腰,基本成型。表姐用废纸捏两只小团,塞在娃娃平坦的胸部。她在旁边看着,脸上莫名一红,表姐解释,这样穿衣服比较好看。无人时,她变成了娃娃。两方手帕垫在胸部,制造夕阳下的影子女郎。侧面曲线非常曼妙,她打量许久,非常陶醉。后来,后来当然是被母亲发现,拉过来,搜身,扯出手帕,扇耳光,骂贱货。两个字一出口,女儿不见了,多出了一个陌生的小婊子,眼神不干不净,像偷窥性事被抓包的小丫鬟,视网膜还滞留着残像。才八岁,就已经不纯洁了,以后不知道要拿她怎么办了,母亲一边用鸡毛掸子抽,一边叉着腰想。半大不小的年纪,小孩子是当不下去了,离大人还早,这么想着,又在她身上来了一下。
小腿记起了久远的皮肉之苦,那鞭鞭解痒的痉挛。它们被妥帖地藏在厚斜纹布材质的萝卜裤下,再也不敢臭不要脸了。
她趁乱摸清了过道另一侧的格局。按照这边的分法,那边有三个三号、一个四号。男人们看上去互相认识。没有五号和六号,三号就是正常的三号。精英模样,外表拾掇到你刚好能意识到这种拾掇。黑皮衣肩部没有头屑,贴近了能嗅见好闻的新皮子味儿。
狼是帅气的,羊很脏。不洁的白毛,失真的眼珠,案板上被翻动的内脏,肉汤表面的浮沫,几日缭绕不去的膻气。这一切,都如同黑色痦子,腌臜到必须被摧毁,被吃干抹净。在肉身与夜色里那道黑闪电合并之前,他都是该杀的。十年后的五号,二十年后,一只老羊,依然不依不饶地被老狼啃。一时羊,一世羊。她叹口长气。
这个袜子,穿了冷不冷?
三号捏起一小块透明尼龙织物,六号哎呀一声,伸手去打,晚了,是哑的。指缝里一个小黑三角帐篷,刚支起,就平了。对面三个三号笑声震天,五号笑得很慢,他小心地观察六号,随时准备收回这笑。
怎么能触碰展品呢?
她看向窗外。漂亮的宝蓝灯链,嵌进夜的黑丝绒,粒粒晶亮,完好无损,勾出环城立交的弧线。寒夜之景冰镇着她的眼珠。
曾经,她有一个改签的机会,但她放弃了。她替换掉自己,假装坐在另一班车上。那趟列车比较正派,当时夕阳还在。庞大的金属机械物在漫天宝光里缓缓驶来,车窗上有块方方正正的红。炊烟根根,田野的绿浮起晚雾的蓝。路灯新亮,随时会被天光湮灭,让人想用手拢住。所有人浸在怀旧的蜜黄里,结局一定不一样。
六号终于觉出裸露的危险,用手提包遮住大腿。包不够大,只能分批次遮,隔一阵就换另一个部分。手提包是人造革材质,软得像另一双假手。六号陷入充满褶皱的不安。三号似笑非笑,把食指和拇指举高,先搓,再嗅,接着杵到五号鼻下,五号慌忙避开了。
老派的调情,来自老港剧里的风流少侠。录像厅深处的少年,暗暗排练着遥不可及的触觉。几十年后,这个场面终于得以正式还原。香滑粉腻的活体,浅表性接触,肉体冰山,半公开的密室,你推我挡,不会将手粗暴伸入屏幕的观众。他框起现在的自己,放入年代久远的黑白荧幕。
他真的对六号有兴趣吗?如果他们都退场,他还会碰她吗?
她悄悄捻动手指。
再吃!再吃下去卖都没人要了!
十二岁的六号,前几天还被骂,小小年纪就来月经!现在已经可以“卖”了。“卖”字摁上脑门,嵌入皮肉,形成一枚直达裆下的按钮。骂一次,就启动一回。鹬鸟的尖喙下,粉嫩的、光洁无毛的蚌肉猛烈收缩。
卖。粉红灯光,大额纸币,扫黄报道里一排乌压压的头,闪光灯在漆黑的头顶上留下一圈高光。六号消化掉这个字,继续吃螺蛳。舌头探进,在海腥气里拆开一枚小圆盖,嘬出一粒肉来。黏答答,乳头大小,用门齿切断尾部。为了更加无耻一点,她吧唧嘴,抖腿,举高右手,张嘴去接。六号突然成了个老手,不抬头,不用目光挑衅,每个动作都在恰当好处地宣战,将母亲的情绪控制在爆破点以内。她逐渐点燃边上一对杏眼,使其亮如射灯。
这个年纪最丑,成人身形娃娃脸,贪吃、爆痘、爱偷窥,太肥或太瘦。性事结束,母亲提起隔壁小房间里那具嗷嗷待哺的身体,有“一双不干净的眼睛”。欲望的袋子瘪下去,困意上浮。父亲的脑海里,固执地残存着某个冬日午后,树影斑驳,人字呢黑大衣裹着沉甸甸的小女孩。三岁,也许是四岁,擎一支冰糖葫芦,颗颗红亮。爸爸可以帮你挡一挡。于是爸爸谈起呼啸而过的消防车、农学院门口的煎饼摊、黄嘴小雀,以及,美国一个老头把遗产留给狗。生理卫生课上,父母是少男少女们想起来的第一对交媾的男女。可是那又怎样呢?就近选择嘛。母亲没有跟父亲提的还有,她观察过她,观察过她的胸、胯、大腿,她对异性的态度,她对她的偷窥,以及,她们的攀比。她依旧天真烂漫,穿大码童装,水晶塑料凉鞋,裤子膝盖处缝着防止磨破的长颈鹿布贴。但她已经正儿八经地开始排卵,每月一次。
三号此时也许刚刚结束一场苦恋,在香烟烟雾的形状里辨认前女友的身体线条。女友离开小镇,嫁给了南方的小老板,走的时候粉泪莹然。她带走了他世界里所有的适龄女性,他统统看不见她们,无论是纺织厂的小张,还是供销社的小李。更简短点,那个双眼皮的,那个罗圈腿的。就算他在大街上遇见六号,顶多轻描淡写地看一眼,不上档次的胸,不上档次的腿。六号会为这来自年龄差的轻视发怒吗?用表姐抽屉里的断头唇膏宣战,或者,踩着对同龄男孩子的鄙视,让自己显成熟一点;再或者,把母亲衣柜的服装挨件上身,在穿衣镜里上演换头大戏。
交手的时刻极其隐秘漫长,春夜的某个时刻,乘客的包围下,优劣重新洗牌。她的左右膝盖各有一個小凹坑,显得脆弱,呼唤着强有力的破坏。两条交配的蛇,裹在渔网袜里,互相纠缠。猎物引诱着猎手。
母亲不在这趟列车上。
再继续下去,她会完完全全地替换六号。她会使这件事变成六号的逆袭,三号其实是被设计的那一方。他上钩越深,她赢得越彻底。
夜灯密集,车内明亮,乘客身处双重璀璨之中,景色被横着刷出细丝。这人人端坐的夜总会。真想打碎这整洁,把他们连根铲起,放进某个小镇的台球室,或者国道旁边的小饭店,穿更放松的衣服,吃更放松的食物。摸两把也没关系,女人的尖叫更像是欢呼。这再也回不去的,淤泥中的纯情。
烟头挤爆了易拉罐,花生壳被踢成一小堆,瓜子皮撒一身,隔一阵,就拍几把。空酒瓶子总会倒下那么一两只,地下满当当的空烟盒、竹签、面巾纸、纸杯、啤酒瓶盖,大家愉快地跳着走。搂抱的男女身后,三号的轮廓被辨认出来。他在极远处的路灯下,读一本小说。那份认真与夜车上的调情无异,出格者永远只爱出格。
他的出现比预想中的晚。
迟到的英雄,有点馊气。他要求六号跟他换个位置,在本应该给出解释的停顿里,他又把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座位就在他们背后一排,他的出手绝非偶然。六号敏锐地意识到,受害人跟婊子,她必须选一个。
六号带着她庞大的童年走了,新人带着一种“这就对了”的神情昂然入驻。
她避开那灼灼的探照,他们这群懦弱的娘家人,在外来者的视网膜上成像,是罪犯存档拍照。五号缩得极小,四号更淡了,二号近乎透明。新人将压轴留给了三号,他前倾上身,扬起下巴,慢悠悠地整理衣服下摆。很久没有审判了,他要慢慢享用。
她保持着表面上的低眉顺眼,就像她刚才保持着表面上的视而不见。
他跟三号是截然相反的吗?不。很可能,他是他的另一个分支。独居母亲卧室的异响让他攥紧了拳头,他在她面前摔摔打打,他在她梳妆打扮的时候盯紧她,他释放出血脉中属于父亲那一方的鄙夷与冷淡。五岁,他用鞋底碾死一对交尾的飞蛾。二十五岁,他一边冲撞一边气喘吁吁地命令身下人:说好舒服!快说!
三号主动终止了与五号的友谊,望向过道对面的邻座,邻座们郑重地抱怨房价的不合理,他们没有给他留下哪怕一条缝。没有票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参与过,散场后的观众最无情。三号开始看窗外,他的悠闲过于认真,以至于他发现了一个规律:近处的景物跑得快,远处的跑得慢。最远处,近乎不动,好像是固定的轴心。高楼上有奇怪的尖顶,亮如毒蕈。车厢是临时收容所,旅客从甲逃到乙,再从乙逃到甲。车厢里年轻人太少,婴儿缺失,像某一个灰扑扑的人生阶段。
自动门开合一致的时候,能够连接看穿好几节车厢。每个人都在心里或多或少地渴望清场,渴望拿掉这自己也有份的芜杂,观赏整齐划一的机械美。车门上方滚动播放着当前的时速,行李的杂乱打破了“梦之蓝”广告牌的有序。所有人正确地坐在红蓝混色的座椅里,受困于一种崭新的熟悉。
(责任编辑:费新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