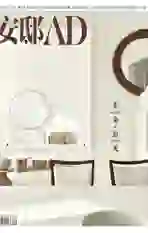如胶似漆
2021-09-10朱海
朱海

在干固的苎麻上刮由生漆伴瓦灰和矿物铁红粉的髹涂过程,是漆艺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步骤,髹涂、叠加、覆盖、研磨、显现,循环往复,并经由天然大漆的氧化特质,形成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宏观与微观直接的对话。
艺术家翁纪军的漆艺工作室位于上海近郊。刚一进门,我们就看到院子一角栽种了几棵小漆树,它们被寄予了期许,希望八、九年后可能割漆。两层的建筑被划分为创作、制作、展示、学习多个空间。由于需要制作干燥大型的画幅和立体作品,工作室的大漆荫房宽阔而专业。一打开门,混合着大漆气息以及高达75%湿度的空气扑面而来……

翁纪军,1981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1994年于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现任上海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员会主任,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工艺美术大师,现生活于上海。
对于翁纪军来说,天然大漆这种中国传统材料是他一见钟情且长情至今的。他曾经历插队落户、恢复高考、杂志美编、中央美院进修、回沪工作等,但他身上仍然散发着通透的少年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天然大漆和相关工艺,翁纪军告诉我们,那是在大学时期的材料课上进修。这种在7000年前就在中国传统器物制作中使用的材料,对他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吸引:从漆树上刚割下的大漆液体像乳汁一样润白,经过自然氧化,它便转变为熟红砖色。在髹漆、打磨后,这种材料又会展现出内敛质感中不可预期的升华。“大漆不只是一种材料,它有生命,会动、会变,有脾气。我不只是簡单地把它作为材料进行创作,大漆更像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在互相理解和不断对话碰撞中达成一致,最终使它变成一件能表达出我思、我想的作品。”
艺术家翁纪军和大漆打交道已有四十余载。在他的漆艺工作室里摆放着即将展出的“集聚”系列作品,它们仿佛浩瀚的宇宙星辰,又似微观的细胞内核。他用这种见微知著的方式连接起不同维度的世界,投射出人与大漆、人与世界的联系。
虽然天然大漆的工艺历史悠久,但有关于大漆的艺术作品创作尚不太为大众所了解。翁纪军认为这一创作和认知上的断层是由于传统漆艺作品或太侧重于绘画,或太侧重于工艺,“脱离时代审美,脱离现实生活”,很难将漆这种媒介的特质展现出来。他反复向我们提及“当下”这个词,这也很明晰地展现在他本人“出世入世,坦然自若”的真实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早在江西插队落户时,骑着自行车带着当时还是女友的妻子去博物馆看八大山人的作品;还是在90年代时,只身一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前往巴黎看展;还是平日鲜少管教,到了寒暑假便带着女儿旅行写生;甚至在长达数十年的上海工艺美院工作时,每天下班后在深夜进行个人创作……日常生活里会遇到的困难和获得的趣味同样在翁纪军的生活中反复出现。也许,正是这真实的生活,成为他和大漆直接对话的源头,进而升华为艺术。
纵观翁纪军的作品系列,可以清晰地了解他关于“当下”的思考线索。他早期的“头”系列作品中,用具象的头状胎形与计算机芯片的嵌入等异质材料碰撞来表达对社会变化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思考。近期的“集聚”系列作品则发展为更为抽象的处理方式。他以大漆材质的质感变化和对比来展现宇宙和细胞之间的关系。这是物理层面的探索,更是人文及哲学上的思考。中国传统髹漆技法中的“犀皮”和“金虫”工艺被翁纪军以一种现代抽象的方式展现。画作中似犀皮非犀皮的圆点布满整个画面,并通过数遍髹涂、打磨后,呈现出一种宏观如浩瀚宇宙星辰,微观如细胞内核般的视觉效果。更值得一提的是,除丰富的质感呈现以外,贯穿于翁纪军作品中的还有各种以天然矿石粉为原料创作出的、令人心情舒畅的色彩,它们让天然大漆以现代的模样展现在观众面前,没有半丝陈旧过时感。

除了以传统苎麻材料作为基底以外,亚克力等新型材料的尝试,在翁纪军的作品中也可以经常见到。墙挂作品的原材料为透明亚克力、干漆和金箔。

地上是翁纪军自2000年开始创作的“头”系列,以抽象的人性头部混合各种充满时代特征的细节甚至电子芯片,探讨时代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翁纪军的作品中,关于大漆的表达方式丰富无限制,从具象至抽象至质感细节,展现了大漆这种材料的无穷可能性

《. 矗2018》是由三根脱胎立柱组成的装置,展现了大漆创作的各个阶段:髹涂、裱布、刮灰、打磨、贴箔、抛光等,以及各个阶段特有的肌理和质感。
年轻时翁纪军便十分喜爱达利、罗斯科、塞尚等西方当代艺术家。当聊及自己作品的精神内核时,“中国传统”被清晰且肯定地提了出来。“大漆这种媒介,无论物理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是非常传统的,它的内核也完全与中国文化哲学相吻合。”的确,在中国古代,无论在器物上呈现软还是硬的质感,都可以用大漆材料进行包容。而在漆艺作品中,通过髹涂、打磨又可以呈现出如同“犹抱琵琶半遮面”般极具中国审美意趣的效果。
翁纪军的作品也以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打破了天然大漆在工艺和艺术之间的对立状态。他尊重规则和方法,却不拘泥于人为界定的平衡状态,从而展现出了这种材料媒介的本质。正如他自己曾经说的:“我的作品可以被理解为用大漆这种媒介记录一种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一个过程,或者是某一个阶段性的定格,画面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明确的符号,只是髹涂和打磨,探索由大漆这种媒介和工艺所产生的最为本质的视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