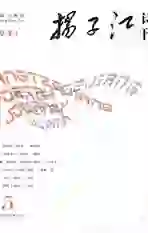转引(组诗)
2021-09-06臧棣
臧棣
转引自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起点是无限颂。因为很显然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不仅仅需要填补。与自然搏斗,
这是诗的最基本的形象;
其次,诗的任务是超越自然,
将我们带回生命的故园。为此,他赞同
梦,应该得到一个现代的解释:
梦不止是一面古老的镜子,
更包含着对生命的解放。
精神方面,席勒常常能引起共鸣,
但他身上“幼稚的敏感”又破坏
灵魂的完整性。最难忘的快乐,
是在《季节女神》上,措辞微妙地谈论
天才的“无所事事”。弦外之音,
歌德的存在近乎“大理石般的上帝”,
已严重妨碍到人类的反讽
对“永恒的灵活性”的清晰的把握。
性格就像荨麻,但他的一生
也印证了命运的青睐:有时候,
真正的友谊的确能给混乱的人生
带来“一片光明”。比起歌德,
更神秘的启发常常来自诺瓦里斯——
如果存在着“审美革命”,重点无疑是
必须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
不平凡的深意。或者委婉一点,
针对人性的瑕疵,“所有的美都是隐喻”。
费希特的回声:诗是一次占领行动,
身体的沦陷恰恰为人的可能的救赎
铺就了一条通向“最高者”的路。
转引自伊本·西拿
人生的烦恼,多数情况下
都源于人对灵魂的分类
缺乏敏感。痛苦里
最多的,就是痛苦的假象;
告别世界之前,最好先去吻一吻
骆驼身上的尘埃;或者现在
就去沙漠深处,参观一下
古老的日出;喜悦的火球
没准能蒸发掉所有自怜的眼泪;
日落的宁静,如果没能
给你的内心带来一种平衡,
你不妨摘一朵花,插在狼的粪便里。
如此,白天和黑夜分别
是灵魂的两个账本,记录着
神秘的债务。没有轮回,
你必须学会用你的健康
来发动一个誓言。世界的宽广
和生活的狭窄,则意味着
一个人的成熟是否达到了
可以独自凭经验使用
麻醉剂的程度。无论如何
不要被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
这些临时的说法所迷惑;
尊重每一粒灰尘,因为
真正属于你的黄金,都不是
挖出来,而是神秘的乐观
对想象力的渗透;殷勤的擦拭下,
奇异的光,突破了一个表面。
转引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雨夜里有一场告别。
将人类的静音在地板上慢慢铺开,
可以听到浪漫的思想
正輕微在深色的序曲中;
卢梭的问题是,他的手有点苍白,
搬不动自由的基石。心灵的
动向,不该简单地沦为一次投票。
人的行为近乎一出大戏;
角色的分配中,作为一种罕见的
例外,理智高于智慧,
也算是对历史之恶的
一次纠正。给终极目的浇点油,
固然痛快;但从瓦尔登湖归来,
很显然,个人的自由
不再是自然之谜。和诗的成就一样,
选择的空间越多,语言的气氛
就越活跃;直到那一刻,
剥除自然的伪装,你拍打
文明的支柱时,旗杆上的黑鸟
再也不会冲着你吹口哨。
转引自赫拉尔多·迭戈
非常奇妙,这一幕
确实不常见:将命运女神催眠后,
颜色比开屏的孔雀
还丰富的鱼,突然摆脱了
大小,求偶般游向
裸体的结晶。你不会猜到
动情的躯体在受到
启发后,纠正了多少真实性。
不必羞涩,因为此时,没有人
会注意到你的舌头
也曾是一条颜色鲜艳的鱼
拼命游向世界的窄门。
这种事情上,方向有没有弄反,
非常重要。毕竟,美和真理
都想先于对方,在生命的游戏中
将我们逼进死角;在那里,
你和你的影子都不会想到
每杀死一个魔鬼,
天使的面目也会跟着模糊;
整个现场,只有雨似乎看懂了
花朵的决心,从未犯过一次错。
转引自惠施
至少他反思过作为
我们的化身,蝴蝶并不可靠;
他甚至也没放过
过分的思想;毕竟存在着
这种可能性:与其说蝴蝶不可靠,
不如说人更不可靠。
甚至怀疑蝴蝶是否具有象征性的人
根本就不配抱怨蝴蝶
可不可靠。别忘了,
万物都有各自的角度;
拟人时,鸽子甚至是比我们
更形象的角色;没准这就是
鸽子的角度:人,不过是物。
换句话说,蝴蝶再怎么
不可靠,毕竟同时拥有过
美丽和轻灵;而且蝴蝶也愿意
与我们分享寄存在它身上的
心灵的图案。所以,任何时候,
化身都只是一种角度。
另一场决胜,发生在秋水边。
他的口吻很像谈及语言的边界时的
维特根斯坦:我们不是鱼,
怎么可能知道鱼的快乐。
尽管遭遇到聪明的反驳,
但实际上,没人比他更懂得:
逍遥不完全是态度端正
不端正,逍遥是对自我的发明。
自我才不在乎大小呢,
在水里差一点淹死;
表面上,自我小得已经输给了
一只绿头鸭;但其实,
从时间的角度看,每个人
如何拥有自我,更像是
会不会看地图。可千万别拿反了:
因为毕竟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自我就是人在南方。
转引自希罗多德
关于永生,最开始
鸟类比我们更关心它的
现实性。在它们浩渺的感觉中,
死亡的临界点定于
每五百年会有一次新生;
于是,一只大鸟出现在虔诚的想象中,
直至不朽的焦虑得以超越
灵魂的争吵,超越地域的界限,
集中于一个纯粹的体会:
永生不是对死亡的克服,
更非绝缘于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治愈,
是一个生灵敢于朝向死亡,
在火的影子里不断死去又不断复活。
想想看,一只大鸟对五百年的
时间界限,都有如此清醒的觉察,
人的羞耻感难道不更有潜力吗?
一个更现成的羞耻的例子是,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菲尼克斯
最好有一个外号叫凤凰。
都是不死鸟。关于它的模样,
精通历史故事的希罗多德
却并不打算讨好历史的企图;
难得他如此坦率:自赫西俄德之后,
没有人见过不死鸟的真容,
但它的外形很难和巨鹰
脱得了干系;而且很显然,
它的羽毛,应以金色为主,
以便人类对黄金的虚荣心
随时都能得到醒目的烘托。
相形之下,人的死亡临界点
只有一百年;且整个过程中,
大部分时间已被恐惧所腐蚀。
即使偶尔意识到语言带来了
一种飞翔,但已经沉溺于
怀疑论的我们,实际上
已很难自觉于这样的事实:
我们的翅膀只能是人的语言。
转引自康拉德
“青春是记忆的壮举……”
——约瑟夫·康拉德
异样的摩擦来自
巨浪的好奇心。炽热的红光,
伴随着桅杆的断裂,
放大了热媒的爆炸
在甲板上造成的混乱,
一幅逼真的末日景象;
但作为一种衬托,拜伦式的
人物也获得了他的新生。
盲目的青春是加速旋转的陀螺,
停止键像一个出卖过
最美花瓣的器官,被藏在了
黑暗的中心。命运的公平
则是另一个尖锐的谎言;
就好像不如此,时间的残忍
便会在我们身上失效。
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楚
作為一个还算老练的小说读者,
我为什么会毫无来由地偏爱
康拉德的《青春》。毁灭如此缩影,
但也如此轻佻;而正是
在这强烈的反差中,我仿佛
也第一次获得了选择的权利——
只需轻说一声,再见!
那无尽的黑夜便成为告别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