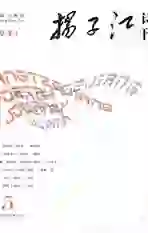山国与珠贝之心
2021-09-06谢君
谢君
1
我喜欢那些依赖于平淡的、陈述性的句子而又具有转折力量的诗歌,就诗歌阅读而言,通常我的速度较快,但遇见独特文体或让我惊喜的文本能够使我缓慢,并且抓起一支铅笔,在喜欢的段落画写。毫无疑问,叶丽隽的诗歌能够让我抓起铅笔,这意味着专注,也意味着愉悦的奖励,因为她的诗歌充满追忆之光,并且谦逊、毫不张扬,将自己置于低处。当她将自己的存在铭刻于语言之中时,在春雷的震动中,幽暗与不平静的时刻就将被细长茂盛的败酱草的美丽闪烁所缓和。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种我非常喜欢的矛盾混合,因为我们的世界和写作本身基于悖论。
当一个作品进入你的记忆,那么这个诗人也就进入了你的记忆。多年来,我有幸认识叶丽隽并分享她的诗歌。作为诗人,我认为她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因为她的作品随性、坚韧、真实、鲜明,就像晨曦到来时的曙光一样吸引我:强烈、清晰,并且有一种可以感受到的震撼力。
父亲总是在最前面
握着锄头轻轻挥舞,嚓、嚓、嚓
鲜嫩的春笋应声倒下
母亲紧随其后,一根根捡起
竹叶和泥巴沾到了装笋的麻袋上
又湿漉漉地掉下
如果,我的哥哥还在
他会朝我竖起食指:“嘘——”
曙光到来之前
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
在幽暗潮湿的竹园子里,在这里,那里——
——《黎明前夕》
一个简洁、朴素、生动的挖笋场景,这个诗歌的全部片段是图像细节,父亲在挥锄,母亲在捡拾并用一只麻袋装笋,一个小女孩在静听春笋破土的声音。除了图像呈现,诗歌的陈述,还在音响之间急速转换,从“嚓嚓嚓”的锄声,到记忆中的哥哥朝我竖起食指的“嘘”声,到春笋破土的声音。世界与影像被包裹在日出之前的光环中旋转,这样的描写永远不会褪色,虽然很多年过去了,《黎明前夕》依然在我喜爱的诗歌清单上。在我印象中,这是叶丽隽第一首停留在我的大脑中的诗歌。
在充满家庭親密感的描写中,当竹园最终归于寂静,我似乎又有某种悲伤的感觉,因为在阅读诗的后半部分时,我在那里停顿了一会儿——“如果,我的哥哥还在”——我震撼于这句,在愉悦中带上了隐约的刺痛。因为我突然发现诗中“哥哥”是缺席的。这句脱口而出的台词将现实与回忆结合起来,叶丽隽的很多诗歌的情感深度,或者说震撼力,就在这种隐含的方式之中。失去总是伴随着我们,但叶丽隽并不纠结于悲伤性的沉思思维,而以隐约、细微的生命细节呈现。从这个角度说,独特的细节就像石头,扔出去可以杀人,猛烈而不妥协。
在写作中,我一直认为,基于自传的细节异常重要。所幸的是,叶丽隽做到了。叶丽隽是这样一位诗人,忠实于在微观世界中编织,并信任图像并置的力量。当自然、场景和事件随时间框架展开,在宁静的氛围中,通过记忆和联想,它又咬合着悲伤的锯齿,她的语境的叙述线圈总是能够细微巧妙地放松或收紧,这就是叶丽隽的“珠贝之心”。
夜深人静——槐湖边,哥哥打着手电
我不出声地跟随
父亲找准位置,将特制的加长鱼抄子
慢慢地探进湖底
待搅浑的水面归复平静
父亲和哥哥合力,将鱼抄子迅捷地撤回
有时,网兜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也有时,伴随着潮湿的泥腥味
一些螺蛳、虾蟹、草鱼和黝黑的河蚌
在星空下幽幽地闪烁
螺蛳和鱼虾类,都细心地分拣好;
唯独河蚌
沉重而价廉,鲜有人食
父亲随手就扔回湖里,或者搁置一旁
当我们离开,岸边的河蚌已聚集成堆
夜正深,岁月正浓——
漫长的黑暗中,弃物沉默不语:紧闭着
粗糙的石头身体
和可能的珠贝之心
——《夜渔》
这是一首充满诗意刺激的诗歌。记忆中的一切在夜深人静中流淌,槐湖、波光、将鱼抄子探进湖底的父亲和打着手电的哥哥,当他们合力将鱼抄子迅捷撤回后,幽深中挖掘出来的东西,螺蛳、虾蟹、草鱼和黝黑的河蚌就在星空下的湖岸上了。《夜渔》一诗就这样充满了幽微的闪烁和喜悦,并且刻录在诗人的记忆库中从未离开。
诗歌是通过事物而发明的,叶丽隽创造了一个视觉和动作组合的场景,从而让我们站在她的童年时光中。而随之,又将我们带入她当下的或某个瞬间的内心,因为诗歌真正的主题是对于自我的“凝视”,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重要部分,孤单、坚硬和发光的部分:“漫长的黑暗中,弃物沉默不语:紧闭着∕粗糙的石头身体∕和可能的珠贝之心。”
可以说,流淌与凝视,喜悦与孤单,影像和意识,叶丽隽的诗歌在这两者之间连结、呈现、走钢丝,从而将节奏和声音融入了冷峻和感伤的时刻,这种悖论是语言的核心,它的表达方式非常迷人,这是叶丽隽的天赋,潜伏在她的语言之下的一台隐形的发动机。
十八九岁,各地辗转
曾经学画度芳年
有段时间,求学于高村的一个画室
我,育红、竹林和小园
彼此形影不离
一起写生、临摹、挨训
一起高谈阔论、踌躇满志
我们曾漫步于广阔的原野
在一座空坟前停下脚步
看四脚蜥蜴在阳光下热烈地交尾
也曾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偷挖村民的地瓜
当黄昏来临
我晃着脚,坐在窗台上用单音吹口琴
她们则跟着曲调轻轻哼唱
郑钧的《灰姑娘》
……是的,一群真正的灰姑娘
在那时
摇头晃脑地吹奏着,哼唱着
每个人都觉得来日方长
——《灰姑娘》
就像黄昏时多彩的晚霞,就像电影中的一个情节,这首诗是如此年轻、美丽、苗条、无忧无虑而自信。一群求学、画画的年轻女孩,正在高谈阔论,漫步于原野,坐在窗台上,吹着口琴,哼唱《灰姑娘》。她们的脑袋在摇晃,两条腿也在空中晃动,她们正在期待着她们的未来。
我想《灰姑娘》这样的文本足以印证,叶丽隽是一位可以给我们不断带来语言惊喜的诗人。她的流淌或者说跳跃剪辑,她的凝视或者说悬念制造,为我们记录了如此孤独和美好混合的时光,一个生命中如此神奇、不可能而可能的时刻。它将记忆素材转化成了新的现实──具有令人回味的梦幻般的感觉。
从生活中原创,从孤独中提炼,深刻的记忆,它永远是一种栩栩如生的东西。叶丽隽生动的表达,或者说令人信服的表达,全部秘密皆在于此——写作的永恒技艺是写下你生命中最震撼的。她的写作具有自己非常清晰的可识别的标志——坚持自传的恒心,并坦率地暴露自我,毫不畏惧,直截了当,直言不讳。简言之,她的诗就像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之中一样,它是一张记忆中的真实旧照,经由语言召唤而来,从而让我们返回曾经感知的生活的神奇之处——一个闪耀着记忆和风景之光的世界。
2
这个世界看起来很真实,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真实,很多时候的真相令人悲伤。作为一个诗人,我们之所以关注生存事实,从不转移视线,因为我们需要传递真相。叶丽隽的诗歌编织图像、轶事与声音,给我们新颖的感觉,让我们见证了她的灵巧,她的流动,她的视觉目光,除此之外,她的诗歌最重要的部分,我认为,是心灵的颤抖。她的诗歌正是这样的容器,当诗人通过它而倾注,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熟悉的世界中的那些创伤性的旋涡,也就是真实生活所呈现出的破碎性。
当一个诗人探索记忆与存在,对于存在的本能和自我的难以捉摸的反思,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也唯有如此,诗歌才能让我们着迷。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真正的写作永远是真诚的,是世界赋予我们的本真:白与黑,幸与不幸,多样而不规则。从《灰姑娘》的清澈,到日漸混沌,叶丽隽大胆地呈现了那种令人不安的魅力,深刻的困扰。它距离我们当代的经历并不遥远。或者说,叶丽隽的写作从不远离我们的当代经验。
命运的偶然性使我们无法远离悲伤,在对现代生活的观察中,叶丽隽的诗歌经常会将我们抛向一个未知和意想不到的世界,很多时候,她的叙述规则就是无缝地突变,在突变之后,审视自我使诗歌走向追问。
列车过金华,漫长的中转
硬卧车厢。折叠小凳。她缩紧身子
贴着窗玻璃,不出声,尽量与黑夜
保持着一致
山峦黝黝,远灯如豆
连绵相似的风景,此处,亦是他处
然而……金华……一个尘封的瞬间突然
浮现,猛地击中了她
二十多年前,哥哥送她
赶赴金华考学。贫寒兄妹,搭上了
一辆过路的货车
到了金华郊外,他们被卸下
哥哥背着她的绘画工具,牵着她的手
徒步至市区
详细叮嘱后,告别返家
而她,一头扎进了
属于她自身的命运旋涡里,从未回头
和停驻,也从未细想:
从金华到丽水,一百多公里,她那
无以为生的哥哥
是如何返的家?
啊不,她不明白自己怎能如此轻佻——
……惊悸突袭,她蓦地明白
原来哥哥,并非罹难于
一场车祸,她早已失去了他
在多年前
在此地,那个她不曾回头的
告别的瞬间……哐当声中,列车重又启动
却似乎掉了个头
开往来时的方向。泪水中她愕然
随即又闭眼,更紧地贴着窗户,一个
心碎者管不了一列夜行的火车
一段不堪的人生,一个追问
—— 《夜行列车上的心碎者》
某一天,诗人坐在夜行列车上经过金华,就在列车穿越的加速度和牵引力中,整个世界突然扭转了:“一个尘封的瞬间突然/浮现,猛地击中了她。”击中她的是一个二十多年前的画面,从金华到丽水,搭货车一百多公里,哥哥送妹妹赶赴金华考学的情景。它为我们提供了记忆,然后触及的是死亡与悲伤。
叶丽隽有一种处理生命旋涡的天赋——在记忆和即时体验之间转移。在她的叙述中,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飞跃或者说马蹄型拐弯常常令人惊叹。此诗在列车飞驰的动态画面中,以一个瞬间的嵌入,使过去和现在不可思议地并列,使诗歌成为一首挽歌,一个追问,展现了刻骨铭心的创伤。确实,读这样的诗很痛苦。令人心碎的不仅是它描述了亲人在一场车祸中罹难所遭受的灾难性丧失,还传递了一个时代贫困的现实。现实的疼痛像尖锐的边缘锯齿,包裹着我们独一无二的生命。
世界无时不在扬起尘埃、飘浮阴云、密布骤雨,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对社会世界的感知中,也有这种感觉。作为一个生命感受力敏锐和强大的诗人,叶丽隽显然不会止步于浅层生活流的描写,因而她的诗歌中不和谐的、令人困惑的、危险又脆弱的东西,总是像一个迷一样突然出现。通过时空转换,日常与幽暗交织,叶丽隽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真实而又恍惚,遥远而又贴近的世界。
母亲年轻时,在陈寮山上砍柴
不慎滚落
幸好被山腰的一棵树挡住
捡回了性命。以至于,每次回想起
她都非常笃定:这棵树
应该是上天的安排
我曾问她是否害怕,她说只记得山谷间
回荡着“啊——”的声响
——我也常常遇险。在梦中
更是多次突然地临渊,并从悬崖坠下
随着猛烈的蹬腿
我在黑暗中惊惧地弹起身——
啊,又是一个失重的
喑哑的夜晚,没有破胸而出的呼喊
没有回音……我的树
那属于我的树——
它还未出现,还不肯出现
——《崖上》
叶丽隽的叙述逻辑是联想飞跃,或者说拼贴,借此建立快速联系。拼贴作为主要的创作策略,它现在或者正在成为一种新颖的方法,我甚至可以说,拼贴即将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典型方式。《崖上》一诗,两代人,母与女,母亲年轻时一个遇险的片段与我在梦中的失重,两个画面的并置与对比,动荡、黑色、诡异、惊悚,创造了一首令人不安的奇异诗歌。这就是文字的魔幻力。
在这诗歌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不能用语言压缩和描述的生命困境。叶丽隽曾在《在我母亲家的庭院》一诗中坦承:“我的母亲,中国最早的知青。”当返城之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青春年华了,被忽略和遗忘的挫败感使一个人的性格执拗易怒,最终成为家庭沉重的阴影。在诗人,她的踏空失重,肯定也有现实的因果关系,并且不可撤销。事实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距离细节记忆最近,它们徘徊在日常生活之处,徘徊在视野之中。虽然生命困境未必能够使人高尚,但作为蒙受者来说,能够进一步拓展诗歌的强度。
我认为这是诗歌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诗歌最大的可能性,一个诗人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和潜力。当你意识到之后,混乱与黑暗,乃至苦难的侵扰就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并不那么糟糕。也唯有如此,我们的诗歌才不会成为空洞的语言体操和迂腐的思想体操。实际上我们明白,一首在意识边缘的黑暗诗,基于恐惧的驱使,也必然基于爱的驱使,这是融而为一的事。荣格说:如果没有悲伤提供平衡,快乐这个词就会失去它的意义。叔本华也曾表达:从整体上看,每个人的生活,强调其最重要的特征,都是悲剧,但经过详细观察,它又具有喜剧的品质。
哲人的言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理解:作为一个现代人,心灵与21世纪同步、诗歌与生命体验同一,十分重要。基于当代生存经验的当代性写作,它是现实与超现实的融合,悲剧与喜剧的融合,恐惧与幽默的融合,高尚与低俗的融合。对于叶丽隽的诗歌,这是一个恰当的描述,她的悲伤与不安的魅力在于——聆听与敬畏某种来自最边缘的、未知领域的神秘。
3
有一年春天,我在乡下的青屋里
平息了身体的波浪
也曾夜观星象。在院中,用高倍望远镜
搜寻着大大小小的月坑
一座座亘古的环形山,对应着浙西南
我蛰居的谷地
没有欢乐,没有悲伤
常去的是附近的峡谷
坐在溪石上,四野寂寂,青峰朗朗
听周遭草木隐忍地拔节而不惊
直到,一天晌午,几声短促的呼哨后
一只红嘴蓝雀
出现在视野上方,它那长长的
凤尾似的白羽,优雅从容,静止在山谷
瓦蓝的空中……哦这孤独的翱翔
这山国岁月,秘密的赐予——我的心
碎了。万物在春天,皆有分裂的痛
而我,有了深处的动静
——《我的山国》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美国奇幻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的一句话:“人类最古老和无法解释的情感是恐惧,而最古老和无法解释的恐惧是未知。”夜晚的星空是我们最直观的未知领域,抬头仰望,我们知道存在没有边缘,没有外部,即使是眼前飘浮的月亮,物理距离也是如此遥远。
我们无法抗拒未知、定义世界,因而只能沉浸其中。虽然人的存在及其情感是渺小的,但山水和山水中的一间青屋与我们的孤独相呼应。这里,一个我们可能反复离开但必然返回的地方。这里,走过的每个峡谷、每座青峰、每片溪石、每棵隐忍的草木都可以被心灵吸收,也可以充满心灵。这里,赐予我们生活的疲惫、分裂与疼痛,也赐予深处的动与静。无论上升,还是下降,当我们在这里静止片刻,都可以平息身体的波浪,随一只孤独的红嘴蓝雀一起翱翔。这就是叶丽隽的孤独山国,如同她在诗歌《山水课》中所述:“丽水,我的家乡/你早已存在于我的五脏六腑//今生,就是这个让我心醉。”
叶丽隽生活在丽水,丽水生活在她的詩歌里。在她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对于丽水的敬意——它作为生命寄存器,被命名为山国,并成为写作重心与诗歌作品中的精确制图。同样,当叶丽隽沉浸在这片空旷中,也将被丽水命名——一棵埋首于低处的败酱草:
惊听一夜春雷。晨镜中,果然
燎泡上唇——唉,多么令人羞愧
我那虚弱、不洁的本性……
谁能预料,季节滚动着的深喉,繁殖的
是新生,还是新的恐惧?
还以为,我已远远地退后
败酱草一样
埋首于人世的低处
在苦涩的陈腐气中,沉溺并懂得:
山野之间,有着本然的救赎
几乎是一种呼唤呢——怀揣一腔虚火
我惦念着郊外
乱丛之下,那清热解毒的草木
诚如,再粗鄙的个体,也需要一个隐蔽所
一个在暗中,不断过滤的自我
——《败酱草》
时间拥有自己的逻辑、纹理和震动,在数字时代的速度中,在世界环境的不稳定和摇晃中,从季节的深喉里发出的一声春雷使人震惊似乎很难解释,但我们理解并且知道,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每一秒都在被驱动,被腐朽,被流逝。在晨镜前的恐惧中,一棵败酱草的自喻里,叶丽隽正在试图救赎,清空内心的羞愧、迷失与疯狂,将之减少到一种光谱的残余,从而变形为另一个自我——平静、接受和愈合。
败酱草,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秆细长直立,可以高达一米,根紫色,黄白花,果圆形。通过它,这一诗意或者说并不那么诗意的事物,叶丽隽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平衡,平息恐惧、不洁和身体的波浪,而在语言的世界里,她的诗歌也降低了激震,趋向朴素、平缓、沉静和深邃。
母亲喜欢赶早。清明前后
第一餐豌豆饭
是我们全家团聚的时辰
糯米和香米的配比,全凭母亲
多年的经验,淘洗干净后
用清水泡上;带肋骨的咸肉
在沸水里焯过,备用
豌豆和雷笋,则需要当日的时鲜
有一年,也许是时节太早
父亲从菜场回来
买到的是冰冻豌豆。我随口说了句:
“我还是喜欢吃新鲜的……”
父亲二话不说,再次出门找寻
此刻,豌豆饭焖熟了,袅袅的热气里
咸肉金黄、雷笋白嫩
碧玉一样的豌豆点缀其间
粉糯鲜甜——
母亲烧得累了,她要小憩一会儿
静静地,看着我们吃。窗外
蓬蒿遍野,青峰凛冽……我们的父亲
正置身于这场无边无际的葱茏之中
置身于眼前
这钵豌豆的翠绿中
——《豌豆饭,或早春》
强大的观察力和情感的亲密使这首诗引人入胜。在很多时候,叶丽隽的目光关注父亲和母亲,这首诗的镜头也植根于此,专注于母亲为家人准备饭菜,并极为细致地叙述了豌豆饭的制作过程,包括糯米和香米的配比,淘洗,咸肉、豌豆与雷笋一丝不苟的整理,以及烧煮。琐碎,但充满敬意,似乎是在进行一项庄重的仪式。特别是最后一个画面,是温存的注视,当母亲专注于窗外,她的目光捕捉着春天和春天所控制的蓬蒿、青峰、父亲以及这个世界最大的色彩——翠绿,父母亲之间长期的疏离结束了,春天的翠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于生活的理解的隐喻。
因而诗意的光源投射,是朴素的敬畏和奉献,叶丽隽对此进行了坚定明确的刻画,世界的混乱消退了,现实的锋利冻结了,不安的阴影被切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零碎化的叙事、视角的切换、独白的加入、无边无际的风景的融合,它的编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松散。也许这正标志着叶丽隽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有意识的转变,她的写作更加宁静、放松与活泼了。
在无尽的文字道路上,我喜欢宁静、放松与活泼,并用生存见证进行创造,我也喜歡她的文字所容纳的世界——丽水,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之地,青山环抱一如卧室窗帘幽静地垂挂。无论我们的存在处于哪一片时空之中,无论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是否都是他者的,只要你写下生存之地有形的、有质量和重力的存在,它就是你的,丽水就是一个人的山国,前方就是山水,是记忆、悲伤和敬意。
“山水无穷尽,身体有枯荣”,有时候,我感觉,阅读叶丽隽的诗歌,最好是沿着街道漫步到窗外的南门江公园之中,在一棵垂柳的树荫下静坐,或者四肢伸展在一片草丛中,敞开自己,然后掏出随身携带的诗集,一会儿举着铅笔,一会儿在书页上赞赏性地勾勒。宁静和放松是阅读她的作品的最佳状态,很快,她诗中的图像和感觉,她描绘过的春雷与败酱草,以及语境中的其他景物,就将随心灵之声在你的脑海中漫游、碰撞、延伸和放大。因为这就是叶丽隽诗歌的敏锐或者说与众不同之处,重视心灵与冥想,而又具有强大的自然环境的描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