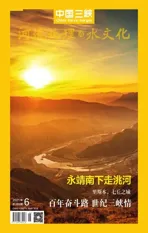流淌石头的河谷
2021-08-12项丽敏编辑王芳丽
◎文、图 | 项丽敏 编辑 |王芳丽
等待一场雨

等待一场雨
入冬后,浦溪河进入枯水期。
其实两个月前,浦溪河就开始进入枯水期了。
皖南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春夏两季多雨,秋冬两季雨量较少。只是近年来,大自然的性情变得不可捉摸,无章可循,去年整个冬天全在雨水里泡着。
这种反常早先几年就露出端倪,下雨的日子太频繁了,一年四季如同在雨廊穿行,好在隔一段时间,会漏下几个晴朗的日子,让被雨水憋闷的人长舒一口气。鸟雀们也赶紧从藏身的角落飞出,去太阳地里亮开嗓门,呼朋引伴。
但是很快,雨又落下来,落得忘记了季节的边界线,忘记大地上的生灵在入冬后多么需要阳光的慰藉。
我原本是喜欢下雨天的,喜欢雨声带来的静寂悠闲感,但经历了去年那么漫长湿冷的冬雨,终于将我对雨天的喜爱度透支为负数。
开春后雨总算歇下来,久违的阳光让生机重返大地。母亲坐在院子里,将患有风湿骨痛症的腿脚伸进阳光里,眉头却不见舒展,嘴里嘀咕着:久雨必有久旱,今年怕不是个好年成。
母亲让父亲今年少种点菜,不然天天早晚浇水抗旱,吃不消的。父亲对母亲的话不置可否,仍旧按时令播种,把十几畦菜地种满。母亲见父亲不听她的话,就让我去劝阻:你爸从来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还是你跟他说吧。
我相信这世间万物遵循着能量守恒的定律,对久雨必有久旱这句话也是相信的。而母亲之所以说出这句话则是凭着她大半生的灾难经验。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母亲一直陷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中,直到中年以后,她的日子才算安稳下来,这时候疾病又开始缠住她。事实上这些疾病很早就埋伏在她身体里,只不过到中年才露出狰狞面孔。
早些年母亲还能帮着父亲种菜,这两年连菜地也不能去,走路对她已不再是轻易的事,也是她年轻时走了太多的路——在偏远的村落里教书,出门就是翻山越岭,几十年下来,腿脚所受的压力早就超负荷了。
我将母亲的话传给父亲:少种一点吧,就当锻炼身体,种多了会变成劳累负担,再说你俩也吃不了那么多菜。
种地不累人,每天来菜地拔拔草浇浇水,看着菜一天天长大心里也舒坦。
父亲的回答让我无法辩驳。
好吧,只要父亲觉得种菜能给他带来愉悦,那就种吧。就像我写作,也是如此,和父亲在菜地里的劳作一样,是为了获取内心的安宁满足,如果长时间不写,会觉得心里长满荒草,变得不安且烦躁。
干旱的天气从九月开始,起初十天倒不觉得什么,以为很快就会下雨。黄山周边受地方小气候影响,很少有超过十天的晴日。可过去半个月,还是没有下雨,天不厌其烦地晴着。
每次打电话回家,父亲都在菜地浇水,果真应了母亲的话——得天天浇水抗旱。有几次,城里倒是下雨了,雨不大,也有久旱逢甘霖的喜悦,赶紧拨父亲的电话,问家里可有下雨,父亲说没有,家里一滴雨也没有,河都干了。
后来才知道,城里那几场雨皆是人工所降。
三十天过去,四十天过去,五十天过去,老天还是没有认真下一场透雨的意思,这时乡下已经开始定时供水,只在每天晚上七点放闸供应自来水,两个小时后关闸。
村里很多人家的菜地早抛荒了,往年碧青的油菜地也大片大片地荒着——吃用的水都那么紧张,哪有水浇地。父亲的菜地还剩着一点萝卜和蓬蒿菜,不用我说,父亲也不会再往地里种什么——原本冬天也没有什么菜可种的。
干旱已延续了两个月。城里人对持久的干旱并不像持久的雨水那么厌烦。城里人如果不去乡间走走看看,甚至感觉不到这样的天气有什么不好,自来水还是和以前一样,随时拧开就有,哗哗流淌。唯一有点感觉的就是蔬菜价格贵了不少,但这也不至于让人恐慌,总归还是能买到。
如果不是住在浦溪河边,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在乡下过着和农民一样的生活,我也不觉得每天都是大晴天有什么不对头,我会喜欢这样的天气,会觉得整个冬天都这样——被太阳从头到脚地晒着才好,也算是对去年冬天那么长久见不着太阳的补偿。
但这样无止尽地干旱下去,终有一天,城里的自来水龙头也会不再有响动吧。
据说明天会有再一次的人工降雨。能下雨终归是好事,但人工降雨并非自然之道,是否会加剧破坏大自然的规律呢?
当我说出自然之道这个词,自己也觉得迷惑,什么是自然之道?听凭大自然的本意就叫自然之道吗?可如果干旱遥遥无期地延续下去,这自然之道不就是绝望之道?
此刻窗外已有云层堆积,也许夜半就能听到雨声,河水将涨上来一些,我生活在河里的邻居——小䴙䴘、黑水鸡、鹭鸶、斑嘴鸭也会为这久违的雨水而欣喜吧。
有魔力的林荫小道

有魔力的林荫小道
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诗人红土从合肥驾车过来。每年这个时节,红土都会来皖南看秋色。有时春天油菜花季也会过来。
红土有皖南情结。我为数不多的外地朋友均有皖南情结。皖南或者说徽州在他们看来就是前世的故乡,是心里天然怀有亲切感的地方。
说起来我和红土都是有社交困难症的人,喜欢独自呆着,喜欢在清静无人之地游走,最大的安全感和快乐来自大自然——一踏入大自然就会自动卸下成年人的盔甲,手脚轻盈,简直要从地上飞起来。
两个并不热衷社交的人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仿佛是我们同时在新浪博客里读到对方的诗,看到对方的照片,默默欣赏、关注着对方,这样过了两年,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居然不期而遇。
你是丽敏?
你是红土。
不用介绍,我们一眼认出彼此。
距离第一次见面差不多已过去十年。这十年里我们几乎走遍徽州的每一条乡村公路。有些路反复走,有些村落重复去,仍然会欢喜得大呼小叫,得意忘形。
这十年里,我们反复走过的路还有一条林荫小道,如同绿色的缎带,被合肥这座城市挽在腰上。我不知道这条林荫小道叫什么名字,问红土,她也不知道,只告诉我紧靠着小道边就是合肥的环城河。
在很多个夏天的黄昏,我和红土沿着环城河在林荫小道上走着。我们头顶,众多叫不出名字的鸟雀从一棵树飞往另一棵树,殷勤地为我们领路,用好听的声音朗诵着晶莹透明的诗句。知了的声音也很密集,如同一条流动在空中的河流,使我有种错觉,以为自己仍然置身在皖南山间。
知了的鸣唱延伸了黄昏的长度。落日将余晖投在河面,缓慢流淌。我们在林荫小道走的也很慢,呼吸着树木在盛夏的味道,一棵树一棵树地辨认:无患子、毛白杨、枫树、银杏、栾树、重阳木、水杉、盐肤木、杜仲……红土说她很多诗歌就是在这里漫步时写的。说写不准确,因为那些诗句根本就是从树上掉落下来的,像风吹落的花朵、浆果和树叶,落在她的肩上。
红土擅长写童话诗,说起话来也颇有童话感。
下过雨后来这里是最好的,每棵树都把自己的味道干干净净地摆出来,空气里有很多水泡冒啊冒,咕噜噜,咕噜噜,我就在树下站着,大口大口把味道吃下去。红土边说边比划,仿佛自己是一条鱼,在绿树浓荫里快活地游动。
林荫小道有几个出口,其中一个出口通往三孝口书店。
通常在天黑之前,我们会到书店里去。
一进书店的门,红土就真的变成了鱼,眨眼不见,不知游去了哪里。在转了几层楼之后,突然看见红土,盘腿坐在地上,和学生模样的孩子们坐在一起,身边摆着一摞书,手里捧着一本,那专注的模样,显然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也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那时候红土还没有自己的书房。这距离她居所很近、有吃有喝、设施齐全的书店就充当了她的豪华书房。不上班时,红土可以一整天呆在这里,一本书一本书地读下去。有一次,我在皖南的山谷游走,突然收到红土发来的图片,是我刚出版的散文集,和几位畅销作家的书排在一起。很快红土发来短信:在三孝口书店遇见你的书,悄悄拿出来摆在显眼的地方,好开心。
说真的,我还从没在书店里遇见过自己的书,那该是多么大的惊喜。
林荫小道的另一个出口通往杏花公园。
不记得杏花公园里是否有杏花,也许有,只是我们去的时候不是杏花盛开的季节。在我的感觉里,杏花公园仍旧是林荫小道的部分,就像岛屿也是河流的部分。
对合肥这座城市我仍然还是陌生的。事实上,在认识红土之前,我几乎没有去过合肥,这源于我的都市恐慌症,或者说,源于我对过于复杂的交通、迷宫样的街道的恐慌,担心自己会找不到方向,会迷路,尘埃一样消失在车流之间。
好在合肥有这样的林荫小道(也许有很多条),让我在其间漫步时如同在山间一样自在。这是一条有魔力的林荫小道,能把大人变成孩子,把孩子变成小鸟,把小鸟变成诗人。每一位走上小道的人都能看见河流上空的星光,每一个小道的出口都通向精神绿色的家园。
冬日山林

冬日山林
十一月末尾的几天,下了一场催冬雨。
也不知道有没有催冬雨的说法,应当有吧。既然有催春雨,就该有催夏雨、催秋雨和催冬雨。
和往年比起来,今年的催冬雨下得有点蹊跷,伴着电闪雷鸣。按说到了这时,雷早就应该把声势收敛,如冬眠的动物那样,蜷起身子藏到地下,到第二年的惊蛰再苏醒,钻出地面。
可今年到现在,雷还驾着它疲倦的车马,在天空游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进十二月,雨就停了,天气转晴。
冬天正式到来,温度骤然降下不少。虽不喜这骤冷的天气,心里倒是踏实了些——十二月了,是该冷下来的时候了,冬天就该有冬天的样子,就该朔风卷地,有冷霜和冰雪。
天一晴,在屋子里就坐不住,想往山上去。
此时上山,当然不是奔着“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色,这样的秋色,在半个月前已让眼睛饱餐过。此时上山,为之挂念的是“落叶满空山”的情景。
“落叶满空山”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句,我读到这句诗,却是在德富芦花的书里。
德富芦花在书里写道:当我吟诵着“落叶满空山”的诗句,独自在深山缓缓而行,看到果树自行爆开,果子落到地上,耳畔仿佛听到闲寂原本的声音。
目光停留在这行文字上,反复品味。落叶满空山,这是一句诗,也是一幅画,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与境界,有着虚实相生的禅意之美。
出门即是深山,这是在山区生活的最大好处,无须借助任何交通工具,迈开步子,走上一刻钟就置身山林了。对于生性喜爱丘山的人来说,这种便利也可算是福利——这也是我一直生活在这里,而毫无倦意的原因。
上山不久便遇见一个消瘦的妇人,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手里提着长柄锄头,另一只手捏着空空的麻袋,猛一抬头看见我,有些惊讶。妇人没有说话,侧身从我身边走过。她大概是这附近村子里的,来山上挖冬笋。
入冬后,山上常会遇见挖冬笋的人。
妇人很快又钻进了路边的茅草丛,看起来又不像是挖冬笋了——茅草丛里是没有冬笋的。过了片刻,她又从茅草丛里钻出,手里的麻袋还是空空,一无所获。
“你是在挖葛?”妇人返身再次经过我身边时,我问道。
“是的,想挖点葛,没事的时候嚼嚼。”妇人作答。
“这里的葛多是多,就是不好挖。”妇人像是为自己的空麻袋作解释,补上一句,接着问我:“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去那边看看。”我举起一只手,向对面的水杉林指去。
几天前我就来过这里,那时水杉林还像大火一样燃烧着,将半边天空染得彤红。现在,经过催冬雨的浇淋之后,水杉林只在树冠上留着浅浅的锈红。
微弱的、未燃尽的余焰,如同黄昏落日,在天空留下的夕晖。
流淌石头的河谷

流淌石头的河谷
河谷在浦溪河上游,狮子峰下。
进入河谷后,我就变成了羚羊,身边的余君也变成了羚羊,身姿敏捷,善于跳跃,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脚前掌轻轻落下,再躬身一跃,跨过溪流,落在对面的沙地上。
冬天的河谷水流清浅,在石头之间缓步徐行,遇到凹地就蓄成小小的水潭,遇到陡峭处就跌宕而下,从石壁间迸出晶亮的珠花。
河里那么多的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块地垒着,看似凌乱,却保持着默契般的平衡。每块石头都稳当得很,像是经过了一双手的安放。
谁知道呢,或许这山里的东西都经过了一双手的安放,树放在树的位置,藤放在藤的位置,草放在草的位置,就连随风而下的落叶也放在它该落的地方。只不过那双手就像风一样,有形又无形,是人眼所不能看见的。
河谷的石头多为花岗岩,和黄山的峰岩同质。很久以前,它们也曾是黄山群峰的成员,矗立云端,只有第一抹日出之光能够踏足其上。从山峰变成石头,从绝顶之上到峡谷之底,这中间究竟经历过什么?如果石头有记忆,能够开口说话,像泉水那样娓娓道来,就是一部出神入化的《山海经》了。
河谷的石头,无论大小都有着圆弧形的触面。从峰顶到谷底的过程,以及水流年复一年的冲刷,早已磨去石头的棱角。
也有保持着棱角的,黄山玉就是。
黄山玉的另一个名字就叫黄蜡石。黄山的每一道河谷都有黄蜡石。以前——三十年前,黄蜡石在河谷里只是普通的石头。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黄蜡石突然就有了奇石的光环,身价大涨,采者趋之若鹜。
如今河谷里很难找到黄蜡石了——偶尔还是能够见到——当余君在一股很有力道的水流边蹲下,鞠水而饮时发现一块,小小的,刚好握在手心,质感细腻光滑。
余君将石头举在额前,对着正午的阳光,石头温润如脂,发出蜂蜡的色泽。
“真好看,我能把它带走吗?”余君问。
不等我回答,余君又把石头放回河里。
进入河谷后余君一直处于兴奋中,像刚从牢笼解开绳索放出来的麋鹿,甚是欢腾,时不时地发出惊叹,嚷嚷着要把这样那样带回城里,不过很快又改变主意:“算了,也许它们并不想离开,还是让它们安安静静待在原地吧。”
“你怎么知道它们的想法?”我笑。
“正是不知道才不能将他们带走,再说了,带回去也还是搁在角落吃灰。”余君说。
也是,我家里就有几块从河里捡的石头、碎瓷片,捡回去后再也没有仔细看过。对它们一时的兴趣与热情不过是出于占有的欲望。
“那就是菖蒲吧?”余君指着一块巨石的石缝问。
一丛有着细长叶子的植物从石缝里探出来,碧青,葱郁,浑然不知隆冬已至。
是的,菖蒲。
余君弯下腰,用手捋着菖蒲的叶子,又将鼻子凑上去,嗅它的气味。
“好闻吧?”我问。
“好闻,山里的味道都好闻。”余君说道,贪婪地深嗅几口:“真想把这山里的味道做成香水随身带着,想闻的时候就打开。”
“那得制出至少一百种香型”,我说。山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味道,不同时令有不同的味道,黑夜和白天闻起来不一样,正午和傍晚闻起来不一样,下雨前和下雨后闻起来也不一样。
嗯,那就做一个山中岁时的香水系列,就像你的书,每个节气有每个节气的颜色和味道。余君拍了拍她的背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山中岁时》。
一周前见到余君时,她手里就拿着我的《山中岁时》。她说自己原本想找个深山老林独自待一段时间,又不知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在书店遇到我的书后按图索骥来到这里,没想到居然遇见书的作者。
“那天在浦溪河边一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拿着相机走路的样子和书里的照片一个样,我跟在你后面走了好几分钟,心想,喊一声你的名字,如果你回头就没认错。”余君说。
我笑起来:“你没有认错我,我却认错了你,以为你是我高中的同学。”
“怪不得你跟我说好久不见,很奇怪,你笑起来的样子也像我的一个同学,说话声音也像。”
“说不定我们真的同学过,对了,你以前来过黄山吗?”
我将河边林子里摘的野柿子递给余君。野柿子的个头很小,味道却足,一只储满蜜糖的小罐子。
余君说她读大学时来过这里,没有在山下停留,在南大门换乘后直接上了黄山。
黄山太美,美得让人窒息,想从峰顶跳下去。余君伸开手臂,做了一个跳的动作,然后将野柿子的薄皮剥开,塞进嘴里。
余君说的并不夸张,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十八岁那年,学校组织春游,第一次上黄山,在排云亭的绝壁站立,鼓足勇气往下看,瞬间就被深不见底的峡谷之美震慑住,闭上眼睛,又忍不住睁开,耳边一个声音不停怂恿:跳下去,跳下去。
我当然并没有真的跳下去。但我深刻地感受到那种来自深渊的、诱人纵身而下的吸引力。或许正是这种带着磁场的力量,使山岩崩裂,成为坠落河谷的石头。
余君手里又剥开一只柿子,这回没有急着吃,而是数起柿子的果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枚,这么小的柿子居然这么多果核。
是的,我们本地人叫它八角柿,这山上到处都是,鸟儿们冬天的甜点。
余君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下号码,眉头皱起。
接完电话,余君对我说她下午就得回城,这次出来原本请了一个月的假,可公司那边出了点状况,要赶回去处理。
“这果核能发芽吗?”余君摊开手心问。在她的手心里躺着十几枚半月形的果核。
“当然能。”
“那我带回去,种在花盆里。”余君把果核用纸巾包起,放进口袋。
不知什么时候阳光已经移出河谷,两边的树林显得更为幽深。在石头上蹦跳着并不觉得冷,停下来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风的寒意,吹得肩头凉嗖嗖——毕竟是十二月了。
走出河谷,余君又忍不住回头张望。这些石头也在流淌,只是我们觉察不到,她说。
是的,石头也在河谷里流淌,那是另一种时间的流速,近于静止,也近于永恒。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的时间流淌的过于迅速、匆忙,来不及安静下来歇一歇,就到了河流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