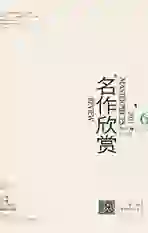太阳史诗的书写与神性空间的召唤
2021-08-03蒋雷
摘 要:海子的诗歌《秋》只有短短六行,五十三个字,却相当晦涩。同一文本下的晦涩和清晰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这股张力使它在三十三年里像“谜”一样被一解再解。诚然,诗歌的创作是一种“灵光乍现”,但其也必然蕴含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本文试从创作阶段的转变和神性空间的召唤来谈谈对《秋》的理解。
关键词:海子 《秋》 神性空间
海子的诗歌《秋》只有短短六行,五十三个字,却相当晦涩。“神”“鹰”“集合”“言语”“王”密集出现,仿佛令人置身于创世神话里的高加索山脉,神秘而庄严。同时,“秋天”“深了”出现三次,再加上“得到的尚未得到”“丧失的早已丧失”,任谁也能感受得到诗歌中那份化不开的浓浓悲凉。同一文本下的晦涩和清晰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这股张力使它在三十三年里像“谜”一样被一解再解。诚然,诗歌的创作是一种“灵光乍现”,但其也必然蕴含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本文试从创作阶段的转变和神性空间的召唤来谈谈对《秋》的理解。
一、创作阶段的转变
一般来说,海子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地乌托邦时期和太阳史诗时期。前者以麦子、土地为主要意象,而后者以天空、太阳为主要意象。两个时期一般以1987年创作完成的《太阳·土地篇》为分界线。当然,海子的诗歌创作极为丰富,这一分期并不能很好地概括,但为了称说方便,本文暂且使用这一分期之说。
1987年之于海子无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月亮、水、南方在海子的诗歌中完全消失,柔情的、温情脉脉的诗歌情调不再,诗歌风格为之大变。实际上,这一转变从1986年就已开始,终于在一年后形成质变,父性的暴烈与死亡的冲动最终构成其创作的大部分命题。正如西川总结的,“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
《秋》同样创作于1987年,从时间维度上,恰巧属于大地乌托邦时期和太阳史诗时期的交汇处。虽然《秋》作为一首抒情短诗,并不能被简单地归入某种创作类型中,但是我们仍能从诗歌末四句探得海子与土地决裂,转而奔向太阳的转变过程中心底的那份悲凉。
“王在写诗”作为整首诗歌的中心点规定了诗歌的“命题走向”,也就是说,整首诗歌可以视为海子自身诗歌创作的一份独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王在写诗”“得到”“丧失”也就有了解释的底本。“王”在海子诗歌中大量出现是在1987年以后,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虽然海子一直将自己视作与神沟通的使者,但是“王”作为一种自我体认与太阳史诗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太阳史诗本身即海子创建的“诗歌王国”。所以“王在写诗”一句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海子在进行太阳史诗创作”的表达,而这一表达显然与后两句的“得到”与“丧失”是紧密联系的。第三个“秋天深了”前的“在这个世界上”正是联结这两部分的通道。这个世界上的“得尚未得,失早已失”既是“王”从神性写作回到人间话语后的哀叹,又是“王在写诗”的根本动因。因此,“得”与“失”成为理解此诗的突破口。
置身于自由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80年代,海子从创作伊始就主动肩负起“重建完整的精神与信仰的历史”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一个衰竭实利的时代,我要为英雄主义作证。这是我的本分。”海子首先试图通过歌咏麦地、乡村来寻找建设永恒的精神家园的可能。这种歌咏不同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寄情山水田园,陶醉于趣味,这正是海子所深深厌恶的。相反,他认为只有人们辛苦地劳作,艰难地生存,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子把拯救大地作为拯救自身、拯救人类的方式,大地独有的神性成全了他,但大地的死亡力量也毁灭了他。“土地,这位母亲/以诗歌的雄辩和血的名义吃下了儿子”,“土地的死亡力 迫害我 形成我的诗歌”……在《太阳·土地篇》里,原本代表着健康、美好人性的土地被贪婪的人类欲望破坏殆尽,“大地乌托邦”也由此被宣布破产。海子终于意识到他精心构筑的精神乡村根本是虚幻的。这也即《秋》一诗中“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虽然土地因为欲望的入侵已经死亡,但是海子并未陷入绝望的虚无之中,他将拯救人类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大书“太阳史诗”上。因此,即使“秋天深了”,土地已一片荒凉,“王”仍在“写诗”。
二、神性空间的召唤
《秋》中最难解也是争议最大的无疑是“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两句。有人认为“鹰”代表了强力和掠夺,而“集合”和“言语”是它们在密谋,因此本该丰收的季节只剩下一片荒芜,而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合理的。
首先,海子在《太阳·土地篇》中宣布了土地的死亡,土地的死亡不是由于侵略者的掠夺,而是由于人类自身,也就是诗中以“情欲老人”“死亡老人”為代表的贪婪堕落的人类欲望。其次,“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神的故乡鹰在言语”背后显然存在一个草原的空间背景。虽然这一地域空间并不是诗人创作当时所置身的,但是草原之于海子有别样的特殊意义,而且这一意义绝对是正向的,海子断不会将掠夺、密谋与这个空间联系起来。
南方乡村和华北平原是海子的主要活动空间,但海子在1988年8月却在《雪》这首诗中将青藏高原称为自己的故乡——“千辛万苦我回到故乡”。由此观之,198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海子选择“海子”作为笔名,已经有了某种宿命的味道(笔者注:在蒙古语中,“海子”意为沙漠中水草丰美的水泽)。1986年,海子第一次去往蒙藏地区。据燎原还原,海子的旅游线路大致为:西宁→青海湖→格尔木→西藏拉萨→格尔木→当今山口→敦煌→祁连山北侧→嘉峪关→额济纳→包头→呼和浩特→北京。这是一次浩瀚的远旅,一次地理文化资源的开掘,更是一次精神的漂泊。当海子循着昌耀、杨炼等人的文化足迹,置身于西北这个广阔空间时,他无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对他的神性召唤。游牧民族原始的生命力、与自然的和谐、对神灵的敬畏,都让海子看到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共存的状态,这也是海子将青藏高原视为自己“精神故乡”的原因。同时,游牧文化所激起的大诗声音也与西方《圣经》《荷马史诗》那样“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暗合,指引着海子的史诗创作。
因此,“神的家中”“神的故乡”并不是泛指自然界,而是指向以青藏高原、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草原。诗一开篇便将环境置于意念中的草原的深秋,基调确是苍凉的,却与草原的神性气息相契合。而“鹰”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带着力量与通灵。“鹰”在海子的诗歌中出现得并不多,但海子自己曾在《诗学:一份提纲》中阐述过“鹰”的独特意义:“鹰是一种原始生动的诗——诗人与鹰合一时代的诗。”“鹰”无疑代表一种原始的力量,而“诗人与鹰”的“合一”也即诗人所说的“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所以“鹰”本身也是一种“诗”。海子怀着大地乌托邦幻灭的绝望在草原上找到了他得以继续前行的资源和方向,那就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力的呼唤建立起“诗歌王国”,以达成追求永恒精神价值的愿望。同时,“鹰”又是通灵的。创世神话中它总是伴神左右,传达神旨。在《秋》这个文本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鹰”是能给海子带来“神启”的使者,它召唤着海子进入神的世界。“鹰”的“集合”与“言语”正是接受神旨和传达神旨的过程。“王在写诗”也意味着“召唤”的成功。
三、结语
《秋》的三部分看似毫无联系,实则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现世的精神困境和“大地乌托邦”的幻灭需要诗人重新寻找建立永恒家园的可能,神性世界的召唤让诗人为自己带上王冠,化原始力量为主体力量,构筑起自身的“诗歌王国”。在构筑过程中,诗人得以有寻回神性的可能。当然,海子的结局证明了太阳史诗拯救人类的不可能,但在《秋》一诗中,海子依然从“尚未”二字里透露出他对这一理想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西川.海子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 燎原.海子评传[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3] 付元峰.海子十读(一)[J]. 名作欣赏,2010(1).
[4] 丛新强.海子诗歌的神性向度[J].理论学刊,2005(5).
[5] 张清华.“在幻象和流放中创造了伟大的诗歌”——海子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8(5).
作 者: 蒋雷,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