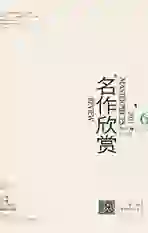《诗·大雅·行苇》主旨流变小考
2021-08-03郎雅涵
摘 要:对《诗经》的注疏古已有之,但受时代背景影响,学者对同一文本往往有不同见解。就《诗·大雅·行苇》而言,其主旨解读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差异。先秦两汉时期至唐普遍采用“忠厚说”,宋至清“忠厚说”与“祭祀说”并行,现当代学者通常认为该诗与祭祀相关,并将其作为研究先秦仪礼的材料,总体上从政治解读趋向就诗论诗。
关键词:《诗·大雅·行苇》 主旨 流变
《行苇》一诗是《诗·大雅·生民之什》的第二篇。《雅》为周王畿之正乐,“言王政之所废兴也”,依照政之小大分为《小雅》与《大雅》,主要反映贵族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雅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赞颂周民族祖先的功绩,一类描绘王公贵族的生活,一类忧虑社会不公、抨击腐败黑暗。《大雅》共31篇,多为西周王室贵族所作,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乃至武王、宣王等之功绩,“曲而有体”,有“文王之德”。《行苇》属于第二种“雅诗”,全诗共三十二句,描写了西周王族祭祀、宴饮的场景。具体诗面如下: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坚,四鍭既均,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鍭。四鍭如树,序宾以不侮。
曾孙维主,酒醴维醽,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
在分章上,毛诗分七章,第一、二章每章六句,第三至第七章每章四句;郑玄《笺》分八章,每章四句;朱熹《诗集传》分四章,每章八句,后世多沿用朱熹的划分方法。整首诗以第一视角记述了一场宴会的始末。第一章从宴会的周边环境入手,以初生苞芽嫩叶的芦苇在路边随风摇曳之景,表现出安乐祥和的气氛;第二章描写宴会场景,众人设席布菜,饮酒奏歌,热闹非凡;第三章转入射艺,宾客挽弓引射,井然有序;第四章以祝酒作结,小辈向长辈敬酒祝福,阖家欢乐,其乐融融。
按时代顺序整理各家之言,能够了解不同时期学者对此诗的解读倾向,进而可结合社会背景分析产生不同解读的原因。
关于此诗的评论最早可见于《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这出自左丘明记述完周郑交质这一历史事件后所做的评价。平王东迁后,郑国与东周交好,但因后期周平王宠信他人,双方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了郑庄公与周平王交换人质一事。左丘明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缺乏信任和礼教约束,《诗》中本有彰显忠义诚信的《行苇》等诗,双方却弃置不用,以此暗示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虽然该评价对《行苇》的主旨一带而过,但仍可以看出此诗代表统治者“忠信”的说法为当时所认同。
先秦時期尚未出现“文体”“纯文学”等概念,解《诗》常常从实用角度出发,甚至跳开文本,赋予其各种政治、礼法含义。例如孔子整编《诗》篇以正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为《诗》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首先可以激发个人志气,促进人生的兴起,扩展至社会人群后,便能发挥观察政教风俗盛衰、协调社会人群关系、讽刺怨谏弊政败俗等功能。战国中晚期,《诗》文本出现亡佚、散乱、讹错等现象,使《诗》义不足凭信。即使是一贯尊崇上古的儒家也有“《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和“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等诘问和看法。这使《诗》面临着严峻的存废问题。新的历史环境下,荀子延续孔子的正乐事业,用礼来规范《诗》义,使其升华为先王之道、圣人之道,而《诗》的文本也相应地升格为“经”,逐渐具有教化作用:“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大雅》之所以为大者,取是而光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汉代的《诗经》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后期的教化意义,对其注疏具体分化为今古两派。
今文经学方面,刘向《列女传·晋弓工妻》“君闻昔者公刘之行,羊牛践葭苇,恻然为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于天下”,王符《潜夫论·德化》“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践履生草,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边议》“公刘仁德,广被行苇,况含血之人,己同类乎”,班彪《北征赋》“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赵晔《吴越春秋》“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等言,主要侧重公刘的个人仁德,均从政治高度进行解读。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仁及草木”等言显然属于夸大其词,即便是“忠厚仁德”之说也难觅其迹,从内容上看更偏重记述宴会祥和欢乐之景。然而在先秦两汉时期,“诗以言志”之思想深入人心,学者在解读诗歌时习惯性地将其与政治相联系亦不足为怪。《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也有赵文子对叔向明确提出“诗以言志”的记载,且此处《左传》中所言之“诗”并非自行创作,而是《诗经》中现成的诗篇。其他非儒家典籍中也有关于“诗”与“志”的论述,例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言“《诗》言是其志也”。两汉时期的儒者尊崇上古,通常会完全按照《左传》《孔子诗论》等典籍的记载解释《诗经》。
古文经学说方面,《诗大序》在继承了前代诗言志之说的同时非常重视诗与政教的联系,认为诗歌反映了国家政治、社会状况,进而引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总结之辞。郑玄在《诗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又于《笺》言“敦敦然道旁之苇,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伤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王为此爱之,况于人乎”,完全延续《左传》的“忠信说”。在《诗谱》中,郑玄将《行苇》列为“正雅”,这种正变说反映了汉儒将作品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但《诗大序》和汉儒对于《诗经》中作品的阐释注重诗的功利性,“要求诗歌为政教服务……不可避免地把大量实际与政治并无关联的作品,牵强地与史实相比附”a,不免有过度解读之嫌。同理,《毛传》之训释由于去古未远,所解内容当偏向原意,“然而由于它尊王美王的诗用观所形成的思维定式, 解诗从美教化出发”b,则难免流于形式,于具体诗歌主旨有所忽视。
汉儒两派的解读均存在功利色彩,注重《诗经》的“兴”,以断章取义、取予所求的方法重建其与政教的关联。在《行苇》一诗中,他们紧抓“牛羊勿践履”这一片面的物象来申发忠厚之德,将其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做政教的比附,却未兼顾诗面本身的意思。
两汉学者的注疏影响着后代对此诗主旨的研究。《三国志·魏书(十九)》“盖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恶终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则《行苇》之诗作”,唐代李华的“属时清无狱,朝尚宽政,《行苇》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恺悌流乎颂声”,都延续着彼时的忠厚仁德之解读。
宋代学者们对《行苇》的解读态度有所变化。段昌武《毛诗集解》依旧持“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之说,而郑樵《诗辨妄》称“《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朱熹在《诗集传》(卷十七)中表示不从《行苇》之诗的《小序》。他首先反驳《毛诗》的章节划分,认为“《毛》首章以四句兴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协韵;《郑》首章有起兴而无所兴,皆误,今正之如此”,进而提出“疑此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故言敦彼行苇,而牛羊勿践履,则方苞方体,而叶泥泥矣”的说法。虽然只是推测,但其已开始怀疑《行苇》实际有关祭祀,主要表现祭祀后的宴会之乐。
受疑经惑古、以义理解经之思潮的影响,宋儒逐渐建立起一套有别于汉唐传注之学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不再全盘迷信前代的“权威”著作,甚至对《毛诗序》、郑《笺》、孔《疏》等进行了激烈批判。当然矫枉常常过正,郑樵之说就难免有为怀疑而怀疑之嫌,且以己意解释《诗经》亦容易产生新的偏颇和失真。就《行苇》一诗而言,朱熹的解读较为中肯。在他看来,首章“言其开燕设席之初”,二章“言侍御献酬饮食歌乐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乐也”,四章为“颂祷之辞,欲其饮此酒而得老寿”。与此同时,朱熹在其《诗序辨说》中认为“《毛诗》内容谬戾的认识论原因有二:不明于诗和不通于理。方法论上原因有三:一,随文生意;二,强就美刺;三,以史说诗”。虽然疑古,但他仍能保持相对客观的学术态度。
宋儒的“祭祀说”显然是综合《行苇》全诗得出的结论。宋学能够反对汉学,基于彼时诗经学领域的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欧阳修著《诗本义》,辨郑《笺》、孔《疏》,反对汉儒单纯根据某个物象来取义的观点,确立了“据文求义”的研究方式,从而帮助宋儒走出断章取义,联系诗歌全文来还原诗意。后苏辙《诗集传》始疑《小序》,存首句而弃其余,动摇了《小序》的权威地位,对解《诗》释《诗》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宋儒提出“兴不取义”的观点,即物象之兴与后文并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此一来,汉儒的兴义解说便显得过于夸大其词了。
清代的解说基本承续宋儒而来,更加重视《行苇》的礼文化解读。清初姚际恒言:“《集传》谓父兄所以答《行苇》,《行苇》既未必为祭诗,又何答也?且后数章皆从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谢答之辞也,此祀宗庙礼成,备述神嘏之诗。”他既不赞同两汉的“忠厚说”,也不认可朱熹的“祭诗说”,而是另辟蹊径,认为此诗应该是在陈述神的赐福。但从“宗庙礼成”来看,姚际恒并不否认此诗有关祭祀。他所著的《诗经通论》力图“寻绎文义,辨别前说”,摆脱汉、宋门户之见,从诗的文本出发探求意旨。乾隆年间的胡承珙提出,“案此诗(《行苇》)章首即言亲戚兄弟,自是王与族燕之礼,与凡燕群臣国宾者不同。然所言献酢之仪,肴馔之物,音乐之事,皆与《仪礼·燕礼》有合。则其因燕(宴)而射,亦如《燕礼》所云,若射则大射正为司射,是也……《序》以睦族为内,养老为外,盖由养九族之老而推广言之,以见周家忠厚之至耳。”该解读结尾虽回归先秦之“忠信说”,但已经开始从文本本身进行解读,辅以对当时射礼等礼仪制度的考证,认为所谓“忠厚”只是针对西周族人本身,而非所谓“仁及草木”“广被行苇”。但晚清学者唐晏坚持仁德之论:“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犹感德。”从宋至清,传统的“忠厚说”与新起的“祭祀说”各执一词,成为解读《行苇》的两个方向。
自近代至当代,学者们就《行苇》一诗的主旨基本达成一致,即此诗与祭祀有关,表现了西周王族的宴饮之乐。马其昶言:“李光地……又云雅有《行苇》《泂酌》,分明是说祭祀。”杨钟羲以为:“《行苇》兼存践履慈,茁葭漫赋春田美。圣神举动殊寻常,此事悠悠古谁比?”潘雁飞则通过此诗研究西周的射礼,盖“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故,传统“周家仁德”的解释被摒弃,为学者们祛除过多的政治意义,从文本进行解读提供了环境。
总体来看,对《行苇》一诗的解读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由于不同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诉求有所不同,学者根据新的文化语境赋予《行苇》新的思想主题,对其认识亦有不同。先秦两汉时期从忠信仁德的角度解诗,辅以“诗言志”的政教观念,及至唐朝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宋朝受疑古思潮影响,“祭祀诗”之论兴起,逐渐与“忠厚说”分庭抗礼,延续至清。近代起基本抛弃“忠厚说”,从祭祀角度理解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注解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日趋重视对诗歌本身内容的研究,即站在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立场上,得出更符合诗歌原意的结论。
综上所述,在解读《诗经》时,不但要了解“诗以言志”的时代背景和各篇所属类别的总体特点,也应该回归诗的内容本身,去审视典籍记载内容的合理性,从而得出更恰当的结论。推而广之,在解读古代经典时,一要通读文本,如果从文面能说通,则无须附加多余的政治内容,反显累赘;二要考察前人注解是否合理;三要契合相关文化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以尊重、平视的姿态去研究典籍,既可知人论世,又不掩盖文本原意,将时代的普遍性与作品的特殊性相结合,对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a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40页。
b 潘雁飞:《一种训诂、一种礼制和一章诗的意味——〈诗经·大雅·行苇〉“四鍭如树”新释》,《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5期,第122页。
参考文献:
[1] 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M].孔祥军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9
[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20
[6]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邵炳军主编.今文尚书文系年注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李华.李遐叔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0] 郑樵.诗辨妄[M].上海:朴社,1933.
[11] 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研究[D].浙江大学,2008.
[13] 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4] 胡承珙.毛诗后笺[M].合肥:黄山书社,2014.
[15]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马其昶.诗毛氏学[M].安徽:力行书局,1970.
[17] 杨钟羲.雪桥诗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作 者: 郎雅涵,上海大学在读本科生。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