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重要争议性字词考辨(三)
2021-08-02汪韶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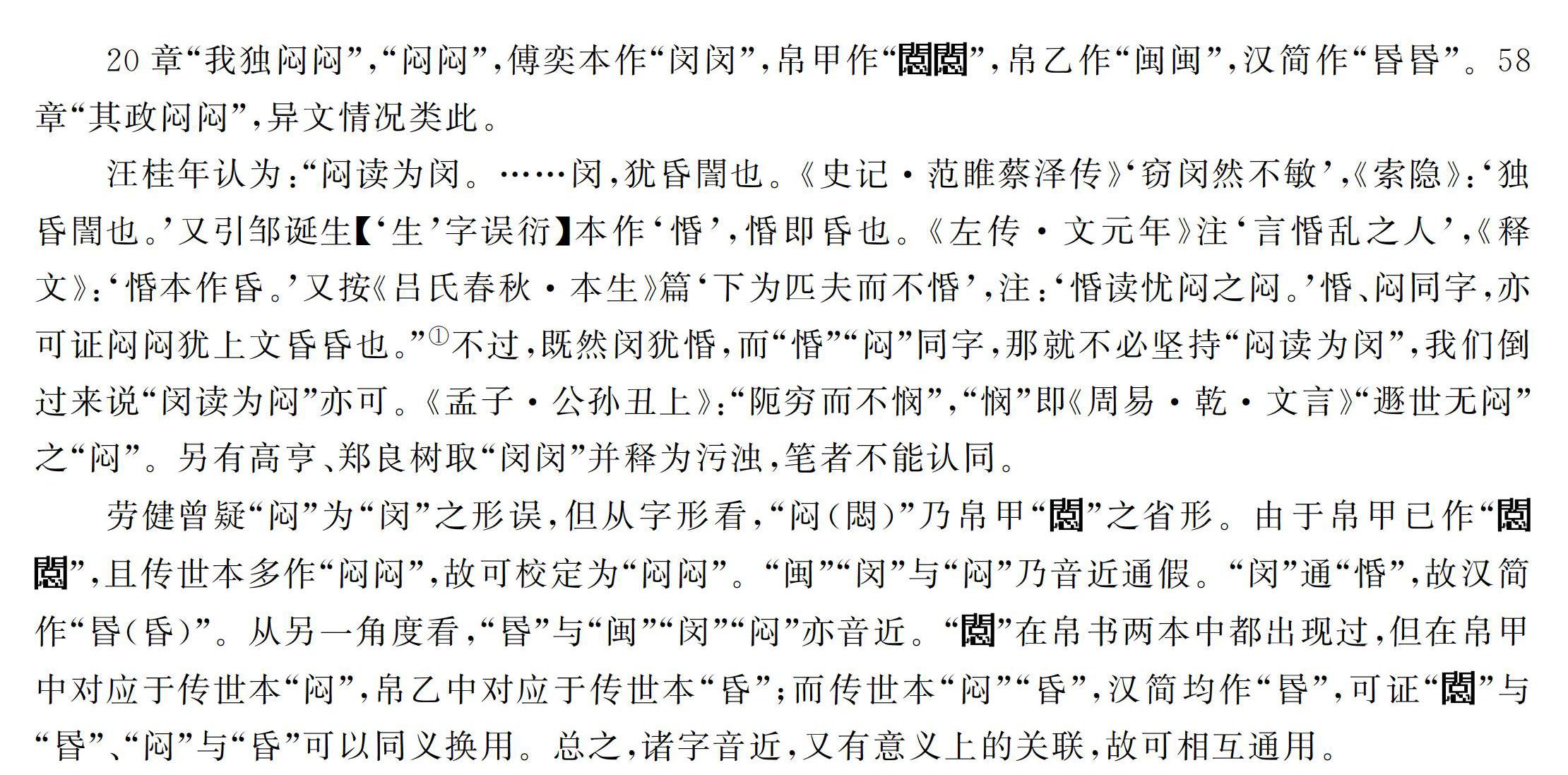
[摘 要]古今的《老子》诠释似乎陷入到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诠释学的无政府主义”窘境。但通过对地上地下几个重要版本的对勘,可获取更为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择取一些争议性字词进行考辨,以确定“此其不善已”“高下之相呈也”“有弗盈”“挻埴”“沕芒”“蠢蠢呵”“未孩”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关键词]《老子》;争议性字词;简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可能的《老子》——文本对勘与思想探原(道篇)”(16FZX004)。
[作者简介]汪韶军(1973-),男,哲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口 570228)。
九、此、訾、斯
2章传世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被普遍理解为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表示美与丑、善与不善相对峙相依存。这其实是误读,而误读与版本异文的识断有一定关系。为直观起见,笔者将几个主要版本中的这两句逐字纵向对齐,排列如下(“传世”代表古今流传的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乃至敦煌五千文本,末行为笔者校订结果):
楚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 恶已皆知善 此其不善已
帛甲:天下皆知美 为美 恶已皆知善 訾 不善矣
帛乙: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恶已皆知善 斯 不善矣
汉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 不善矣
传世: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 不善已
订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恶已皆知善 此其不善已
“已”通“矣”,句尾语气助词。帛甲“訾不善矣”,整理者原据帛乙释为“斯不善矣”,疑非。“訾”从言,此声,当为“此”之音借,楚简正作“此”。楚简“此其不善已”,廖名春认为“其”的本字是“斯”,意为“则”
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非是。“其”就是本字,它在这里的作用是加强语气。此处《老子》祖本本无“斯”,后来有它,是“此”被替换成同义词“斯”,然后以为“其”字衍而删之(“其”“斯”形近)。加工者继而将前句“恶已”补为“斯恶已”,以便与“斯不善已”一律;又将“皆知善”补为“皆知善之为善”(“之为善”本是蒙上文“皆知美之为美”而省),于是本来错落有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变为整齐对仗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文本是整齐了,文义却变得隐晦且易生歧解,这种“改善”是需要避免的。
一○、呈、浧、盈、顷、倾
2章王弼本“高下相倾”,“相倾”,传世本皆如此;汉简作“相顷”,属同音假借。但帛书两本皆作“相盈”,整理者认为:“盈,假为呈或逞,呈现。”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3页。楚简作“相浧”,廖名春也读为“相呈”:“《老子》原本当作‘呈,楚简繁化增加水旁,写成‘浧。‘盈、‘呈古音相近,帛书甲、乙本‘盈乃‘呈之借字。”
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第167页。陈徽则批评如此释读乃“以今昧古”。
陈徽:《老子新校释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今按,楚简本无“盈”,而“浧”共出现4次,其他三处(9章“持而浧之”“金玉浧室”、45章“大浧若中”)皆通“盈”,这就能解释何以本章楚简本为“相浧”,到了帛书本那里变成了“相盈”。不过,此处“相浧”“相盈”确宜读为“相呈”。15章末尾“不欲盈”,“盈”在楚简中就作“呈”,说明“呈”“浧”互通,故“呈”亦可假为“盈”。另从语义角度看,“相盈”“相顷(倾)”有点令人费解,而“相呈”意同其前“长短之相形也”之“相形”,互见也,于义为佳。早在楚简本出土之前,帛书整理者即指出帛书“盈”乃“呈”之借字,颇为有见。
一一、有、又、或、久
4章河上公本“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或不盈”,帛乙与汉简作“有弗盈”,五千文本与傅本作“又不盈”。关于“有”“又”“或”三字之异同,清末易顺鼎做过如下辨析:“古‘或字通作‘有,‘有字通作‘又,三字義本相同。……窃谓王本作‘又,河上本作‘或。王注云:‘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足证王本作‘又无疑。《淮南·道应训》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文子·微明》篇亦云:‘道冲而用之又不满也。此皆作‘又之证。又《御览》三百二十二引《墨子》曰:‘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是古本一作‘有弗盈矣。”
易顺鼎:《读老札记》卷上,清光绪甲申秋程颂藩署首。
易氏辨析甚精。《老子》祖本当作“有弗盈”,后世诸本或作“又不盈”,或作“或不盈”。王弼本貌似亦作“或不盈”,但据王注可知,王氏所见应是“又不盈”。王本作“或”者,乃有人据河上公本误改。另有俞樾、罗振玉、马叙伦、朱谦之认为当作“久不盈”,经查,那是因为唐景龙碑本“又”字比较模糊而被严可均误认作“久”,之后此误被俞樾等人延续了下来。
一二、湍、揣、耑攴、扌短、梪
9章“揣而锐之”,传世本多如此,傅奕本“揣”作“耑攴
”,楚简本作“湍”,帛甲残,帛乙作“耑攴”,汉简作“梪”。
究竟孰为本字?徐梵澄读“扌短”为“抟”(结聚),魏启鹏、赵建伟、邓各泉读“湍”为“抟”,李先耕读“湍”为“端”(使……尖锐)。诸说皆非。今以字义衡之,凡字形中有“豆”者,皆不可读如字。2章楚简“耑”,它本皆作“短”,可证此处帛乙“扌短”即“揣”,而汉简“梪”盖“扌短”之省形。从“耑”诸字中,“湍”明显不可读如字。本字当作“揣”,“湍”“耑攴”皆其借字。《说文·攴部》:“攴,小击也。”“攴”从“(手)”,故“耑攴”“揣”实为一字。
揣,初委切,其意盖为捶打、锻击。清人孙诒让指出:“此‘揣字当读为‘捶,王云‘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即谓捶锻钩针使之尖锐。……《说文·手部》云:‘揣,量也。一曰捶之。盖‘揣与‘捶声转字通也。”
孙诒让:《札迻》,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28-129页。奚侗亦云:“《广雅·释诂三》:‘捶,击也。《庄子·知北游》篇‘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释文》引或说云:‘江东三魏之间,人皆谓锻为捶。此‘揣亦训‘捶,即锻击谊。”
奚侗:《老子集解》上卷,严灵峰辑:《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
一三、、允、锐、棁、捝、悦
“揣而△之”,△处有如上诸异。关于△的字形演变,有两种相反的看法:其一,赵建伟、李零、刘信芳、韩禄伯倾向于本字为“羣”,因音近而写作“允”,又因形近而讹为“兑”,之后就有了“锐”“捝”“棁”“悦”。比如赵建伟说:“‘羣是积聚众多之义。帛书‘允字为简本‘羣字之音假(允、羣皆为文部字);今本‘锐又为‘允之形讹(《书·顾命》‘执锐,《说文》引作‘执鈗)。”
赵建伟:《郭店竹简〈老子〉校释》,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3页。其二,廖名春、聂中庆、郑良树认为本字从“兑”(“锐”之借字,捝、棁、悦皆为“锐”之别字),因形近而误作“允”,又因音近而写作“羣”。其中廖名春论此最详,其言曰:“楚简‘
字即‘羣字,从羊,从尹即君省。王存乂《切韵》‘羣正作‘。‘尹古音与‘允同,而从‘允之字与从‘兑之字可通用。……《集韵·狝韵》:‘抁,动也,揣也。或从捝。王弼本《老子》第56章:‘挫其锐。楚简‘锐作‘,上部为‘金之省文,下从两‘尹。下从两‘尹与下从两‘允同,而‘允、‘兑形近,从‘兑之字与从‘允常混,故下从两‘允实即下从两‘兑,其字当作‘。是‘尹、‘允、‘兑相通之证。由此可知,‘、‘允与‘棁、‘捝一样,皆为‘锐之借字,故书当作‘锐。”
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释》,第364页。
我们从文义角度来对二说做一裁断。作“允”无义,故应考虑“羣”“锐”何者能与“揣”形成意义上的关联。“揣”既然意为捶打、锻击,则与“锐”能形成意义上的勾连,故此句仍应读为“揣而锐之”。“锐”,古人多写作“”,“兑”则写作“兊”,脱上方之“儿”,即成“允”,可惜诸贤似均未意识到这一关捩。此处的文本演变应该是:兊→允→羣,而“锐”“捝”“棁”“悦”皆从“兑”。
唐代成玄英一说亦有理,其言曰:“揣,磨也。锐,利也。夫揣剑磨刀,虽利必损,况励己陵物,宁不困乎?”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393页。“揣而锐之”与56章“挫其锐”一正一反。既然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则当自挫其锐(圭角、锋芒)矣。
另有司马光、胥六虚、何道全、憨山德清、邓晅、张其淦等多人理解为尖头利脑之人专事揣度,锐意钻营,比如明末德清说:“揣,揣摩。锐,精其智思。如苏、张善揣摩之术者是也。谓世人以智巧自处,恃其善于揣摩,而更益其精锐之思,用智以取功名,进进而不已。老子谓虽是善能揣摩,毕竟不可长保。如苏、张纵横之术,彼此相诈,不旋踵而身死名灭,此盖揣锐之验也。”
德清:《老子道德经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45页。此说貌似有理,《孟子·尽心上》就说过:“其进锐者,其退速。”但此说未顾及此处“锐”显然是使动用法,故其释义有违经文本义。
一四、、、挻、埏
11章传世本“埏埴以为器”,首字帛甲作“”(整理者直接读为“然”),帛乙作“”,汉简作“挻”。
关于此字,多数人未做辨析便继续袭用“埏”。
由于古今有个别版本作“挻”,奚侗、劳健、朱谦之、李水海、辛战军等人从之。比如劳健认为,“《说文》:‘挻,长也,从手从延。会意。……范与开元石刻皆如《释文》从手不从土,是也。他本多误从土作‘埏。”
劳健:《老子古本考》卷上,见《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朱谦之找到了更多文例:“《字林》:‘挻,柔也,今字作揉。朱骏声曰:‘凡柔和之物,引之使长,抟之使短,可折可合,可方可圆,谓之挻。王念孙曰:‘……《淮南·精神篇》:“譬犹陶人之克挻埴也。”萧该引许慎注曰:“挻,揉也。”《齐策》:“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为人。””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马叙伦、石田羊一郎、蒋锡昌则进一步认为“挻”是“抟”之借字。
王垶、梁海明、戴维取“然”,理解为“燃”(燃火以烧烤土坯),比如王垶说:“只有经过‘然才能成为‘器。(《乙本》作‘,虽误,但也证明这个字义是火烧土。)”
王垶:《老子新编校释》,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162页。黄钊、郑良树则疑“然”“”借为“扌然”。
笔者以为,在现有文字能够顺通文意的情况下,不应考虑通假现象,这就排除了借为“抟”“捻”的可能性。笔者最终取“挻”,理由如下:其一,以帛乙为例,“△埴而为器”与“有埴器之用也”相对,说明“△埴”应是埴器未成形以前的工序,而烧制是成形以后的工序,故△不宜作“”或“”。其二,《管子·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通“埏”,故“埏”似为陶范。而从手之“挻”可与“埴”构成动宾结构。其三,取“挻”也有版本依据。属河上公本一系的敦煌写卷S.477、唐开元石刻、南宋范应元所据古本作“挻”。另据唐初陆德明的记载,王弼本其实也作“挻”。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6页。今又添汉简本这一新证。
综上,笔者以為本字当作“挻”,“埏”乃假借,或涉“埴”字而误从“土”。也有可能是,“挻”音山,“埏”“”“”皆音近借字。
一五、沕望、沕芒、芴芒、惚恍、忽怳
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常令我们困惑不已。而“惚恍”一词在不同版本的《老子》中存在着大量异文。笔者统计发现,与“惚”相应的有“忽”“沕”“芴”“没”“昧”与“恍”相应的有“怳”“慌”“荒”“莽”“芒”“言亡”“望”,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为便于比对,现将诸异文整理为下表:
由此表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忽”“沕”“芴”“惚”皆“勿”声,音同相假。其二,“望”“芒”“言亡”“莽”“荒”“慌”“怳”“恍”亦皆音近相假,其义则要扣住具体语境讲。其三,多个版本存在不同字并用的情形,比如帛乙“忽”与“沕”,汉简“芒”与“言亡”,五千本“忽”与“惚”、“恍”与“慌”,王弼本“忽”与“惚”等,表明古人用字不拘偏旁,通假比较随意。上述字通过音、形、义辗转相假,具体情况可能如下:
昧←没←沕→芴、惚、忽
望←芒→言亡、莽→荒、慌→怳、恍
我们理解时,需要抓出本字。汉简整理者主张读为“惚恍”或“忽恍”,这也是多数人的做法。笔者则以为,本字宜作“沕芒”。“沕”有潜藏义,义近“没”(本义为入水而不见)。《玉篇·水部》:“沕,没也。”16章“没身不殆”,帛甲便作“沕身不殆”。“芒”者,混沌芒昧也。《庄子·至乐》:“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天下》篇:“芒乎何之?忽乎何适?”“沕芒”,二字皆为暗昧不明义,正是承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而言。而以往一直沿用的“惚恍”易使人误解为若有若无、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刘小龙即如此:“‘忽为‘灭,‘恍为‘现,‘忽与‘恍连用,则为表示‘若无若有,若隐若现的状态。”
刘小龙:《老子原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一六、保、葆、抱、服
15章传世本“保此道者不欲盈”,“保”,帛书两本作“葆”,汉简作“抱”,《文子·九守》《淮南子·道应训》却引作“服”。汪桂年解释道:“《淮南子》引‘保作‘服,‘服亦执持之义。《国语·吴语》:‘应中(当作‘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注:‘服,执也。‘服、‘保双声,又为之出旁转,故可同义通假也。”汪桂年:《老子通诂》,《北强月刊》国学专号,1935年。括号内文字乃笔者随文附注,下同。廖名春也认为“服”因义近得与“保”通用。
今按,“葆”“抱”显为“保”之音假。《文子》《淮南子》引作“服”者,盖因“抱”古通“捊”,进而因音同而讹为“服”。《说文·手部》:“捊,……从手,孚声。……(抱),捊或从包。”段注:“古音孚声、包声同在三部。”
一七、、晐、咳、孩
20章河上公本“如婴儿之未孩”,“未孩”,传世本中有作“未咳”,帛乙同,帛甲残,汉简作“未咳”。这是《老子》中理解上的一个难点。我们先来看看几种解读:
孩:通“咳”。《说文》:“咳,小儿笑也。”人见可欲之外物会以笑表示喜欢,但初生的婴儿不知外物之可欲、可乐,故视外物如无物而不笑。鄢圣华:《老子旨归》,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训为如婴儿之未笑,俚浅无谓。若读孩如字,“如婴儿之未孩”,婴儿岂不可称孩乎。至圣人皆孩之,尤为不辞。按古从亥从其之字,每音近字通……咳期迭韵,应读作如婴儿之未期,言婴儿尚未期年,天真未漓也。
于省吾:《老子新证》,《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如婴儿之未孩”的“孩”当读为“骸”,训为“骨”。……婴儿在母体中尚未长出骨头也即还没有发育成“人”形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无知无觉、混沌蒙昧的状态,这显然也更为符合老子所要比拟的“未兆”之态。
侯乃峰:《〈老子〉“如婴儿之未孩”解》,《第二十三届全国医古文研究学术交流会论文集》,2014年,第175页。
“孩”当读为“”,意为动,“婴儿之未孩”是说腹内婴儿尚未胎动,《老子》是用这种人尽皆知的胎动现象发生前的所谓“静止”之态去喻释圣人“泊”而“未兆”之态的。王凯博:《〈老子〉“婴儿之未孩”解》,《语言研究》2017年第2期。
古今多照着“未咳”理解为婴儿还没学会笑,就像鄢圣华那样,非是。但于省吾读为“未期(尚未期年)”,侯乃峰读为“未骸(未长出骸骨)”,王凯博读为“未(尚未胎动)”,则偏离甚远。另有史杰鹏读为“未荄”,“荄”有萌生、开始义,由此进一步联想到胚胎,最终解释成“就像婴儿还未成胚胎”。
史杰鹏:《也谈〈老子〉“婴儿之未孩”之“孩”》,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16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6-51页。这也是联想成分居多,且在婴儿未生之前做文章,不可取。
今按,《说文·口部》:“咳,小儿笑也。从口,亥声。孩,古文咳,从子。”观此可知,“咳”“孩”本一字。《颜氏家训·教子》:“子生咳口是”,“咳口是”即“孩提”。后人始分“咳”为笑貌、“孩”指婴孩。
“未孩”指尚未成长为孩童。南宋林希逸曰:“婴,方生也。孩,稍长也。婴儿之心,全无知识。”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元代何心山则明确指出:“如婴儿初生,未至于孩。”
《道藏》第1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第562页。其实《庄子·天运》已有提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不至乎孩”即“未孩”,喻纯而又纯的婴儿心境。大田敦、许抗生、王博曾引此为证,甚是。
因此,我们不能把“未孩”读成“未咳”,而要反过来将“未咳”理解为“未孩”。汉简“詧”音“该”,当是“咳”之形讹。49章有类似现象,河上公本“圣人皆孩之”,“孩之”,帛甲、傅奕本作“咳之”,帛乙残,汉简作“晐之”。“咳之”亦当读作“孩之”,而汉简“晐”乃“咳”之形误。
一八、蠢蠢、湷湷、屯屯、沌沌、纯纯
20章传世本“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沌沌”,五千文本作“纯纯”,汉简作“屯屯”,帛甲、帛乙分别作“蠢蠢”“湷湷”。
“沌沌”,其意当是浑沌无知。奚侗指出:“‘沌沌,愚无知也。《庄子·齐物论》篇‘圣人愚芚,司马本作‘沌。”
奚侗:《老子集解》上卷,平灵峰辑:《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纯纯”“屯屯”乃“沌沌”之借字。毕沅、朱谦之曾执于“纯纯”而否定其余,非是。帛乙“湷”,古通“浑”,15章帛乙就有“湷呵其若浊”。笔者依帛甲取“蠢”,正与前文“愚人之心”相契。从下文亦可知,老子反对昭昭察察,而独守于昏昏闷闷,宁愿做一个七窍未凿的“傻子”“混蛋”。
一九、察察、詧詧、蔡蔡、计计
20章“俗人察察”,“察察”,帛乙同,帛甲作“蔡蔡”,汉简作“计计”,傅奕本作“詧詧”。58章“其政察察”,异文情况类此。
今按,本字当作“察察”。《说文·宀部》:“察,覆审也。从宀,祭声。”段注:“察与覈同意。《释训》曰:‘明明,斤斤,察也。从宀者,取覆而审之。从祭为声,亦取祭必详察之意。”《春秋繁露·祭义》:“祭者,察也。”帛甲“蔡蔡”乃音近而成为“察察”之借字,或因形近而讹(58章帛甲则直作“亓正察察”)。傅本“詧詧”即“察察”,《玉篇·言部》:“詧与察同。”汉简作“计计”,是因为“计”有“察”义。《管子·八观》:“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高亨释曰:“众人察察,我独闵闵,言众人皆清我独浊也。意各相对。《尔雅·释言》:‘察,清也。是察有清洁之义之证。”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第49页。笔者则以为,察虽有清义,此处宜释为明察秋毫之察。贾谊《新书·道术》:“纤微皆审谓之察,反察为旄(疑通‘眊)。”结合《庄子》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骈拇》篇云:“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离朱是先秦的一个传说人物,又作离娄,据说能察毫末于百步之外。察察属骈于明者,在道家那里,此乃多骈旁枝之道,爚乱天下者也。道家不是嫌人不够明察,而是嫌人太能明察。又《胠箧》篇:“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明察之明非但不是道家心目中的明,反而是有待捐弃的一个对象。
二○、闷闷、、、闽闽、闵闵、昬昬
20章“我独闷闷”,“闷闷”,傅奕本作“闵闵”,帛甲作“”,帛乙作“闽闽”,汉简作“昬昬”。58章“其政闷闷”,异文情况类此。
汪桂年认为:“闷读为闵。……闵,犹昏誾也。《史记·范睢蔡泽传》‘窃闵然不敏,《索隐》:‘独昏誾也。又引邹诞生【‘生字误衍】本作‘惛,惛即昏也。《左传·文元年》注‘言惛乱之人,《释文》:‘惛本作昏。又按《吕氏春秋·本生》篇‘下为匹夫而不惛,注:‘惛读忧闷之闷。惛、闷同字,亦可证闷闷犹上文昏昏也。”
汪桂年:《老子通诂》,《北强月刊》国学专号,1935年。不过,既然闵犹惛,而“惛”“闷”同字,那就不必坚持“闷读为闵”,我们倒过来说“闵读为闷”亦可。《孟子·公孙丑上》:“阨穷而不悯”,“悯”即《周易·乾·文言》“遯世无闷”之“闷”。另有高亨、郑良树取“闵闵”并释为污浊,笔者不能认同。
劳健曾疑“闷”为“闵”之形误,但从字形看,“闷(悶)”乃帛甲“”之省形。由于帛甲已作“”,且传世本多作“闷闷”,故可校定为“闷闷”。“闽”“闵”与“闷”乃音近通假。“闵”通“惛”,故汉简作“昬(昏)”。从另一角度看,“昬”与“闽”“闵”“闷”亦音近。“”在帛书两本中都出现过,但在帛甲中对应于传世本“闷”,帛乙中对应于传世本“昏”;而传世本“闷”“昏”,汉简均作“昬”,可证“与“昬”、“闷”与“昏”可以同义换用。总之,诸字音近,又有意义上的關联,故可相互通用。
《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意为隐藏。倘若个体时时处在他人“察察”之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从人我关系看,察察一方对他者不够信任并缺乏包容精神,另一方则在火眼金睛般的审视之下活得很不自在甚至动辄得咎。如果施之于政(58章“其政察察”即用于为政),又会造成什么后果?金代李霖对此体会甚深,其言曰:“小明为昭,不明为昏。察察,苛细也。闷闷,宽大也。流俗之人,务学作智,察见细微,智料隐匿,以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绝学之人,体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别,故若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意以从政,则察察然苛细矣,所谓人太察则无徒也。推若昏之意以从政,则闷闷然宽大矣,所谓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也。”
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道藏》第13册,第8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