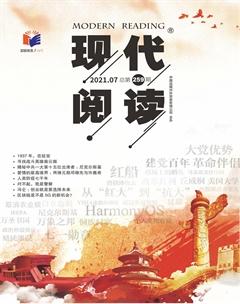爱情的最高境界:两弹元勋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
2021-07-28


和平岁月未居安,一线奔波为核弹。
健康生命全不顾,牛郎织女到终年。
酷爱生活似顽童,浩瀚胸怀比草原。
手挽左右成集体,尊上爱下好中坚。
铸成大业入史册,深沉情爱留人间。
世上之人谁无死,精忠报国重天山。
——杜祥琬院士悼念邓稼先
70多年前,随着日本广岛、长崎的一声声巨响,日本被迫宣布战败投降,两城瓦砾遍地。广岛、长崎的一朵朵蘑菇云,标志着世界进入核时代,各国暗自角力。而美国则在核时代的大潮流中抢得先机,拥有了大国所必备的重器。
邓小平曾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重器在一个大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器不仅是国家武力的象征,更是国家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第七舰队悍然进入台湾海峡,妄图阻止中国统一的步伐。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企图故伎重演,多次密谋使用核武器对中国核讹诈,核战争一触即发。新中国成立初期恶劣的国际环境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处于核大国的巨大威胁下。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明白:既然美国敌视的局面无法改变,“以核制核”就是唯一有效的自卫途径。大批的留美知识分子也十分清楚,中国在科技上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们在思索自己能够为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带来什么,也深知核科技对于新中国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上述复杂背景下,为了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中央果断地作出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在短时间内突破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究其原因,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众多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筑起了新中国精神上的钢铁长城,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的支撑下奋发有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1945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至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1950年10月到中科院工作。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邓稼先带领几十个大学生进行研制核武器的工作。在其后的28年里,邓稼先为中国的核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热忱。由于常年的辛勤劳作和核辐射的影响,1986年,邓稼先因癌症去世,享年62岁。
他愿意为了国家的核事业放弃在美国的优越条件,离开自己的妻儿老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大漠之中的核基地,甚至最后因为核辐射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使他功成名就、青史留名。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经说过,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困难的时候,有种力量,什么坎儿都能过去!这样的爱情宣言虽然不像经典爱情故事里那般轰轰烈烈,但是这样朴实无华的语言也令我们心生敬佩。他们的爱情故事烙上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印记,两人28年的爱情故事见证了邓稼先舍小家为大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这种奉献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坚定的理想信念。
“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你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
“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这是1958年8月邓稼先在接受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后回到家中与妻子许鹿希的一段对话。在接受任务之前,邓稼先向组织保证,绝对会保证工作秘密,不向家人透露一字一句。妻子虽然不知道丈夫到底要去做什么,但那句“为它死了也值得”所蕴含的坚定信念让妻子认为这必定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
一句“我支持你”道出了许鹿希的坚毅和对丈夫工作的支持。此后,许鹿希便默默地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两个年幼的孩子、体弱多病的双亲、单位的工作全部压在她身上。当然,许鹿希要承担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内心的煎熬与等待,对于丈夫的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对于丈夫的工作地点一无所知,甚至连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成为夫妻间的奢望。
此外,她还要承担的是邻里之间的非议和年幼的孩子们的多次问话。邻居们经常会问,孩子的爸爸到哪里去了,好久没看到了,该不会是“那个”了吧。她没法回应,只能说出差去了,他没事的没事的,我相信孩子的爸爸。两个孩子一次又一次的问话也让这位坚毅的母亲无言以对,心中的委屈和不解多次涌上心头。
这一走,邓稼先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国家,而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在“基地”搞科研,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而多年里她唯一有盼头的事,就是“基地”有同志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她会骑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一大堆的糖果、酥皮儿点心,还有能放置稍长时间的好吃的,最不能忘的是好烟。疯狂采购之后,再立刻托同志带回到“基地”去。
许鹿希多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看到新闻报纸里播报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她似乎猛然间明白了什么,它们印证了自己之前的想法。许鹿希感到,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都是在为这个家庭乃至国家作着自己的贡献。1971年夏,邓稼先因杨振宁回国要求见面而从青海的核基地回到北京,其间抽空回了一次家。当邓稼先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妻子大吃一惊。从1958年到1971年,这次见面是这对分别了13年之久的夫妻第一次重逢。谁都无法揣测在这13年中,邓稼先到底有多少次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国家利益面前,邓稼先有的是不变的信念,有的是爱国情怀。
别离后的重逢让夫妻两人有点儿不知所措,相见但无言。刚刚回过神儿来的许鹿希略微有些不自然地走向丈夫的身边,想像往常一样接过他手里的提包,但邓稼先抓得紧紧的。妻子强忍住就要流淌出来的泪水问:“你回来啦?”这一刻,邓稼先松开了手中的提包去拉住许鹿希的手,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邓稼先摇着妻子的手说:“给口水喝吧。”许鹿希转身拿着茶水递给邓稼先并说道:“再不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这样的对话在常人看来,也许显得十分生疏,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温情可言。但这也许就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吧,这也许就是两人爱情的特别之处吧。
1985年,邓稼先因被诊断出癌症而回北京治疗。这是自1958年夫妻分別以来两人待在一起最久的一次,但命运似乎并没有给两人的团聚留下更多的时间。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更多的时候,邓稼先是在和生命赛跑,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没有和妻子孩子有太多的交流。“20多年的等候,分别得这么快?”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后,许鹿希这样说道。
28年的爱情中,两人固然不在一起,固然聚少离多。28年的爱情故事固然令人心酸,令人感慨。28年里,两人有限的几次见面也不能说出工作的秘密。28年里,邓稼先什么时候回来,妻子不知道;邓稼先什么时候走,妻子更不知道。我们不得不说,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无言胜似有声,他们的爱情里蕴含着牺牲小我为了大我的情怀,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爱情与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利益联系了起来。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信仰的力量: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编著:本书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