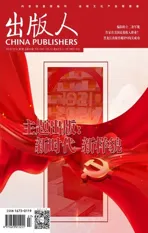诗意生活和受难史
2021-07-27李嘉平
文|李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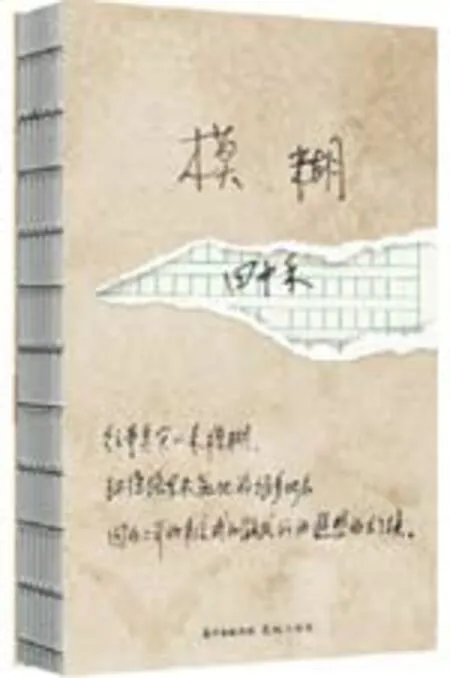
田中禾 著
花城出版社
出版:2020年12月
定价:68.80元
《模糊》是作家田中禾的最新长篇作品。在当前的文学作品里,《模糊》的题材是不常见的:在《模糊》的开头,年过花甲的“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的邮包,这个邮包里有份书稿,书稿的主人公叫章明:20 世纪50 年代,知青章明被下放到新疆的库尔喀拉,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收获了真挚的爱情,也遭遇了亲人与朋友的背叛。“我”在这部书稿中,看到了自己失踪多年的二哥张书铭的人生经历,带着这部书稿前往新疆,寻找兄长的踪迹。但现实中的寻找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最终“我”决定不再寻找,让二哥模糊在记忆中。
作者无疑意识到了这部小说在题材上是小众的,在小说的开头,他便借“我”之口说:“如果没有这个邮包,我不想把一段涉及个人情感的往事翻腾出来……谁愿意陪你为陈年旧事感叹,被过往的伤痛扫兴,耽搁了当下的快乐时光?”
这句话的最后部分,又让读者看到作者创作的一部分用心:《模糊》与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消退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在题材上相似,但出发点完全不同,它写在“当下”,来回顾一个人的创伤与磨难。在八十年代许多当事人的相似题材创作中,存在着“更多的惶惑,和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在《模糊》中,八九十年代这段被用以反刍和反思的中年时光,在某种意义上缺席了:无名书稿中的故事起于在章明二十岁左右(50年代)被下放库尔喀拉,止于他获得平反的那一年;“我”对二哥的寻找,则大约起于2010 年以后,“我”至少70岁的时候。可以说,这部小说跳过了“中年反思”的人生阶段,将人生的青年与老年连接在一起。
在《模糊》属于“青年”部分的那卷书稿里,我们很难寻见历史悲剧、旧理想、人性的扭曲与软弱等过往常见的要素,时代的特殊性消解了,创伤与磨难成为个人的、甚至具有诗意的生活经历。章明对自己被下放,“没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反而对“到这座充满民族风情的小城来,摆脱烦恼,改换一下心情,他很高兴”,到了书稿的最后,他问自己的最后的问题,依旧是私人性的:“我爱过她(宋丽英)吗?”“我爱过李梅吗?爱过小六吗?”书稿中的许多人物是独立于历史时代的,不是桃花源式的遗世独立,而是红楼梦式的遗世独立:就像大观园建在世俗的贾府中一样,章明、宋丽英、小六等人也生活在某个历史的大背景里,但他们依然拥有个人的诗意生活。
与“青年”的部分相对的,是“我”看完书稿,动身寻找二哥的“老年”部分。老年指的当然是“我”与二哥张书铭等亲历者的年老,但除此之外,是否也存在一种情景的蜕变:青年时代的诗意生活,在年老者的回溯中,逐渐失去了光晕?与书稿里的章明相比,二哥的最后两次出场,展现出的是一个被痛苦压抑了几十年、满嘴粗话的形象;在他后来写给“我们”几个兄弟的信里,则充满了被迫害的妄想;在二哥的愤怒的前妻的口中,张书铭又是一个无能、多疑的落魄人——“档案里的张书铭,我记忆里的张书铭,母亲心中的张书铭……哪个更接近张书铭本人?”“我”认识到,张书铭的真实面貌是无法得知的,“我”越是思考、寻访、挖掘他的人生,他的生活就越是呈现为一种“模糊”的受难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人,他真切地患上了时代的后遗症。
田中禾在《模糊》的尾声写道:“文学中的人物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人只是一个假象。”把这句话解释为逃避现实无疑过于轻率。这句话首先是判断,判断世事屡迁、变动不居,过往的写作者的心愿——在考掘和反思中重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种大愿终不可得;其次是认同,认同虚构的东西能比真实活得更为长久,人们也可在虚构中获得救赎;最后,这句话也是选择,在诗意生活和受难史之间,作者选择站在更加美好和人道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