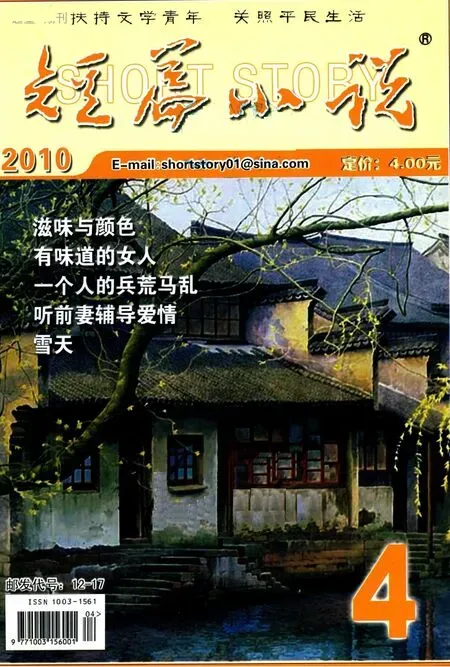袁店河戏事
2021-07-25赵长春
◎赵长春

高山吼
高山吼,嗓门大。这与他从小放羊有关。
放羊,上罗汉山、丰山,最远跑到鹰卧山;下袁店河,沿河边上下,能走十几里。跑来跑去,吆喝头羊,放声壮胆,应答他人,声音低了不行。
与别的放羊娃儿不同,高山吼的大嗓门瓮声瓮气,底气足,气韵好。人们说,这放羊娃儿,不学戏就亏欠了一个好嗓子。
不过,高山吼学不起戏。他得放羊。放羊能卖钱,有钱了,将来才能娶媳妇。
这是他爹说的。
他爹也是放羊长大的。
与他爹放羊也有不同,高山吼喜欢说话,喜欢唱。唱天,唱树,唱山,唱云,唱水,唱戏,唱蝴蝶。说这说那,一个人的时候,也说,说给树,说给草,说给花,说给羊,说给空中的鹰隼。
罗汉山的杉湾,对于高山吼来说,是个好地方。三面坡,一凹窝。一拐,两拐,三拐……顺着古石梯,得走十二拐,才能到达半山腰的这个地方。别人嫌累,不来,高山吼来。一进杉湾,就唱。羊们沟里吃草,听高山吼唱,眯着眼睛,摇着小尾巴,嚼着细草。上山时,呼吸山风,扩开了嗓,打开了喉;进湾后,杉高,草密,气爽,滋养声音。唱起来,说起来,更高,更冲,更有穿透力,几里外都能听到。
人们就说,高家这小子,是高山吼,聚气,聚音。
懂的,说,高家这小子,小小年纪,却发苍凉幽邃之音,不好。说着,摇摇头。
高山吼不放羊的时候,就去袁店镇上卖羊。他家的羊好,都知道,好卖。卖完羊,高山吼听着别人的吹拉弹唱,嗓子就痒痒,也就想来一段。他的段子,自编的,就是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风风光光。他说,用快板、数来宝、快书的调韵。他唱,用的坠子、豫剧、越调、二黄的调韵。说起来,唱起来,有韵有致。放羊时见啥唱啥的他,练就了一个绝招,街面上的人来车往,山货水产,吃喝叫卖,他都能唱,张口就来,韵脚合腔,更合意。听者开心,被唱者顺心,他自己也可舒心。
所以,卖羊的日子,袁店镇上更热闹。
南街到北街,东巷到西巷,高山吼几乎要走唱一遍。
到老。
也有几年不让唱。女人就劝他:“街上不叫唱,咱就不唱,咱回杉湾里唱。”去杉湾,得走十二拐,腿脚不太灵便了,不好上去,就在自己院子里唱。唱得憋屈,高山吼总觉得不爽利,就一下子老了,老了好多。叫人看着心疼。女人更心疼。
女人是靠山吼唱来的,不是靠卖羊的钱娶来的。这一点,高山吼很得意。当年,他上山放羊,她放牛。他下河放羊,她放牛。他唱她放牛,唱她放的牛,唱放牛的她。说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在清水中漂流的脚丫子……每天的词,不重样,一大段,再一大段,好听。开始,她恼。后来,装恼。再后来,就不恼了,一起放牛羊。再后来,两人就好了。有一段词如下,“五妮儿你是顶呱呱,在娘家发娘家,到婆家发婆家,地里带风旺庄稼;袁店河里洗洗手,大鱼小鱼跟你走,一溜儿都是发财手!”
女人叫大五妮,手大,脚大,屁股大,五大三粗,比高山吼小好几岁。大五妮说,他唱得好听,说得好听,对我也好。与爹妈怄了几场气,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高山吼唱了不少的山河草木,说了不少的人情世故。他的一个本家侄子闲着没事,记下来了一些,“读起来,都是大实话,没滋少味儿;听我吼叔唱,那才有意思,入脑入心……可惜那时候不知道录下来”。他对南阳师范学院来袁店河采风的音乐专家说。
音乐专家推推眼镜,说,高山吼的真正唱法,叫“靠山讴”。讴,古意中有民谣之意,“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教授说得很带劲儿,可是袁店河的人不认可,依旧坚持是高山吼。
那就高山吼吧。不过,大学讲台上,专家讲授说,这种流派叫“靠山讴”,民间的一种唱法,有着独特的发声、用气之道。南阳的地方剧种宛梆,就源于这种民间表达。
高山吼有一个镇台之法,上得台来不说话,眼神和观众打招呼,平静沉稳中,不急于开口。观众纳闷一会儿,静下来,神就拢了过来,看他绸扇一展,亮相,开嗓。
高山吼常执一把扇,包括秋深冬冷,嗒嗒嗒地击腿敲肩。不是扇风,是打节奏。
高山吼还有一个本事。客人手举空中,隔着几尺远示意,高山吼能轻巧地把香烟抛到客人的指缝间。还有,隔着桌子,他能把嗑好的瓜子仁用舌头一弹,落在对方的嘴里。当然是一些女客。这些,后来成为他遭批斗的理由。高山吼开始还辩解,说是为了谋生多挣钱,在花船上学的;后来就不说了,闭眼,听任拳脚相加。
高山吼到老,九十来岁了,依然“虎坐”,有着科班出身的谱派:腰杆笔直,目光远望,手心朝下,掌扣膝盖,双脚并排,腔含元气。
那天,就在院子里如此坐着,坐着。孙子喊他吃饭,不答应,一推,出了一口长气,合了眼睛……
大五妮说,和他徒弟一样的走法。
高山吼平生就收了一个徒弟,小红豁。
小红豁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可惜,比师傅走得还早。
方老大
方老大,小个头,豁子嘴,唱红脸,人送艺名“小红豁”。
个头小,穿高靴。豁子嘴,红白粉上妆。一腔好嗓子,红脸韵味。刘皇叔,李世民,关二爷,还有薛平贵,唱得舒服,演得洒脱,看不出他的豁嘴。下场来,方老大接过女儿递过的梨水茶,可口,甜蜜。喝着喝着,心头一丝苦涩。
成角之前,方老大卖炒螺,袁店河的白螺。
袁店河水好,风好,沙好,出螺。拇指大小。不同的是,袁店河的螺白。采螺水中,弯腰,探身,入手,投篓。看似不累,要有功夫,得忍住腰酸背痛。河螺采好,倒入铁盆,上下振摇五六下,流水洗净;如此反复数回,壳色如玉,白亮亮的。接着炒螺。热锅,多油。姜片滑入,蒜炒黄香,河螺入锅,翻炒,加干红辣椒丝,白糖,酱油,盐,翻炒到螺盖掉了,加水适量,中火焖,起锅。就可以去袁店镇上卖了。烤蓝莲花纹的搪瓷扁盆里,白螺泛着微红的酱色,好看,更是好的下酒菜。不喝酒,也甜欢嘴,女人、孩子买上一包,细竹签挑了吃,咂摸起来,津津有味。
十八岁前,方老大就这样过着日子。水中泡,风里走,一个人有些闲,就唱。闲唱,不瞎唱,唱学来的戏文。偷学的,镇上有戏园子。方老大好戏,没钱看,也舍不得花钱,就听。一边卖螺,一边支着耳朵,听着鼓点。他悟性好,一出戏,听完,就记在心里了。回家路上,推着小车,方老大唱,男角,女角,有板有眼。都说唱得好。进村了,方老大不唱了,怕爹说。他说过想学戏,爹打消了他的念头,说,好好卖螺,攒钱娶媳妇吧!
那时候,唱戏的名声不好。
——方老大就捡螺,淘螺,炒螺,卖螺,听戏。螺越卖越好,卖得快,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听戏,记在心里。遇上好戏、名角,方老大忍不住,一狠心买票进园子看戏。靠背木椅,香瓜子,热手巾把儿,彩妆,大汽灯,好看!方老大记戏就更认真,用劲琢磨,想象自己是舞台上的将相。不觉中,也“抚髯”,就碰到了豁嘴,心头一丝苦涩。爹妈说,当年下地干活,把一岁的他放在家里,老鼠把他嘴角咬吃了,就成了豁子嘴。想及此,方老大心头一丝苦涩,可难受。
十八岁的那个初春,方老大又是一样地不顾水冷风凉,捡螺,淘螺……年年春上,袁店镇起会。会上人多,看戏,找乐,吃喝不拘,螺就卖得更多。螺炒好,盛入烤蓝莲花纹的搪瓷扁盆里,方老大推着小车出门。推车要技术,屁股得活顺地扭。方老大扭着出了村,沿河往袁店镇的方向走,吸了水气,润了嗓道,就开唱“西门外放罢了三声炮,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
一嗓子,惊动了船上的一个人。船是花船,人是名角高山吼。高山吼是艺名,底气足,唱腔高亢,如靠山而吼——高山吼从船中探出头,看方老大的身板、架子,听着他的嗓音,就敲着船帮,打起了节奏,“好小子,有功夫!”
船家就说,“卖螺的穷小子,喜欢自拉自唱,嘴里有锣鼓家什,还有男腔女调……”高山吼昨晚上的船,按照习惯得歇晌。后晌的戏,时间还早,水声恰是催眠曲。船家怕惊扰了高山吼,说着,划船的动作停了下来,想让方老大先走过去。
高山吼却没有了睡意,也不再关心船娘呈上来的酒菜,催促着船家,“跟着那推车的走!”
方老大自顾唱,高山吼用心听。风好,水顺,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小伙子,你唱得不赖呀!
嘿嘿,我唱着玩的。您尝尝我的炒螺,鲜着呢!
好,先来一包……扔得怪准啊!好,接着唱吧。
我唱着玩的。镇上园子里,西安来的剧团里有个高山吼老师,唱得好!
你看过他的戏?
没有。听过,好听。我这小本生意,买不起戏票!
哦,再给我来包炒螺。到镇上,给你钱,包你能看到他的戏。不过,你能不能先学几腔他的,叫我听听有没有他的戏味儿?
方老大没有敢停步,继续扭胯向前,同时昂首开唱,“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学的是高山吼的韵腔,很地道。
高山吼就在船上鼓起掌:“好!好!有味儿!再往下赶一节儿!”
船游,车走。方老大边推车边唱,地里干活的也拄了锄头听。有人上前,买一包炒螺,叫唱一段再走。方老大指指河中的船,指指天,“我得到镇上赶戏点,好卖炒螺……”
就这样,船到码头,人到寨门,高山吼等着方老大,一起进镇。高山吼说:“小伙子,跟我走吧,晚场戏,我推你打炮。”
打炮,术语,有功夫的唱家初上舞台,一试身手。要么一炮走红,要么一炮而哑。方老大发愣中,高山吼一拍胸脯,“我就是高山吼!”
那晚,乐队开始伴奏了,高山吼伸出五个指头,蘸了红白粉,在方老大脸上三勾两抹;箱官掂起白蟒给他穿,他一嗓长声,起腔轰然,台下雷动。那个春天,方老大唱了三场《武家坡》,薛平贵三次搀扶王宝钏,程式不重样,感情次次深!
从此,方老大不再炒螺,拜师高山吼,艺名“小红豁”。
与老师不一样的是,小红豁终生不收徒弟。
那时候,唱戏的名声不好。那个春节,小红豁从汉口回来,高兴地去参加婚宴。同桌上的七八个亲戚,见他坐下,都起身而去。人们说,你戏唱得好,是在舞台上。台下,你还是你。
还有,因为唱戏,他晚育的小女儿一直嫁不出去。后来,眼看女儿一天天老去,小红豁忍痛把她许给了一个外地的麦客,并把半生积蓄陪嫁,“只求你好好对我闺女。拜托了!”
用的是韵白,一字一音。女婿跪地叩头,女儿一脸泪水。
大五妮
大五妮个头大,头大,脚大,手大,眼大。
大五妮生下来就九斤多,把她妈折腾得不轻。老产婆一身汗水,所有的经验都不管用,就下了狠心,硬是拽出一脸乌青、满身紫块的她,扑通摁在了灰堆上,都觉得没救了。等她爹送走老产婆又烧好一碗鸡蛋红糖水端进屋时,她“哇”的一声哭出来,声腔猛亮,如拨惊弦,风生雨来!屋外真的下起了大雨,淋得半道上的老产婆回去后一场风寒。她喝着中药汤,打着喷嚏,说,大五妮不是个善茬儿,命硬,会妨男人。
善茬儿,袁店河方言,多用来形容人心古朴,善良。
妨男人,也是袁店河的说法,指命硬的女人,谁娶了,不长寿。
大五妮会走路就开始喂鸡。再大,就放羊。再大,就放牛。三五头牛,踱在她的前后,脚步扑扑踏踏,铜铃叮叮当当,悠进袁店河,漫步罗汉山。
小咬,花腿花脚的草蚊,叮进皮肉,牲口疼得哆嗦。还有牛虻,咬劲儿更大,嘴管儿伸进肉里,不一会儿肚子呈现鲜红的血色,鼓囊囊的。大五妮最恨这些,一见,噘嘴,咬牙,细心地揪下,举在牛的眼前晃晃,在石板上一搓,鞋底下一拧,才长舒一口气,像是报了大仇。
大五妮这样的时候,小红豁看得有些害怕,就赶着自家的羊,离开十几步,不远。大五妮就走过来,捉羊身上的小咬,“哑巴牲口,你不管,它只有疼。多疼啊。”
小红豁一直觉得从开始放羊,大五妮就在那里放牛了,好像大五妮一直在等着他,等他长大,等他来放羊。
大五妮就是等着小红豁的。村口,河边,山脚下,她一直等,等着小红豁。
她说,你个小屁孩儿就得跟着我,不然狼会把你吃了,狼扒子会把你拉到罗汉山上去,“先吃头,后吃脚,留个骨壳当窝窝……”唱着说。
那时候,山上有狼,不假。
那时候,人们都会唱“先吃头,后吃脚,留个骨壳当窝窝……”
小红豁也会,用各种调门,豫剧,二黄,宛梆,四平调,唱起来有味道,听起来,更有味道。
跟着大五妮放牲口,小红豁总觉得有点儿别扭。心里不敢说,就唱,哼哼叽叽地唱。唱着唱着,想大声唱,就大声。他不管大五妮听还是不听,就自己唱,唱一唱心情就好了,这是他会唱的原因之一。
可是,他的唱惊动了一个人,花船上的高山吼。
那时候,袁店河上还有花船。高山吼不唱午场戏,只演夜场。灯光下,戏装耀眼,光彩照人,高山吼容光焕发。唱罢夜戏,高山吼就上花船,喝花酒,睡到过午。听到了小红豁的唱,高山吼探头,看到了岸上的他,还有大五妮。
大五妮正骑着牛,听小红豁唱。
夕阳在落,河风正好,大五妮的花布衫子单单薄薄,风一吹,更凹凸有致!高山吼就招手让大五妮上船……第二天,高山吼就来大五妮家提亲了。换了八字、帖书,人们才知道大五妮还有个大名儿,雨,孟雨。可惜,大名到底没有叫起来,人们还是叫她“大五妮”。
对于这门亲事,大五妮不嫌高山吼比自己大。况且自己也不小了,因着命硬,没人敢娶。后来,人们说是孟家图高山吼有钱,收了二百银圆。大五妮说不是,是我图高山吼对我好,天天给我唱戏。
还有,大五妮嫁时,给高山吼提了一个条件:收小红豁当徒弟,教小红豁唱戏。
哈哈,好!一口好腔,当我干儿子!高山吼答应得可痛快。
大五妮不放牛了。
小红豁不放羊了。
小红豁唱戏。先跟着高山吼上台,后来也挑“头牌”。袁店镇是水陆码头,人多,戏园子多,唱家也多。大五妮呢,坐在戏场里面的人群中,听人们的评价;还到厕所里,蹲坑,听票友们闲评。关于高山吼、小红豁的话,就原汁原味儿,说给他两个,就在饭桌上。
高山吼“吱儿”一口酒,点头,摇头,不觉就与小红豁对上几腔,“娃儿,你就这样唱,听爹的。”说着,目光溜向大五妮的肚子。
大五妮的肚子开始鼓了。
大五妮肚子鼓得再大的时候,高山吼又上花船。小红豁就跟着,悄悄地。潜到水里,趁花船上热闹时,突然腾浪……
大五妮有了孩子,身子更大了。有时候喂奶,不避小红豁,撩起衣衫,扑扑棱棱,白得晃眼。小红豁一脸的红,低了头,只吃了半碗饭。出门,截着去花船的高山吼:“别再去了。好好对大五妮……我妈。”
小红豁说:“要是再这样,有人就对她好了。”
高山吼一愣,看了小红豁好大一会儿,就跟着回来了。灯光下,大五妮大手大脚大胯骨,忙活着,可亲。
大五妮盘有一块儿玉,放牛时捡的,心形,觉得好看,就一直带在身上。盘玉,有文盘、武盘、意盘之说。文盘,佩玉在身,温暖温泽彼此,互为营养。武盘,干净的白棉布擦拭,起热,逼出玉中土气,从而晶莹。
大五妮盘玉,没想那么多。总觉得一块好石头,静默时胸暖手捂,自然而然。袁店镇“来玉璇”老板看过那块玉,说大五妮“你是意盘。不经意中养护了玉,净化了心。好人,好玉”。
就又多了个说法,说大五妮胸大,能含下那块玉。
所以,关于大五妮的大,头大手大脸大脚大之外,总有其他另外的一个说法。比如,老产婆说她命大,硬命,谁娶她,都会被妨。
还有人说大五妮心大,情怀大。她不止盘玉,还盘成了两个唱家:高山吼和小红豁。
唱家,也是袁店河方言,说谁唱戏好,成了名家。
后来,《南阳曲艺志》收有“高山吼”“小红豁”的词条,称他们为艺术家,却没有提大五妮。
大五妮不在意这个。她依然给袁店河畔爱戏的人讲戏。先遛嗓子,再喊嗓子,气顺了,嗓热了,吃豆腐脑、小包子,六七分饱,才能吊嗓,“可不是张嘴就咿咿咿呀呀呀哇哇哇哈哈哈,学问大着呢!”
人们就又说,大五妮学问也大。
去袁店河,巧的话,还能见到她,拄杖河边,注目河水,一看一大晌,不知道在看啥。她脑后的髻,古式,被一块老发卡挽住。很雅致。
那枚老发卡,就是那个下午,花船上,高山吼给她别上的,一下,一下,很慢,很慢,很轻,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