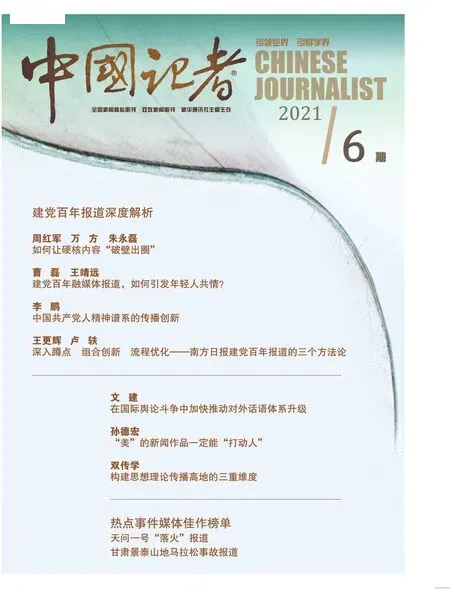在民族报道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
——黄昌禄民族报道阅读笔记
2021-07-24马昌豹
□ 马昌豹

黄昌禄(1930.2.28-2014.8.27)
新华社著名记者,以民族报道闻名于新闻界。先后在新华社云南、青海、陕西、四川分社工作,曾任陕西和四川分社社长。
从1952年到1981年,他在云南、青海两个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近30年。在云南,他先后担任过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长驻记者,并多次深入德宏、怒江、迪庆、大理、楚雄等少数民族自治州采访。在青海,他跑遍了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和所有的自治县。在4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采访过傣、彝、哈尼、白、景颇、纳西、傈僳、瓦、拉祜、布朗、德昂、基诺、独龙、藏、蒙古、土、回、撒拉、哈萨克等20多个少数民族;在他写的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中,最多的是民族报道。
他把民族报道作为长期投身的事业。在云南和青海,他对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作了系统调查和材料积累。他还努力学习民族语言,1955年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驻点后,更加系统地学习傣文和傣语。
代表作有:《苦聪人有了太阳》《孔雀开屏》《千里传艺》《路》《大理三月街》《配种站和“财神阁”》《世仇部落结姻亲》《阿佤山区办学记》《沧海桑田话孟朗》《欢乐的红河》《攸乐山上》《国境线上访布朗人》《夜宿瓦窑》《依蓝波》《这里没有冬天》等。
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阅读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报道真有隔世如梦的感觉。生活环境的差异、发展理念的不同、读者背景的多元都让我们读黄昌禄作品时,产生强烈的羡慕和向往。黄昌禄的民族报道没有市场经济的浮躁和金钱的铜臭味,有的似乎只是自然、喜悦、团结和进步。“群众路线”是我党工作的一大法宝,也是新闻工作的一大原则。从黄昌禄的民族报道中,我们看到群众路线在其中的贯彻运用,对如今民族问题及其报道有一定的启发。这也就理解了其作品为什么能够那么真实地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同胞的美好生活。
一、30年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把民族报道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真正把群众观点融入血液。黄昌禄同志从事新闻工作40年,有30年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写了上千篇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变革和精神风貌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散文和评论。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边境、山区、高原,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他有时候在原始森林里一个人走好几天,有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不仅采访条件艰苦,他还和爱人分居多年,经过努力把爱人从首都北京调到艰苦的边疆工作。这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新华精神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体现。他把民族报道作为自己长期的事业,坚持调查研究和积累资料,坚持写采访日记,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把少数民族当朋友、当兄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
我们应当学习黄昌禄这样的老前辈,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受社会环境的干扰,不为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诱惑,在新闻传播中呈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关注民族议题,体现少数民族的传播权利,推动民族之间的平等沟通,缓解民族报道与其他报道的不对称的状况。
二、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是解答当下民族问题及其报道的一个路径。民族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当今世界,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民族或种族矛盾冲突不断,团结进步的局面较少。1993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黄昌禄民族报道选》里有这么一段话:“一次,有个外国通讯社的代表团访问我国,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国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总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落后,产生不了新闻。问我们的少数民族报道如此有声有色,到底有什么经验。”如今这个问题若再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未必能回答好。但黄昌禄的民族报道作品从一个侧面窥探出解答当下民族问题及其报道的答案。

▲ 1975年7月,黄昌禄骑马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草原采访。
作者在书中说:“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局面,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制订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其中最基本的是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这既符合各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实际,又保障了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还有许多保障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口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笔者认为,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在民族政策中坚持贯彻群众路线。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一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在特殊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情况下引发了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的民族政策能坚持一贯的群众路线,就能确保民族安定团结和繁荣进步。
三、以多样化的议题内容来体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传播多元化。在黄昌禄的笔下,有哪些议题呈现出来?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发展建设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鲜明展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其作品一系列主题都是关于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1960年8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孔雀开屏》写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1961年11月3日《工人日报》上刊登的《千里传艺》是写民族服饰和纺织行业的发展;1962年4月《云南日报》上刊登的《路》是写怒江两岸公路的发展;1963年4月《大理三月街》是写民间街市贸易的;1963年9月《配种站和“财神阁”》写畜牧生殖发展;1964年3月《世仇部落结姻亲》写民族部落间的融合;1964年3月《阿佤山区办学记》写民族教育。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眼球,才会成为公共话题,少数民族才能更多获得国家资助和参与国家发展的机会。对少数民族来说,这是实现当家作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如果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没有群众观念,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少数民族的一些议题可能被忽视,可能被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发展就很难进入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视野,不利于民族地区发展。
四、人物报道《依蓝波》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民族地区扎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映人民群众心声,为人民群众谋利,是我党贯彻群众路线的目的所在。1957年初,黄昌禄访问了一个18岁就当了合作社副主任的傣族姑娘依蓝波,这个报道讲妇女当家办事,首先体现了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理念。比如,“两年多前,人民政府派的一些工作同志来到曼藏宰。说实话,我以前看见汉人心头就会打颤,这回来的汉人可完全不同啦!帮我们舂米、挑水、砍柴,一有空就给我们讲民族自治的道理,说再没有汉人敢来压迫傣人了,要我们自己起来管自己的事情。”提拔少数民族青年干部成为民族自治的重要途径,大家选依蓝波当组长,选送她到西双版纳民族干部学校去学习。
此外,民族地区合作发展的问题,不仅涉及土地改革,而且采用“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少数民族的土地改革,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建设委员会,修水利,贷款给穷苦人家买耕牛添农具。合作社的政策公开透明,比如私人的牛可以入社,由社里出租金,这些政策都是由社务管理委员会来讨论决策。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合作发展这些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议题得到报道,可见当时我们的民族报道理念对社会主义精神的理解和体现。
五、以对比方式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展开。由于作者工作的年代具有特殊性,作品充满了历史厚重感和鲜明的对比性。但并不是历史的线性罗列,而是以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对比的目的是展示新社会的美好,旧社会的腐朽。比如,报道《沧海桑田话孟朗》从清朝光绪年间写起,经过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把红旗插到云南边疆之后,少数民族人民才开始了发展和建设。1955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欢乐的红河》,以对比的方式“吐诉过去的哀怨”“表达今日的欢欣”,描述了哈尼族人民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家园。1957年1月的《这里没有冬天》也以土地改革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变化来描述傣族人民在新的生活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1957年5月写的《攸乐山上》描述了民族压迫使攸乐人长期停滞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上。但互助组成立后,人们不仅能吃饱,还盖上了新房子,还成立了贸易小组满足人们生活物品的需要。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问题都得到解决。

□ 1955夏,黄昌禄身着傣族服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曼京兰寨采访。

□ 1990年7月4日,黄昌禄重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时,摄于中缅国境线上打洛镇的国界桩旁。
除了纵向的对比,作者还使用了中外对比。1959年9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苦聪人有了太阳》是作者的代表作,在讲到“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时间,在原始大森林里找到了二千多苦聪人”时,作者说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们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两百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英、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残酷地屠杀他们。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马去找寻他们,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们的苦聪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们不但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不深入群众、深入研究,这些报道是写不出来的。
六、以散文游记的笔法描写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和家园的美好。作者描述了诸多的少数民族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园图。如:曼藏宰是一个幽静秀丽的村寨,几十座轻巧的竹楼被枝叶茂密的菩提树、凤凰树和黑心树包围着,两株高大的椰子树垂着长长的叶辫俯视着全寨,一条清莹的小河从寨旁流过,每天中午,傣族妇女们便到河里来浣衣和洗澡,寨旁还有一座鱼塘,塘里浮着娇艳的睡莲花。
1957年1月的报道《这里没有冬天》,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具有民族风情的热带大花园。除了描述种类繁多的热带水果和植物,黄昌禄的一系列作品还留下了少数民族的生计、饮食、居住环境、衣服穿戴、婚姻风俗等方面的珍贵场景。比如民族人物报道《依蓝波》:依蓝波请我们在走廊上坐下,她的身体很健壮,皮肤被亚热带的阳光晒得红里透黑,袒露着上身,一条筒形花长裙高系到胸上,罩住乳峰,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不住地打量着我们。这样的描写也许会被理解为只能出现在消费主义的娱乐杂志里或新潮流的小说里。但我们读这篇报道时,感受不到商业环境下的旁骛杂念,而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少数民族少女的装扮,给读者的感受是敬意、平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