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那把不熄之火
2021-07-22陈洪澜
陈洪澜
在巴黎先贤祠的地宫里有一座墓,墓面上建有两扇门。门缝微启,从中伸出一只举着火把的手。若是在墓园内观看这个火把,它若明若暗,似乎很弱小。若是你洞悉世界历史,回望两百多年来世界各地连绵起伏的政治风潮,便可知道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竟然烧毁了强大的法兰西封建王朝,然后这把星星之火竟然形成了燎原之势,一直由欧洲烧到美洲、亚洲,继而把整个世界都给照亮、熏染了。点燃这把火的人如今就躺在这座墓穴中安眠。可是,他的魂灵仍然在世界各地游逛,人们时常还扯着他的旗子为“自由”和“民主”而呐喊。说到这里,你一定会想起墓中的这个人来—―他就是卢梭。
提起卢梭这个人,虽不能说是妇孺皆知,但他逝世两百多年来在思想文化界却仍像个明星似的受人热捧。人们在他的头上戴了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多顶桂冠。当然,也有不少人敌视他,把他当作“疯子”“野蛮人”“一切革命的始作俑者”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等等,有人甚至还说他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灾祸”。那么,卢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
在世界思想史上,卢梭是个毁誉参半、争议极大的人。他在介绍自己时说:“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因而他就显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在瑞士日内瓦风景如画的莱芒湖畔。他的父亲依萨克·卢梭是个钟表匠,母亲苏萨娜·贝纳尔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在卢梭出生的第10天因产褥热去世。卢梭在姑母的抚育下得以活下来。因此,卢梭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生而不幸的人。
在卢梭列举的诸多不幸中,首先是他生来丧母,10岁时又失去了父亲的庇护——他父亲在1722年与议会官员产生纠纷惹上了官司后远逃他乡。孤苦无依的卢梭被舅父贝纳尔送往包塞,托付在牧师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学习基本知识。也就是在这里,卢梭初次遭遇了不公正的暴打,起因是牧师的妹妹怀疑他掰断了她的梳齿但他却不承认。愤怒的火种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他说:“即使我活到10万岁,这些情景也一直历历在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无论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是谁,也无论是什么地方发生的,只要我看见或听到,便立刻怒发冲冠,有如身受。”可见这件事对卢梭的一生影响有多大。他觉得自己欢畅的童年生活到此戛然而止,随后他便中断仅有的两年学习生活去当了学徒。

卢梭早年的许多丑事都是他在自传中抖露出来的。他在记述学徒生涯时说:
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终于使我对于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这一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回忆起来,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我谨言慎行;到了我师傅那里,我就变得胆小如鼠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孩子。
他甚至说:“我生来就是为挨揍的。”直到晚年,卢梭对于自己少年时因何撒谎、因何偷东西、因何挨打的经历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读书癖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
许多人都说卢梭是一个天才,事实上他是靠勤奋自学成才的,他从来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他说:
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连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可知,卢梭的第一任老师是父亲,引导着卢梭走进了书中的有趣世界。
卢梭常以自己拥有读书的嗜好而沾沾自喜。因为读书上瘾,他经常遭到师傅的毒打,租来的书被撕毁或烧掉,可他说:“我的读书癖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热状态了。”在当学徒的几年间他把自己的零花钱都送给了租书的老板娘,有时还用自己的衣物作抵押。他这种读书的嗜好到老都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是劳累饥饿,或是流浪途穷,甚至身染重病之时,他始终把阅读和求知当作一种解厄除困的灵药,他甚至说:“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
为获得更多的知识,卢梭博览群书,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到自然科学,无所不读。他读书纯粹是因为兴趣,没有目标、没有界限,也没有人督导劝勉,如同荒原跑马,经常在文学、哲学、史学、数学、天文、地理和音乐等领域自由驰骋。广博的学识不仅丰富了卢梭的精神世界,也铸就了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对抗种种压迫的坚忍品格。
“我这颗兴奋起来的心更渴望的是爱情”
卢梭是个浪漫而又多情的才子。爱读小说使他早早就萌生了朦胧的爱情。据他自白,11岁时就假想自己是个骑士,可以保护女人,并同时爱上了22岁的德·菲尔松小姐和11岁的戈登小姐,初尝了爱情的滋味。这种孩童们过家家般的恋爱说起来像是笑话,但这种爱的感受却给卢梭留下了持久而又甜蜜的记忆。
卢梭长着一双爱美的眼睛,他喜欢长相秀美、肤色柔润、谈吐优雅、举止大方、穿着飘逸的女子。他曾经模仿小说中的人物,凭着甜美的歌喉到城堡附近或深宅大院的门口去唱歌,幻想能够邂逅公主或者贵族小姐。他为此曾经唱哑了喉咙,等到的结果却是无人理睬。不过,他与华伦夫人的相逢也应是一种奇缘。他认为自己一生中只有和华伦夫人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才算是幸福,但与华伦夫人的不伦之爱又让他终生处在既温暖甜蜜又羞愧悔恨的矛盾中。
那是1728年,16岁的卢梭不堪忍受雕刻匠师父的暴虐性情而出逃,流浪途中他经人介绍去投奔华伦夫人。“本以为她一定是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然而我现在见到的却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庞,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我立刻被她俘虏了。”
华伦夫人是个有故事的人。她出身于一个老贵族之家,出嫁后陷在不幸的婚姻烦恼中。当她听说国王到该地游访时,竟然冒险越过了安讷西湖匍匐到国王的膝下寻求庇护。这个楚楚动人的小妇人当即就打动了国王的心,被赐予2000法郎年金后皈依了天主教。教会的神父们常常把一些流浪者送到她那儿去救急。
华伦夫人比卢梭大12岁,她称卢梭为“孩子”,让生来就失去了母爱的卢梭从此有了华伦夫人这个“妈妈”。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形同母子,相互关心,相互照顾。但随着卢梭年岁的增长,他们之间的情感日益微妙复杂起来。卢梭看待华伦夫人若母、若师、若友、若情人,最终在他20岁时冲破了“母子”关系的束缚,在亲爱的“妈妈”怀里吃到了禁果。
卢梭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那秀美柔润的文字曾博得了不少贵夫人的喜爱,如杜宾夫人、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和卢森堡夫人等都曾与他有过极为亲密的交往,他身边还有其他各色女子的纠缠,曾留下了一些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但他似乎对这些女人并没有太多兴趣,他说:“我这颗兴奋起来的心更渴望的是爱情。凡是可以用金钱得到手的女人,在我的眼里她们所有的动人之处都会荡然无存。”
尽管卢梭被标榜為浪漫主义文学家,但对于爱情却有着悲观主义情绪。他说:“我易于动情,这就注定我在爱情上要栽跟头。爱情战胜了我,我会倒霉。我若战胜了爱情,也许倒霉得更加厉害。”在对待婚姻方面,他也未改变其平民本色,选择的伴侣是非常务实的。1745年,卢梭在下榻的旅馆里遇到了善良而又痴情的洗衣女仆戴莱丝·瓦瑟。此时卢梭33岁,长戴莱丝10岁。他记述了初次见到戴莱丝的情景,被她那双活泼而温柔的眼睛吸引了,他们彼此互生好感,成了情侣。戴莱丝虽然没有文化,却对卢梭温柔体贴,不离不弃。直到1768年,年过半百的卢梭在布戈市市长的主持下,才与戴莱丝补办了婚礼。
不过,平庸的婚姻并没有化解卢梭心中的浪漫情愫。1761年,他创作了一部情意绵绵的书信体爱情小说《新爱洛伊丝》,借用一对恋人的情书讲述了一场在封建社会压迫下的爱情悲剧。书中的故事如催泪弹似的让无数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泪水浸湿了手帕。

“我是为音乐而生的”
卢梭自幼喜爱音乐。他声称:“可以肯定,我是为音乐而生的。”虽然在他获得的诸多桂冠中并没有音乐家这个美称,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既有终生的音乐实践,也有丰富的音乐作品和系统的音乐理论体系。
据卢梭自述,他在音乐领域里的成就也完全是自学自练、盲打盲撞得到的。最初的音乐喜好来自幼年时照料他的姑姑,她有一副甜润的嗓子,经常哼出一些优美的乡村小调。他常跟着姑姑哼唱,学到了不少小调。从此,音乐就成了卢梭向生活进军的号角和慰藉。
卢梭能获得系统的音乐知识受益于华伦夫人的帮助。她发现卢梭的天赋异禀、喜欢音乐且有一副好嗓子,就教他唱歌弹琴,还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使他有机会结识一些乐界人士并读到许多乐理方面的书籍。为了快速记住乐谱,卢梭竟然有了独到的发现,即用阿拉伯数字识记乐谱,并写下了论文《新乐谱记谱法》,呈交给巴黎科学院。不料主持评审的三位评委扒出了1665年巴黎方济会修士苏埃蒂的论文,认为简谱的提法早已有之,只是由于当时受到抵制而胎死腹中。倔强的卢梭自然不肯罢了,他继续补充完善自己的音乐理论,后来将其改写为《现代音乐论》并公开出版。
为了能在乐界立足,年轻的卢梭加大火力,先后写下了百余首歌曲,创作了6部歌剧。据说这些作品收益不大,唯有歌剧《乡村占卜师》最受欢迎,相继演出400多场。他的音乐才华也受到了百科全书派的赏识而成为《百科全书》音乐部分的撰稿人。他于1768年还出版了一部《音乐辞典》。
此后,卢梭始终没有放弃音乐这个饭碗。他时常为人抄乐谱,当家庭音乐教师,晚年落难时还以替人抄乐谱为生计。他去世后,有人根据他的账单做过统计,在最后的7年里,卢梭替人抄写的乐谱有12000多页。
“金钱金钱,烦恼根源”
卢梭在金钱面前一直是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心理,让这个满腹才华的作家一直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清贫生活,终生都未能改变其贫穷的命运。
其实,在卢梭的一生里并不是没有碰到发财的机会,而是他在金钱面前总选择退缩。比如,卢梭曾受聘到威尼斯法国大使馆给蒙太居伯爵当秘书,还在法国财务总管弗兰格耶处担任过出纳并经管金库等。这些职位都是肥缺,但他却烦于周旋、苦于应酬,没干多久就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由辞去职务。
当卢梭的歌剧、论文和小说在巴黎出彩之后,他的声望日高,报酬也增多,若能努力写作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卢梭却说:“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写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很难高尚。为了能够大胆地说出伟大的真理,就肯定不能屈服于对成功的追求。我将我写的书交到公众面前,相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惜。”
卢梭出名之后也就有了名家的烦恼。因各种应酬缠身,他觉得自己连享受清贫生活的自由也给剥夺了。“我深刻地体会到希望中的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只是一种奢求。”他拒绝接受权贵们的馈赠,甚至退还人们送给他的礼品。于是人们骂他摆臭架子、傲慢无礼。为了躲避各种烦扰,卢梭离开了热闹的巴黎,搬到乡下居住。可是无论他逃到哪里都难以摆脱金钱的烦恼,比如那些黏着他的“年金”。
第一个要赐予卢梭年金的人是法国国王。1752年,卢梭的歌剧《乡村占卜师》在巴黎火起来,从巴黎的多家大剧院一直演到了枫丹白露宫。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后看过这个歌剧后都很喜欢,就派使者找到卢梭,说要召见他并赐予一项年金。卢梭犹豫再三,便以健康不佳为由推脱了。卢梭放弃年金的行为遭到了亲友们的谴责,朋友还批评他是“愚蠢的骄傲”。
时隔10年,卢梭的名气更大了,却因出版 《爱弥儿》遭到了法国当局的通缉。他逃到普鲁士境内的莫蒂埃居住,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庇护。1763年,腓特烈国王为了表示自己爱惜人才,不仅馈赠礼品,还决定赐予卢梭年金。他再次谢绝了普鲁士国王的馈赠和年金而离开了普鲁士。人们纷纷说他是个十足的傻冒儿、伪君子,故作清高、不识抬举等等。
1766年,他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帮助下逃往英国避难。转年他的朋友帮他向英王乔治三世申请到了每年100英镑的年金并帮他代取,为此他与朋友闹翻了。由此可知,在他发出“金钱金钱,烦恼根源”的感叹背后曾有过怎样的辛酸经历。不明就里的人在读过卢梭《忏悔录》中的解释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身上的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我摆脱所有那些诱惑,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心一意过慵懒的生活,让精神安静下来——这从来就是我最突出的爱好,最持久的气质。”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也许是卢梭早年的伤痛太多、疤痕太深的缘故,在他的心灵深处似乎埋藏了一个易燃易爆的火药罐,让他的论著处处充满了火药味。面对社会的各种不公和压迫,他那犀利的言辞仿佛连珠炮似的越发越猛。
1749年,卢梭写了一篇应征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在巴黎一炮打响。当时他偶然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看到了第戎学院的一则征文——“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灵感的火花顿时点燃了他许久以来愤懑的思绪。他顾不得社会大众对科学与艺术的普遍性赞美,而以慷慨激昂、惊世骇俗的言辞斥责它们都是些虚浮的东西,束缚和掩盖了自然的美和真,“抛掷花环于人类所戴枷锁之上,终致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堪重负”;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由于科学、艺术和文学同财富、奢侈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們不但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卢梭的征文以其论点新奇、论证有力、文笔优美而得了头奖,寂寂无名的他由此一鸣惊人。那一年他38岁,思想体系日趋成熟。
1753年冬,卢梭看到第戎学院又发布了一条“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的征文,这个题目正是经常盘旋在卢梭头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他又写下了题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应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考察了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起因。他指出:文明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私有制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唯有用暴力推翻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权,才能建立起平等、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篇论文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欧洲。结果这篇征文不仅未能获奖,而且无法在法国面世,几经努力在荷兰出版后还导致了敌对阶级对他的迫害。

1762年,卢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政治学代表作《社会契约论》,随之又出版了他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这两部著作犹似暴风雨前夜发出的两颗响雷让全天下震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开篇就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却比其他一切是奴隶的人更是奴隶。”而这个让人们失去自由的枷锁就是国家的强权统治。在这部四卷本著作中,他系统阐述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指出我们应该建立的国家最高权力应属于人民;人民的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侵犯、不可替代。他还向所有遭受奴役的同胞们呐喊“: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他在这本书中的呐喊后来被人们评为“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他提出的“主权在民”主张也被看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不仅影响了欧洲的革命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长篇小说《爱弥儿》原本是讨论儿童教育的,他却指责是罪恶的社会把人给染坏了,认为“自然曾让人幸福而良善,而社会却使人堕落而悲惨”。
卢梭的这些激扬文字惹怒了欧洲统治者,于是政府、教会乃至曾以朋友相称的达官显贵们都视其为敌,说他胆大妄为、亵渎宗教、试图打倒教会和推翻政府。巴黎高等法院向卢梭发出了通缉令;政府查封、焚烧了他的书籍;巴黎大主教毕蒙发布文告把卢梭列为上帝的敌人;沙龙和文化媒介也印发宣传品、编造谣言,用各种恶毒的语言羞辱、诽谤他……这让形单影只、孤苦无援的卢梭在余生的岁月里一路逃亡,一路为自己鸣冤叫屈,写下了一系列浸满血泪的著作——《忏悔录》《对话录》《漫步遐想录》,它们被称为卢梭的“自传三部曲”。
“卢梭将永远是原来那个卢梭”
1762年,卢梭遭到法国当局的通缉之后,开始走上漫长的逃亡之路:从法国到瑞士,到普鲁士,再逃往英国,然后又潜回法国。8年之间辗转于多个小镇和荒岛,或寄人篱下,或栖息于窝棚、茅舍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纷纷围剿过来,都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最让他痛心的是朋友的背叛,尤其是自己曾经尊敬的、亦师亦友的学界泰斗伏尔泰,竟然也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猛烈轰击,说他将自己的五个孩子丢弃给育婴堂,性生活糜烂导致染上梅毒,还谴责他为人狂妄自大、傲慢无礼等等。随着这些揭发和宣传,卢梭被人们看成是疯子、骗子、野蛮人、人类的敌人……眼见自己被人抹得一团漆黑,逃亡期间的卢梭便开始撰写《忏悔录》为自己辩护,他要还原一个真正的清白的卢梭:“休想按照他们的模式塑造一个让—雅克;卢梭将永远是原来那个卢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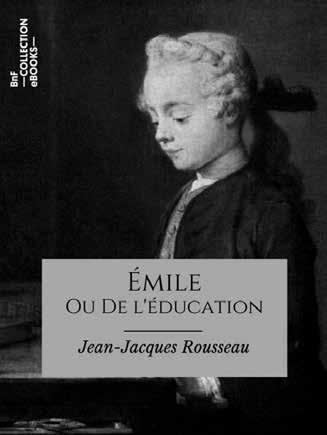
卢梭的《忏悔录》在逃难途中断断续续写了4年。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自他出生至1766年被迫离开法国圣皮埃尔岛这50多年间的人生经历,也勾勒出了自己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他说:“当时我是什么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言之切切,掷地有声。他希望通过《忏悔录》能为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做些澄清:“我绝不愿有虚假的名声,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绝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像我自己。”然而当他完成了这部书稿之后却无法出版,他曾寻找一些场合去朗读也被人阻止了。
卢梭逃回法国后到处躲藏,经孔迪亲王斡旋,法国当局于1770年默许他回到巴黎却不能随意发表言论,卢梭便寄望于通过写作来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1775年他完成了《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简称《对话录》),1776年他又开始撰写《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简称《漫步遐想录》),而当他写到第10次漫步时,尚未结篇就去世了。
老天不负有心人。卢梭去世仅10年后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顺应了卢梭的愿望。革命者奉卢梭为“法国大革命之父”,并替他昭雪了冤屈。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给“大革命的象征”卢梭树立雕像,并以金字题词:“自由的奠基人”。1794年,革命政府又将埋葬在巴黎北郊埃尔姆农维尔小镇的卢梭遗骸隆重地迁进巴黎的先贤祠。墓碑上刻的铭文说:“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爱自然与真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