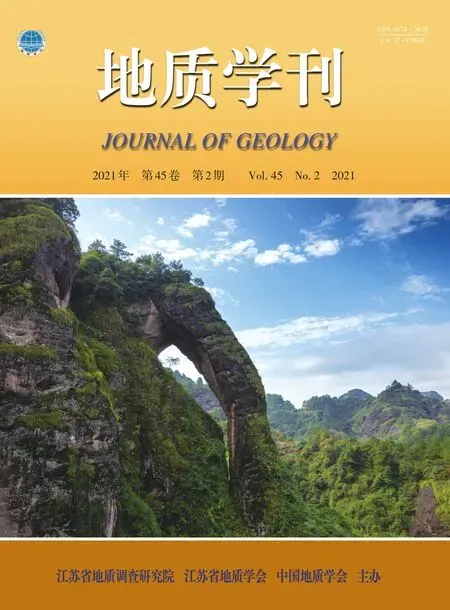南京花化石产地的保护与利用
2021-07-21傅强
傅 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8)
0 引 言
古生物化石是远古生命演化和环境变迁的实际见证,在地层划分与对比研究、古地理和古气候研究以及矿产和油气资源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孙革等,2018)。我国是世界上古生物化石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近百年来,发现了多个具有极高科研价值的化石群,很多化石的发现修正甚至改写了对生命演化历史的认识。
南京地区地处宁镇山脉西段,古生物学研究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为我国古生物学发展的摇篮之一(Von Richthofen,1912;刘季辰等,1924;李毓尧等,1935;卢衍豪,1954)。南京地区化石资源丰富,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1933年李四光根据南京栖霞山地区二叠纪地层中所产标本建立的南京蜒属(NankinellaLee),1954年卢衍豪根据南京汤山奥陶纪地层所产标本建立的南京三瘤虫属(NankinolithusLu),1983年陈均远根据汤山奥陶纪标本建立的南京角石属(NanjingocerasChen),1993年在汤山葫芦洞发现的南京直立人(Homoerectusnankinensis),后在原址建立了南京直立人遗址博物馆。其他化石虽然同样十分重要,但由于缺乏“明星”效应,除极个别外,大多产地缺乏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2018年至今,最早的被子植物——南京花(Nanjinganthus)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是近年来南京地区古生物研究的一大亮点。与南京花化石伴生的大量植物化石新类型,以及罕见的鲨鱼卵壳化石是重现南京地区早侏罗世古环境的珍稀载体,也是破解三叠纪末大灭绝后生态系统恢复的重要窗口。然而,其产地南京栖霞区西岗街道乌龟山为一采石场,采石对化石资源的破坏十分严重,保护工作亟待开展。从南京花化石发现的重要意义出发,结合该化石产地的现状,探讨南京花化石产地的保护和利用。
1 南京花化石发现的重要意义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石。当今地球上生活着大约30万种形形色色的植物,包括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四大主要类群,其中最为丰富的是被子植物,至少有25万种。被子植物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不仅是人类起源、发展和延续的物质基础,还深刻地影响着很多其他动物类群的发展。
虽然被子植物的多样性是植物各类群中最高的,但究其演化历史,却比其他类群短得多。苔藓植物大约起源于5亿年前,蕨类植物大约起源于4亿年前,裸子植物大约起源于3.6亿年前,而被子植物的起源时间却一直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最早只能追溯到1.3亿年前左右。
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植物有着漫长的进化历史,但直到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早期才开始出现大量的被子植物化石记录。因此,被子植物的起源及其在白垩纪的迅速崛起,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植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讨厌之谜”(见达尔文1879年7月22日写给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的信)。
自此之后,无论是研究化石的古植物学家,还是研究现代材料的植物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开展工作,试图破解这一谜题。100多年来,古植物学家一直在更老的地层中追索更老的被子植物化石,发现了早白垩世的古果(Archaefructus)和蒙特赛克藻(Montsechia)等,中侏罗世潘氏真花(Euanthuspanii)、渤大侏罗草(Juraherbabodae)和石叶(Phyllites)等,晚三叠世毛籽伊甸籽(Edeniavillisperma)和总领叶(Pannaulika)等化石,为认识早期被子植物、破解达尔文的“讨厌之谜”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尽管如此,国际上对此持十分审慎的态度,2017年之前,一直认为在白垩纪之前并不存在被子植物的确切证据(Herendeen et al.,2017)。然而,分子系统学的分析表明被子植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75亿年前的二叠纪后期,甚至是3亿年前的石炭纪。此外,早白垩世的被子植物已经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因此被子植物应该起源于白垩纪之前。
白垩纪之前缺乏被子植物化石记录有很多解释。例如,有观点认为原被子植物是长得很小的、匐地生的草本植物,花小而简单(Taylor et al.,1992);还有观点认为最早的被子植物仅生活在森林的下层,直到白垩纪才开始辐射发展(Doyle,2012);高地假说则认为被子植物在白垩纪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生活在难以保存为化石的高地区域(Axelrod,1952,1970)。
2018年南京花化石的发现(Fu et al.,2018)(图1),为寻找早期被子植物化石记录、破解被子植物的起源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献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Taylor et al., 2018; Coiro et al., 2019; Rümpler et al., 2019; Sokoloff et al., 2019; Bateman, 2020)。

图1 大量散落的南京花化石(a)和复原图(b)Fig. 1 Field photo (a) and restored picture (b) of scattered Nanjinganthus fossil
笔者经过多年的努力采集了一批南京花的标本,可供后续进一步研究。然而,化石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生物学属性,其赋存岩层的岩性特点、化石在岩层中的保存状态以及埋藏学反映的环境特征等同样重要,因此不仅要对化石标本进行保护,还要对其产地进行整体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化石产地,也是重要的自然遗产和破解被子植物起源之谜的宝库,南京花化石的产地应予以重点保护和利用。
化石资源是古生物学的核心基石,保护好珍贵的化石资源,不仅是我国努力进行科技创新的需求,也是人类对科学文化的需求。
2 南京花化石产地现状
南京花化石产地乌龟山(图2a)北邻312国道,距栖霞山直线距离仅2 km,南距仙林湖公园直线距离仅1 km,东侧距在建小区约500 m,距产地最近的居民小区直线距离仅300多m。随着仙林湖区域的大规模开发,乌龟山采石场已渐渐被城建所包围,已不再适合石料的开采。
南京花化石所在地层主要为南象山组(图2b),即传统的象山群下段(鞠魁祥,1987),主要为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砂岩,夹灰白色粉砂质泥岩、灰黄色薄层粉砂质泥岩、浅灰白色黏土岩和煤线。根据动植物化石的证据,南象山组被定为下侏罗统,北象山组被定为中侏罗统(鞠魁祥,1987)。综合孢粉和碎屑锆石的数据,南象山组的时代为早侏罗世晚期(Fu et al.,2018; Santos et al.,2018)。

图2 南京花化石产地的位置简图(a)和南象山组剖面局部(b)Fig. 2 Nanjinganthus fossil origin map (a) and the section of partial South Xiangshan Formation (b)
象山群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侏罗纪地层的代表,主要见于长江沿岸区域,由西向东自安徽宿松、太湖至芜湖、当涂,直到宁镇山脉一带都有露头分布,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Von Richthofen,1912;刘季辰等,1924;李毓尧等,1935;江苏省地质矿产局,1984,1989;鞠魁祥,1987)。南象山组内含丰富的植物化石,象山植物群几乎全产自该组地层。前人对象山植物群的研究虽有零星报道(Sze, 1931;王国平等,1982;黄其胜,1983,1988;曹正尧,1998,2000),但因缺乏好的剖面,化石的采集均不系统,也不深入。
1.7亿年前后的侏罗纪早期是地球上生命的重要转折时期,经历了三叠纪末的大灭绝之后,恐龙开始辐射并统治陆地生态系统1.6亿年,种子蕨类大规模消失,被子植物开始兴起。南京地区当时位于古长江的上游,江水自此向西至云南附近注入古地中海。在高山河流和湖泊周围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其中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南京花就生长于此。
乌龟山采石场是南京及周边地区象山群出露最好的剖面之一,采石场采石工作揭露出大量新鲜露头,为化石采集提供了有利条件。除已经报道的南京花之外,还产有鲨鱼卵壳Palaeoxyris化石和大量有待研究的新化石类型,是认识1.7亿年前南京地区古环境的重要化石产地。
自1993年开始,乌龟山采石场作为水泥配料用砂岩矿开采至今,化石产出层位不断被挖掘,大量珍贵的化石资源遭到破坏。该采石场最近的开采有效期限是2016-11-01至2019-09-04(图3a、b),但开采仍然在继续。经过多年的开采,乌龟山已经从原来的高山逐渐被挖平,并在局部地区形成坑(图3c、d)。不断的挖掘不仅破坏了当地自然景观,采石产生的粉尘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图3 乌龟山砂岩矿公示资料(a、b)和南京花化石产地的变化(c、d)(a) 2015-02-25;(b) 2019-11-03;(c) 2015-02-25;(d) 2020-02-23Fig. 3 Wuguishan public information of sandstone mine (a, b) and changes in the origin of Nanjinganthus fossils (c, d) (a) Feb. 25, 2015; (b) Nov. 3, 2019; (c) Feb. 25, 2015; (d) Feb. 23, 2020
无论从景观和环境保护,还是从化石资源的保护来说,乌龟山采石场均应该予以关停,并进行适当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3 产地保护与利用
经过长时间的开采,乌龟山采石场产化石地层遭到了大量破坏,因此关停采石场,并加以保护和利用已迫在眉睫。基于前期的工作和近期的思考,提出以下几点保护和利用建议。
3.1 建立江苏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
古生物化石的形成和保存都是地质历史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全面保护化石所含的科学信息,需要对其产地进行科学保护,并适当加以利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南京花化石产地,为以后的科研和科普提供助力,提出在乌龟山采石场设立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的设想。
乌龟山所在区域面积并不大,总面积(北至312国道、南到经天路、东界仙林湖路、西至山脚)约41万m2(图4),建议设立的保护区总面积约31万m2(白线区域),其中核心区约10万m2(黄线区域)。乌龟山采石场位于乌龟山的中央,面积小,环境相对封闭,管理难度小。

图4 建议的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示意图Fig. 4 Proposed simplified map of Nanjinganthus fossil conservation area
从保护对象、性质和功能看,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属于自然历史遗迹型古生物遗迹类保护区。该保护区的管理既需要专业力量的介入,也需要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具体操作可分3步:① 首先由南京市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南京市环保和栖霞区有关部门,关停乌龟山采石场,然后进行先期调研;② 会同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为主的科研单位,对南京花及其他伴生化石的赋存环境、赋存规律、发掘现状与潜力,以及保护区的规划设计等理论问题开展详细研究,提出初步方案;③ 报送省有关部门,建立“江苏省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设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进行管理和研究利用。
3.2 设立南京花研究站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是世界三大古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以古植物和古无脊椎动物为研究对象,具有深厚的科研背景和实力。南京花化石的发现也是该所近年完成的重要成果,基于此,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与该所进行合作,在此设立研究站,系统研究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以及南京地区1.7亿年前古环境和古生态等诸多重要科学问题。
3.3 建立科普教育基地
南京花化石产地位于南京近郊,交通便利,毗邻仙林大学城,科教资源丰富,是进行科普教育的良好场所。依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与科普实力,以南京花研究站为核心,结合周围的多所中小学,建立科普教育基地,开展地质古生物和自然科普教育。
连通汤山和栖霞山的江南—小野田铁路从化石产地边缘经过(图5)。随着以后江南-小野田水泥厂的关停,该铁路将停止矿石运输。这一国内罕见的900 mm轨距、单线、电气化“小铁轮”,可以改建为连通汤山(南京园博园)、仙林湖(万达茂)和栖霞山(文化休闲旅游度假区)三地,融公共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轨道交通,将汤山、青龙地铁小镇、仙林湖和栖霞山四大板块串连在一起,而乌龟山的南京花科普教育基地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图5 南京花化石产地与小野田铁路、栖霞山、仙林湖和汤山的位置关系图Fig. 5 Location map of Nanjinganthus fossil origin, Xiaoyetian Railway, Qixishan Mountain, Xinlinhu Lake and Tangshan Mountain
4 结 论
通过总结回顾早期被子植物南京花化石发现的重要意义及其产地的现状,结合古生物化石保护和利用的理论和实践,得出以下结论。
(1)南京花化石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化石,对破解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的达尔文“讨厌之谜”具有重要意义。
(2)鉴于南京花的重要性,应对其化石产地乌龟山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然而,该产地一直处于采石过程中,对化石资源的破坏严重,保护的需求十分紧迫。
(3)为更好地保护利用这一重要的自然遗产,政府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尽快与科研机构合作:① 建立江苏省南京花化石产地保护区;② 建立南京花研究站;③ 建立科普教育基地。
致 谢
论文撰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王鑫、陈孝政研究员,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8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峰博士等给予了热情指导,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