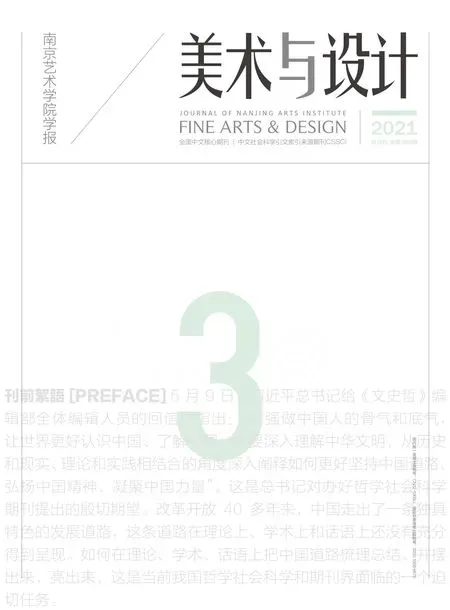“链接”
——以设计与舞蹈之名①
2021-07-21张应鲲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张应鲲(南京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舞蹈在源头上不是理智的而是酒神似的。它要获得最终的外观、形式和比例,这种无意识的活动就必须精确。”—— 奥斯卡·施莱默[1]159
一 、研究缘起
100年前,包豪斯这所为现代设计而创办的教育机构,首次以舞台工作坊的形式,实验性的将舞蹈中的“运动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穿着“笨拙”甚至略带几分“滑稽”戏服的设计专业的青年教师与学生,将自己运动中的身体作为研究空间关系的重要依据,以当时轰动一时的演出作品与“包豪斯舞台”相关的研究著作,第一次学理性地展示了设计专业与舞蹈专业跨学科研究的链接方式。令人遗憾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导致这些研究仅在包豪斯工作坊教学中短暂的实践,在其逐渐清晰并试图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时,随着工作坊主持人奥斯卡·施莱默的被迫离开戛然而止。
今天,当“跨学科”方式在各领域的研究中大行其道时,我们重新回顾这段似乎已被尘封近百年的“经典”,透过当代种种对包豪斯舞台“致敬”的复制式演出,不禁试问,看似“理性”的设计与“感性”的舞蹈结合的形式,是否只是特定时期中包豪斯艺术家们“乌托邦式”的实验?在当今的语境中,我们是否能够重拾大师的研究,在他们“设想”的方向中继续走下去?又或者,是否能够以新的形式、新的技术手段将设计与舞蹈的对话重新建立起来?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选择包括包豪斯舞台研究的开创者与践行者——奥斯卡·施莱默在内的四位“舞蹈”理论家作为特定研究案例,以他们的主要编舞理念与典型作品作为切入点,寻找其中与设计专业相同或相近的研究方法与表现形式,展开对“设计——舞蹈”链接点的探索。我们能够看到,四位大师在其个人背景、创作方式、作品呈现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可见“设计式”的工作方法与表达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他们的作品在关于“空间思维”方面上跨越时空的“相似”之处。也许正是基于此种“相似”,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辨析出设计思路介入舞蹈空间研究、舞蹈作品编创的过程与结果。
二、四个研究案例
(一)鲁道夫·冯·拉班与“拉班舞谱”
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匈牙利现代舞理论家、教育家,被誉为西方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有关“拉班舞谱”及“人体动力学”的相关研究,对20世纪至今的世界现代舞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界对拉班及其论著的研究众多,笔者不欲在此赘述,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涉及对拉班另一重身份的认知——“美术家”或是潜在的“设计师”:他曾就读于巴黎美术学院,青年时期对绘画、建筑、装饰艺术与舞台设计的学习使他能够对人体运动产生更为理性客观的理解,他试图从“空间”分析的角度研究舞蹈,这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同时为我们建立“设计——舞蹈”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1.舞谱及其图面表达
1928年,鲁道夫·冯·拉班受弗耶舞谱影响,创造出新的舞谱体系“拉班舞谱”,并以Kinetography[2]7-14命名,意为“动作书写”。拉班舞谱基于数学、人体解剖学、力学等相关理论,以一套严格、繁复的图式系统记录肢体动作、空间的位移路径以及各类动作的质感,使瞬间的运动状态得以“定格”于二维纸面,并在阅读与识别后能够准确重建于三维空间。
拉班自身的美术与设计素养使其能够以清晰严谨的图式系统,可视化复杂的肢体语言与空间位移,借鉴弗耶舞谱①18世纪法国人R.A弗耶发明的用曲线表示舞者走向,用符号沿曲线注名步法、手势和身段的较为实用的舞谱。的表示方法,他将“方向”“时间”“水平”和“符号在谱表上的位置代表不同身体部位”四者结合,记录各类舞蹈动作,完成不同种类舞蹈作品的准确再现。正如他在拉班舞蹈编导研究所的宣传手册上所写:“舞谱,允许使用一个简单的符号去记录芭蕾和表现主义舞蹈风格,独舞和群舞,舞剧,社交舞,体操动作组合,和运动及工作所使用的动作。”[2]7-14
值得注意的是,舞谱符号本身已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图像,其反映“运动、时间、空间”等信息的功能属性也使其呈现出设计图学的基本特征。(图1)

图1 拉班舞谱对动作的可视化呈现
2.“球体空间”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球体空间”概念的理解是认知拉班空间理论的基础,它极具“设计意识”地、直观建构出身体外围的隐性空间结构,在界定人体动作的中心点后,很容易表示出高、中、低三个运动平面及上下、左右、前后各空间向度的位置关系。如图所示(图2),围绕中心放射构成的27个基本方位点,可视为肢体末端能够触及的终点位置,与其说此隐性的结构框架及方位点是对肢体运动的主观限制,不如说其事实价值在于舞蹈运动过程中对空间方位的理性提示与科学引导。与之带来对单体动作的清晰定位,也使得舞者或研究者对群组动作的拆解分析、清晰表述、准确记录及有效重建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依据拉班的“二十面体及12个方位点”理论,舞者以“离心力的动作向外放射运动,或以向心力的动作向内回归”[3]的运动形式,能够呈现出更为繁复的空间建构的可能性与复杂多变的视觉样式。

图2 空间中的27个基本方位点与各空间向度示意
(二)奥斯卡·施莱默与“姿势舞蹈”
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德国画家、雕刻家、设计师,二战前在绘画、雕塑、剧场和舞蹈等多领域都曾发挥过源起性作用。
1920年至1929年,施莱默任教于包豪斯学院,作为形式大师先后主持多个工作坊,并使得舞台工作坊在包豪斯短暂的历史中留下耀眼的光芒。这个时期,施莱默以“编舞者”身份完成多部极具实验性的舞台作品,并开创性的以设计视角从极为敏锐的角度——“人与空间关系”——展开对舞蹈艺术的深入探索。
1.“包豪斯舞台”的实践
奥斯卡·施莱默致力于肢体抽象运动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运动的数理(关系)、[4]90机械化的关节、严格的节奏韵律与体操,发挥到极致,也可以通向一种艺术。在他的作品中,似乎很难准确获得清晰的剧情信息,相反,强调立体空间与运动空间的一系列方法持续刺激着观众的视感神经。例如,以金属线对角方式连接出线性空间网,以此将置入其中的运动人体视为空间的重要构成;在地面绘制几何图形,作为引导人体位移的不同空间路径;通过人体关节上连接的长棍,将人体结构放射至立体空间之中等等。当演出开始,运动的人体、几何形式的道具、变换的灯光、复杂的声效,共同交织出空间中的动态关系网,舞台似乎瞬间转化为一台独立运行的机器。
在其众多的舞台实验中,施莱默想要呈现的一直都是人与空间的对抗或调节关系,这种关系在多人出演的作品中则更为复杂,不同运动区域的舞者以各自的节拍和舞步,对演出场域(舞台)进行强势“侵占”或“干预”,构成蕴含“时间性”的空间结构体。正如1931年,他在日记中回忆:“仅仅通过舞者们有时间差的运动和整个过程中的流动状态,这个舞蹈就以惊人的强度表现了空间”。[1]365
1923年,上演于包豪斯周的作品《三元芭蕾》,较为明确地反映了包豪斯时期施莱默的创作与研究思路,舞者(通常为包豪斯学生)跟随舞台表面的平面几何以及运动中身体的立体几何,完成从诙谐到庄严的三幕表演。地板上的几何图形决定了舞者的运动路径,服装的几何结构限制或引导着肢体的运动模式,脚步行进是对场域的介入,肢体动作是对空间的切割与建构,作品无不显示出施莱默以“应对”空间为主的编舞思路。
2.“姿势舞蹈”的空间图式
“姿势舞蹈”是施莱默在德绍包豪斯最重要的空间“实验”之一,集中展示了这个时期他对“人与空间关系”深化研究的分析性思路。从现存的关于“姿势舞蹈”的运动图解及声音图解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施莱默对于舞台空间及声效结构的把控。
运动图解展示出多名舞者同时以不同节奏位移带来的复杂空间路径,正圆、中心点、中轴线、切线、螺旋线、弧线和谐交织的图形,构建出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箭头标示出运动方向,星号、圆点暗示舞者定位及停顿。笔者认为,这张图解所呈现的复杂信息量及其可视化瞬间运动的方式,甚至比舞蹈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艺术效果更具研究价值,它也同时印证了施莱默对运动空间建构的理性逻辑。除此之外,这张图式所绘优雅的图面结构、完美的图形比例,同时也反映出施莱默作为设计师的审美自觉。(图3)

图3 “姿势舞蹈”及其运动轨迹图解
声音图解是舞者发声、舞台声效的展示(图4)。图面显示出单词、发音符号、标点符号等元素的构造秩序,虽然各译本都保留原版未做翻译,但我们仍可以通过音符与停顿符号、转行格式判断音节的对位、协同、冲突等严谨的结构。在演出中,声音被用来辅助建构空间,强化肢体姿势的运动结构,是作品中的重要环节,从现存重演版本的视频影像中,可以印证这一点。

图4 “姿势舞蹈”声音图解
以“图纸”形式展示编舞思路,似乎较为清晰地反映了“设计师”施莱默的专业“自觉”,我们能够从中看出,施莱默尝试以空间图式的方法阐释作品中对“肢体运动”与“空间建构”关系的探讨。在说明两张图式时,施莱默认为这种方法无法提供绝对详尽的画面,因此仍然会失去对姿势(动作、表情)和高音的精确显现。但是,他同时指出,过于细节化的描述会使图式失去它的真正目的,即,使这些关系“清晰可辨”。[4]81笔者认为,比起对舞蹈表演形式的探索,施莱默关注的也许始终是有关“人与空间关系”的本质性论证。
(三)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与“小提琴相位”
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比利时舞蹈家、编舞家,罗莎舞团创始人。1982年,安娜的首部作品《相位——为莱许音乐所做的四篇章》震撼世界舞蹈界,至今仍被认为是“法兰德斯浪潮”①“法兰德斯浪潮”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比利时法兰德斯,以比利时编舞作品与剧场作品的兴起为代表。的开端。1983年,安娜创办著名的罗莎舞团。
在安娜与罗莎舞团的多数作品中,舞蹈语言设置极简且抽象,试图以肢体的运动探索舞蹈与音乐之间的对位关系,以复杂的空间调度与动作编排完成对音乐结构与语法的转译。值得关注的是,作品结构与形式本身所呈现的设计学特征,为我们探索“设计——舞蹈”的链接关系找到了极佳的切入点。
1.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作品的设计学特征
从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够较为清晰观测到她的编舞思路,这归因于作品中空间组织方式的清晰呈现。在多数时候,舞台上总是预先绘制出结构复杂、极具数学美感的几何图形,演出时舞者以身体循“迹”而动,或是以看似重复的个体单元动作或多人组合动作对其进行“加强”及“拓展”。由此,水平界面(舞台地面)的图形形态通过瞬时动作的重复性“堆叠”,得以转移至立体空间,继而建构出繁复的、瞬时性的“空间形体”。
这些预制的几何图形,根据不同的作品主题被设置为“直线”“圆形”“方形”“斐波那契数列构成的黄金螺旋”“螺旋与矩形的移位叠合”等结构复杂、且具有数学特征的图形样式。笔者认为,它们在安娜的作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直观反映出她在作品中试图传达的极为理性的美学秩序。安娜称这些图形为作品中的“基本几何设计”,它们将舞蹈动作框定在近乎严苛的图形结构之内,即便是看似即兴的运动形式,也遵循着这一“限定”式的规则,这使安娜的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极具设计特征的“结构”之美。(图5)

图5 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作品中的“基本几何设计”
同时,作品动作的编排似乎同样展示出清晰的“设计”意识,以安娜成名作《相位》①《相位》作品的创作来源于极简主义音乐家史蒂夫·莱奇的同名作品,由四部作品构成,分别为:《小提琴相位》《钢琴相位》《come out》《拍手音乐》。其中《小提琴相位》为独舞作品,其余均为两位舞者完成。为例,肢体动作在“重复”中创造“突变”,显示出特定运动规则中“秩序”与“冲突”混合的复杂美感。持续的重复,看似偶发的变化,重复有序的动作在空间中堆叠成形。在理解上,似乎可将这样的动作序列视作其编舞语汇中的“短句”。在持续的重复中,短句不断进行规律的变异、重组,并逐步增量为具有清晰逻辑及复杂结构的“长句”。在这样的“造句”(舞蹈)过程中,肢体运动轨迹反复叠加形成具有几何结构及抽象美感的空间形态,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极具设计特征的“形式”之美。
2.《小提琴相位》的空间特征
《小提琴相位》编舞灵感来源于极简主义音乐家史蒂夫·莱奇的同名乐曲,乐曲由莱奇采用(磁带循环创造的)“相位语法”编创,由此形成的结构及声效模式直接促成作品的编舞结构与表演方法。与《相位》系列四部作品中其他三部不同,《小提琴相位》是唯一采用单人舞者表演的作品,也是身体运动在“基本几何图形”上空间变化最为丰富的一部。我们看到,相同动作单元在不同空间方位上持续重复、叠加,速度与力度极为精准契合乐曲的旋律与节奏,不同动作单元之间的相互转换完美对应乐曲中四把小提琴演奏同一曲调的相互追逐、相位偏移。与其说这部作品是舞者随着乐曲舞蹈,不如说是舞者用身体运动完成对乐曲的可视化呈现。
《小提琴相位》设定的基本几何图形为“圆”,这与音乐本身的回旋曲结构直接相关。非常巧妙的是,演出场所被设置在沙地上,以便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几何图形在舞者脚下像“玫瑰”一样逐层展开,几何图形即是舞者运动所展示出来的空间位移路径。在最初的编舞笔记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关于这些图形的“设计”,安娜力图在纸面上预设出极为复杂的空间关系,并以图示的方法标注出运动的次序、方位,以及在各方位重复位移的次数。这种图示化的编舞方法,极易让人联想到上文所述施莱默“姿势舞蹈”中的运动图解。(图6)

图6 《小提琴相位》的空间位移路径
此外,《小提琴相位》在肢体运动的增量与变化中,同样体现出某种数学规律。舞蹈动作与音乐保持一致,以相位的原理出发,通过微小的变化开始,从最初与音乐完全同步的单元动作逐渐开始扩展,叠加中形成不断变化的形式。例如,如果为第一个单元动作命名为A,重复数次动作A后增加新动作B,随后重复A与B数次后去除A,建立B的重复,然后增加新动作C,建立B与C的重复,进一步去除B建立C的重复……,如下列组合:
“3×A,1×B,2×A,1×B,1×A,1×B,1×A,2×B,1×A,3×B,1×C,2×B,1×C,1×B,1×C,1×B,2×C,1×B,3×C, etc.”[5]
以此动作语法组织看似单纯的各单元动作,将身体各部位的瞬时运动在立体空间中逐渐编织成网,使《小提琴相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视觉效果及“形而上”的抽象美感与设计之美。
(四)威廉·弗赛斯与“同步对象”
威廉·弗赛斯(William Forsythe),美国舞蹈家、编舞家,被誉为当代芭蕾的旗帜性人物。
威廉·弗赛斯早期作品以拉班“球体空间”理论为基础,以身体运动在不同空间层次中创造动态的空间图形,在发掘这些图形关联时创造繁复的动作形式,使高雅的芭蕾舞式变得极具探索性。近年来,弗赛斯及其团队专注于将编舞视作“基本艺术组织原则”展开大量跨界尝试,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呈现的艺术效果,极具设计特征,可视为有关“设计——舞蹈”跨界研究的又一经典案例。
1.“同步对象”——弗赛斯的跨界探索
2009年,威廉·弗赛斯团队发布网络互动项目“同步对象”(Synchronous Objects),项目使用舞蹈表演、动作捕捉、数据演算、实体建构等多种方式重新解析弗赛斯2000年的作品《一道平面,重制版》(One Flat Thing,Reproduced)中复杂交错的编舞体系。“同步对象”研发团队体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质:除舞团成员外,项目合作方俄亥俄大学“艺术设计前沿媒体中心”(ACCAD)的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哲学、设计、建筑、编舞、信息、统计等多领域的研究机构。多学科协同介入,使舞作的肢体思想能够以一种崭新的、可视化方式呈现:一系列动态的三维视觉图像展示了编舞中各组织系统的交错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带来的复杂艺术美感。
在这些项目中,研究团队将舞蹈呈现为可视化交互界面,以便观者最大限度了解作品结构,与此同时,大量对运动方式的分析工具及相对应的延伸性设计工具被研发出来,团队试图最大限度的发掘项目在各领域的研究价值。
2.“同步对象”的作品研究方式
“同步对象”项目所展示的第一部分为“作品研究”,以“后台”界面的方式呈现了舞作《一道平面,重制版》的基本属性数据。如截图所示(图7),中心板块展示现场演出影像,右侧板块对应观看视角的转换模式,观众可任意切换“正视角度”“顶视角度”以及“近景视角”。底部板块以时间轴方式,清晰展示约15分钟时长的作品中极为庞大的信息数据。其中包括:17位舞者的出场顺序及时长、舞者之间的运动组合方式、舞蹈中呈现的25个动作主题、①威廉·弗赛斯公司成员通常把作品中固定运动的不同部分称为主题,并根据各主题出现的时间进行编号。动作主题的重复及数次被分解、多位舞者之间被规定的(或突发的)数个“结构即兴”表达、舞者动作同步的触发点②此处“触发点”指编舞中被设定好的动作模式,当有舞者启用这个动作模式,其他舞者将同步进行被设定的相同或不同的动作行为,因而造成一种视觉上的一致性。以及同步方式与时长等极为复杂的信息数据。左侧板块对应于时间轴,并将这些复杂信息以文字形式在演出播放时提示性输出。

图7 “同步对象”项目中的作品研究界面
“同步对象”极为大胆地为观众打开了一种“解密式”欣赏舞作的方式,或者说是分析舞作的方式。在这里,17位舞者繁复、优雅的动作组合被准确无误地转化为一串串具有关联性的编码结构,舞者之间隐秘的“结构即兴”以符号、色彩、连接线等形式标注,观舞过程中视觉难以瞬间捕捉的“同步”动作被数字图形清晰展示。在界面上尝试转换观看视角(点击视角选项),观者即刻便可得到更为全局(俯视)或更为微观(近景)的动作信息。
有趣的是,面对如此“和盘托出”式的演出表达,非但没有降低观者对作品的预期值,反而促使其主动思考并尝试理解《一道平面,重制版》复杂的运动体系及严密的编舞逻辑。显然,研究团队试图以极为“设计化”的输出方式,改变观者对舞蹈作品常规的“审美式”欣赏,从而激发出个人对作品的主观“探索式”体验 。
3.“同步对象”作为设计工具
关于“同步对象”,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其为促发新的设计方式、思维方式及审美方式产生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就此,项目联合创意总监诺拉•祖尼加•肖(Norah Zuniga Shaw)在研究中阐述:“我们借鉴了许多学科的方法——舞蹈、设计、计算机科学、地理和统计学——并在必要时发明了新的方法……我们有能力将这种严格的数据收集过程带入新的创作空间。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择、美学和分析,为正在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与研究产生新的可能性。”[6]在此理念上,“同步对象”最终产生了一系列子项目,包括:动作可视化、运动数据分析、图形生成以及三维形体建构等。
项目研发机构之一俄亥俄州诺尔顿建筑学院,对舞作中25个编舞主题进行取样研究,将其各自属性数据与对应形态展开分析,并以分析结果作用于拟设的空间体块,最终生成具有“表演性”特征的系列空间形体。研发团体试图以此模式探索舞蹈肢体运动的属性数据创建建筑/家具形态的可能性。
“Performative Architecture/Matrix”项目集中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如图所示(图8),每一组图像都来源于对舞蹈中特定主题的诠释,同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体块在特定时间内的“动态”特征,此外,通过对各主题定性特征的捕捉,最终的各组空间形体在形态与材质上反映出明显的差异性。

图8 “Performative Architecture/Matrix”项目以计算机数据创建建筑及家具形态
研发团队曾对“Performative Architecture/Matrix”项目进行了如下描述:“我们对舞蹈的每个主题进行分析,并将其翻译成带有描述的正式图表。通过加法、减法和组合的过程,产生了形式的目录。结合计算机数控铣削纹理产生的变化,我们创造了超过1000种可能的形式。”[6]
从这个项目中,我们切实看到了“同步对象”在对舞蹈作品研究之外,同时作为设计工具的可能性,令人惊喜的是,“同步对象”以一种极为科学的、开放的、系统的研究方式展开了对设计学科与舞蹈学科链接关系全新的探讨模式。
结 语
1927年,奥斯卡·施莱默在给好友奥托·迈耶的信中写道:“我每天都花时间和他(指挥家赫尔曼·舍尔兴)一起研究‘音乐——舞蹈——数字命理学’……我得说,大赋格在主题上的发展和多样的变化,加上戏剧化的处理手法,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震撼。我想把它的乐符表现成图形,这想法让我不能自已。……他建议把这个赋格转换成舞蹈时不要用音乐,让舞者跟随他们自己脑海里的音乐跳,会有很棒的效果……”[1]265
也许是偶然,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在安娜·特蕾莎·姬尔美可的作品中看到当年令施莱默无比振奋的构想,无论是身体对赋格的演绎,还是由地面几何形决定的舞者运动路径,甚至是动作中蕴含的数学逻辑,安娜都以极具个人化特征的形式表达出来。与当年不同的是,这次表演的是真正的“舞者”(而不再是包豪斯学校那群热情而勇敢的舞蹈“爱好者”了)。
同样令人嗟叹的是,威廉·弗赛斯团队在新的千年以数字技术将舞者运动中建构的“隐性”空间结构完整呈现在屏幕上,而在20世纪初,拉班曾试图以质朴的手绘图示展示极为相近的内容,施莱默甚至设想在舞台上拉出实体的线来呈现这种身体外围隐性的空间结构。
或许,正如篇首所述:“他们的作品在空间思维方面跨越时空的相似”,由此引发这些作品产生无形的却又可感知的“关联”。与此同时,他们的作品在编创与表达上呈现的种种设计化特征,导致这种关联的建立与设计式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或许,未来我们需要时间与大量的实践去证明这种和设计思维相关的隐性关联,它能够成为我们展开“设计——舞蹈”之间链接关系研究的关键线索。幸运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终于有条件在奥斯卡·施莱默开启的道路上持续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