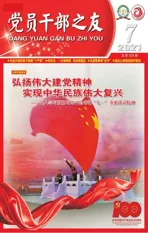延安答卷的奥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上)
2021-07-19厉彦林
□ 厉彦林

孙大勇/摄影
故事一:“陈嘉庚之问”。
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社会动乱的局面,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与抗争,渴望寻找新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未能实现民族独立的希望,所有这些都没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一批探求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开始觉悟。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诞生之日就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题。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红军初到陕北,这里战乱频仍、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如何发展和巩固根据地、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成为我们党的新考题。1940年陈嘉庚等爱国华侨冲破国民党当局重重阻碍来到延安,看到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及与民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有一天黄昏,夕阳温煦的光辉挥洒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门前的黄土地上,延水河畔时而传来阵阵动人心弦的歌声。会谈结束,毛泽东凑了一顿饭,在窑洞门外院内露天招待陈嘉庚。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桌面陈旧不光洁,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毛泽东仅以白菜、咸饭相待,还有一盆鸡汤。毛泽东高兴地解释说:“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有远方贵客,送给我的。”陈嘉庚这位腰缠万贯却以艰苦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的华侨富翁,十分高兴,他对比国共两党,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延安地瘠人贫,不如重庆物资丰富,共产党即使想搞腐败,也没条件。如果将来抗战胜利,打下富庶之地,共产党能否将现在这种气象传袭下去?”陈嘉庚的疑问留给毛泽东深深的思索。这其实已经涉及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了。
故事二:《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脱稿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为考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致明朝灭亡300周年而作的长文,3月19日在《新华日报》连载。300年前的3月19日正是“闯王”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标志明朝灭亡的那一天。文章中用较多笔墨叙述了李自成的优长劣短,认为李自成进京42 天就迅速败退,是由于胜利后军队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与享乐主义。国民党方面看到此文后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
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早在1926年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就开始关注了。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提到明末农民起义。正当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正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防止骄傲情绪滋长时,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统总结,恰恰提供了极好的反面历史参照,于是他指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文件学习。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意谈到他让全党学习的用心:“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他还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据一些老干部回忆:“当年,差不多每个人都以李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做对照检查,并且揭露出少数已经腐化堕落的人,纯洁了革命队伍。大家懂得了‘不忘艰苦奋斗,继续战斗’的道理。”此后,陕甘宁边区相继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等法规,开始探索从民主法治上加强廉政建设的途径。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1945年前后,毛泽东对廉洁政治、从严治党的思考已日渐系统。正如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同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窑洞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毛泽东这种理论上的升华,与受《甲申三百年祭》的启发有一定关系。
故事三:延安“窑洞对”。
1945年7月1日 上 午9 时,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当天下午1 时许安全到达目的地,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的热烈欢迎,随后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
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也很舒心。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杨家岭窑洞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黄炎培从延安回来后撰写了一本书《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回忆了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各种污蔑和攻击,记录了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交谈内容。
毛泽东问黄炎培:“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完黄炎培这一番耿耿诤言,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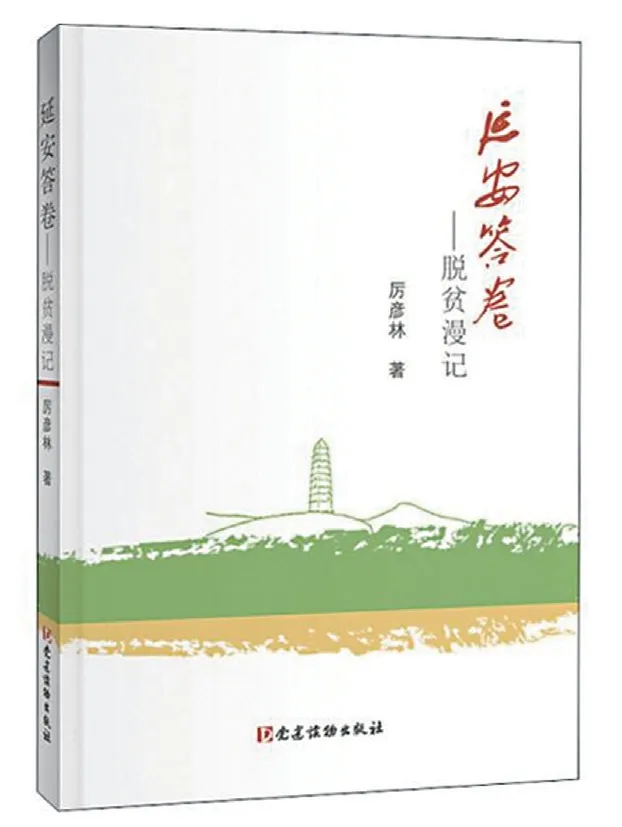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被称为“窑洞对”,被后人作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这段历史佳话,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厚友谊,反映得淋漓尽致。“窑洞对”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善意的警告和长鸣的警钟,它庄严宣示: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批评和监督政府,紧紧依靠人民实现民主执政,这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