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思考音乐:作曲家梁雷访谈
2021-07-12文/陈涵
文/陈 涵

梁雷,著名美籍华人作曲家,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前音乐系主任、作曲学科主任。梁雷近年获多项奖项,包括罗马奖、古根海姆奖、科普兰奖、美国国家艺术基金奖等。他的萨克斯与交响乐队作品《潇湘》获2015年普利策作曲奖最终提名。纽约爱乐、波士顿现代交响乐团、柏林爱乐室内乐团、钢琴家陈必先、琵琶演奏家吴蛮等著名音乐团体与演奏家曾委约他创作。他的作品包括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民族器乐、电子音乐、室内歌剧等70 余部,他的全部作品由纽约朔特音乐公司出版。2018年梁雷被聘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高通中心艺术研究员,同年被聘为星海音乐学院“周文中音乐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和艺术总监。
引言:2021年1月14日,青年钢琴家陈涵对作曲家梁雷进行了线上采访。此次采访录像收录于《迁徙之乐》系列影片的第三集。《迁徙之乐》由陈涵于年前开启,每集介绍一位移民美国的作曲家,通过采访及演奏的方式讲述了各自的移民故事并反映了当代音乐的文化多样性。在介绍梁雷的第三集当中,除了以下采访,还包括了其钢琴作品《月亮飘过来了》的演奏视频。采访以英文进行,由陈涵记录并翻译成中文。

◎2019年8月15日,陈涵(右)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演奏梁雷《我的窗》后与作曲家合影
C:陈 涵
L:梁 雷
C:梁老师好!2020年刚过去,能与我们聊聊这一年疫情下,您的生活状态如何?
L:陈涵你好!啊,这真是艰难的一年。我还算比较幸运,毕竟我教书的加州大学有很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课程在疫情下都顺利进行。但我的不少朋友受到了疫情的冲击,必须面对音乐演出活动取消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在家照顾孩子的额外负担。往正面想,这次疫情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能时刻与儿子在一起。我们做了很多疫情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包括在院子里打羽毛球,或是每天一起散步。疫情的限制反而使我能更多地与儿子相处,这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时光。
C:那真是美好的一段时光。儿子是您创作的灵感源泉,比如您2015年的钢琴作品《月亮飘过来了》,这个标题就是他五岁时无意间说出来的一句话。可以聊聊儿子给您带来的影响吗?
L:我想,将生命所承受的重量投入创作之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吧!自从我的儿子Albert 出生后——不,甚至在他出生前,他就是我的灵感源泉了。我为他写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首受到纽约爱乐乐团委托的创作,使用了18 支弦乐器,叫作《境》(Verge),代表他快要出生了。我写了至少五首受我儿子启发的作品,包括你所说的《月亮飘过来了》。在他五岁时,他开始会说一些像这样片段的话。有一天在傍晚回家时,他在车上望着月亮说:“爸爸,月亮飘过来了!”我心想:这真是充满诗意的一句话啊!(笑)
我必须要说,我们从小学习、成长并发展,但到头来,最终还是要追求孩子的那种天真自然的创造状态。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多少会失去最具创造力的自由。但当我看着Albert 在大提琴上即兴演奏创造出新奇声音时,想象与现实融为了一体。对他来说,想象即是现实。而那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吗?
C:是的,这让我想起画家马蒂斯及毕加索在晚期的创作,他们都越发向儿童的笔法靠近。毕加索甚至有句名言说:“我花了四年画得像拉斐尔,但我花了一辈子才画得像一个孩子。”回到《月亮飘过来了》,在您创作这首作品时,灵感不仅来自于您的儿子,还来自于您与加州高通研究所的合作。可以谈谈您们的研究项目吗?
L:我们在人生中会时不时无意地留下种子。有时候直到它成长为参天大树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们有多重要。对我来说,这颗无意的种子就是艺术家黄宾虹。黄宾虹是中国最伟大的山水画家及书法家之一,我通过其它画家认识了他。例如著名画家潘天寿就经常敬畏地提及黄宾虹,而我对潘天寿的景仰使我对黄宾虹产生了好奇。我心想,为什么我尊敬的画家总是不停地讲到黄宾虹呢?潘天寿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名家,但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人认可黄宾虹,其作品也很难找到,出版的画册有限。我们知道伟大的钢琴家傅聪最近刚去世,令人很伤心。

◎ 2009年,纽约爱乐首演梁雷作品
C:非常令人惋惜。
梁:他的父亲傅雷,一名著名翻译家及学者,曾是黄宾虹的支持者。他是最早认识到黄宾虹重要性的学者之一,当时别人都不太了解其作品。黄宾虹有着相当长的职业生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而他的成熟画风是七十岁时才发展出来的。无论如何,这都是我在大学时无意的邂逅,因为当时我在图书馆里手抄这些画家的文献,它们使我甚是着迷。这颗种子便种在了我心里。虽然我不知道它会带我去向何方,但我感觉得到它们是有一定意义的。认识到黄宾虹的作品像是给了我一把开启大门的钥匙:通过研读他的文献,我学习到了中国传统画派的复杂性、原理及丰富程度,也学习分辩高低的眼力。后来,我甚至将他所阐述的绘画技巧转化成我的音乐想法,比如我的配器法,就是向黄宾虹学习而来的。
C:这也太神奇了,您是怎么进行跨领域转化的?
梁:大多国画都只用几种层次与墨色,山水画更是注重其简洁性。黄宾虹则非常不同,我们知道他会在每幅画卷上叠加五十到六十层的水墨。除了他之外很少人这么做,这就令他与其他画家拉开距离。我有幸被高通研究所聘请为驻地作曲家时,我便决定用科技来分析黄宾虹的作品,而在这段时间的研究里我们也有相当有趣的发现。现在人们已经越发了解黄宾虹的作品,其价格也水涨船高,但我不热心其价格高低,我只知道我们还有更多要向他学习的地方,也有更多人会从中获得灵感。

◎ 2021年,梁雷获得格文美尔大奖奖章
C:太有趣了!我对于您从别的艺术领域来摄取养分感到着迷。您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如此之深,不知道对于当今的中国艺术与音乐有何看法?
梁:噢,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主题,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中国”对于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当然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中国也会相当不同。我是在文革的最后几年间出生的。以我对中国音乐及历史的理解,那是一段最脆弱的时期,一段在历史长河中最惨烈的自我毁灭时期。当我开始接受教育时,许多丰富的传统已经濒临瓦解。以前面谈到的黄宾虹为例,他身处的文化底蕴已不复存在了。他那个时代的画家们能自己创作题画诗,也是造诣深厚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们是所谓的文人。他们之后,我们仍有许多优秀的画家,但题画诗的能力已经几乎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孕育出题画诗的那个文化已经破碎了。
音乐也是一样的。我有幸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大,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早的十七年时光,相邻其图书馆所收藏的各种中国音乐历史音响资料。我在如此年轻时就能接触到这些音乐是相当幸运的,但直到我离开中国后我才知道它们对我有多重要!我们或多或少会有这种体验:在背井离乡后,我们开始思考“故乡”、“归属”以及“家园”的真正含义。那便是我在十七岁时离开中国的体验。

◎ 2019年,梁雷与海洋研究专家Josh Jones 合作
C:您是在十七岁时离开中国的,当时是1990年。那时出国的感受如何?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要做出留学的决定是什么样子的。
梁:是的,那时我的父母做出了相当勇敢的决定。他们当时认为出国能给我更好的教育及未来,从而对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当然,那时的中国远不如今天富有,我记得一段时间我每天只有一美元的饭钱。这对于今天的留学生有点难以想象,但那就是我当时的生活。我先是去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读了两年高中,期间我经常去得克萨斯大学的图书馆。当时对我冲击最深的是我第一次走进开书架式图书馆的那一刻,那真是令我毕生难忘!那之前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读,借书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首先书就很少,再来借书又必须通过图书管员,而他们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但图书馆是思想革命的起点,因为它代表了知识。若你不读书,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过去、历史、以及真相?所以当我在得克萨斯州第一次走进开放式图书馆时,天哪,我可以阅读各种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有英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
我了解到知识的力量与能力:如果你能够获得足够信息与不同的观点,你可以重建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因此我经常这么说:我在离开中国后发现了中国!(微笑)
当然我很幸运,在得州两年后我去了波士顿,我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度过了数不清的时光。从那时起,我在赵如兰教授家住了八年。她是哈佛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我将她视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她有非常珍贵的图书收藏,所以我基本上就住在一个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实在学到了太多的东西,那真是我特别的幸运。人们常说自己是在某所学校接受教育、获得文凭。而对我来说,我是在开架式图书馆以及赵如兰教授的私人图书收藏里获得了真正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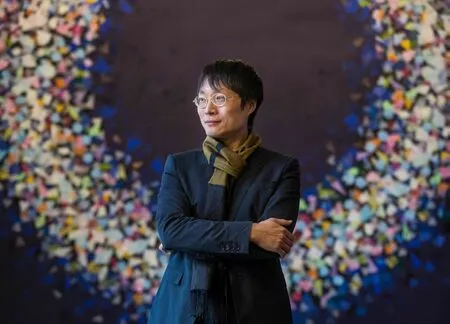
◎ 2016年,纽约时报专访梁雷时拍摄
C:2020年,一本关于您的书《百川汇流的声景:作曲家梁雷的人文叙事》(洛秦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在里面读到了许多您留学时的心路历程,很是感慨。在书中有一个概念非常打动我,那就是“自力”。您写道:“‘自力’是指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精神的归宿,不依赖外界的承认,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作为老师,您如何引导您的学生取得“自力”?
梁:当然,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衡量标准,不是吗?我们要生存、要过上好生活、还要在竞争激烈的世间取得成就。若是我的学生取得成就或是奖项,我会为他们感到非常开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么做自我评判。我很幸运,因为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奖项与认可,但是内心深处我保有自己的标准和榜样。我面对这些前人,扪心自问:我做得如何?我是否对已经完成的一些工作感到满意?然而我必须说我对自己并不满意。(笑)
黄宾虹先生是在七十岁后才找到自己绘画的个人风格的。他最精彩的作品,也是我用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分析的作品,是在他八十七岁,已经失明后才创作出的绘画。那真是最神奇的绘画作品集!就像是贝多芬失聪后的作品。当我想到黄先生时,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只是比他幸运。当黄宾虹在创作这些重要作品时,很少有人关注他。当他撰写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绘画史的文章,以及对绘画技术所做的分析时,年轻人并没有追随他,他甚至不受欢迎,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书呆子。只有像傅雷这样的少数人会认识到黄宾虹是多么的重要。但黄宾虹还是坚持了下来,我认为他在将来还会持续被认可,成为过去二百年来中国传统中最伟大的艺术家。这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理解其作品,因为他的贡献如此深远和巨大,以至于实际上很少人可以理解和欣赏,所以这需要点时间。当我看着他的作品,我只能赞叹不已,将其视为最高的一座顶峰使我终生追求。
总会有各种领悟驱使我向我崇拜的伟人们看齐,而他们的成就并不被奖项所定义,他们甚至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想想那些我们崇拜的伟大音乐家们吧!我想到的是蒙泰威尔第、巴赫等人,这些伟人们或许生活得不如我们,但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样的音乐,而我们又创造出了什么样的音乐?我只能感叹:天啊,让我们再更努力一些吧!
C:感谢您如此激励人心的分享!作为一名钢琴家,我从小的经历就是不断地受到评价。这种比较心理以及永远无法满足的外在评价伴随着我求学的岁月。在过去一年,感谢于疫情,使我能停下来反思这种心态,并学习如何自己创建出一套自我评价系统。我也希望在未来能取得您所说的“自力”。
梁:那真是太好了!我必须说,取得“自力”后你会感到自我解放。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这么做,只是我从中收获了许多。当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那也是个充满竞争的环境,有各种音乐节及比赛可以参加。我基本上不怎么参加那些活动,不知为何比赛竞争就是不那么吸引我。但我当时通过对蒙古音乐的研究找到了我的精神向导。
我从小对蒙古音乐感兴趣,特别是对蒙古音乐家色拉西,一位仅凭自身便奠定了一代演奏风格的大师。我当时参与发掘保护并重新发行其历史录音的整个过程。他不仅不是汉族人,我们语言不通,他还演奏一件基本绝传的乐器;而我在一个充满现代音乐的环境里,学习当代技巧及前卫风格。然而,有色拉西在我的生命中拯救了我。无论我写什么样的音乐,我把色拉西视为我的精神导师。我没兴趣取悦现实中可能出现的评委。我只想着把我的音乐呈现给色拉西,我想知道他会对其有何评价。他不会知道当代音乐风格,也不会在意我们怎么用语言描述音乐。当然,批判性思维是重要的,但我们也不能被语言困住。我若要把音乐呈现给色拉西,我该怎么做?他会觉得我的音乐有想法吗?他会为之动容吗?这样想之后,我就从当下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了,因为我找到了内心的衡量标准,而不是依赖于外在的评判。总而言之,“自力”帮助了我许多,而我到今天仍然督促我的学生们要把他们崇拜的大师放在心里,与之相伴,才能继续前行。(微笑)
C:(鼓掌)太感人了,我不知不觉就拍起手来了。最后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您在这里生活了超过三十年,是什么体会呢?
梁:我觉得我身处在一个能让我进行自由实验的环境里。我不想被任何名称束缚自己,甚至希望不断给我做的工作找到新的可能。我很幸运在一个能让我超越音乐学院规范并重新建筑我的音乐的环境里。通过研究黄宾虹的作品,我与大学里的一批科学家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及合作伙伴,而合作的喜悦带来了更多新项目以及新成员,至此已扩展到了海洋学及地质学等领域。
这样的机会让我能重新思考音乐,以及其在当今社会的意义。音乐创作为什么在当今这社会有重要性?音乐创作是否能反映时事?特别是反映我们的生活状态?我通过与科学家的合作来探讨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把工作环境称为一个生态环境。就如同在一个园林里,我们在此尝试不同的品种与创新,提供养分与阳光,通过共同的努力寻找发明新的工具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保持音乐这个艺术形式与时代共存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