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泳与截当
——《一花一世界》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纹理
2021-07-12程乐松
◇ 程乐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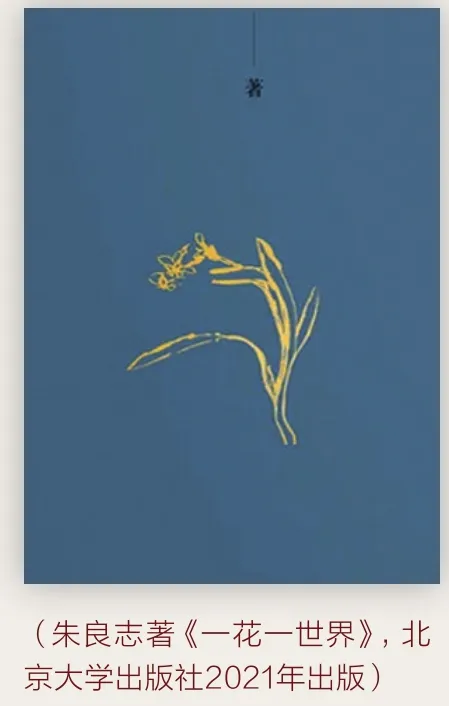
宗白华先生眼中,美的感受是不堪筹划的随性、无须苦思的豁然。如同散步一样,“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鲜花与燕石,其妙处在偶尔,而不在其美艳与异型。这样的感受本来就是从自然之中流溢出来的,等待着能感能知的“我”的悠游和徜徉中的感应与共鸣。其中既有活泼泼融入天地的自我,也有超迈于一己之限的精神。
如果美的呈现是基于自我与自然的共在与共鸣,那么艺术就是从感受到表达中被揭显出来和具象起来的,我与天地万物的和应。艺术里的精神也需要以揭显与具象为载体,体会和默契这样的精神世界,始终在生命与自然的交融鸣应中入手着眼,却无法析取任何成规定式。可感却难言的艺术精神却并不是无迹可寻的杳冥,而是在无限丰富的自然与活力充沛的主体之间开放且绵延的摩挲中映透出纹理。这种纹理不是基于有效论证的体系与命题结构,而是反复涵泳与多视角抵近在作品中体现的艺术家生命感受。
从美的呈现到艺术的精神,横亘着人的审美经验与“造作”实践。如果美是自然的(natural)或自发的(spontaneous),那么审美就是感受性的(perceptual),而艺术则是表达性(expressive)和实践性的(performative)。艺术精神是凝结在实践性产物中的感受性内容,而艺术作品又不是艺术精神的全部载体。艺术创作者对艺术创作过程及其技巧的反思、观赏者对于审美感受的涵泳,都构成了艺术精神的二次表达。
这样一来,艺术精神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要做分析性的建构,说明从自然的美到艺术精神的形成的内在机制,就不得不面对层层细分、条理细密的论证和描述。然而,朱良志老师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方法论的空间,即以截当的方式描绘艺术精神中的生命感受的当下性与自足性。纹理呈现而非结构分析的进路,让艺术哲学呈现了活泼泼的体验感和当下性,更彰显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生命底色。
《一花一世界》中所见的艺术哲学将生命感受的中国性与艺术表达的丰富性结合起来,以“截当立住,涵泳成说”的方式揭示了传统中国艺术精神中“在世之我”的即时体验与天地阔落的永恒之维的互现,以及在这一图景中呈现于艺术创作技巧、思想主题与价值诠释中的主体性紧张。截当直指的透彻和锋利很大程度上打断或暂停了习焉不察的俗见与常理,回到当下圆满、自性真纯的浑然与质朴的心灵状态;立事成例的敷衍让艺术透出从观念到技法的跨世代的精神纹理,不绝如缕的绵延感和截断俗见的断裂性构成了相互照应的两个层次。与此同时,从诗画到草木、从时空到境界的多视角抵近,让信手拈来的叙述构成了对思想主题的反复涵泳,不断抽取和淬炼出艺术精神的醇然与浑厚。由此,当下圆满的自我真性、即时体验的永恒绵延一起构成了悬置在艺术表达和诠释之上、随时可能被激活的超然视角。超然于彼此是非的二元结构,进入浑然的体验和当下的自足。从体验和生命精神出发突破自我的囿限,对浑然的觉解让自我不滞于横亘的他者及外物,又不致在悠游自然中彻底丧失活泼的精神和感受力。这样的精神状态显然并不是被设定了的精神生活目标,也不是所谓艺术修养工夫的必然效验,而是用思想的力量扯出的渊鍳。悬置的理想超然境界让我们始终保持着对自我囿限的敏感和反思性自觉。
朱良志老师强调的是一种觉解了的生命认知,对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对永恒之维的尊重。唯有突破俗常的自我,自觉地将有限的我投入到浑然之中,才能回归与天地同在的活泼状态之中。《一花一世界》的艺术哲学是从中国艺术精神中生发出来的一种“主体哲学”建构,其核心关切是:他者的横亘何以成为自我的阈限。截断浑然之化才让他者与自我对举起来,互不相容的彼此之别,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对他者的价值判断逐步将自我限制起来,让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逐步失去了亲切感与整全性。
《一花一世界》以截当的方式直指艺术精神主题,以量、名、全、时、境、性、美、情为经,以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觉解为纬,形成骨架与羽翼,在涵泳反复中抵近艺术精神的纹理。从物别到时空,从境界成立到价值评判,始终坚持着“否定的辩证”,在巨大的语义张力之中超越俗常的价值阈限和认知架构。价值与认知的结构让自我疏离了置身其中的世界,从而从“在其中”的本然状态转变为“观看者”的对举状态。这样的思想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对象本身存在的给定性和现实性,而是重新将其存在悬置起来,等待观察者的评判乃至证成。对象化的操作截断的是自我与世界的浑然关系,形成了自我的双重外在性,既有自我内部的对象化和疏离,也包含了世界对于自我而言的外在化。
自我与世界的原初状态是交融和互显的,自我在世界之中,世界才一时明亮起来。一个虚怀的自我才能融入世界的浑然之中,而世界中生命与存在的本然自足状态只有在不分彼此的状态下才是洞彻分明的。正如朱良志老师强调的那样,“让世界敞亮”,世界的敞亮是一种回归,而不是否定,更不是建构。从这一点上说,理论本身的建构性和体系性要求就被超越了。“这种哲学不是再现或者表现,而是呈现,让世界依其真性而自在呈现。”不妨说,艺术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引致或造就了某种哲学反思的方向,并且保持了自我理解的开放性,自我与世界的浑然性,乃至自身经验的未完成性。
当然,在指向艺术精神的体会与涵泳之中,并不要否定秩序和价值本身,而是要超越一种遮蔽和扭曲的状态。对截断和遮蔽状态的反复提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当下圆满的体验哲学’是一种反知识、反秩序、反传统、反法度的思想观念,它只是在知识、秩序之外,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回向生命本身和体验自足的当下,使得艺术精神指向了一种哲学玄思和人生境界。这也是中国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实践和精神修养的独特价值。
阐释上述的立场,需要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和叙述方式。《一花一世界》中的经纬互显、截当骨架与事理羽翼的叙述结构很大程度上拓展并实现了上述立场和艺术精神境界的可言说性。首先以险峻和直截的方式提出核心的观点,这些观点并非理论命题,而是简洁有力的判断,精神实践的现场,乃至艺术作品中所见的创作感受。生动活泼却景色各异的艺术精神的现场,让同一精神主题的闪现变得十分丰富且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构成了涵泳反复的绵延感,以及跨越历史、时代和主体差异的连贯性。从这个意义上凸显了艺术精神的奠基性与共通性,从而为艺术精神的哲学性提供了规范性的力量,即任何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现场都指向了某种最根本的关切,并朝向同样的境界和精神态度。
在表达上通过语义的对举实现了精神表达的迂回,将反思和精神感悟的连贯性落实在持续的否定和不断的回溯之上。在局促与自足、支离与大全、残缺与圆满、破碎与浑一的几组对举之中,语义上的差异和感受上的转化共同提示了视角转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不同的着眼处,自足与局促等之间的“矛盾”或差异并不是固然和本质的,而是因顺和表象的。在此基础上,重组、整体、圆满与联系等“一偏之见”和价值评判标准都需要重新反思。来自艺术精神实践的体悟和感受在表达上就不得不依赖某种语义的对举和持续的回溯。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怀古的非历史性”,将历史性做了两重区分,古意与史实不可等量齐观,“站在历史的高岸上,洞察生命真性,在非历史中寄托深层的历史感。怀古,是为了抹去古今相对的时间绵延和情理缠绕,呈现亘古不变的生命真实”。不可言说的体悟在言外的余味被独特的言说方式提示并强调出来了。在语义层次的抽绎和对举中,不可言说的,以一种不言自明、言尽意续的方式被指呈出来。在表达上的绵延和迂回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也指出了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的回返性。对于传统中国的艺术精神实践而言,抽象和虚悬的道并不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具体而微、严苛全面的规则或理论的起点,而是直接在给定了的生命当下的圆满体验中找到自身的本心。正如朱良志老师在论及石涛时强调的那样,“一画,不是要归于某个抽象的道,某个更合理的、具有决定性的真理,而是将一切创造的起点交给生命真性,交给艺术家集纳于平素、濬发于当下的直接体悟”。艺术家的本心并不源自抽象的道和具体的技,而是平时累积且随感而应的觉解和体悟。觉解与本心互相发明才能保障从真性中体会生命与自然的直截性和了悟力。
从语境化的层叠、否定的迂回,以及哲学表达中的回返(回溯)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一花一世界》的涵泳之道。截当的断言提供了涵泳的前提,而涵泳则不断多视角抵近的方式反复闪现艺术精神的纹理和实践指向的境界与体验。涵泳的迂回和绵密总需要在艺术创作的整体语境中展开。艺术作品并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形质、可供分析的具体对象,而是整全的事件和持续展开的当下。就创作者而言,作品是表达当下体验与即时本心的载体,创作则是一个精神实践的现场。
饱含着艺术精神的作品,其内蕴的精神价值和当下圆满的自足来自创作者“在场的自忘”,体贴当下圆满与自我真性的融合,在投身与自忘之间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主体性觉解。进入作品的观看或欣赏,也是在以切近的方式感受自忘和自适的状态,探索一己真心的觉醒和发明。艺术精神的纹理归根结底并不是物的状貌与时的精确,而是人心的真性与浑然的自适,只有在持续展开并始终活泼的精神现场才能闪现当下圆满的境界。天地之间的维度是艺术精神展开的情景,而本心当下的体验则是在情景中成就的主体性的自足。
《一花一世界》中所见的艺术精神的哲学反思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精神的热忱和对自我界限的敏感,这样的敏感来自艺术的实践性、作为行动现场的当下性,以及作品激生的共情与理解体验的绵延性。自我,抑或主体,在艺术的语境中完成了双重的超越:既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共情的方式实现了创作当下整全体验与精神实践的“永恒的现场感”;也实现了对自我与他者二元结构的超越,从浑然与圆满的角度理解自我向他者乃至世界的敞开,并在敞开中实现自我的觉解,而非遗忘。
朱良志老师对于这种现场感和事件性的强调是在截当为经的断言基础上,择取中国艺术史中的人物、话语、作品乃至历史现场,形成了对截当的贯穿性连缀。无论是东坡还是倪瓒,王维还是石涛,他都尝试回到艺术家的生命现场和当下体验中找到与艺术精神的纹理共轭之处。以此说明传统中国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精神态度与境界追求的丰富性中始终若隐若现的主题和主线。
“一朵小花”的自在与自足虽不能目为中国艺术精神的全部根底或完全底色,却可以提供一种回向艺术精神实践现场的视角。当下圆满的“非历史性”与万物块然的“自性自足”,加上真性为美的无量世界,这些都可以从“一朵小花”中抽绎敷衍出来。《一花一世界》就是用“一朵小花”引出了整个世界与不断闪现的精神事件的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良志老师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理解的视角,也不仅仅是艺术精神的解说,而是一种贴近艺术的哲学方法。
“一花一世界”之所以可以成为贴近艺术的哲学方法,是因为她充分体现了艺术精神的中国性,其精神的脉络和纹理始终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涵泳与截当。在艺术作品中闪现的艺术精神的纹理只能截当直指,截当直指的艺术精神更不能用概念命题的方式展开论证,建立一个外在于自我体验的理路和框架,只能在不断回向的艺术创作事件的现场和艺术家精神生活的当下,用当下与现场为背景涵泳反复。这种方式不是以理论的细密和论证的严谨保持反思者或理解者的外在性,而是对所有人的邀约和迎请。当下和现场中的即时体验与共情,以投身的方式完成自忘,才能进入到艺术精神的境界之中,发现原本被欲望、知识、情感遮蔽了的本心。不妨说,这样的邀约,其目标不是对艺术的理解,而是重新发现自我。
朱良志老师以丰富且具有内在理路的艺术史现场及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营造了一种哲学反思的语境和空间。只有在艺术精神的纹理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反思视角的自我的觉解与当下圆满的体验;只有在自我觉解和当下圆满的纹理中,我们才能体会到作为精神世界载体的艺术作品的内涵与审美意蕴。《一花一世界》以超脱二元的方式克服主客、大小、名质等的对举,也同时超越了境界与世界的对举。境界与世界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两种单向的通路,而是一种自我觉解的迂回,让当下圆满的自我觉解也同时将世界的万物改造为浑然的亲切,并且在自适与自足中将世界改造为境界,将境界回向世界。正如朱老师强调的那样,“艺术的超越境界,于凡俗中成就,在亲近生活中践行”。
《一花一世界》的开头就引述了倪瓒的小诗作为全书的题眼:“兰生幽谷中,倒影还自照。无人作妍暖,春风发微笑。”野花的自足并不需要外在的肯定,而是来自当下圆满的给定现实,受此启发,从朱良志老师在宏阔深湛的艺术史修养之上展开的倏忽来去又悠然自在的哲学反思出发。本文展开的讨论也是如“一朵小花”的当下一样,以思考和表达力的穷尽展现了理解力与思想性的残缺,何尝不是另一种自足与圆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