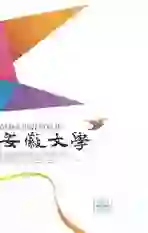经典文本跨媒介叙事的“女性向”
2021-07-01赵皙
赵皙
自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两文中提出,将“立人”的思想,主张以“尊个性而张精神”和“重独立而爱自繇”作为新文学发展的核心开始已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也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建立了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学价值观,构建了新的审美原则。
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人”和“妇女”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现,例如下文首先要谈的《伤逝》,就是在该时期易卜生有关社会问题剧引发的创作潮流中较为特别的一篇。由于受到《玩偶之家》的影响,大批“娜拉剧”就此而生,如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作品,但《伤逝》一作独立于众“出走者”的形象之外,借子君的命运传达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伤逝》)的冷静声音,尖锐地指出知识青年(尤其是女性)仅凭满腔虚无的热血而对人生的实际出路缺乏正确认识的不可行性。鲁迅的这种理智,某种程度上也启示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聚焦在“问题”意识上。而如今距离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人性独立与解放,也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之久,《伤逝》就仿佛一剂显影剂,此后关于女性独立的主题探索在将近一百年显影时间中始终未曾断裂,只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文学创作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一、从《伤逝》到《我的前半生》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并且指出了女性独立是需要经济实力作为前提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1925年,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在1926年收入《彷徨》之前未曾发表。鲁迅在《伤逝》中塑造了一个符合五四时期新女性显性特征的女性形象,在听取爱人“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时,“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甚至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时代“最强音”。这让同是时代新人的涓生感到震撼,“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但就在与原生家庭决裂之后,她随涓生进入吉兆胡同,开始了盲目的同居生活,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耗尽了财力储备和激情,“比我(涓生)还透彻,坚强得多”的子君终究无法突围生存及现实问题对爱情的遮蔽所带来的困境,在与涓生分手之后不久便黯然逝去。子君的结局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具象化体现,反映出鲁迅对这一时期女性独立思潮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的预见性思考,以“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结局表达出对被启蒙者去向问题的质疑。
对这一质疑的回应,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1982年香港女作家亦舒发表的中篇小说《我的前半生》,从其中的人物名字和失婚的经历不难看出与《伤逝》的互文关系。亦舒本人也承认对鲁迅作品的喜爱,“我一直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喜欢到这种地步。有人说他很刻薄,很刁钻,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只觉得他好。我只看《红楼梦》与鲁迅,我竞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书。在《快报》上写东西的也斯,天天推荐一个新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也一点不觉得惭愧,真是奇怪。我希望他看曹雪芹,或是一篇叫《伤逝》的小说,然后写他的意见。我能力不逮,有人应该这样做,新的意见总是漂亮……要写从前没有人写过的意思,那么这稿,无论怎么样,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从旧书里发掘新的意境,才是真的探讨吧。”(亦舒《新意》)但《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与鲁迅时期的子君明显不同的是,新一代子君已经不再徒有“独立”虚表,被迫从婚姻中走出之后的子君,非但没有就此消沉,失婚这一经历反而成为了新一代子君命运的转折点,新一代的子君还在同性朋友的鼓励下,从事业的打拼中收获了可供独立的经济资本,还因此转变了自我认知的态度,在自主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与女儿、妹妹等女性家庭成员的关系,积累了优厚的人际资本。这一变化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已经打破五四时期女性出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传统逻辑,虽然亦舒笔下的子君诞生于香港,但这新一代子君的命运,也如实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于女性独立话题探讨的阶段性进展,同样有着典型性与启示意义。
无独有偶,2017年改编自亦舒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上映之初就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一时间,与该剧相关的话题性文章在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等一系列大众媒体中迭出不穷,形成了热闹非凡的“伴随文本”现象。例如在百度贴吧、豆瓣电影版块均设有对《我的前半生》(2017)的专属讨论区,并且实时更新;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还连载了《我的前半生续文:这一年如风如歌》(wawaliuning)、《我的前半生之煜贺难平》(皓月无影)、《我的前半生之唐晶》(钰小哥哥)、《我的前半生之曾经守候》(一世妩虞)、《我的前半生——怎么舍得他们分手》(姝婢)、《(我的前半生)密斯吴》(江孟渚)等一系列网络衍生文;而在微信公众号、微博上推送的关于这部剧作的评论更是多得无以计数。由此可见,鲁迅《伤逝》及其相关文本已经作为经典IP(TnteuectualPmpeny),在大众媒体中延续对本时代的现实意义。有关女性独立的这一话题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在一系列大众媒介的傳播过程中,收获了空前的“高人气”,传统的文本也因此获得一次次的生机,可见女性独立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流量级话题。
二、媒介话语中有关女性独立的三重比较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独立在“人性独立与解放”的旋律中逐渐舒展。这期间大量的文本、剧作涌现出来,形成了国内对于该话题的第一次热议;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问,正值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实体化阶段,此时亦舒笔下的子君,已然成为该时期香港地区众多独立女性的一个典型缩影,这时的子君的独立既表达出亦舒向鲁迅经典文本的敬意,又有向五四时期女性对独立的本质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形作出告别的意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临末,这一话题的热力未见减弱,反而又在跨媒介的转型中得到了再一次的释放。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对于女性独立的关注与讨论一直延续,甚至在传统文本走向跨媒介的多元形态中,再次强化了这一主题的张力。但是,百年问的社会形态与现实语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女性的地位也不同以往,甚至在文学表达、作品传播的方式和路径等诸多方面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其中,女性话语权的表达途径是所有变化之中最为显著的,以三代子君为例,五四时期的子君,是话语权完全丧失的典型代表,《伤逝》中的子君是一个失语者,我们无从得知子君的容貌、想法和一切关于她个人的细节,靠近子君的个人描写也仅仅在她的脸色和眼神中稍作短暂的停留,于是读者了解子君的唯一渠道,完全是靠涓生的叙述。暂且不问这种叙述是否可靠,单就缺乏表达自我的途径这一点,就足以见得当时女性对独立的理解尚未进入更深的层次;而亦舒笔下的子君,在全文开篇时由一句“闹钟响了,我睁开眼睛……”就完成了上一代子君“完全失语”状态的一次全方位转折,新一代子君在这种典型的第一视角中展开叙述,不仅在话语权的问题上构建了女性表达自我的途径,而且这种“内聚焦”以人物视点而展开的叙述,伴有子君强烈的个人感受,更加直接地体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影视改编版本《我的前半生》的开头,以演员的独白——“三十三岁的我,是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奠定了这部作品的女性话语主导性,除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子君的形象、个体经验和内心感受都可以通过这种主导性充分地展开,影视剧带来的不仅是主角光环下女性的主体意识,还将通过演员的表演、布景的烘托、人物对白和背景音乐的渲染全面而具体地展现子君的形象和内心世界。所有的情节全部围绕女性主角的成长历程而进行,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再一次升级。
第二个显著的变化是三代子君对待婚姻的态度,以及婚姻之于女性的关系。《伤逝》中的子君在失去爱人不久之后,也随之香消玉殒,这直接体现了婚姻在那个时期对于女性“真空式”和“绝对性”的掌控;但是对亦舒版的子君来说,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之后,子君一改之前的依赖思维,凭借自己的学历、韧性和才华,在职场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发誓不再结婚。但是从结局来看,子君、妹妹子群以及新时代独立女性的代表唐晶分别走入婚姻,依然可见作者与时代仍然未跳出“女性必须回到家庭,回到婚姻中去”的定势思维;虽然影视改编版本的第三代子君形象常常在大众媒介上被评论的声音所淹没,并没有收获多少正面的评价,多被认为在独立意识上并没有超过亦舒笔下的子君。但仅从作品的结尾上看,罗子君最终并没有选择与一直以来帮助她、呵护她的男性友人贺涵走到一起,而是选择了跟随上级Miss吴去深圳开拓新事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女性对独立意识追寻与认可的主动性,还可以直接感受到女性自身价值的重塑过程,更凸显出了婚姻不再是当代女性的“首选项”和“必选项”。
三、跨媒介语境中的“女性向”趋势
沿着这条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作品在向大众传媒不断靠拢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到女性是其庞大的受众群体,由此,“女性向”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明显。由此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对女性经验的放大,从这三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子君形象由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过程,并由失语态走向了“主述”的中心话语位置。因此我们在《伤逝》之后,才得以一改对于子君“印象派”般的了解,真正进入全面而具体的女性成长与奋斗历程。不止是话语权,同名剧的热播和“伴随文本”涌现的现象也证明了女性开始作为主体逐渐向审美的中心甚至是主导地位移动的事实,这其中对原先性别秩序的反思和质疑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不仅如此,在经典文本跨越文本本身和媒介传播的过程中,还显现出一种更为有趣的现象,即女性不再是唯一被消费、被观察的性别,一部分男性也逐渐退回到了审视者的对立面中,成为被审视的对象。例如在近年的影视荧屏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流量级男星涌现出来,他们大多拥有跟女性差不多的容貌,甚至也持有跟女性相似的妆容,尤其在年轻女性中间,接受度极高,甚至在网络平台上,一大批男性美妆博主(如李佳琦)成为了女性提升形象的“意见领袖”,这批新兴的男性形象与此前荧屏中标准的男性形象相去甚远,“女相化”的趋势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态。而在近日的影视剧作中,无论题材和地域,不乏有对男性相貌、身材的长镜头和特写,并且这种趋势在全球蔓延,尤其是亚洲文化中最为凸显。“女性向”起源于日本流行文化中,自带排斥男性的文化倾向,但在进入中国并参与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也渐渐开放了原本的封闭性。媒体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原生态,也让其中不同的亚文化倾向得以生发,反作用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形态与接受维度。不仅如此,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文艺创作也在这种“女性向”的影响下不断探索,一方面,承袭着五四以来对女性独立主题探讨的传统,将这一主题不断延伸,以女性成长为中心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如《三十而已》(2020)、《安家》(2019)、《都挺好》(2019)、《谈判官》(2018)、《北京女子圖鉴》(2018)、《我的前半生》(2017)、《欢乐颂》(2016)、《杜拉拉升职记》(2010)……这类被称作“大女主”的作品,多数能够在播出时就即刻引发关注,报刊、网络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上一时会出现大量与之相关的话题性文章,围绕女性在当下的语境中探讨生存价值、婚恋关系、子女问题、人际关系和心理问题等关乎女性体验的所有一切,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伴随文本”现象,已经明显地“溢出”作品本身,回到社会现实中,也回归到了“问题小说”的社会价值中去。另一方面,在网络文学中有更为明显的“女性向”倾向,比如有意与“男尊女卑”性别秩序抗衡的“女尊文”、专门描写男子美貌供女性读者欣赏的“耽美文”等类型文的出现,足以见得女性在媒体发展过程中参与度的提升。
在《伤逝》发表后的近百年问里,女性独立的话题虽然没有停止,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作品发布的载体、作品传播的渠道、作品评价与接受的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虽然影视改编剧和网络文学整体的创作水准和审美价值参差不一,但其创作内容的世俗化倾向和鲜明的娱乐功能在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体所提供的便利下,能够迅速反映受众群体的审美态势并做出迎合,由此可见在与大众传播媒介互动过程中,女性话语权力转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