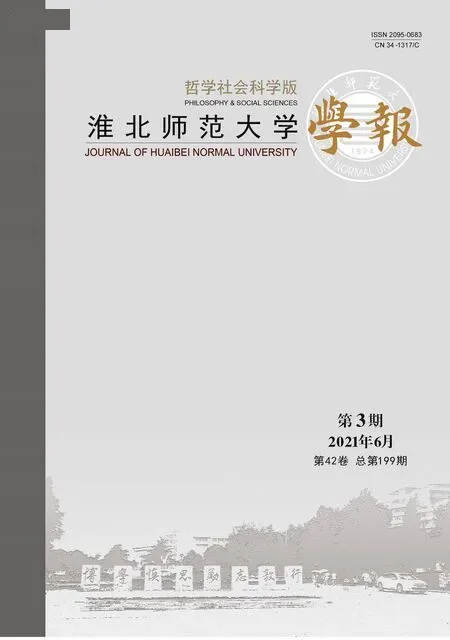理想政治境界的政治修辞基本原则
2021-06-29吴礼权谢元春
吴礼权,谢元春
(1.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2.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政治都是有境界之别的,可以将之分为理想政治境界与非理想政治境界两种。“理想的政治境界,是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向往的。但是,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是善良的人们在精神上的一种寄托。而非理想的政治境界,亦即现实的政治境界,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是一种连续性的、‘写真’式的常态。”[1]
理想的政治境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曾有过向往,也曾有过论述。如中国古代就有过三种模式的理想政治境界”[1]。其中,“第一种模式是最高层级的,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大同’的社会。这种模式的政治境界,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普遍向往的理想政治境界”[1]。“第二种模式的理想政治境界,就是孟子所向往的‘王道社会’,是次高层级的”[1]。“第三种模式的理想政治境界,就是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所向往的‘桃花源’社会,跟先秦时代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有点相似,是最低层级的。”[1]这三种模式的理想政治境界,不仅在中国古代未曾实现过,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实现过。因此,这三种模式的理想政治境界,“虽然真实地反映了无数理想主义者对现实政治境界的不满之情,真切地流露了他们对理想政治境界的热烈向往之情,但毕竟只是一种善良而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1]。
至于西方思想家,“不论是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诸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还是近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诸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又 作Sir Thomas More,1478-1535)、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1568—1639)、英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 国 的 夏 尔·傅 立 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等人,虽然都未曾像中国的先哲孔子、孟子、陶渊明那样具体描绘过理想的政治境界的模式图画,但都提出过他们对理想政治境界的设想”[1]。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思想界,尽管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近现代的托马斯·莫尔、托马斯·康帕内拉、罗伯特·欧文、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等都曾对理想政治境界有过设想与规划,但“跟中国古代思想家与文学家所憧憬的理想政治境界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一样”,“事实上至今都是未曾实现过的,也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已”[1]。
总之,理想的政治境界,虽然在中国上古传说中有过,汉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还作了具体的人事描写,在孔子、孟子、陶渊明的想象中也曾被具体描述过,在古希腊与西方近现代思想家的笔下也有过勾勒,但在事实上,理想的政治境界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政治家所作的理论上的一种构想。如果人类社会真的有理想的政治境界,那么政治修辞的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只要遵循“坦诚相见”“友善合作”“慎言其余”三个基本原则,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一、坦诚相见
坦诚相见,作为理想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无论是政治观点的表达,还是政治主张的提出,均本着“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吾口道吾心”,心里是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说出来之后,就准备怎么做,不需要为了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而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则准备了另做一套。换言之,也就是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只需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对政治修辞受体讲清楚、说明白(也就是在“消极修辞”方面下功夫就足够了),而不需要为了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而在语言表达技巧上下功夫、在玩弄文字游戏上费尽心机。简言之,就是真心诚意地表情,明白清楚地达意,保证政治表态、政治承诺与其行为结果相一致。
虽然理想政治境界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理想政治境界与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并非水火不融,而是有所交集的。事实上,在现实政治境界下,有时也会有理想政治境界的因子存在。因此,“坦诚相见”的原则并非因为理想政治境界不存在而无用武之地。相反,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适应特定的政治情境,积极、主动地遵循“坦诚相见”的基本原则,有时会使政治修辞产生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秦孝公时代的秦国在当时诸侯各国中并不是强国,而是偏远贫弱之国。但是,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国却迅速崛起,很快成了天下霸主,并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终极目标。究其原因,就是卫鞅(卫人公孙鞅,后被秦孝公封为商君,号为商鞅)为秦国变法打下的坚实基础。而卫鞅作为一个外来的客卿,之所以能在秦国将其所拟定的新法推行开去,并最终取得变法的成功,则跟新法颁布前卫鞅的一个政治动作有着极大的干系,这就是秦都南门“立木取信”事件。卫鞅第一次发布“移木得金”之令,之所以秦人觉得奇怪,无人敢应,就是因为秦孝公时代不是“天下为公”与“讲信修睦”的时代,而是一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境界下,老百姓不相信政府的任何政令,乃是自然之理。卫鞅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清了这一现实社会现状与政治情势,所以采取了逆时代潮流的思路,通过“立木取信”而为即将开始推行的新法创造了一个“讲信”的理想政治境界。事实上,正是因为卫鞅“立木取信”的政治修辞行为,让秦国老百姓重拾了对政治人政治修辞“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格信心,由此为新法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也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现代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是如何贯彻“坦诚相见”原则,从而在混乱的现实政治境界下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环球网报道记者 侯佳欣】据《纽约时报》10月6日报道,此前遭降职的美国抗疫要员、资深疫苗科学家里克·布莱特6日辞去了他的最后一个政府职务,称自己被边缘化,无事可做。今年春天,他曾因抱怨科学领域的“任人唯亲”和政治干预而被降职。
报道称,六个月前,布莱特被解除了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的职务,并被重新分配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个影响力较小的工作岗位,该机构也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那里,布莱特带头开发新型即时新冠病毒检测(方法)。根据其律师介绍,他组建了一个团队,为推进病毒检测相关工作,他们促成了8份合同并将所有的预算全部用尽。
然而今年10月,他还是决定离开。究其原因,根据一份最新附录,布莱特的律师称,“出于政治考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官员拒绝了布莱特提出的全国性新冠检测的想法。律师还指责他们无视布莱特的请求,即投入100亿美元,以快速推进新冠疫苗。
尽管已经辞去政府职务,但其律师6日表示,布莱特博士“仍然非常担心”白宫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尤其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到白宫之后。阿特拉斯是一名神经放射科医生,没有接受过流行病学或传染病方面的培训。阿特拉斯对戴口罩表示反感,他还相信“群体免疫”可以阻止新冠,这些令其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青睐,成为白宫新的顾问。
布莱特的律师称,特朗普总统的新任科学顾问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没有传染病方面的背景”,在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布雷特·吉罗尔每周一次的会面中,他显然是在替白宫“发号施令”。
据此前报道,4月22日,布莱特指认,自己一天前遭降职的原因是反对使用羟氯喹等关联政治因素的药物来抗击新冠疫情。羟氯喹和氯喹一直为白宫所推崇,但布莱特认定这两种药物应对新冠疫情“缺乏科学价值”,屡次拒绝扩大其应用范围。布莱特也被媒体称作美国政府“吹哨官员”。
布莱特5月5日向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书面举报材料,称上个月自己被解除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署主任职务,是因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报复。当地时间5月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布莱特相关情况时称,“我没见过布莱特博士,我都不知道他是谁……”特朗普还提到,“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心怀不满的员工,试图帮助民主党赢得选举。”(http://news.163.com/20/1007/19/FOC0CP7200018AOR.html)
上面是来自环球网2020年10月7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题目是:《美“吹哨官员”辞去最后一个政府职务,此前曾称自己因反对特朗普推荐“神药”被降职》。从这篇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局长、抗疫要员和资深疫苗科学家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之所以在2020年10月6日宣布辞去在美国政府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因为面对席卷美国近一年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不断恶化的现状,他不断地秉持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追求真理的理念,将疫情的严重性与对美国人民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性如实地告诉了公众与媒体,这是恪守理想政治境界的“讲信”理念的表现。但是,2020年的美国不是理想政治境界下的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为了其竞选连任的政治目的,不断淡化疫情的危害性,置美国人民的健康于不顾。因此,里克·布莱特在如此严酷的现实政治境界下仍然抱持“讲信”的理念,在政治修辞中秉持“坦诚相见”的原则,就显得特别可贵。虽然遭到时任总统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严重打压,政治生涯遭遇了挫折,但里克·布莱特却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努力在现实的政治境界下秉持“讲信”理念,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言(政治修辞)时遵循“坦诚相见”的原则,因而赢得了美国媒体的普遍赞誉,被誉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府的“吹哨官员”。
与里克·布莱特相反,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却始终为了其政治目的,极力回避问题,淡化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其有关疫情问题的发言(政治修辞)总是谎话连篇,完全没有在政治修辞中要遵循“坦诚相见”原则的意愿。正因为如此,特朗普的政治人格只能停留在现实的政治境界中,他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始终只是一个天下为私、尔虞我诈、说谎好斗、残忍不义的政客形象,而不是中国人所称许的谦谦君子,或是西方人所认同的优雅绅士。下面我们来看腾讯新闻网2020年10月9日一则有关特朗普的新闻报道,题目是:《纽约街头出现特朗普“谎言之墙”,民众:我觉得写少了》,由此便可知美国人对他人格形象的定位。
近日,在美国纽约市的格拉坦街头,出现了一面特朗普的“谎言之墙”。墙上展示了特朗普自2017年上任以来说过的超过两万个谎言。

据外媒报道,这堵墙于10月4日在纽约市的格拉坦街上公开展出了一整天。(https://new.qq.com/omn/20201009/20201009A05MAB00.html)
由上述新闻报道所彰显的美国卫生官员里克·布莱特与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定位来看,在现实的政治境界下,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是否遵循“坦诚相见”的基本原则,对于其人格形象的塑造事实上是有决定性影响的。由此也可以见出,在现实的政治境界下,自觉遵循理想政治境界下“坦诚相见”的基本原则,对于政治修辞的成功事实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友善合作
友善合作,作为理想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或是跟政治受体(政治人或自然人)交流互动时,均本着与人为善的心态,抱持友好合作的态度,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是要反驳对方的说法,也能心平气和、态度和蔼地进行解释和说服,重视表达的方式方法,最大程度地展现自己的善意,给对方留足面子,让对方充分感受到合作的诚意。换言之,就是政治修辞主体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友好善良的意愿,“修睦”合作的态度,在追求实现特定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的同时,努力营造友善和谐的人际关系。
虽然理想的政治境界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但是对理想政治境界的追求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大有人在的。事实上,在现实政治境界下,理想政治境界的某些种子有时也会落地生根,在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活动中有所萌发。因此,正如“坦诚相见”原则一样,“友善合作”的原则并非因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不存在而无实践的机会。相反,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适应特定的政治情境,有意识地贯彻落实“友善合作”的基本原则,往往会使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修辞闪现人性的光芒,不失人世的温情,不仅有利于塑造政治修辞主体的人格形象,还会产生出乎意料的、具有正向积极意义的接受效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据说,罗斯福在当总统之前,曾在海军里担任要职。一天,一位朋友向他问起海军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
罗斯福向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问:
“你能保密吗?”
“当然能。”
“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李春生等编《世界名人幽默精品》)
上述故事中的罗斯福,就是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英雄并且连任了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文中所叙之事,应该是发生于1913年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美国海军助理部长时期所发生的。罗斯福此时虽然还不是美国总统,但是作为美国的助理海军部长,也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了。而作为政治人,当他的朋友(是否是政界中人不得而知)向他打听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时,他无论怎么回答朋友的问题都是政治修辞。因为他跟朋友交际的内容事涉美国国家秘密,政治属性非常明确。按照常理,罗斯福的朋友是不应该向罗斯福打听美国在加勒比海建立潜艇基地的计划。但是,事实上他的朋友已经开了口,这无疑让作为政治人的罗斯福感到非常为难。如果为了朋友情谊而据实相告,作为政治人特别是身为美国助理海军部长的罗斯福就泄露了国家最高机密,犯了政治的大忌;如果严词回绝,虽然维护了军人的职业操守,但却让朋友大丢面子,也让外人觉得他不近人情,这对他日后与人相处,以及竞选总统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主要是靠人气与人望,一个不近人情的候选人很难让人亲近并愿意相助的。令人欣慰的是,罗斯福对于朋友给他出的难题,以高度的智慧与高超的表达技巧(运用了“设彀”修辞法)予以从容应对。他既没有告诉朋友想知道的军事秘密,也没有让朋友为此而丢了面子,反而让朋友被拒绝后更加敬佩他的睿智与幽默,情感情绪上觉得非常愉快。可见,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修辞若是能够有意识地主动、积极地遵循“友善合作”原则,不仅有助于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而且还能凸显其作为政治人的人格魅力、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与上述故事情况正好相反的例子: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饰,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於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於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於外,义强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乱於治,迷於言,惑於语,沉於辩,溺於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槖,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上述历史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商鞅(即公孙鞅、卫鞅)得秦孝公信任,帮助秦国变法成功,从此使秦迅速走上强国崛起之路。但是,秦孝公死后,秦惠王继位执政,就不再信任商鞅,反而因为商鞅当初变法时对他触犯新法予以罚处之事而记恨在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商鞅被迫无奈,为了自保,最后只好举其封地商、於徒众起而反抗。最后,商鞅兵败被擒,被秦惠王处以车裂之刑。就在秦惠王诛杀商鞅不久,苏秦到了秦都咸阳,意欲游说秦惠王接受其“连横”之策。秦惠王虽然因为商鞅的缘故而在内心厌恶外来游士,但为了秦国的长久发展大计,还是接见了苏秦。苏秦见了秦惠王,便开始了上述一番洋洋洒洒的游说。但是,这次游说秦惠王没有取得成功。之后苏秦又十次以上书的形式向秦惠王推行自己的“连横”之策,结果都没有受到秦惠王的重视而予以采纳。因为在秦国呆得时间久了,苏秦原来所穿名贵的黑貂之裘都破了,黄金百斤的资用耗尽,生活没有着落,只好离开秦国而回故乡洛阳,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书囊,挑着行李,神情憔悴,脸色漆黑,面有愧色。回到家里,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做饭吃,父母不跟他说话。
苏秦游说秦惠王的时代是中国政局最动荡、社会最混乱的战国时代。因此,毫无疑问,苏秦与秦惠王所处的政治情境属于典型的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尽管如此,刚继立为王的秦惠王虽因商鞅反叛的缘故而内心排斥外来游说之士,但仍然不失大国之君的风度,接见了前来秦都咸阳的说客苏秦。苏秦此行的目的是要游说秦惠王接受其主张的“连横”之策,帮助秦国实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战略,最终实现独霸天下的终极目标。从历史上来看,苏秦的想法跟秦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契合的。但是,在秦惠王刚刚即位之初,觉得实行“连横”之策的时机尚不成熟,加上刚刚跟同样是游士出身的商鞅闹翻,所以他就更加无心采纳苏秦的政治主张了。但是,在拒绝苏秦时他没有直言,而是本着与人为善的心态,抱持对远道而来者的友好态度,运用“引用”修辞手法,借前人之言,婉转而又心平气和、态度和蔼地向苏秦作了解释说明:“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善意,给足了苏秦面子。很明显,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秦惠王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自觉遵循了“友善合作”的原则。因此,秦惠王拒绝苏秦的政治修辞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也非常得体,既有人情的温度,又有政治的高度。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东道主的待客之道,展现了大国之君谦谦君子的风度。但是,跟秦惠王相比,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苏秦的表现就很是令人失望了。秦惠王虽然拒绝接受其主张,但却表达得非常婉转,且以“愿以异日”为说辞预留了回旋空间,算是给足了他面子。可是,苏秦却并不领情,反而情绪失控,直接抛出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将秦惠王一棍子打死,认定他就是一个听不进正确意见的昏君。然后,又连篇累牍地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给秦惠王的感觉不仅是在炫耀才学,还有教训他的意味。这无疑会激起秦惠王内心更大的反感。至于结语的几句:“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乱於治,迷於言,惑於语,沉於辩,溺於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指着秦惠王的鼻子在骂人了。可见,作为政治修辞主体,苏秦游说秦惠王的第二轮说辞既有失政治人的风度,也有失做人的厚道。因此,最终导致了其游说秦惠王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彻底落空,只得狼狈地离开了秦国,回到故乡洛阳则备受亲人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苏秦在跟秦惠王的政治交际活动中,没有主动适应非理想的现实政治情境,分析揣摸秦惠王的心理,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知人论事”原则,更没有像秦惠王那样有意识地突破现实政治境界的疆域,自觉遵循理想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友善合作”原则,展现出政治人的人格高度。正因为如此,苏秦最终不能让秦惠王回心转意,实现自己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
三、慎言其余
慎言其余,作为理想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涵义是指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无论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或是跟政治受体(政治人或自然人)交流互动时,均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披露事实、提出证据或展现才学时,不为了实现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而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或是有选择地提出证据,或是为了拔高自己的形象而强不知而为知、以外行充内行。换言之,就是政治修辞主体在政治交际活动中要体现科学、客观、谦虚的态度,慎重措辞。无论是提出观点,或是得出结论,都要基于客观事实,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对于未知的事实或尚未了解的详情不轻率发言,对于不懂的知识领域不轻率置喙,以维护政治人诚实可信的良好人格形象。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政治人,还是自然人,都应该遵循“慎言其余”的原则。《论语·为政》曾记孔子教导其弟子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谓: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表现)。《论语·为政》又曾记孔子教导其弟子子张如何从政为官时说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意谓:从政为官,要学会多倾听,对于不懂的,就存留于心;对于真正懂得的,就谨慎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不懂的部分,就保留意见不表达意见。这样,就能少犯错误。从政为官,还要学会多观察,对于不明白的,就放在心里;对于真正明白的,就谨慎地予以实践。这样,就能减少事后的懊悔。说话很少犯错误,做事很少有后悔,官职俸禄就都在其中了)。孔子教导子张从政如何发言的话,其实说的就是理想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慎言其余”的原则。
前文我们曾多次说过,人类社会几乎不存在理想的政治境界,而只有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但是,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理想政治境界的政治修辞原则并非就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理想政治境界下的“慎言其余”原则,在现实政治境界下的适当运用就非常具有价值。运用得当,不仅有助于政治交际活动中特定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得以顺利实现,而且还有助于树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诚实可靠的人格形象。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
汉哀帝语尚书郑崇曰:“卿门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明·何良俊《语林》卷四《言语第二上》)
上引文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哀帝时,大汉王朝已经现出了没落气象。汉哀帝刘欣早已不能与其先祖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相比了,更不用说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相提并论了。正因为汉哀帝没什么能耐,执政也没什么作为,所以在臣子眼里也就没什么威信。尽管如此,当时大汉王朝表面还是平静的,所以慑于传统的皇权观念,汉哀帝的许多臣下见了他还是有所畏惧的。当时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名叫郑崇,字子游,出身于汉时高密世代高门望族。郑崇年少而为郡文学史时,因显现了不凡的文学才华而被大司徒(即丞相)傅喜所赏识。后来,傅喜得到一个机会,就向汉哀帝举荐了郑崇。汉哀帝对傅喜的意见非常重视,遂破格提拔了郑崇为尚书仆射。郑崇履职之初,因为接近汉哀帝的缘故,有机会向汉哀帝提了很多忠谏,汉哀帝也大多采纳了。由于忠诚能干,不久郑崇就得到了汉哀帝的倚重。郑崇为人俭朴,上朝时总是穿一双草底朝靴,走起路来窸窸窣窣,所以汉哀帝常常跟他开玩笑说:‘我识郑尚书履声。’正因为郑崇位高权重,又是最接近汉哀帝的人,所以当时朝中官员都想走他的门路,希望得到晋升。虽然郑崇并没有收受他人的贿赂,但每天自己府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情景,却让人产生了联想。于是,就有人将此情况密奏了汉哀帝。汉哀帝闻奏,大为震怒,于是立即召郑崇来问。看在平日关系亲近的份上,汉哀帝虽然没有恶形恶状地质问郑崇,但口气中透着威严,柔软之中带着骨头地问道:‘卿府上为何整日门庭若市?’郑崇一听,知道情况不妙。如果不向皇上解释清楚,那便有灭顶的无妄之灾了。稳了稳神,郑崇从容答道:‘臣门前若市是事实,但是臣心如水也是事实。’汉哀帝一听,终于明白了,从此对郑崇信任有加,不再怀疑他”[2]255-256。
上述故事中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九五之尊的大汉王朝皇帝汉哀帝,一个是位高权重的尚书仆射郑崇,均为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他们对话的内容涉及国家法律与人事制度,属于典型的政治话题。因此,这场君臣的一问一答明显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属性。这场君臣对话,之所以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乃是因为二人的对话都具有高度的修辞技巧。汉哀帝的问话:“卿门何以如市”,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问句,好像云淡风轻,但内里却含着深意:‘为什么有那么多官员要走你这个尚书仆射的门路?你是不是结党营私或是收受了人家的贿赂?’很明显,这句话是透着杀气的。如果郑崇不能解释清楚,那么势必就要被坐实结党营私或是收受贿赂的罪行”[2]256。可见,汉哀帝的政治修辞是相当高明的,可谓是柔中带刚,绵里藏针,既没有拂去君臣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君臣之间良好的信任,又在事实上发挥了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申明了朝廷吏治的刚性原则。至于郑崇,作为跟汉哀帝进行政治交际活动的政治修辞主体,其政治修辞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更显高明。
先说战术上的高明之处。作为政治修辞的受体,面对汉哀帝的质问,“应该如何解释,才能说服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呢?郑崇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像一般人那样遇事慌神,也不像有些人慷慨激昂地急于辩解,更没有像有些人摆事实讲道理以驳斥皇帝的无理指责与无端怀疑,而是云淡风轻地以两个‘比喻’文本来回应:‘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这两个‘比喻’文本的高妙之处在于,前一个‘比喻’文本:‘臣门如市’,是顺着汉哀帝的意思予以肯定;后一个‘比喻’文本:‘臣心如水’,是暗中对前一文本予以否定,从而为自己辩白。因为皇帝是九五之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无理还是有理指责臣下,是有端还是无端责问大臣,都是不容辩驳的。郑崇懂得这一点,所以对于汉哀帝的责问,他没有采取顶撞式辩解,而是采取顺水推舟、逆来顺受的方式予以接受,坦诚地承认自己府前确实每天门庭若市,有很多官员找他。这样,就很快消解了汉哀帝的怒气,让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他下面为自己辩白的内容。这叫礼尚往来,让汉哀帝知道,我不驳您的话,但您也要听听我的话。这是打心理战,是高明的侍对策略。事实上,正因为郑崇对于汉哀帝的责问:‘卿门何以如市’予以了肯定,最大限度地消解了汉哀帝因不了解实情而早已蓄足的怒气,这才让郑崇后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臣心如水’易于为汉哀帝接受。‘臣心如水’是一个寻常的比喻,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比喻。因为以‘水’来比心境,也是老生常谈,在‘喻体’的选择上并无多少独创性,但是在此情此境中,郑崇以‘水’来比自己面对众官员求托时的心境,则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因为‘水’在中国是有特别含义的一种意象,老子说‘上善若水’。水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平静的意象,而且还有一种清澈纯洁的意涵,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因此,郑崇用水来比喻自己面对众人求托时的心境,既表现了他面对诱惑的一种定力,也表现了他清澈纯洁的心灵。很明显,这样的表白是足以感动汉哀帝的,足以让汉哀帝相信他的人格。既然人格被肯定了,那么还需要举什么事证来自证清白呢?相反,如果郑崇面对汉哀帝的责问,不运用‘比喻’修辞策略,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应对,而是实打实地据实论辩。比方说,不肯定‘臣门如市’的事实,而是辩解说:‘我家并非每天都有很多人上门’、‘上门的人也并不都是求托我做官的事’等,那么势必会越描越黑,让汉哀帝疑窦丛生的。不以‘臣心如水’来表白心迹,而是辩解说:‘我一向俭朴清廉,从未贪图过别人钱财,也未结党营私’,那么汉哀帝会越发觉得他心里有鬼。可见,郑崇自证清白的话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乃是因为其所建构的‘比喻’文本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软实力”[2]256-257。
再说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郑崇生活的汉哀帝时代并非是“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理想政治社会,而是“天下为私”的时代(汉代是中国封建君权最集中的时代之一),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臣臣之间,都是尔虞我诈,彼此互不信任,互相防备,为了个人权位与利益而不择手段。汉哀帝对郑崇的猜疑,朝臣走郑崇的门路,都证明了郑崇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理想的现实政治社会。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郑崇,虽然身处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之中,但却在侍对汉哀帝的质疑时,有意识地遵循了理想政治境界下“慎言其余”的政治修辞原则。面对汉哀帝“卿门何以如市”的强烈质问,郑崇坦然承认有“臣门若市”之事实,但却没有跟汉哀帝辩解说上门的大臣们没有求托、走门路之意。这就是坦然、坦诚,有什么说什么,知道多少说多少,不以自己的臆测作为解脱嫌疑的依据。因为上门的大臣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用意,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作为当事人同时也是被汉哀帝怀疑的嫌疑人,郑崇是不能轻下断言的。事实上,因为郑崇有意识地遵循了理想政治境界下“慎言其余”的政治修辞原则,遂使汉哀帝彻底打消了对他结党营私的疑虑,认为他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所以继续对他信任有加。可见,郑崇政治修辞的成功,是跟其身处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之中而能有意识地贯彻落实理想政治境界下“慎言其余”的政治修辞原则有很大关系。我们认为,相对来说,郑崇对“慎言其余”原则的遵循,比起上文我们说到的他在比喻修辞文本建构方面的高度技巧,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皇帝面前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君子形象出现,事实上要比巧言令色更能博得皇帝的信任。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与郑崇表现相反的例子,这就是前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防治用药的相关发言。美国媒体不止一次地报道过特朗普有关新冠病毒肺炎用药问题的公开发言。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同时也是一个对医学完全无知的门外汉,为了自己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多次“强不知而为知”,不断向美国民众推荐瑞德西韦、羟氯喹等药品,并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药品具有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的特殊效果。结果,不仅误导了美国民众,造成了美国防疫政策的巨大混乱,最后连自己及其周围幕僚、家人都染上了新冠病毒肺炎,成了世界政治上的一个笑话。事实上,作为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发言,不仅对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形象造成了重创,也对美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巨大打击。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第一则报道是来自2020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网站,题目是:《世卫组织:瑞德西韦、羟氯喹等对治疗新冠似乎疗效甚微》:
新华社日内瓦10月16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由其主导的新冠“团结试验”中期结果显示,瑞德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干扰素等疗法似乎对住院患者的28天死亡率或新冠病人的住院病程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据世卫组织15日发布的“团结试验”中期结果,该项目涉及30个国家的405家医院,共有11266名成人新冠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各个药物组别,包括瑞德西韦组、羟氯喹组、洛匹那韦组、干扰素加洛匹那韦组、干扰素组,以及不使用研究药物组。
结果显示,没有任何研究药物能明确降低新冠患者死亡率、开始使用呼吸机时间或住院时间,上述治疗方案对新冠患者住院治疗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世卫组织同时表示,“团结试验”取得的进展表明,即使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开展大型国际试验也是可能的,这类试验有助于快速、可靠地回答与新冠疗法有关的关键公共卫生问题。目前,试验结果正在接受同行评议,之后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
世卫组织“团结试验”项目于3月启动,旨在通过比较不同药物或药物组合治疗新冠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尽快找到有效治疗方法。今年7月初,世卫组织曾宣布停止该项目中羟氯喹和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两个分支的试验,理由是这些分支试验中的住院新冠患者病亡率几乎或完全没有下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680806319260793389&wfr=spider&for=pc)
第二则报道来自2020年10月16日《观察者》网,题目是:《世卫:特朗普的“神药”几乎没用》:
特朗普大吹特吹的“神药”瑞德西韦到底对新冠肺炎有没有用?世卫组织也专门做了个试验,但他们认为,瑞德西韦可能真的没什么效果。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10月16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5日公布了瑞德西韦、羟氯喹等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称这些药物对于降低新冠肺炎致死率“收效甚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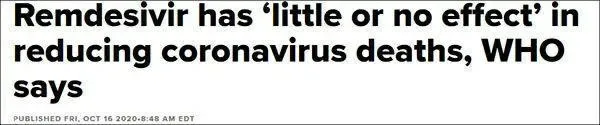
CNBC报道截图在过去7个月里,世卫组织在30个国家的405家医院对11266名新冠患者进行了对比试验,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患者分别使用瑞德西韦、羟氯喹、洛匹那韦、干扰素、干扰素加洛匹那韦治疗,剩余患者则不使用试验药物作为对照。受试患者中,使用瑞德西韦的患者数量最多,达2750名。报道称,世卫组织进行的这一试验,可能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冠病毒治疗随机对照实验。但最终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死亡率、接受呼吸机治疗时间及住院时间这些方面进行对比,这些试验用的药物全都“对新冠治疗收效甚微,或是根本没有效果”。根据报告的数据,最终使用瑞德西韦的2743名重症患者中有301人死亡,与之对照的2708名重症患者中则有303人死亡,两组患者死亡率之比为0.95,28天试验期的死亡率曲线高度重合,几乎无明显差距。其他几种药物的结果也大同小异,死亡率没有明显差异。
对此,研发了瑞德西韦的吉利德科学公司立即作出回应,称试验及受试患者情况的不同可能影响结果,“目前还不能得出任何盖棺定论的结果。”吉利德在声明中称:“世卫组织的试验似乎与同行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不同,这些研究极为可靠,已经证明了瑞德西韦的临床效果。我们担心这项全球试验的数据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以进行建设性的科学讨论,尤其考虑到试验设计可能有局限性。”不过世卫组织专家表示,试验主要就是为了评估药物对降低住院患者死亡率的效果,“结果极为充分”。此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曾发表过一份瑞德西韦试验报告,对1060余名新冠患者进行了试验。这项报告显示,瑞德西韦治疗确实能“降低重症患者死亡率”。但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当时也坦言,这项死亡率的改善数据还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尽管瑞德西韦的实际效果仍存在争议,但美国已经开始将其投入“实战”。5月,美国食药监局就给瑞德西韦紧急授权,允许重症患者使用。8月,美食药监局更是把授权范围扩大到了轻症患者。10月2日特朗普本人“中招”住进医院后,也接受过瑞德西韦治疗。(https://m.k.sohu.com/d/489686583)
上述两则新闻报道,都是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先前向美国民众推荐瑞德西韦、羟氯喹等药品之事而对其进行“打脸”的。由于引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权威医学机构的实验数据,因此更具科学性与权威性,是用事实说话,反衬得特朗普有关新冠病毒肺炎防治用药的发言更显愚蠢。可见,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也是需要自觉遵循“慎言其余”原则的。否则,不但其特定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难以实现,甚至连自身的政治人格也要破产,从而导致政治生涯的彻底失败。
结语
政治自古以来就有理想与非理想两种境界。理想的政治境界,在事实上是不存在,只是善良人的一种幻想。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则总是如影随形,始终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存在。因此,每一个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人,虽然“在实施具体的政治修辞行为时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以把握,也没有现成的操作指南可以作为指导”[3]7,但都必须直面现实,在其政治交际活动中主动适应其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政治情境,自觉遵循相应的政治修辞基本原则。如果有幸生活于理想的政治境界之中,那么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遵循“坦诚相见”“友善合作”“慎言其余”三原则,基本上就可以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特定目标预期。如果不能生活于理想的政治境界之中,而只能直面非理想的政治境界,那么就必须遵循现实政治境界下“知人论事”“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政治修辞三原则。否则,肯定不能顺利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理想政治境界与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并不影响在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政治修辞主体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有意识地贯彻落实理想政治境界下“坦诚相见”“友善合作”“慎言其余”的政治修辞三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是非理想的现实政治境界下,理想政治境界的政治修辞三原则也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只要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有自觉贯彻理想政治境界政治修辞三原则的意识,不仅有助于顺利实现其特定的政治修辞目标预期,而且还能展现其作为政治人的人格魅力与良好的公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