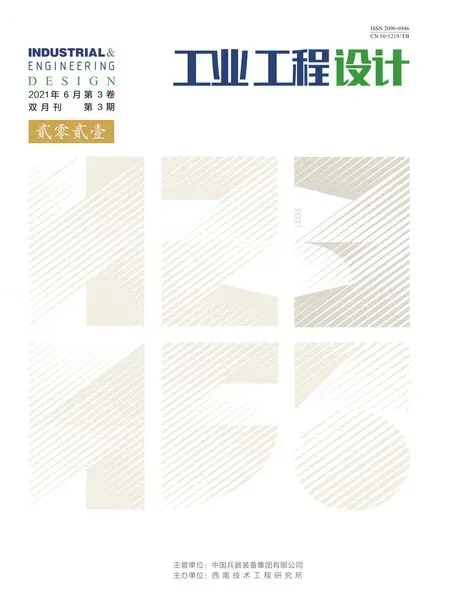何谓“新女性”?
——从电影布景看20世纪30年代的设计文化与性别区隔
2021-06-27汪燕翎贾茹
汪燕翎,贾茹
四川大学,成都610207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电影以其特有的媒介技术描摹了都市的物质文化和摩登生活。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左翼影人在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产品中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意识,揭示了当时都市摩登生活下深藏的矛盾与危机。在左翼电影的视像中,女性呈现出不同的阶级身份和性别区隔,展开了与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诸多左翼电影均提出何为“新女性”的历史命题,特别是蔡楚生完成于1935 年的作品《新女性》,更是直接以“新女性”作为片名。这些电影对“新女性”不约而同的召唤使人们不禁要追问,20世纪30 年代的“新女性”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有什么关系?这些关于性别的话语反映在日常生活和设计层面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回响?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从电影布景这一角度切入电影《新女性》中的性别视角,并对照同一时间切面上的国货运动,进一步探讨20世纪3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性别塑造在银幕内外发生的共鸣。
一、《新女性》角色的阶级区隔
首先,回到左翼影人对“新女性”故事的讲述中。在影片的开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韦明,便呈现出崭新的女性形象。她毕业于北平的大学,生活在摩登都市上海,既是中学的音乐老师,又是业余作家。她的身份中既有新文化运动的“新”,又有都市现代性的“新”,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最为理想的都市女性形象。但剧情的发展将韦明拽向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韦明任教学校的校董王博士,也是她大学同窗的先生,对韦明十分垂涎,但韦明对王博士不予理睬,因此遭到王博士报复失去工作。此时,一直被寄养在北平姐姐家中的韦明,与前夫之女前来上海治病。经济困顿的韦明为了救女,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但没想到嫖客竟是王博士,韦明倍感屈辱。女儿最终因得不到医治而身亡,韦明因来自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服毒自杀,临终前发出“我要活!”的呼喊。
影片将韦明这一貌似“新”的女性角色设计在一个充满陷阱的现代都市中,城市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和性别结构中,她们的阶级局限性使得她们必然成为城市的牺牲品。电影运用了大量的电影特技来解答韦明之死因——即“新”女性通过出走、教育、奋斗都不能救赎,只有通过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觉醒才能获得救赎。为了说明女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左翼影人为这部电影塑造了3 个阶级特征鲜明的女性角色——王太太、韦明、阿英,并对她们涉足的社会空间和生活世界做了专业的布景设计。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一个工人的月薪有20~30元,技术工人稍高一些,有50~60 元,而一个中学的校长月薪可以达到160~200 元,相比之下大学教授每月400~600 元的薪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薪了[1]。通过观影,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左翼影人所设计的3 位女性角色分别代表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正是根据不同阶级间的区隔和冲突而展开。如果借助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进一步剖析,会发现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不仅是由以简单、垂直的资本总量来划分的社会阶层,还是由其居所,服饰、产品、装饰、艺术、交友等微观日常交织成的社会空间来形塑的。不同于马克思依据经济资本来划分的社会阶级,布尔迪厄认为实体的社会阶层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无处不在的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因此阶层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区隔和建构出来的[2]。布尔迪厄以惯习、场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来构建了他的社会阶层模型,他在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这一三维的区隔模型中不仅需要考量资本总量,还需要更进一步考量资本的结构以及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3]。郭恩慈在《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一书中也借助布尔迪厄的理论模型,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中角色所能涉足的空间场所(布景设计),所使用之器物(道具设计)以及生活方式和品味差异,将常见的角色分出4个阶级: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低下阶层、新文化阶层[4],并由此拼出了一幅20 世纪30 年代上海社会空间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以《新女性》电影布景为样本,也同样列出电影中3位女性所涉及的社会空间,以此来还原电影中“新女性”的阶级图景和性别位置(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王太太与韦明两人是北平时代的老同学,受过同样的教育,生活方式和生活品味有一定重合,都具有摩登西化的一面和消费文化的色彩。但在经济资本上王太太是资本家夫人,是财产继承人,属于布尔迪厄所划分的统治阶级范畴,以物质享受和名利追求为生活价值。韦明是中学老师,资本结构上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但她同时又是作家,本身富有才华,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属于郭恩慈划分的新文化阶层,重视友谊,追求自由恋爱。布尔迪厄提出资本拥有的构成性差异划分了阶级内部的各个部分。统治阶级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而在内部发生分化[4]。王太太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以及与之不相称的文化资本,而韦明拥有较好的文化资本和薄弱的经济资本。因此她们的生活空间和物质世界会有重叠。譬如,她们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选择同样的发型和时装款式,抽同样品牌的洋烟,活动在同样的都市空间中。电影中的女工李阿英没有信息表明她受过高等学历,从她的家居环境可见,也几乎没有消费。阿英在按照资本总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垂直区分的社会阶层中属于底层阶级,但左翼影人有意将社会底层的李阿英塑造为在思想和文化上最为先进的阶层[4]。不同于城市最底层的女性(比如电影中的妓女),阿英有着固定工作。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是缫丝工会补习班的业余老师,负责教授识字、写字、唱歌等,还自己改编、创作歌词,其文化资本具有先进性。阿英的价值取向不是以“稳定生活、友谊、爱情和女性贞洁”为重,而是信奉为大众服务,是思想先进的无产阶级女工。从经济资本总量上看,李阿英和韦明差距不大,她们租住同样的亭子间,选择同样的国货,但韦明和阿英的区隔界限在于惯习和行为模式上。布尔迪厄将“惯习”定义为行动者不同的消费、社交、趣味和举止。李阿英身上没有任何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惯习,甚至没有女性的特征和女性的烦恼,这使得她和韦明形成了社会空间中的鲜明的区隔标志。

表1 《新女性》中主要女性角色的生活空间和物质世界
电影塑造的3位女性,她们不同的阶层、品味和区隔形成了电影中富有张力的性别色彩,为何为“新女性”这一命题铺垫了前情。
二、《新女性》布景中的社会空间与物质世界
那么3位女性的社会空间图景又是如何以布景设计的形式在电影中展现的呢?20世纪30年代中期,电影美术布景开始摆脱舞台美术的限制,发展出有丰富变化层次的、贴近电影需要的场景空间[5]。《十字街头》的导演沈西苓这样描述当时左翼电影的制作条件:“中国的电影界,既没有很完整的机器,也没有充分的资本,在整个的制作的物质条件上已到达了十二分贫穷的地步……[6]”在如此窘迫的客观条件下,布景还需要考虑摄影机的调度、各种镜头的切换和营造,以及光线、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因此,左翼影人要想在电影中更为隐晦和巧妙地传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需要借助布景设计来塑造不同人物的性别身份,并营造出不同的社会空间和情景冲突。结合电影布景,可以看出3个女性角色选择的居所、器物与服饰,区隔出了她们在社会空间中不同的坐标位置。
20 世纪30 年代上海大众媒体十分关注于营造富裕阶层女性的物质环境,在《良友》《玲珑图画杂志》《美术生活》等杂志上渲染了新式家居的细节。电影布景师们利用大众传媒和大众心理,复制了上海的奢靡世界。王博士和王太太的住宅布景是高度现代化与西方化的(见图1),既有鲜明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也有现代主义的包豪斯风格。装饰艺术运动中象征速度的锯齿形图案,既出现在床头装饰画中,也出现在壁灯等室内陈设品上。1934 年《美术生活》第八期中出现了由设计师西平所设计的装饰艺术风家具和壁灯,与王太太家客厅十分契合[7]。钢管家具在王太太家的出现也暗示了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设计已经化身为中国富裕阶层文化象征的符号。1934 年《美术生活》第七期的妇人秋装宣传照中,一位摩登女郎倚在钢管椅的面前,展现着这一季都市生活最时尚的搭配[8](见图2)。钢管家具在西方诞生不久,就很快传入了中国,出现在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月份牌和广告画上了[9]。尽管马歇·布鲁尔(Marcel Breuer)、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或马特·斯塔姆(Mart Stam),以及其后索耐特(Thonet)公司设计的钢管椅,都没有一款能与王太太家的钢管椅细节相吻合,但影片布景中这些钢管家具的出现展示了更为重要的符号意义,即“富人们的物质世界,已脱离了传统古旧的中国而与外国最主流的物质文化接轨”[4]。

图1 电影《新女性》中王博士家

图2 1934年《美术生活》杂志的时装写真中的摩登女郎与钢管椅
王博士常常涉足的舞厅等娱乐场所是买办阶级男性所追求的都市现代性的重要部分。舞厅门口的装饰线条和乐队背后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图案采用了更加典型装饰艺术风格(见图3)。舞厅中的壁灯也和王博士家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来韦明见老鸨的地方也采用了装饰艺术风格的壁纸(见图4)。当这些相同的装饰风格出现在舞厅和旅馆时,暗示着特权阶层男性权力的延续,它们成为男性“交换欲望货币”的“经济”[4],而踏足此空间的女性则成为了消费和欲望的对象。因此,影片中代表新文化阶层的余海俦也在韦明邀请他去跳舞时说:“并不是我不肯陪你出去,实在跳舞这种糜烂的享乐生活,不是我们应该过的。”

图3 电影《新女性》中的舞厅

图4 电影《新女性》中老鸨带韦明来到的卖身之处
对于韦明这一剧中关键女性角色的生活空间的打造,布景师则调用了传统中式和现代西式两种室内布景的对比。电影中韦明老家的大宅是阴暗的中式空间,客厅正面的墙前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侧面是博古架,正中是一张中式圆桌和太师椅。整个老宅唯有大厅天花板上的玻璃灯罩电灯中透出一丝现代化的意味(见图5)。1931年的《玲珑图画杂志》的一篇文章批评到传统中式家居陈设:“阴森森、暗沉沉,森严万象之旧式家庭陈设,乃应当时之求而来,而适足配肃静回避高脚牌的尊严,我们现在既向平等自由之途径求新生活!则室内中一椅一桌之设置,纵不能在前领导我们之思想活泼,最低限度亦不容许一般呆板之装饰来约束我们之观念自由。”[10]老宅幽深古老,暗示了前现代中国的性别空间,其中布满血缘、家族和男性的权力控制。在诸多对《新女性》的研究中,女主角韦明都被赋予娜拉的镜像,她勇敢地逃出幽深的闺阁内景,闯入了上海的社会空间。对比老家的宅院,电影将她租住的亭子间设计成简洁现代,又充满文艺气息的独身女子居所(见图6)。从很多布景细节可以看出韦明作为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力所能及的消费范围内所展现的个人品味。例如,韦明家中茶几、餐桌、钢琴、梳妆台上也都陈设有花瓶,显示出其生活旨趣。家中的吊灯灯罩是民国时期常见的花朵型玻璃灯罩,这种灯罩在《神女》(1934年)、《马路天使》(1937年)等众多左翼电影中都有出现在新文化阶层的空间场所中。而梳妆台上的台灯灯罩则是装饰艺术风格,暗示着韦明对资产阶级西化生活方式的模仿。

图5 电影《新女性》中韦明老家的宅子

图6 电影《新女性》中韦明租住的亭子间
钢琴是韦明家中最有阶级意味之物,它和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籍一起,暗示了女主人的文化资本。从影片中可以得知,这钢琴并不属于韦明,而是她每月15元的租金向上海钢琴公司租借的。上海钢琴公司也就是日后“施特劳斯(STRAUSS)”品牌钢琴的生产公司。1893年中国第一家民族琴行成立了,1895便诞生了“施特劳斯”品牌[11]。可以说,这台充满小资情调的钢琴也是“国货”。这台钢琴在电影中暗示着韦明的社会阶层和她的性别命运,在她被中学解雇后,钢琴和房间的租金都无法支付。钢琴是韦明独立形象上最脆弱的表皮,当这一层表皮被撕裂后,她的窘困与绝境被电影层层展现。此外,韦明的桌子上和梳妆台上还出现了国产的热水瓶和搪瓷脸盆,布景中的国货产品传达了角色对于消费的态度,她既不拒绝洋货,也乐意扮演爱国消费者的角色。布景中还出现了一架传统的竹制鸟笼,与房间的装潢风格有些格格不入,并且没有承担任何叙事功能,是对韦明没有彻底解放的思想的一种暗喻。
作为韦明的邻居,居住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的李阿英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阶级差异。李阿英剪着齐耳短发,全片只穿过一件深色的素色旗袍,没有任何装饰品,她是彼时的上海社会空间中是最远离消费文化的女性。阿英的家居布景也可谓是简单至极(见图7)。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把“出于经济资本不足而被迫的、对必需品的选择”感受为一种剥夺,而是感受为一种偏爱——对于“必需品的趣味”。这种趣味把实体置于形式之上,把非正规置于正规之上[12]。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所有艺术革命,这些艺术革命是以纯粹和净化的名义、以拒绝炫耀和拒绝资产阶级的装饰趣味的名义实现的……”[3]李阿英的房间只有一些必要的木质家具,天花板灯泡外面甚至没有正式的灯罩,而是用报纸替代。在她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也出现了国货温水瓶。墙上没有粘贴韦明一样的影楼照片或月份牌,而是出现了一周工作的日程表。但正是这份日程表暗示着现代性以时间为表征,嵌入到李阿英的生活空间中,它不同于以消费为表征的都市现代性。

图7 电影《新女性》中李阿英租住的亭子间
通过电影布景师对当时上海女性生活世界的营造,我们会看到性别的区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不仅是体现在宏观社会结构上的两性权力差异,还在于微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间的结构性差异。当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社会空间地图中互动与位移的时候,她所选用和遭遇的物品与设计构成了她们性别和阶层的标签。
三、电影、国货与新女性
电影《新女性》不仅让人们看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上海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人生取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窥见当时的左翼影人借电影这一技术媒介所传播的一种新的性别秩序。1935 年,《新女性》的上映,引发了当时社会和知识界关于什么是“新女性”的大讨论,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当时舆论集中讨论了两种“新女性”:摩登新女性和革命新女性。韦明是在五四运动后得以苏醒的女性代表,她扮演着新时代开明的女性角色,自食其力,创造出自己的经济资本,同时也努力提升着自己的文化资本。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她对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洋货有着积极的态度,但她也会通过消费国货来显示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响应。然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和摇摆性,让左翼人士认为其不能代表“新女性”。1935 年《中华日报》有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张秀贞是一个大学生(无疑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心甘情愿作一个男人的玩物,成为买办阶级的太太。李阿英来自于工人阶级,与堕落的环境斗争。韦明的背景似乎在前两者之间,因此,她不可能从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剧中解脱出来。”[13]导演蔡楚生也写道:“像韦明那样软弱摇摆的人,是不能当得起‘新女性’这一称号的,可以当之无愧的只有李阿英[14]。”左翼影人通过电影布景仔细区分了“现代”对于3位女性的不同意义。王太太是包裹在“现代化”镀金外衣之下的“旧式上层女性”;韦明是从五四走来,努力使自己成为现代主体,却最终被都市现代性吞噬的女性;李阿英则是站在“摩登”的都市现代性对立面,具有革命现代性的“新女性”。但无论是王太太、韦明还是李阿英,这3 位女性都是电影中建构的角色。在当时电影的运作机制中,从导演到编剧,再到布景、摄影和剪辑……女性和女性所经历的世界实际处在电影工业链中最次要的位置。在电影最终的屏幕呈现上,韦明这一都市女性的现代性经验被高度折叠和隐藏。而李阿英这一“新女性”的角色则是以反女性的特征来呈现。正是因为“他”的视线和权力替代了“她”的经验,所有在这部名为《新女性》电影中只产生了关于“新女性”的幻象,并没有树立起真正的女性主体。但是电影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召唤却是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并影响到了中国现代设计之路的探索。
20 世纪20 年代末到30 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面临民族和经济双重危机的时候,在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开始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韦明所代表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女性与父权国家所召唤的“新女性”也构成了紧张关系。20世纪初以来,舶来品已经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消费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洋品与国货区隔了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位置,代表着都市现代化和民族现代化两种力量的竞争。葛凯这样形容当时消费文化中的这种矛盾性:“都市精英面临着两种竞争性的需求,在需要购买‘国货’和渴望自己看起来像是世界主义或受过西洋教育的欲望之间挣扎[15]。”对于都市女性而言,她们在消费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的性别角色使得这种挣扎和摇摆更为强烈。1933年,国货运动正达到高峰时期,而上海女性消费进口化妆品的数量依然高达140 万元[16],这使得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十分受挫。《申报》一篇文章这样形容:“都市中的摩登妇女,一天到晚,看电影,跳舞……所谓坐的汽车,来路货也;看的电影,欧美产品也;跳舞吃香槟酒,舶来品也,洋气十足,洋风凛凛,似乎不洋不足以摆期阔,不洋不足以显其荣[17]。”洋货标识了都市摩登女性的社会身份,打造了摩登女性的现代魅力,就如克拉考尔形容的都市“flapper girl”:“这些新的时装……一定要被展示,否则夏天的时候那些漂亮女孩会不知道她们是谁[18]。”作为“时髦制造者”(Tastemaker),这些时髦女性的消费不仅无助于民族工业振兴,还会被来自更底层阶级的女性所模仿,酝酿着更大的国家民族风险。
在国货倡导者的眼中,那些看起来貌似“新女性”的都市女子误读了“现代性”,她们将西方一切舶来品当作“现代”,而背叛了民族国家此时正在艰难前行中的现代化。因此,对“新女性”,必须要重新定义。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分别通过1933年的“国货年”、1934年的“妇女国货年”、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等一系列活动将民族主义消费意识推向高潮。尤其是1934 年的“妇女国货年”直接将女性推向了运动的最前端,女性在消费活动中的政治映射更被无限放大。在1934年《妇女国货年纪念特刊》中的一则广告这样呼吁摩登女性:“适应时代、谓之摩登、处国力凋疲之今日、而犹崇尚浮华、趋用洋货、是为不识时代之落伍者、所望今之妇女、力矫奢靡风习、一致维护国货、藉为国家杜塞漏巵、并为社会家庭亲朋子女作楷模、方是国货年之摩登妇女[19]。”女性,既可以是国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可以是追随“摩登”的“卖国者”。如何将中国女性引导成为前者,是当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在影响大众对商品辨析的过程中,电影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20 世纪30 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因其救亡图存和唤醒民众的诉求与国货运动合为时代的声浪。此时左翼电影推出的一系列“新女性”形象均与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运动背景息息相关。如1933年孙瑜导演的《小玩意》,女主角便是以挽救本土设计为己任的国产玩具设计师。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女主角最后离开物欲横流的上海消费空间,创办了一家国货商店。银幕之下,女明星也身体力行宣扬国货产品设计,1933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幅阮玲玉坐在钢管椅上的广告照片,介绍了上海南京路大华铁厂制造的国货钢管家具[20]。坐在全套国产钢管家具中的阮玲玉,妆容妩媚,姿态优雅,为消费者树立了国货也同舶来品一样优质,一样摩登的印象(见图8)。

图8 1933年《东方杂志》中阮玲玉坐在钢管椅上的照片
电影《新女性》正是在这一年开始拍摄。电影布景中刻意营造的生活空间,以及围绕女性们的洋货与国货,也是对发生在中国政治经济层面这一议题的回应。尤其在电影中通过布景被清晰区隔出来的两位新女性角色——韦明和李阿英,她们是左翼男性知识分子的假想的性别,但她们身上折射出的现代气质和革命气质却在国货运动中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气质相重叠,最终化身为新的文化性别,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之路上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
1934 年《申报国货周刊》中采访了六位不同的女性,其中有单身独立女士,有家庭妇女,也有名流夫人,可以从中听到现实中女性看待国货产品的新的声音。其中杨卫玉女士谈道:“国货哪一样没有,装潢美观,并不较外货逊色,经济耐用,且反过之。我们何必定学洋气,仰给于外货?”[21]《申报》董事潘公展夫人认为,“提倡国货应从城市中有知识或摩登化的妇女入手”;还认为“我们妇女提倡国货,要有这样的见解,就是不使我们很宝贝的子女将来成为亡国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如果母爱推广去爱护国货,为着孩子着想,那么我们女界努力提倡国货是值得的”[22]。1934 年6 月夏令《申报》报道中描绘到一幅当时模范家庭的物质生活画面:“经济家王先生与教育家高女士的家庭,为提倡国货的模范家庭。他们家庭,布置很简单、很朴实,明窗净几之下,挂着薄薄的窗帘,是三友社的绿色自由布,又轻又软,上面装的是华生电风扇,轻风阵阵,沁人心脾,书房里几架小的摇头风扇,也是华生出品。我们去拜访他们这对伉俪时,他们正在并肩看书,身上都是穿的五和厂的鹅牌汗衫……”[23]
可以看到,当电影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韦明,在渴望成为现代主体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时候,一群新的女性群体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者。无论是单身女性还是家庭主妇,抑或社会名媛,她们都对国家民族、对儿童教育有着全新的认识,对新的知识与技术有着开明的理念,对消费有着理性的态度。消费国货产品对于这个新兴的女性阶层而言,不是布尔迪厄所言的“必然趣味”,而是建立在良好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的“自由趣味”,换句话说,她们通过消费和使用国货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形成了以独立意识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场域。正是她们的存在,在殖民主义的物质世界中唤起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质量意识,也影响了中国妇女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品位。
四、结语
风云激荡的政治变革通常会下沉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并直接体现在与设计相关的生产、消费与批评中。从文化性别的视角来比照这一时期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和现实社会运动中的女性,会看到“新女性”作为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与大众社会共同召唤的新性别气质,也在中国现代设计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是她们召唤和撞击着中国现代设计主体性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