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斯科帕斯之宫
2021-06-22宋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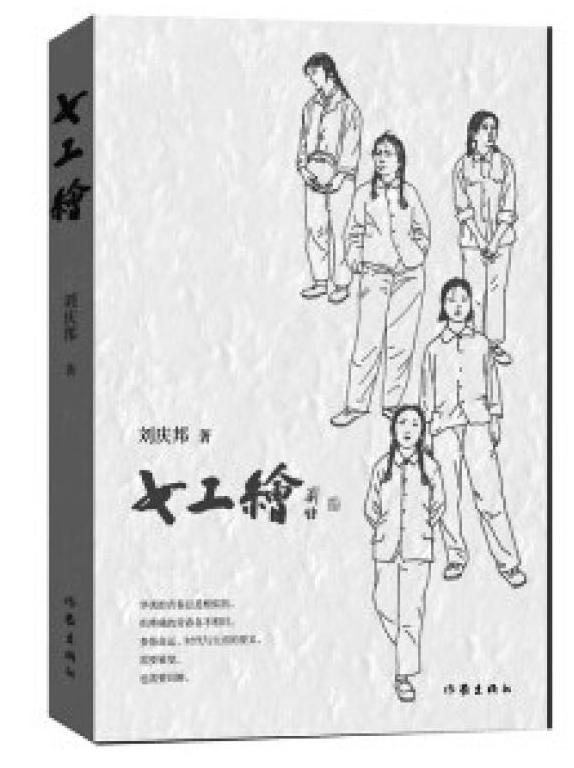
自古以来,“记忆”就是一个长久困扰着哲人们的话题,关于它的成因、关于它的运作方式,一直众说纷纭。在古希腊传说中,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主掌记忆,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即是“缪斯之母”。她的九个女儿分别主司史诗、历史、抒情诗、音乐、悲剧、喜剧、修辞学等一切精神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赞美神灵、祭奠祖先和反思生命——“记忆”孕育了艺术和历史,二者同出一源,而艺术和历史反过来会加深记忆——这便是对记忆、历史与艺术三者之间关系最为本质的阐释。
“记忆术”作为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罗马人心目中是一个贵族必备的素养,因而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古罗马哲人、拉丁语世界中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Cicero)曾在他的名著《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借安托尼乌斯(Marcus Antonius)之口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被贵族斯科帕斯(Scopas)邀请,前往他在克拉农城新落成的宫殿参加私人宴会,并在宴会上作诗赞颂主人。按照当时的习惯,这样的颂诗中除了对商议好的对象的歌頌之外,还通常会包括一段较长的关于神祇的内容,因此西蒙尼德斯在这首诗里用了很多篇幅叙述并赞颂了天神宙斯的双胞胎私生子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故事。但是斯科帕斯对此非常不满,粗暴地告诉西蒙尼德斯说他只能指望从自己这里拿到商定好的酬金的一半,另一半则应该去找被他极力称颂的那两位神仙讨要,因为他们在诗里受到同等的颂扬。这时有人告诉西蒙尼德斯,说门口站着两个年轻人,很想见见他,但西蒙尼德斯走出宫殿后却根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与此同时,一场不幸发生了:斯科帕斯的宫殿倒塌了,把主人和他的客人们都埋在了瓦砾堆下。西蒙尼德斯成了这场灾难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这就是神祇给他的报酬。当斯科帕斯的朋友们想安葬死者却怎么也无法把被压得面目全非的他们辨认出来的时候,还是要仰仗西蒙尼德斯,因为只有他记得他们每个人用餐时的位置,由此才得以把他们一个个指认出来,将他们体面地埋葬,并且能够确信他们为之哭泣的死者没有搞错(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二卷,第86节)。在这个故事里,西蒙尼德斯被视为第一个洞悉了记忆术之奥秘的人,他被神赋予了这种令人羡慕的能力。两千多年后,一位德国学者对此评价说:“他的事迹显示了人的记忆力可以超越死亡和毁灭的力量,并在这个传奇中变得永恒。”(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西塞罗总结道,“在我们的心灵里铭记最深刻的是那些由感觉转达和烙印的东西,……需要设想许多地方,它们是明显的、清楚的,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需要的形象则是要生动的、激烈的、清晰的,要能迅速地在心灵里显现,铭刻于心灵。”(西塞罗:《论演说家》,第二卷,第87节)因为需要由“感觉转达和烙印”、需要“明显、清楚、生动、激烈、清晰”的形象,所以冷冰冰的历史叙事不仅令人生厌,也无益于保存和唤起记忆;我们需要的是借助文学与艺术,借助那些确切的存在与实在的位置来重建斯科帕斯的宫殿。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迟子建发表于2020年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主人公刘建国的哥哥刘光复罹患癌症,去日无多,心情却不像大多数癌症患者那样沮丧和绝望,因为他的妹夫、考古学家(被不理解考古工作的人贬称为“挖棺材的”)老李曾经以一生的考古经验告诉他,“人类的文明史,是从对死亡的发掘开始的,死是绚烂的。考古就是膜拜人类遗址,拾取文明的珍珠。没有永恒的生,但有永恒的死。”老李曾慨叹由于文明的殡葬方式,人人化作灰烬,墓穴没有随葬品,再过千万年,后人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除了从文献获取,从实物角度来讲,只能依赖房屋等其他遗址。因此,刘光复准备选择几件能体现黑龙江地域特点的工艺品和自己一起入土,还准备放置几件他收集的小件工具和零件,“这样几千年后,人家掘开他的墓,不仅能看到文化史,还能看到工业史。他这样就不是去死了,而是带着使命活在地下,等待被发掘的时刻,那样灵魂就真的见了天光了”。没有永恒的生,但有永恒的死,反过来亦可以说,没有永恒的死,但有永恒的生。刘光复生前“自认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拍摄了一部东北工业发展历史的纪录片,这其实也是在试图用一种艺术的形式来为后世存储形象、保留记忆。
无独有偶,作者在小说上部的第六章安排两位主人公逛旧货市场,借女主人公黄娥之眼,烟笸箩、酱油瓶、马灯、炕琴等昔日哈尔滨普通人家里随处可见、如今却几乎消失殆尽的日常器物重见天日,“迤逦摊开的货摊儿,就像一条时光隧道”,而“每个旧物背后,都有无穷的问号”;男主人公刘建国更是在旧书摊上发现了父亲多年前翻译的最后一部译著,而这本书曾经的主人在书页上用俄文写下的若干批注,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给刘建国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的结尾处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从过去剩下来的只是人们从当下的角度能够建构起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回忆”,皆为“建构”,每件旧物背后无穷的问号,每个普通人身上所暗藏的秘密,都有待当下的人们去重建与之有关的故事。大到《烟火漫卷》的真正主人公——哈尔滨这座城市,小到作品中所涉及的芸芸众生,追溯起来都能洋洋洒洒写下一本本厚重的传记。中国人,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交织出了哈尔滨这座移民城市的百年秘史,战争、殖民、革命和商品社会叠加的复调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平民百姓日复一日吃喝拉撒、喜怒哀惧的主旋律。小说分为“谁来署名的早晨”和“谁来落幕的夜晚”上下两部,从白写到黑;而故事的开头写三月末尚未开江的松花江,结尾则是花灯和劈柴燃烧的声音,“好像谁在为年放着爆竹”,从春写到冬。刘建国日本遗孤的身份和青年时代荒唐举动的遗恨、翁子安(“铜锤”)自小被拐的曲折身世、黄娥心底对丈夫卢木头之死挥之不去的忏悔,便在这黑白更替、冬春轮回中渐渐揭秘、显影。其间虽然难免有市民社会小恶小坏、阴损贪占的“杂色”(比如说老郭和乡下老太婆陈秀之间各自打着小算盘的黄昏恋,以及二人转演员胖丫、小刘和刘建国外甥小李之间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的三角恋),中华巴洛克式建筑被擅自改造、传统二人转沦落为色情表演的“变色”,但“正色”仍然是刘建国与黄娥的良心操守、卖菜马车夫一家的善良淳朴,以及刘骄华口中刘家三兄妹身上“半个理想主义者”的气质。
《烟火漫卷》书名的由来,或许就暗藏在小说下部第七章结尾处煤老板四十年后终于揭开翁子安身世之谜时燃放的烟火中。在璀璨的烟火映照下,刘建国和翁子安(“铜锤”)抱头痛哭,正如迟子建在小说后记所说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它完美契合了西塞罗“激烈又清晰,铭刻于心灵”的要求。但在汉语中,“烟火”又是一个多义词,它更多地对应着“炊烟”与“灶火”,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联系在一起,因此“烟火”以及由之生发出的“烟火气”成为描述市井生活常用的词语之一,弥散于小说里榆樱院、菜市场、大戏院之间的生活中。而王松的《烟火》,便是完完全全从这一语义出发,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天津卫侯家后一群引车卖浆者流身上横亘百年“传奇不奇”的故事。迟子建是在当下生活的叙写间穿插和回顾已经褪色的昔日隐秘,王松则是给泛黄的黑白老照片重新上色,使其恢复曾有的光彩。与《烟火漫卷》近似,《烟火》中也包含着若干亲人分离的故事,但不同的是,他们或是至死未能相认(例如老瘪和来子),或是多年后重聚却又因时代的原因很快生死两隔(例如王麻杆儿和王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世间最令人痛心处。就在这一幕幕悲欣交集之中穿插着无数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个已经日渐离我们远去的传统市民社会,及其赖以存在和维系的价值观念、伦理准则又在烟火气中渐渐浮现。尽管日益式微的传统相声在天津人郭德纲的努力之下有复苏之势,但相声行当里的许多行话曾经深深扎根天津老辈人的文化记忆,成为他们日常語言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如今却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作为曾经给相声大师马三立写过段子的作家,王松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选择了一种曾经为市井民众所津津乐道、现如今却只能残存于胡同口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们记忆中的艺术结构形式,将一部《烟火》百年的故事用“垫话儿”“入头”“肉里噱”“瓤子”“外插花”“正底”串联起来,俨然一段结构完整、严丝合缝的传统(单口)相声,幽默但不皮相,诙谐不乏愁绪,擦去眼角残泪,留下只有饱看世态炎凉的人才能打心底由衷发出的笑声。从义和团运动、“火烧望海楼”、天津起义、“老西开教堂事件”到“五村农民抗霸”“壬子兵变”,再到“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半个世纪的民族血泪史悄悄化为小说中五行八作“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背景,融入叫卖的市声和漫天的烟火之中。小说中侯家后蜡头儿胡同里街坊四邻所从事的行业,无论是卖香烛神祃儿、刨鸡毛掸子、做拔火罐,还是绱鞋、打帘子、拉胶皮、卖水,现如今早已泯灭无闻,成为只存在于民俗词典中的冰冷词条,而“狗不理包子”和嘎巴菜虽然流传至今,也早就不是当初的味道。但时光一晃七十年,“福临成祥鞋帽店”掌柜的换了几代,仍然守护着铺子后面的暗室、维护着曾经的约定和誓言,不变的唯有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闪耀着前现代社会,或曰中国式“乡土城市”的最后“灵光”。
这样的“城市记忆”,与贾平凹《暂坐》中的“国际大都市”西京城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农裔城籍”的作家,贾平凹在写下《废都》近三十年后又一次选择都市题材作为长篇小说创作方向。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过,世界上并没有独立存在的身份,它必须借助记忆不断地加以建构和重构。在他看来,人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过去,并把过去的自我与现今的自我连接;不仅如此,过去的一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构和展现;每个人在通过记忆重现过去的时候都有其倾向性。而在近三十年中屡屡通过小说创作“重构和展现”自己“农村人”身份的贾平凹突然拿出一部描写都市生活的《暂坐》,这一举动本身就极为耐人寻味。他此前在《秦腔》《古炉》等作品中呈现的乡村历史和现实,无一不渗透着浓浓的“乡愁”,这或许可以对应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它唯有作为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如果说《废都》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西京城还只能被看作一个放大了的县城,还带有明显的乡土文明气息,那么到了《暂坐》中,所有人的生活几乎都与乡土社会一刀两断了。《废都》里的唐宛儿从潼关县城、柳月从陕北米脂初到西京,举手投足间仍处处透出乡间习气,《暂坐》里同样有一个曾是“秦岭东边的华县剧团演员”的女性徐栖。小说中其他城市女性不认识柿树、不知道何为“老鸹”、将桑树误认为樱桃树,徐栖都能一一指出错误;但当陆以可夸赞她“到底是从县上来的,知道得这么多”时,她“突然不说话了”,还回怼陆以可“不要问了,我也是西京城里人,啥都不知道!”言语中充满了对自己“县上来的”身份的自卑与不甘。徐栖在《暂坐》中只是“西京十块玉”之一,并非多么重要的角色,且常常是和她的同性恋对象司一楠一起出现在小说情节中。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在传统观念中绝对难以接受的性取向,她才极力撇清自己与“县城”的关系,因为在当下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即使是“县上人”也很难摆脱农村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束缚;而作为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西京城不仅有俄罗斯姑娘当店员的“暂坐茶庄”,不仅有可以买到法国、意大利名牌包的“国际商厦”,更(应该)有可以接受多样性取向的包容性。但在小说临近结尾时,面对范伯生的挑衅,陆以可一面维护徐、司二人,一面又表示“同性恋在外国不是大惊小怪的事,但在中国还认作是伤风败俗”。作者借陆以可之口所传达出的态度耐人寻味:究竟是在批评西京城“国际化”的程度不够,还是在暗示徐、司二人的性取向是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暂坐》中的“十块玉”,每一块都不是“白璧无瑕”而或多或少都有长期都市生活浸染所形成的性格瑕疵;具体到徐栖身上,从作者篇幅不多的叙述中,似乎也只能找到“伤风败俗”的性取向这一点)?
贾平凹意欲通过男主人公羿光、女主人公海若及其身边十位女性(“十块玉”)的生活遭遇为当下的都市生活“立此存照”,多年以后人们再翻出《暂坐》,或许能一窥2016年前后中国社会之全豹。有趣的是,小说中也有一处与“照相”有关的细节:“十块玉”之一的虞本温爱好摄影,她将自己四处收集的西京城老照片翻拍放大,悬挂在自己火锅店走廊的显眼处。作者借应丽后之眼,从这些照片中看出了西京城代表性建筑大雁塔和钟楼周边自清末到民国再到建国初期、“文革”时期的沧桑巨变。巧合的是,《烟火漫卷》中也安排了一个黄娥带着儿子杂拌儿在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已改建为哈尔滨建筑艺术博物馆)看百年前老道外生活图景照片的情节。如果再联系到刘光复生前拍摄的纪录片,可以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安排笔下的人物一面通过影像重返城市记忆,一面又以自己的行动为未来构建着“城市记忆”,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所说,“记忆的责任让每个人都变成了其自身的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暂坐》留给后世的记忆,是西京城漫天的雾霾,是国际航班失事的惨痛,是市委书记和秘书长因为一连串政治经济问题被带走、留置后对羿光、海若、“十块玉”乃至整个西京城带来的震动与不安。小说中的俄罗斯姑娘伊娃曾经疑惑“她们是一群那样高尚的人,怎么都有没完没了的这样那样的事所纠结,且各是各痛,如受伤的青虫在蹦跳和扭曲?”然而这“纠结”和“痛”又岂止是在海若诸姐妹身上?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带来精神的充裕,有时还会将其引向反面。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海若姐妹们看似一团和气,但由于观念差异和利益纠纷而导致的裂隙已然隐约可见,想必这都是由于不懂得“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贾平凹接受采访时语)而导致的。“暂坐茶庄”的二楼四壁都绘着壁画,据说是“临摹了西夏王朝白城子的一个地宫画”。作者不惜花费将近八百字的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壁画的内容,据笔者考证,这段文字其实来源于发表在《考古与文物》杂志2013年第3期上的《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简报》,不少语句甚至照搬原文(唯有一处出入,即将“塔下部为六名立姿僧人”改为“十个僧人一字排开”,想必是要与“西京十块玉”对应),因此大多数不习惯考古发掘简报文字风格的读者会明显感觉出它与小说叙述语言的“隔”。如果再结合当期杂志上刊出的壁画照片来读这段文字,你就会恍然大悟:小说中称茶庄二楼为“佛堂”,但其实是将一座深埋了1500年之久的、鬼气森森的墓室从地下搬到了地上,而羿光、海若等人却能够欢宴其中。即使不套用“升格”“降格”之类的巴赫金诗学概念,光是联想到上至《搜神记》下到《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中的相关情节,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而其间诸色人等,也就等同于行尸走肉了。这实在是当下城市中众生深陷精神困境无法自拔的真实写照。
像这般灰色的记忆,还深深印刻在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中。在为北岛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所写的序言里,欧阳江河这样写道:“不是发生了什么就写下什么,而是写下什么,什么才真正发生。换句话说,生活状况必须在词语状况中得到印证,已经在现实中发生过的必须在写作中再发生一次。”作为一个写出了《王小波传》并致力于读解“90年代宏大叙事”的学者,世纪之交长达五年的工厂生活一直是房伟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那段灰暗的日子被他反复书写。《血色莫扎特》并不是房伟的自叙传,但故事显然有其原型。十几年后,时过境迁,由当年的工人蜕变(此处应为一个中性词)为大学教授,房伟需要写下些什么,以此来使“现实中发生过的”“再发生一次”。要写些什么自然无须赘言,关键是怎么写,用怎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来向逝去的时光、逝去的人们致意。这一次,他选择了东野圭吾式的“新社会派”(或“写实本格派”)的悬疑外衣。
小说开头看似平淡无奇,和《暂坐》一样的雾霾,加上麓城春天特有的柳絮,却埋伏下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的苦乐悲欢,人性深处最隐秘的部分,伴随着一场奇情虐恋在时间的底片上渐渐显影,并最终为历史留下了真实却又不堪回首的记录。借主人公在伦理道德上的(疑似)越轨和对社会主流意识的叛逆,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种种飞短流长,房伟和他的偶像王小波都意图彰显在混乱动荡年代里坚守理想主义的可贵。闪耀着“八十年代”所特有的炫目光芒,时代曾无比肯定地向青年们许诺“新的生活”,却化作一场震撼了整个麓城的大爆炸;而随着1998年夏天的又一场大爆炸,以及企业破产、兼并、工人下岗的浪潮,还有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官商勾结、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资本运作、越来越张牙舞爪的黑恶势力,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世纪末回光返照,“卑微的生命燃烧,爆炸,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却一语成谶。就像超新星爆发那样,夺目的闪耀之后便是急速的坍缩,直至化为恐怖的黑洞,将我们所憧憬的“新的生活”卷入其中,直至万劫不复。直接导致小说中人物命运悲剧的那些原因,诸如由国企改制引发的下岗潮、因国企职工医疗福利无法得到保障而被迫卖身救父、官商勾结加黑恶势力介入戕害百姓等,不一而足,早已在近十五年来的“底层写作”中被反复书写,而在房伟笔下又一次集中呈现。但《血色莫扎特》超越某些“底层文学”的地方,就在于作品中的人物摆脱了脸谱化、概念化的弊病。与此同时,那些“恶人”的“恶”也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都是以麓城为缩影的中国社会几十年来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说“70后”作家的创作存在一个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那么,恰恰是在“个体”与“历史”的关系这一层面上,无论是学理还是经验,房伟比起其他“70后”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烟火漫卷》中刘建国眺望病危中的大哥卧室时感到“每个窗口的灯火,都是尘世的花朵,值得珍惜”,整部作品因而被染上了一种寒夜灯火般的暖色调;《暂坐》《血色莫扎特》由于有弥漫的雾霾灰作底色,因而呈现出令人心寒的冷色调。与它们相比,张平的《生死守护》无疑是一抹难得的炫目亮色。作为一个始终对时代和现实保持着高度敏感的作家,继两年前在长篇小说《重新生活》中将当下社会普遍关注的“反腐”主题与“教育”话题相结合并取得成功之后,张平又创造性地在《生死守护》中将公安机关侦破盗掘文物大案设置为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它与聚焦“反腐”、关注“民生”的主题相辅相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因此变得空前复杂而广阔,各色人等在其中穿梭行走,呈现出较作者以往作品更为丰厚、博大的总体性。也正因为如此,《生死守护》在近些年来井喷般涌现的同主题作品中得以凸显出卓尔不凡的品格,保存了质地最为坚硬的时代记忆。故事发生在千年古城龙兴市,该地丰富文物所代表的辉煌历史难掩当下民生的窘迫,因此急需打通龙飞大道并建设龙泉机场。而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焦点,也就集中在工程总指挥辛一飞身上。从计划破格提拔他开始,由于各方利益被触动,原先潜藏于龙兴市政坛的各种复杂矛盾逐渐浮上水面,最终激化成一场惨烈的绞杀。小说描绘了从龙兴市委决定抽调提拔辛一飞主持龙飞大道工程到工程实施方案正式通过这短短一段时间内龙兴市政治、经济领域里所掀起的惊涛骇浪,或者可以说是一场足以决定龙兴市八百万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战役。辛一飞从一开始就被作者置于一种极端情境之中,与既得利益集团展开若干回合交锋,甚至不惜将个人的政治名誉和前途置之度外;其间还交织着龙兴市文物局、公安局同文物贩子崔氏父子之间,以及知名网络作家刘小江同黑恶势力龙江宾馆之间的斗争。在作者朴实而又充满激情的叙述下,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在读者面前缓缓铺开,而辛一飞就是这张大网上的“纲”。几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并不时以闪回和插叙的手法揭开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秘。“反腐”是张平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而“反腐”的最终目的,则是引发对“民生”持续且深入的关注。与小说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行径相比,辛一飞身上体现出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式的悲壮和崇高;张平用他的如椽大笔,为读者塑造了一位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式的时代楷模形象。
在哈布瓦赫看来,不存在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个体“一刻也没有脱离某个集体而单独存在”(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近些年来,时代与社会的急剧鼎革,特別是国际关系的风云突变,促使作家们重新认识了个体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曾经一度流行的个人呓语式的写作随之消弭,进而推动作家们去深入理解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人”。张忌的《南货店》写浙东宁波一带一爿小店、一座小村、一个小镇、最多不过一个小县城里二十年间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此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哭过也笑过,聚了又散了,其间充溢的是浓浓的烟火味道,当然还有浙东沿海所特有的鱼鲞腥气。琐碎的日子里偶有波澜,但很快就归于风平浪静。这是张忌作品的一贯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二三十年来评价越来越高的汪曾祺和他的小说。但流布弥散于汪曾祺小说里的,是一种闲适恬淡的诗意,往往也隐约透露出一股士大夫气,以至于越到晚年,他笔下的人物越趋向“俗世奇人”。张忌虽然也把目光聚焦于市井民间,但他笔下所反映的是地地道道的升斗小民,他的小说里多有宁波一带的方言土语,尤以“讨生活”一词最为传神,此处的“生活”等同于“活计”“工作”,搭配上“讨”字,让人心中无端生出一种艰辛、凄凉之感。“生活”便是为“生”而“活”,不仅要咬紧牙关,更必须要有心计,或曰“生存智慧”。这些在为生计而奔波、为生存而挣扎中不时闪现狡黠的民间智慧,更接近明清“世情小说”一脉。张忌的小说很像他所热衷于收藏的“小插人”——这是一种过去普遍流行于江浙一带大户人家婚床、婚轿上的小木雕,人物形象基本上来源于民间戏曲、通俗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以及种种劝人向善或富有吉祥寓意的民间故事。从收藏的角度而言,张忌所看重的,或许是“小插人”在艺术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精美与繁复,但对于作为其精神来源的民间伦理和情感立场,想必他也是心知肚明,并自然而然地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忌的小说就是彻彻底底的“俗”,他的超脱之处就在于,透过凡俗的日常生活、透过普通人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和斗争,他看出了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无奈、虚无,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意义和悲壮之美。类似的,刘庆邦在《女工绘》中写一群青年女性在特殊年代的矿山里为改变人生轨迹、寻求个人幸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南货店》主人公秋林耳濡目染老师傅们的种种“生存智慧”,渐渐地成长或者说“成熟”起来,以至于豆腐老倌批评他“你后生不要搞得这么世故”;但比起周围绝大多数人来,他的“世故”还是单纯得多,并且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常常感慨自己“不晓得再过几年,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而《女工绘》的主人公华春堂虽然工于心计,身上体现出同样年龄女子少有的要强、冷静和缜密,甚至懂得利用丧父的不幸作为找工作、换工作的资本,但却始终无法摆脱时代语境对个人的形塑:她无法容忍矿山将阶级成分高的张丽之跟自己分配在同一个工作岗位,“这哪里还有什么区别呢!”认为矿山宣传队不选拔自己而选了两个“作风有毛病的人”“简直就是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公平,也没有了正义!”甚至她在衡量一个男子是否适合作为恋爱对象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将阶级成分作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正如小说中刘德玉评价华春堂时说的那样,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样的人物形象常常是可鄙的;然而当这种实用主义同特殊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共同将人物命运推向深渊,读者则或许要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了。胡学文的《有生》从体量上看无疑是一部“大作”,洋洋洒洒五十万字,当下与回忆、梦呓与现实相交织,以一种颇具创新性的“伞状结构”串联起百年家族史、乡村史,同时也就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小说中的若干情节设置初读感觉不合情理,但掩卷沉思,方能体会出其宏阔正大之处,恰如本雅明所说:“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而王尧的《民谣》则寻求开拓长篇小说文体新的可能性,散文化的叙述、情节的弱化、流水般意境的营构,皆可视为作者为避免小说叙事僵化而做出的探索与努力。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20世纪中国散文、“文革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王尧数十年来所致力的研究方向,三者的研究心得,在《民谣》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作者引领读者翻阅发黄的相片和古老的信,抓取散落在少年王大头心间的点滴记忆,用散文笔法抒写日渐褪色的乡村生活,探索历史褶皱里的隐秘,叙述静水流深,字里行间氤氲着里下河地区乡间略带霉味的独特气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杂篇”“外篇”两部分,直接用旧文存档的形式纳入极具特定时期色彩的文本,并适当加以评注,显然是2020年度长篇小说创作试图“重建斯科帕斯之宫”最为直接、同时也最为独特的尝试。■
(宋嵩,《长篇小说选刊》杂志)
